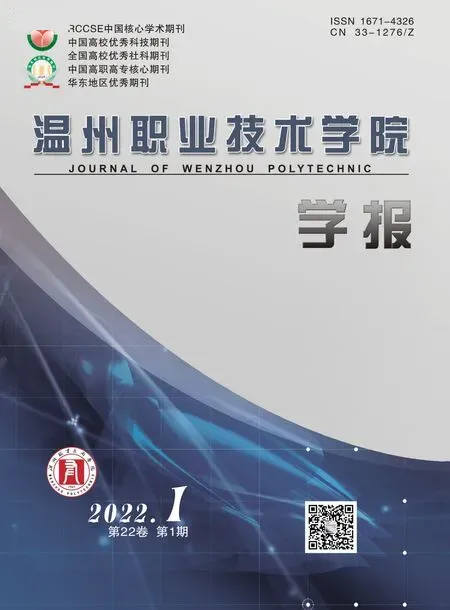刘基的儒学心性思想
李万进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610110)
刘基作为明朝的开国功臣,不仅辅佐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参与了明王朝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还是一位深入研究儒学理论的思想家。从刘基流传于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刘基本人具有极为浓厚的儒家正统与道统的情结,极为推崇儒学的理论,这也是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原因所在。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参与明王朝的政治活动,这是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的立功的理想。同时,儒家还主张立言,即建立一套思想理论传之后世,刘基自然受到了立功与立言的儒家理论的影响。
在刘基流传于世的著作中,有涉及儒学心性论的内容,这体现了儒学理论在刘基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与影响。儒学的心性论,主要是为如何成为圣人,如何实现内圣而外王的理想进行论证,这之中涉及天道与人道的问题。刘基在阐述其儒学心性论时,论述了心与性、情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这是从天道的角度去论证心性的问题。同时,刘基十分注重个人的心性与道德、精神修养的关系,这是从人道的角度去阐释儒学的心性论。儒家理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内圣外王的圣人治理天下的境界,这也是儒学心性论追求的终极理想。儒学心性论的这些内容,在刘基阐述的心性理论中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在刘基生活的时代,思想界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不少儒家思想家都涉及三教的理论,刘基也概莫能外。刘基阐述的心性论的基本取向是儒学,因此刘基本着儒家本位与道统的立场,抨击了佛教心性的理论。这种本着儒家本位与道统立场的心性论,影响了后来明代心学心性论的建立,由此彰显了刘基阐释的儒学心性论在明初思想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一、心与性、情
儒家心性论体系中,心、性、情都是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在先秦儒学的理论体系中,就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阐述。先秦时期儒家心性论对于心、性、情这些概念的阐述,大多与道德伦理的范围有关联。正是先秦儒家心性论将心、性、情这些概念主要定格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之中,才为后世儒家在讨论心、性、情这些概念时确定了基本的理论模式,即:儒家心性论的重要目的在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入手,来阐明心、性、情这些概念的含义与意义。先秦儒家心性论尽管没有建立起像后世儒家特别是像宋明理学那样较为严密的心性论体系,但先秦儒家心性论中涉及的心、性、情、气这些概念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模式,这些核心的概念成了后世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们反复讨论的重要话题。
在先秦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儒学思想家在阐述心性论时都涉及心、性与情这些核心概念。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在讨论心性、性命、性情等问题时,将儒学心性论的这些核心概念与理这一概念相关联,由此建立了将心、性、情等概念纳入理这一范畴的理论体系。刘基生活的时代处于元末明初,理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较为成熟的体系,刘基作为当时的儒学思想家,必然会与理学的心性论发生交涉。刘基在阐述其心性论的体系时,有意识地将心与理进行关联,从理的角度来阐释心的意义:“天之质,茫茫然气也,而理为其心,浑浑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载于气以行,气生物而淫于物,于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胜,于是乎有恶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1]186-187
宋明理学心性论中天理这一概念居于核心的地位,特别是程朱理学一系,直接赋予了理本体的意义,将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纳入理之中。刘基在阐述自己的心性论时,注意到了理这一概念在儒学心性论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将心与理两个概念进行关联,合而为一进行阐述。在程朱理学中,心与理还不是同一的概念,因此才有心统性情的命题,程朱理学强调的是性即理。心与理的关系,在程朱理学看来还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个人之心由于气与情这些不利因素的介入,而不同于圣人之性。所以,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主张的是心统性情,心统性情这一理学命题表明的是个人之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于个人之心渗入了气、情这些不利的因素,这样程朱理学认为心与性以及心与理都不是一致的关系。程朱理学之所以不认同心与理具有一致的关系,在于“二程明确区分了性与情,指出性是理,是本;情是动,是末,从而把性情纳入道德本体论的逻辑结构”。“性作为‘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情则是性的发动。性虽是‘形而上’的道德理性,但必须通过情才能实现。情则是感性的、经验的,人人可以感知的。”[2]也就是说,二程认为气、情这些不利于天理的因素,存在于个人的心中,这样个人之心必然存在着与天理不一致的关系,所以程朱理学主张通过对于气、情这些不利于天理因素的祛除,最终才能够实现个体的本质之性与天理的一致关系。
刘基在阐述心与理的关系时,注意到了程朱理学对于心、理、气、情诸多概念关系的论证。在阐述心与理的关系时,刘基首先是从天生万物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天道与理这一概念具有等同的意义。天道的本质就是理,理与万物之间需要气这一概念的介入,才能够最终衍生万物。不过,刘基在阐述心与理的关系时,注意到了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人世间的万物有善有恶。善与恶是怎样产生的,这就是刘基在论述心与理的关系时需要解决的。从刘基对于天道本性的论述来看,刘基认为天道通过气这一中介来实现万物的生成。因此人世间的善是与气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联的,这就是“载于气以行”。不过,气生万物却存在着千差万别,在所生之物中,既有善同时也有恶的存在,这样人世间善恶的现象由此产生。在论述气生万物时,刘基认为“淫于物”是产生人世间恶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恶虽然是通过气产生的,但是从天道的本质而言,没有恶的存在,所以恶与天道的本性无关。善恶的现象是与人伦道德密切相关的,这样刘基对于心性的阐述与人伦道德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儒学心性论的本质特征。宋明理学建立的理在这一概念,包含了天道与人道的内容。气的运行大多与天道有关,儒学思想家们在阐述天生万物时,一般都会涉及到气的流行与运行的内容,正是有了气的运行从而才有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这样天道与人道的产生与运行都与气这一概念有关。气成为了连接天道与人道的中介。情这一概念属于人道的范畴,气的运行导致了天道与人道的产生,情也随之出现。气与情作为不利于理的因素,需要运用道德修养的方式来予以节制,这样个人的心性必然就与人伦道德密不可分。
刘基秉承儒学心性论的心性与人伦道德密不可分的理论模式,将对于心与理关系的论述,最终落实到人道的人伦道德层面,“就人来说,虽然有理的流行而为其心,但往往又被邪气所胜而成为不善的人。这基本上是讲的气禀物欲和气质之性的问题”[2]。在刘基所阐述的心性论中,气属于天道与理衍生万物的中介,因此气之中包含了正邪之气,这样就会有善与恶现象的产生。但是,恶的现象是邪气作用的结果,不是天道与理的本质属性。由此而论,个人之心的本质也是与天道、理相一致的。刘基对于气与心性、天道、理的关系的阐述,是为了突出气在其所阐述的心性论中的地位与作用:“气者,道之毒药也;情者,性之锋刃也。知其为毒药、锋刃而凭其行者,欲使之也。呜呼!天与人神灵者也,而皆不能不为欲所使,使气与情得以逞其能,而性与道反随其如往。造化至此,亦几乎穷类!”[1]53-54
从刘基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气与情在刘基阐述的儒学心性论体系中,都属于与心、性、理相背离的概念,是与人欲、物欲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基开宗明义地指出,气是有害于道的毒药,这样气在本质上与道是相背离的;同时,情这一概念又是“性之锋刃也”,显然情与性也是不相一致的。为什么气与情是有害于道与性的概念呢?刘基认为是因为气、情这两个概念与欲望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旦个人被欲望所牵引与迷惑,自然就与道、性相背离了。由于个人为欲望所牵绊,气与情这两个概念就左右了个人的意识与意念,从而就会出现与道和性相背离的现象。从儒家心性论特别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体系来看,气与情这些概念都是与极为复杂的人性有着密切关系的范畴。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因为有了气、情这些不利因素的干扰,个人本质上与圣贤一致的心性才有了差别与不同,个人心性才有了缺失。正是从这种角度而言,儒家心性论特别是宋明理学心性论主张祛除气、情等不利因素的干扰,由此来恢复自我本有的与圣贤一致的心性。
针对气、情这些不利因素干扰个人心性这一现象,刘基甚为感慨,认为是个人心性的堕落与沉沦,这种干扰主要就体现为个人欲望的产生。尽管欲望使得个人的心性有可能出现与道、性相违背的现象,但是道与性的本质却是要求个人不为欲望所牵绊与控制,刘基《郁离子·玄豹》认为:“天生物而赋之形与性,夭寿贵贱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谓之天常。”[1]16性作为天道衍生万物的本质,具有“弗可移也”的特征,这也是天道的恒常之性。万物的具体之形与情一样,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与恒常的天道不相干,所以刘基在阐述其心性论时,强调了天道所具有的恒常之性,这种恒常之性。是衍生万物的根基所在,也是万物秩序能够建立的基石:“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则两死,物理然也。何独疑于人哉?故吏与医为二道:活人以为功者,医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无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为医者,业必丧;以医之心为吏者,身必穷。又何怪乎善医者之不屑为吏也哉!”[1]181-182
刘基以医生和官吏两种不同职业人士的心性为例,来分析天道所生之万物的差异。从天道之本性而言,万物都是一体的,但是在形成与产生出万物之后,万物之间的性质就有了巨大的差异与不同,这样万物之间的秩序呈现出纷繁芜杂的特征。刘基在这里以万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来阐明性与情之间的关系,即性虽为一,但是由于情的作用,于是万物就呈现出诸多的差异,这样才造就了万物之间纷繁芜杂的特征。从刘基关于性与情关系之阐述中可以看到,刘基在遵循儒家天道生生的基础上,阐明天道如何衍生出纷繁芜杂的万事万物。尽管刘基承认万事万物存在着差异,也承认人世间存在着善恶与正邪等现象,但这些现象都需要圣人之心进行引导,从而起到正人心的作用,这就是刘基认为的人为天地之盗的原因所在:“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盗斯穷矣。故上古之善盗者,莫伏羲、神农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1]40
人为天地之盗并不是盗贼之义,而是因势利导,以此来教化民众,更正人心,以起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这也是儒学心性论追求的目标。在刘基看来,唯有儒家的圣人才能够“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这之中的天地之心就是天道,就是理,圣人通过对于天地之心的掌握来治理天下,从而使得民众能够在礼乐教化之下,实现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刘基明确指出,一般之人即庶人是没有操天地之心的能力的,只有圣人才有这个本领,因此刘基建立的心性论突出了圣人治理天下的能力。儒家心性论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教化民众,就在于治理天下,就在于最终要实现内圣外王。这些儒学心性论的核心内容,在刘基这里体现为如何实现天地之盗,即如何实现天下的治理。
刘基阐述的心性论,将心与性、情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儒学心性论的显著特征。刘基在论述心与性、情的关系时,涉及了理、气这些概念,以此来阐述天道的运行,以及如何由天道的运行而产生世间的万物,并且还论述了世间万物如何才能够实现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的治理问题。心在刘基阐述的心性论中处于一种变动的位置,即心要与性、情、理、气等发生作用,才能够显现出心这一概念的功能。从理学体系的角度而言,刘基的心这一概念与心统性情的理学命题有着一定的关联。在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中,“心、理关系的实质是,心包含着理,理存在于心中,二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区别处在于:‘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认为理无知觉。理即性,是宇宙本体;心有知觉,是认识主体。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4]131。“在心与气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心属于气之虚灵,即气中的虚灵部分是构成知觉之心的要素,但心又不完全等同于气,心以理为存在的根据,是理气结合的产物。”[4]133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中,心与理不是完全一致的关系,朱熹认为只有性即是理,心与性不能够等同视之。刘基在阐述自我的心性论时,沿用了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理学心性论中的理、心、性、气、情等概念,但却已经具有了重视心这一概念的倾向。于此而言,刘基虽然没有建立起较为严密而精审的心即理的理论命题,但在阐述心性论的过程之中,在涉及心与性情的关系时,已经开启了心与理合而为一的理论模式。
二、心性与精神修养
儒学心性论强调天道的内容,更重视人道的修养,这样儒学的心性论在为儒学的理论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之后,则将重心转移到了如何通过精神的修养提升道德与精神的境界,从而成就圣人之道。儒学心性论对个体心性的阐述,是为了最终论证个人如何通过心性的修养才能够成就圣人之道。刘基建构的心性论也遵循了儒学心性论的这一理论模式,在阐述了理、气、性、情这些具有先天意义的概念之后,将论述的重心转向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即刘基本人极为重视个人如何通过提升精神与道德的修养成就圣人之道。
刘基对于心性与精神修养关系的阐述,体现出刘基对于后天之性即人性的重视。人性在儒学理论中具有后天可塑的因素,因此才有儒学一直重视的精神修养与道德境界的提升这些理论。显然,“刘基在讲到人性时,并不完全局限于先天气禀的原因,他也强调后天环境习染的重要性”[3]。正是基于这种重视后天修养的理论模式,刘基论述了以君子之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以此来克制私欲与邪气,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1]137
刘基对于心性修养的阐述,将重心集中于“正人心,扬公论”这一点上,认为这是君子“以身立教”的根本。尽管儒家思想中,有生而知之者的圣人之说,但是儒家心性论也十分强调后天心性修养以成就圣人之道的境界,因此刘基阐述的心性论在肯定了先天之性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个人精神修养以成就圣人心性的重要性。刘基认为,先天的天性是生而成就的,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但是后天的修养却是需要个人去努力的,这样心性就离不开精神修养与道德境界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刘基主张:“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人心之中的正邪之气,个人意念中的贪廉之别,全在于自我一念之间,这就需要个人进行自我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精神境界的修养,以此来确保不被物欲所迷惑而失却自我的本性,这就是刘基阐述的心性与精神修养的密切关系。通过这种心性的精神修养的作用,就可以最终成就儒家的理想境界:“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1]137刘基在这里阐述儒家追求的大丈夫境界时,明显与《孟子》中的内容有密切的关系,这显示出刘基心性修养论具有浓厚的儒家气息。不过,刘基对于《孟子》中观点的继承与发挥,是立足于其所阐述的心性论来进行的。因此,刘基对于心性修养的阐述,具有形而上的基础,即将心与性上升为天道与本体,以此来阐明儒家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圣人之道具有恒常不灭的意义。仁与礼是儒学的核心理论,刘基将仁与礼纳入心性修养,如此一来,作为伦理范畴的仁与礼,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恒常意义,这也是宋明理学建构心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
刘基在继承理学心性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后天心性修养以提升精神境界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自我能够成就圣人之道的根本所在。并且,刘基参与了明王朝的诸多政治活动,有过亲身参与治理天下的经历,因此很自然地会将个人的心性修养与儒家圣人之道治理天下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心性修养的空洞议论之中:“昔者汤以‘日新’铭其盘,武王以‘敬义’书其几杖,器用朝夕之见,以启其心,迪其德,学圣人者师焉。”[1]150商汤的日新之说,以及周武王的敬义之说,都被刘基统摄到了心性修养的理论中,被认为是“启其心,迪其德”的有效途径,是圣人教化民众逐渐提升自我精神境界、合于儒家之道的治理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基倡导的心性论与儒家治理天下的理论有密切关系,而要实现天下的大治,那么就必须教化民众合乎儒家之道,这也是圣人、君子通过心性修养的途径教化民众,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
刘基论证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那么如何修养自我的心性,即心性修养的途径是什么,这也是刘基在阐述心性论时要阐明的一个内容。刘基认为,民众的心性不同于圣人、君子的心性,多为物欲所扰,而心性在没有精一、安宁之时,心性修养的要点就在于尽力不受外力的干扰:“故性为欲汩则乱,心为物动则争;是以绝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1]263刘基对于心性修养途径的阐述,重心在于绝外而返求自我的内心,保持自我内心的安宁与精一的状态,这样就能够不为外在物欲所扰,就能够神清气明,就能够专注于儒家的精神境界。刘基特别看重个人心性专注于内在的修养模式,其《拟连珠》认为这是能够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有形之器欲虚,惟虚则可以纳理;无形之理欲实,惟实则可以充器。是故性无不诚,然后能明一心;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事。”[1]265刘基在阐述心性修养理论时,提到了虚、实两个概念,并对应于理和器两个概念,这都是儒家思想中经常涉及的。所谓的虚是要求个人之心中,祛除充斥的物欲,替之以儒家的理这种概念。所谓的实,则是以理充斥于自我意念之中,指导自我的行为合乎圣人、君子之道。所以,刘基认为心性修养可以使个人最终恢复自我与圣人、君子相一致的本性,能够达到《孟子》《中庸》所说的诚这种境界,并在诚的指导下应对万物,从容不迫、进退自如、合乎儒家之道。刘基重视心性修养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圣人之道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来完成,所以主张:“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诸外,而民鲜能者,欲昏之也。”[1]147既然孝友这些儒家的根本道德法则在于自我的内心之中,而不在于向外去寻求,那么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重视自我的心性修养,就成了成就圣人之道的有效途径。刘基认为,虽然孝友这些儒家的根本道德法则根植于自我内心之中,但是一般民众却少有知道,故而心性修养的重要性则被一般民众所忽视。并且对于民众而言欲望充斥于心中,无法最终驱除欲望对于自我意念的控制。为了使个人能够循序渐进地进行心性的修养,刘基提出了以敬养心性的说法:“心敬则存,而不敬则昏;事敬则立,而不敬则跲。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维谧维专,式庄弗儇。臧之渊渊,出之虔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捐。既悠既坚,无不显或愆,无息弗干。熟之者圣,守之者贤。故曰敬胜则吉,怠胜则灭。敬而无失,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无术。是用作箴,以谨燕昵。”[1]222
儒学心性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敬,敬则会使个人的心性产生肃穆感、庄重感与神圣感,这样就能够与天道、天理合而为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就专门提出了持敬说,以此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之能够合于儒家之道。显然,刘基受到了朱熹持敬说的影响,也提出以敬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以此来进行个人的心性修养。刘基在阐述心之敬义时,开宗明义地指出,“心敬则存,而不敬则昏;事敬则立,而不敬则跲”,由此可知,敬在心性修养中有着重要地位。儒家一直强调礼乐之治,就是要求个人的言行要符合儒家之道,特别是圣人之道。如何才能够实现个人的言行符合圣人之道,这就是刘基主张的心性修养,就是以敬的态度来应对一切事物,同时还以敬来进行自我心性的反省,以此来体察自我有哪些言行没有做到与圣人、君子之道合一,并进而予以纠正。刘基主张的以敬来修持自我心性的方式,与儒家主张的日三省吾身是一致的,都是通过自我每日言行的反省来切实地体察与践履圣人、君子之道,这也是心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刘基在阐释心性与精神修养的关系时,特别看重个人道德伦理境界的提升,这与儒学心性论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刘基在阐述心性与气、情等概念的关系时,已经注意到了气、情这些不利于天理与圣人之道的因素。个人的心性之所以不合于圣人之道,就在于有气、情这些不利因素的干扰。因此,要使个人的心性最终符合圣人之道,就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实现,那就是通过伦理道德的修养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这样逐渐就能够实现个人心性与圣人之道的合而为一。刘基阐述个体心性与精神修养的关系,就是为了论证个人是如何祛除气、情这些不利于恢复圣人之道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而言,刘基阐述的心性与道德修养的密切关系,是完全符合儒家心性论的基本理论特征。
三、结论:刘基儒学心性论的历史地位
刘基生活的时代是元末明初,当时儒家思想的理论形态是理学,心性论是理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刘基的心性论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黄宗羲等人编撰的重要理学著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录刘基的著作与思想言论,但却不能由此否定刘基建立的心性论在宋明理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刘基阐述的心性论阐释了心与性、情的关系,这种将性、情纳入心的心性论,与程朱理学心统性情的命题有着不解之缘。刘基在阐述心与性、情的关系时,又涉及了理、气等概念,这些都是程朱理学心性论中极为重视的内容。同时,刘基在阐述心与性、情的关系时,“所接受的是宋明理学中由北宋张载首先提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法,‘天地之性’无有善恶,‘气质之性’则导人为不善,刘基在此又加上‘气质之性’乃‘邪气’诱导的说法。”[5]张载的心性论与程朱理学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心统性情这一理论就是源自张载的思想之中。因此,从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刘基的心性论应该是直接承袭了程朱理学的道统。刘基心性论中讨论的心与性、情,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气等概念,都是程朱理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内容,因此刘基心性论的定位,应该属于程朱理学一系。
同时,刘基的心性论也十分注重心性的修养,以此来提升道德与精神的境界,这与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倡导的人性修养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程朱理学与周敦颐思想的关系十分明显,因此刘基倡导的心性修养也与程朱理学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朱熹有《敬斋箴》传世,刘基也有同名著作传世,都强调了敬在心性修养中的作用,这不是巧合,而是表明了刘基心性论的理论渊源传承就在于程朱理学。
由于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宋明理学各派都涉及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刘基的心性论也概莫能外。从刘基对待佛教理论的态度而言,刘基辟佛的倾向较为明显,这与刘基本人坚持的儒家本位、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有关。以儒家心性论为道统、为正统而批评与抨击佛教的理论,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传统。在对待佛教理论的态度上,刘基和与他同时代的宋濂有着差异。宋濂尽管也坚持儒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但对佛教理论采取的是深入其中、为我所用的态度,因此宋濂对佛教理论并没有过激的抨击言论。而刘基则认为佛教与儒家多有不容之处,因此对佛教理论持抨击的态度。刘基对于佛教的抨击,体现在从分析世人信佛的原因、抨击佛教宣扬的生死轮回、抨击佛教诱导世人趋利避祸、以儒家思想的“帝”的观念来打压“佛”的概念这几个方面[6]。刘基的辟佛理论倾向,显示出刘基建立的心性论具有儒家道统与正统的理念。这种儒家本位的道统与正统的理念,在儒佛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与程朱理学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刘基心性论在明朝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北宋初年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思想发展的情况有着相似处:处于时代思想史的初创之际,既有对于前面思想的继承,又有对后来思想发展的启迪作用。只是在刘基生活的时代,由于程朱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显学,刘基阐述的心性论就是在承袭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这种处于明朝初年的思想智慧,对于后来阳明心学的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刘基倡导的心性修养理论之中,特别是将心性修养的重心放在不外求诸物,而内求于自心这一点上。尽管刘基传世的著作多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但这之中也体现出了刘基的理学思想。从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刘基阐述的心性论在明初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