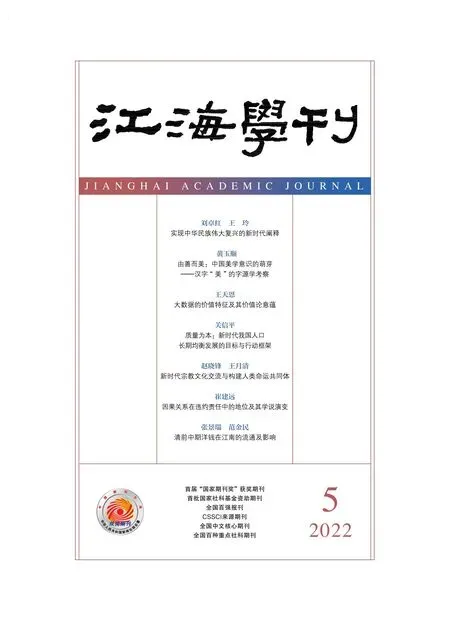民法典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释论
——针对“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分析
崔拴林
引 言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优化营商环境,我国《民法典》对动产担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法典》贯彻了“功能主义”担保观或“实质担保观”,对于形式担保观下的动产担保物权(主要是抵押权)与发挥担保功能的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合同法规则,适用统一的设立、对抗、优先顺位等规则;(1)参见谢鸿飞:《〈民法典〉实质担保观的规则适用与冲突化解》,《法学》2020年第9期;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法学家》2021年第1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动产抵押与这两种动产实质担保制度统一适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则。《民法典》第403条、第641条第2款、第74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则不同于登记(公示)生效的物权变动模式,存在解释和适用上的较大难度,这在2007年《物权法》颁行后该规则引发的诸多争议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故此,在《民法典》对典型动产担保中的动产抵押和上述两种动产实质担保统一适用这一规则之后,相应的法律解释就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理解和适用《民法典》第403条、第641条第2款、第745条以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担保解释》)相关规则时亟须解决的。首先,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中“善意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有哪些?这是《民法典》第403条、第641条第2款、第745条的核心问题之一,可既有的学说都未予重点关注。其次,在多重可登记动产担保物权发生竞存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可以用来确定这些权利的优先顺位,“已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受偿”规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但二者在适用中会导致法条相互排斥的竞合问题。那么,此时应该选择适用哪一种规则?目前学界和实务部门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适用后者而非前者。(2)持主流观点的主要文献参见王洪亮:《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的独立性解析》,《法学》2009年第11期;龙俊:《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3期;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林文学等:《〈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4期。持相反观点的主要文献参见董学立:《如何理解〈物权法〉第199条》,《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席志国:《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动产担保物权效力优先体系再构建——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审稿〉第205—207条》,《东方法学》2019年第5期;石冠彬:《论民法典担保物权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崔拴林:《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规则的法理与适用——兼释〈民法典〉第225条》,《法学家》202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辨析。只有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合理确定相竞存动产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也才能进一步合理界定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中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
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
就我国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规则而言,在《民法典》第225条涉及的准不动产所有权多重让与、第403条涉及的动产抵押物的再处分中,都存在无权处分。此时,善意第三人之善意/不知情的对象涉及在先权利人和处分人两个方面。因为第三人为善意时,其无重大过失地“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与“不知有在先物权人”是一体两面、同时存在的。故此,在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时,要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的“知情与否”。
(一)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
根据《担保解释》第43条,可以认为:抵押合同中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物的,会导致抵押人失去处分权。理由是:第一,根据《民法典》第403、406条,在动产抵押权与抵押物的在后受让人之所有权的竞存中,(1)在先抵押权未登记的,学说上一般认为善意的受让人可以取得无抵押权负担的所有权;(3)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法学家》2021年第1期。《担保解释》第54条第1项持同样的立场,抵押权人不能向已占有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行使抵押权。(2)在先抵押权已登记且抵押合同中没有不得转让之约定的,则认定受让人为恶意,但其能取得有抵押权负担的所有权。(4)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在这两种情形中,抵押人再转让都属于有权处分。假设“情形(2)”中的抵押人再转让构成无权处分,就会产生“恶意第三人基于无权处分获得所有权”的法律后果,这显然违反无权处分的一般规则。另外,既然“情形(2)”都属于有权处分,举重以明轻,“情形(1)”就更应如此认定。第二,《担保解释》第43条规定,抵押合同中有禁止或限制转让之约定时,(1)若约定未登记,而抵押权人有证据证明受让人知道该约定的(此时受让人当然为恶意),“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第1款);(2)若约定已登记(登记能阻却受让人的善意),“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除非受让人代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第2款)。据此,抵押合同中有不得转让之约定的,若受让人为恶意,正常情况下,法律效果是物权变动无效(受让人愿意代偿债务乃例外情形),这与第一点“情形(2)”中的法律效果(物权变动有效但存在抵押权负担)截然不同。既然法律效果不同,对应的构成要件也就不同。由于“情形(2)”所含关键性构成要件是“抵押人有处分权”,则第43条所含关键性构成要件就应是“抵押人无处分权”。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受让人都为恶意时,为何“抵押合同中有不得转让的约定”能产生“物权变动无效”的后果,而“抵押合同中无此等约定”却会产生“物权变动有效但存在抵押权负担”的后果?
对于上述无权处分,《民法典》第403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是否包括处分人?亦即,该第三人是否应该对“处分人无处分权”为善意?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担保解释》第43条,若受让人知道“抵押合同中有不得转让抵押物的约定(该约定导致抵押人无处分权)”,抵押物让与就不发生物权效力,此时,受让人当然不属于“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据此,受让人要成为善意第三人,就须对“抵押人无处分权”为善意。(5)受让人如果对“抵押人无处分权”为善意,当然就对“抵押合同有不得转让抵押物的约定”为善意。
(二)融资租赁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
在融资租赁法中,一般来说,哪方主体对租赁物享有处分权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融资租赁制度的功能主要是让出租人追求融资的利润,让承租人追求租赁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在融资租赁的法律构造中,不会细究处分权问题。(6)参见高圣平、王思源:《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2)》,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87—410页。但是,要分析融资租赁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首先就应明确哪方主体对租赁物享有处分权。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处分权,承租人则不享有。理由主要是:(1)从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承租人本身已经得到了“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特殊保护,即使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承租人的权利也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认为承租人还享有处分权,那么,承租人若要处分租赁物,第三人即使为恶意,也能毫无障碍地获得物权,这显然会严重损害出租人的利益,实不可取。更何况,实践中出租人在租赁期限内一般不会转让租赁物本身,而是会转让其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生的应收账款,或者将该应收账款证券化之后转让给投资者,这实际上是租金债权的让与,而非租赁物所有权的转让。(7)参见高圣平、王思源:《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可见,出租人即使有这种转让行为,也根本不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所以,从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讲,法律上没有理由否认出租人的处分权。(2)依据《民法典》第753条,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的,出租人享有法定解除权。但依据《民法典》第642条,所有权保留交易中的保留买方“不当处分”标的物的,保留卖方仅在当事人无相反约定时才拥有取回权,且该条并未规定卖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可见,就承租人和保留买方不当处分标的物而言,法律上认为前者的可责难性要大于后者的。“承租人不享有处分权”的观点与这种法政策是相容的。
既然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不应该享有租赁物的处分权,那么,融资租赁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也应该包含“存在在先权利人”和“处分人无处分权”两个方面。首先,依据《民法典》第745条,与承租人交易的第三人当然须对“存在在先的出租人”为善意,才能属于“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其次,即使出租人未登记其所有权,以至第三人在查询了相关登记系统后仍然不可能得知“存在出租人”的,第三人仍然要对“处分人是否拥有处分权”负有注意义务。如司法实务中即有观点认为,融资租赁的出租人一般会保留租赁物发票、合格证等单证原件,以明确租赁物所有权仍归属于自己。与承租人交易的第三人则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若在承租人未提供租赁物的相关单证原件时,第三人仍受让租赁物的,则不应认定其为善意。(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三)》,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4页。这种观点值得赞成,因为第三人在承租人无法提供任何能证明标的物权属的单证原件时,其至少应该对“处分人是否拥有处分权”产生合理怀疑,此时,第三人即使不能确证处分人无处分权,其也更接近“应该知道”的状态,而不是更接近“善意”的状态。可见,即使第三人对“存在出租人”确不知情,但其基于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应该对“处分人(即承租人)无处分权”产生合理怀疑乃至形成确信时,法律上就不能将其认定为第745条中的“善意第三人”,否则,也会与上文分析动产抵押时所依据的无权处分规则的法理相抵触。
(三)所有权保留交易中第三人“善意”的对象问题
与前文的理路一样,要分析所有权保留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首先应该分析所有权保留交易中是否涉及无权处分的问题。
第一,一般情况下,保留卖方没有处分权,在其有取回权时,则在一定条件下有处分权。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61、449条,所有权保留交易是一种附条件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否未定前,保留卖方仍然可以为处分行为,但不得妨碍买方的期待权。故保留卖方于条件成否未定前实施的处分行为,当条件成就时,在侵害了买方期待权的范围内,不生效力。同时,为了保障处分行为的相对人,第161条第3款特别规定,在此准用自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的规定,如善意取得制度。(9)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5页;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可见,在德国法上,就保留买方的权益保护而言,保留卖方实际上失去了处分权,故其处分行为会类推无权处分的规则。既然在没有明确推行功能主义担保观的德国法上尚且如此,那么,在我国《民法典》推行了这种担保观,从而保留卖方的所有权已经转化为担保权的前提下,就更应认为保留卖方在一般情况下不享有处分权。不过,如果保留卖方拥有取回权且依法取回了标的物,依据《民法典》第643条第2款,买方在回赎期内没有回赎时,卖方可以转卖标的物;根据该规定,解释上可以认为卖方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处分权。另外,如果卖方取回标的物后必须立即处分,否则标的物价值会明显减损,足以损害卖方权利,那么在解释上,也应当认可卖方有处分权,可以再次出卖标的物。(10)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9页。
第二,当事人有“买方可以处分”的约定时,买方当然有处分权。所有权保留以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条款为原型,它指“在全部货款付清之前,卖方保留交付给买方的货物的所有权”。(11)Gerard Mc Cormack,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5.此外,实务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保留,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类型有:(1)延长型所有权保留,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附加债权让与条款的情形,此时,保留卖方允许买方在正常经营中出让标的物,作为交换,保留卖方事先受让因该出让而产生的、买方对第三人的债权。(12)[德]A.施塔德勒:《德国法上所有权保留的未来》,王洪亮译,《中德私法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此时涉及债权的确定性问题,(13)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斯德:《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页。若承认未来债权具有确定性,就应该认可这种交易模式,(14)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页。而《民法典》第761条明确规定了未来的应收账款债权可以转让,所以在解释论上,当然可以得出我国法也认可这种交易模式的结论。二是附加加工条款的情形,即买方意欲对标的物实施加工行为,此时双方会约定:保留卖方成为因加工而产生之新物的所有权人。德国实务中的通例是,保留卖方在其提供部分的价值范围内,在新物上取得共有权。(15)参见[德]A.施塔德勒:《德国法上所有权保留的未来》,王洪亮译,《中德私法研究》第3卷,第157页。依据我国《民法典》第322条,因加工而产生的物的归属,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据此,这种交易模式在我国当然应予认可。(2)事后设定的所有权保留,其要点是:经保留卖方允许买方再以所有权保留的形式向第三人转让标的物,但不公开先前的所有权保留,故此,保留买方向保留卖方清偿了价款时,以及第三人向保留买方清偿了价款时,保留卖方的所有权消灭。在这种交易模式中,所有权保留中的停止条件多了一项,即第三人向保留买方支付价款,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且不损害他人利益,故我国法应予承认。(16)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1)》,第237—238页。可见,我国法可以认可这几类非典型的所有权保留。在附加债权让与条款的延长型所有权保留、事后设定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当然享有处分权。在附加加工条款的延长型所有权保留中,若当事人约定买方可以处分,则买方自然享有处分权。
第三,当事人之间没有“保留买方不得处分”的约定时,买方有处分权。在实质担保观之下,保留卖方的所有权已经功能化为担保物权,买方取得有担保物权负担的所有权,因而买方在合同不禁止其处分时享有处分权。(17)参见谢鸿飞:《〈民法典〉实质担保观的规则适用与冲突化解》,《法学》2020年第9期。
第四,当事人有“买方不得处分”的约定时,买方无处分权。这种约定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上自然应该认可。基于动产担保规则体系化的考虑,此时应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6条、《担保解释》第43条,从而认定买方无处分权。
所有权保留的登记对抗规则旨在防止保留卖方未登记的所有权形成隐形担保,以保护保留买方之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而非旨在保护保留卖方的交易相对人,故此,与保留卖方交易的相对人不属于第641条第2款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所以当保留卖方无处分权时,不存在因其未经登记而“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只有当保留买方无处分权时,才可能存在第641条第2款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根据上面的分析,保留买方无处分权仅涉及这一情形——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有不得处分的约定,所以,第三人对“存在保留卖方”为善意时,也必然对“存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以及合同的内容”为善意,也就不会知道“保留买方因合同有特殊约定而无处分权”。这是否表明第三人对“存在保留卖方”为善意时,也必然对“保留买方无处分权”为善意?本文认为不然。因为与融资租赁的情形一样,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当事人在交易中都应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当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约定保留买方无处分权时,保留卖方自然可以保留标的物的发票、合格证等单证原件,以证明标的物所有权仍归属于自己。此时,与保留买方交易的第三人就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若保留买方未能提供足以证明标的物权属的单证原件,第三人就至少应该对“处分人是否拥有处分权”产生合理的怀疑。比如,第三人应该想到:既然处分人没有标的物的权属证明,则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是否属于他人?处分人是否出于不法原因而占有了标的物?显然,对于保留买方无处分权的真实状况来说,这种情形中的第三人在法律上并不处于“不应该知道”的状态,而处于“应该努力知道”的状态,故这种第三人并非登记对抗规则所要保护的善意第三人。所以,即使第三人对“存在保留卖方”确为善意,但其基于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应该对“处分人(即保留买方)无处分权”产生合理怀疑乃至形成确信时,法律上也不能将其认定为未经登记的保留卖方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
总之,在所有权保留登记对抗规则中,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也包含“(存在)在先权利人”和“处分人(无处分权)”这两个方面。
动产担保权优先顺位规则中第三人善意问题的中美比较法观察
就同一动产上多重抵押权竞存时的权利优先顺位问题而言,《民法典》第403条和第414条在适用时会产生彼此排斥的结果。依据第403条,未登记的在先权利人可以对抗恶意的第三人,即使后者已登记亦然。依据第414条第1款第2项,第三人只要已登记,即可对抗在先权利人,即使第三人为恶意亦然。那么,此时应该适用哪一条?目前学界和实务部门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适用第414条,排除适用第403条。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为行文简洁,以下将主张适用第414条的观点简称为“414方案”,将主张适用第403条的观点简称为“403方案”。
“414方案”的首要理由是: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继受自美国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UCC)第9编在处理担保物权人之间的优先顺位规则时并不考虑第三人的善意恶意问题。故此,我国的相应规则应该依据其“母法”的逻辑来适用。(18)参见王洪亮:《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的独立性解析》,《法学》2009年第11期;龙俊:《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3期。这一理由值得仔细辨析。
就“在先权利未登记(或完善)时,是否应依据第三人的善意(without knowledge)来确立相竞存担保权之优先顺位”的问题而言,迄至1956年,UCC第9编都遵循传统规则,给予未完善之担保权的主体优先于所有知道其权益的第三人的顺位。(19)D.Baird and T.Jackson,Security Interests in Personal Property:Cases,Problems and Materials,Foundation Press,2nd edn.1987,p.369.后来,法典第9编改变了传统规则,使得第三人对在先未完善担保权的知情并不会剥夺其已完善的担保权的优先顺位。立法政策作出改变的理由是:让优先顺位问题取决于以“知情的状态”(the state of knowledge)为基础的事实调查会产生不确定性并引发诉讼。例如,可能很难确定所争议事件的真相,这会给当事人带来新的困扰:他们可能吃不准是该商定降位协议(subordination agreements),(20)UCC第9.339条规定,享有优先顺位的担保权人可以通过协议降低其优先顺位。——引者注还是该调整贷款利率。另外,一个使优先顺位取决于(第三人)是否知情的制度倾向于奖励那些不调查其债务人的疏忽大意的债权人(careless creditors),而不是那些在作出贷款承诺之前会调查债务人之信用状况的勤勉的债权人。(21)Gerard Mc Cormack,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p.156.由此可见,就担保权竞存情形中第三人的“知道”或“不知道”而言,美国法认为“第三人一旦调查就可能知道,不予调查就终为不知”,(22)有学者在多重抵押权竞存的议题下将之归纳为“一旦调查就可能知道在先抵押,而不予调查就终为善意”,参见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只要未予调查,即使是一个“疏忽大意的债权人”也构成“不知道”。对于“知道”或“不知道”的这种界定,在担保物被处置(尤其是出卖和出租)的情形中同样成立。比如,不论担保物买受人是否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即使担保权人已登记了担保权,但只要买受人没有查询,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得知该担保权益,其就属于善意,因为UCC并没有规定买方负有查询融资声明登记的义务。(23)参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解读》,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23、750页。所以,在UCC第9编规定的动产担保制度中,第三人不负有相关查询义务,“权利竞存者是否查询官方记录并无区别”。(24)Harry C.Sigman,Eva-Maria Kieninger(eds.),Cross-Border Security over Tangibles,Munich:Sellier.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7,p.44.在先的担保权登记后,第三人由于未查询或未以其他方式得知担保权的,也构成“不知道/善意”。可见,美国法上的“善意”乃是依据第三人“是否确实知道在先权利”的主观心态,而不是依据在先权利的公示状况以及第三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认定标准。然而,主观心态又如何举证证明?这显然极大地增加了在先权利人证明第三人之恶意的难度和法官裁判的难度。
再者,与我国实行的电子化的统一动产担保在线登记系统相比,美国法上的登记制度给当事人带来了较高成本。在20世纪末,即有学者指出:“UCC的登记制度使得登记部门彼此独立又多样化,还遍布美国,这是落后于现代技术的例证。”(25)Michael I.Spak,A Modern Proposal:“Suggested Perfection”-for the 21st Century,63 UMKC Law Review 79(1994).UCC第9编在2010年修改后仍然规定:除与不动产有关的财产外,其他任何动产担保物的登记地点都是位于各州首府的州务卿办公室。公众可以选择向登记处或者向从州政府处获得登记信息的商业经营者查询。如果公众以通信或类似方式向登记处查询时,登记处可以依法收取一定费用。(26)参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解读》,第644、660—661页。最关键的是,“UCC第9编的登记制度并不会导致对于一项已登记融资声明的存在或内容的‘推定告知/知情(constructive notice)’”,(27)Harry C.Sigman,Eva-Maria Kieninger(eds.),Cross-Border Security over Tangibles,p.43.故此,在先的登记不会阻却第三人的善意。基于此等善意标准和登记制度,即使在先权利人已登记,也无法阻止善意第三人的出现,这就导致前者交易的风险和安全性难以预测,进而提高制度运行的成本,损害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所以,美国法在确定相竞存担保权的优先顺位时,不再考察第三人是否善意,确实会克服这些弊端,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我国民法中的“善意”将第三人对于在先权利的不知情建立在物权公示原则的基础上,依据在先权利的公示状况以及第三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作为认定善意的标准。就动产担保权的竞存而言,由于相关担保权的登记是客观现象,第三人仅应该就登记系统中是否记载了在先权利负有注意义务。故此,在这种善意之下,在先权利人登记时就能够直接阻却第三人的善意,前者未登记时则可直接推定后者为善意,前者有证据证明后者为恶意时才可以推翻这种推定。《担保解释》第43条就此作了非常明确的有代表性的规定。所以,在我国法上,“善意”的认定以物权的公示为基础,简便易行,这与美国法的做法大相径庭。再者,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国发〔2020〕18号),我国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动产和权利担保由当事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登记。这种贯彻“人的编成主义”的电子化登记制度使得当事人在登记和查询时成本极低、效率极高。(28)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法学家》2021年第1期。由于此等善意标准和登记规则比美国法上的对应制度更加简单明了和易于操作,故此,在先权利人未登记(或完善)时,即使要根据第三人是否善意来确定相竞存担保权的优先顺位,也不会导致美国法上的那些弊端。相反,这样的制度设计具有若干优点:(1)它不会造成善意认定上的不合理的困难,没有增加当事人举证的难度,对于主张善意的第三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民法典》第403条规定的善意指“无重大过失的不知情”,而这种善意的推定属于“善意的一般性推定”,在这种推定中,主张善意者提出主张(该主张应包括构成善意的事实)的陈述本身就可构成一项证据。(29)参见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相应地,它也没有增加法官裁判的难度。(2)它不会造成当事人交易的风险和安全性难以预测。因为在先权利人未登记的,其应该能预测到出现善意第三人的风险;其已登记的,则能阻却第三人的善意,此时,其交易的安全无虞也非常确定。而第三人为恶意的,其应该知道自己不能对抗在先权利人,这也是可预测的。总之,我国的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不会产生不合理的制度运行成本,反而很好地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兼顾了交易的效率与公平。故此,我国法在确定相竞存担保权的优先顺位时需要考察第三人是否善意,并无明显不妥之处。
综上,在美国法与中国法上,动产担保制度中之善意和登记的法律构造不一样,相应地,如果在先权利未登记(或完善)时,要依据第三人是否善意来确立相竞存担保权之优先顺位的制度成本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照搬美国法上不考虑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做法,“母法不可变”并不能成为“414方案”的一个坚实理由。
动产担保权竞存规则应采用“403方案”的进一步分析
除了“母法不可变”,支持“414方案”的学者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这里再择要分析其中的一个。(30)学界支持“414方案”的其他理由参见龙俊:《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笔者对此的初步分析,参见崔拴林:《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规则的法理与适用——兼释〈民法典〉第225条》,《法学家》2021年第2期。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403条是一般法,而第414条是特别法,所以,应该优先适用后者。(31)参见龙俊:《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3期。但该观点对此未作深入论证。实际上,就动产多重抵押中相竞存的在先和在后权利人的关系来说,(I)第403条涵盖的情形是:a.已登记的在先者能对抗已登记的在后者(这一点可以根据物权优先效力的一般原理推出来),b.已登记的在先者能对抗未登记的在后者,c.未登记的在先者不能对抗善意且已登记的在后者,d.恶意且登记的在后者不能对抗未登记的在先者,e.恶意且未登记的在后者不能对抗未登记的在先者。(II)第414条第1款涵盖的情形是:a.已登记的在先者优先于已登记的在后者,b.已登记者优先于未登记者,c.未登记的在后者与未登记的在先者地位平等。显然,(I)a与(II)a是一回事,(I)b、(I)c是(II)b在逻辑上能包含的情形,(I)d是(II)b的例外情形,(I)e与(II)c则是彼此补充、相互说明的关系。据此,就动产多重抵押而言,第403条所涉全部情形与第414条第1款所涉全部情形之间都不能成立一般与特别的关系,相反,倒是第403条包含的“恶意且登记的在后者不能对抗未登记的在先者”这种情形,乃是第414条第1款第2项规定之“已登记者优先于未登记者”的一般情形的例外。据此,第403条才是这里的特别法。可见,“403方案”才是解决第403条与第414条之竞合问题的合理思路。
“414方案”也是《担保解释》所认可的法政策。该解释的制定者就此指出:担保物权人之间的顺位,根据《民法典》第414条、第415条确立的规则确定即可,无须考虑彼此之间是否为善意,“否则有悖于建立统一的可预测的优先顺位规则的目的”。(32)参见林文学等:《〈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4期。
本文认为,“建立统一的可预测的优先顺位规则”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这个目标中,规则的“可预测(性)”并非关键所在,因为《民法典》第403条和第414条的规定都是明确的,所以不论适用“414方案”和“403方案”中的哪一个,当事人交易的风险和安全性都是可以预测的(上文对“403方案”之优点的分析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该目标中的“统一”,亦即,这里所说的是哪些优先顺位规则的“统一”?这些规则被“统一”的标准是什么?显然,“414方案”给出的回答是:这里说的是动产担保权(抵押权、质权、买卖合同中被保留的所有权、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竞存时优先顺位规则的“统一”,“统一”的标准是第414条第1款(尤其是第2项)。本文认为,动产担保中的权利竞存涉及多重担保权的竞存以及在先担保权与在后所有权和债权(主要是承租权)的竞存两个方面,而第403条是旨在“统一”这两方面规则的标准。所以,就“建立统一的优先顺位规则”而言,“403方案”与“414方案”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那么,哪一个方案更合理?本部分以动产抵押中的权利竞存为切入点展开分析。
动产抵押中的权利竞存涉及多重抵押权的竞存以及在先抵押权与在后所有权和债权的竞存两个方面。(33)需注意的是,能与在先抵押权相竞存的在后所有权乃是抵押人“正常经营活动”之外的买受人所获得的所有权,而非“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所获得的所有权。参见龙俊:《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3期。“414方案”提倡的是双轨制:一方面,在处理动产抵押权竞存时,不适用《民法典》第403条;另一方面,在处理动产抵押物的转让和出租时,适用《民法典》第403条、第406条和《担保解释》第54条第1、2项。然而,这种双轨制并不能很好地兼顾不同交易形态中的效率和公平。容分述之。
就在先抵押权与在后所有权竞存时的优先顺位规则来说,“403方案”与“414方案”并无差异,二者都认为此时应该适用“403方案”。该方案在这种情形中偏重于实现公平而非效率。申言之,依据《担保解释》第54条第1项,在后受让人(如买受人)占有标的物乃是其可以对抗在先抵押权人的必要条件,可见,与在后抵押权人仅需登记相比,在后受让人需要支出更大成本(即需要交付和占有物)才有对抗在先权利的可能。此外,直接占有标的物的受让人更容易就该物与他人达成交易,如再转让或再设立担保物权,而不能占有物的在后抵押权人仅能通过债权让与来转让其抵押权。然而,一旦受让人对“有在先抵押权人”为恶意,则:(1)既会影响受让人与抵押人之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受让人如能获得所有权(亦即原抵押合同中没有不得处分的相反约定),也不能对抗在先抵押权;受让人即使在依据《民法典》第524条行使第三人清偿权之后,可以令抵押权消灭并且可以依据该条第2款的规定从抵押权人处获得对于抵押人的债权,也仍面临不能实现该债权的风险。(2)也会影响受让人与其后手之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在受让人不能对抗在先抵押权时,其后手继受取得的权利自然也不能对抗该抵押权。尽管实务中要证明他人的恶意极为困难,但至少在先抵押权人通过诉讼主张在后受让人为恶意时,可以采取申请查封标的物等手段来阻止后者将物处分给他人。可见,尽管在后受让人对物的占有比在后抵押权的登记要支出更多成本,其对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拥有比在后抵押权人更直接、全面的控制力,从而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物展开交易,但受让人的恶意却会损害其诸多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
但是,就多重抵押权竞存时的优先顺位规则来说,“414方案”却将保护效率放到不应有的高度上了。申言之,转让抵押物所有权时,交易成本更高(需要交付),能引发的物权变动数量更多(涉及抵押人与受让人的所有权转让、受让人与其后手的再转让和再担保),相比之下,将抵押物再抵押时,交易成本低(无需交付、登记成本可忽略不计),能引发的交易数量较少(涉及抵押人与第三人的设立抵押、第三人与其后手的债权让与)。然而,在“414方案”下,即使第三人对“有在先抵押权”为恶意,只要其抵押权已登记,就不会影响第三人优先于在先抵押权的顺位,也不会影响其债权受让人的优先顺位。特别是,第三人及其债权受让人的优先顺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也不受影响:(1)在在先抵押权人要求抵押人办理登记的过程中,抵押人为了架空前者的抵押权或侵害其顺位利益,给恶意的第三人先办理了登记;(2)恶意第三人在没有在后权利人时,为了损害在先权利人的顺位利益,抢先作了登记。在这些情形中,在先权利人即使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为恶意,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414方案”(或UCC等不考虑第三人善意与否的立法例)这么做是为了侧重保障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34)Gerard Mc Cormack,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pp.156-157.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然而,如前所述,UCC基于其对“善意”的特殊界定和登记效果的特殊性(在先权利人的登记不能阻却在后权利人的善意),这么做是合理的;但是“414方案”这么做却会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当在先抵押权与在后所有权竞存时,“403方案”会导致成本更大、数量和所涉主体更多的交易遭受效率上的损失,这并未遭到“414方案”的反对;但为什么在多重抵押权竞存时,“403方案”只导致了成本更小、数量和所涉主体更少的交易遭受效率上的损失,却不被“414方案”认可?另外,基于“414方案”,在抵押人与恶意第三人合谋抢先登记损害了未登记在先权利人的顺位利益时,对于成本更高的行为(让与抵押物所有权),法律会给在先权利人提供救济,对于成本更低的行为(再抵押),法律却不提供救济,这岂不是会引发抵押人与恶意第三人合谋侵害在先权利人之顺位利益的道德风险吗?
更重要的是,不论在哪一种权利竞存的情形中,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案,第三人(在后受让人、在后抵押权人)的注意义务是一样的,都要查询相关登记系统中是否有在先权利的记载,并需考察处分人是否具有通常的权利外观;同时,在先权利人未登记时,要举证证明这些第三人之恶意的难度也是一样的,因为此时前者要证明的都是“后者通过登记系统之外的其他途径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存在”。据此,在多重抵押权竞存时采用“403方案”的制度运行成本(包括诉讼的成本),也就与在先抵押权与在后所有权竞存时采用该方案的制度运行成本并无二致。那么,在多重抵押权竞存时,“414方案”到底有什么理由不能容忍适用“403方案”所致交易效率的损失呢?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第三人为恶意时也应该放弃对在先权利人顺位利益的保护呢?“414方案”对此并未作出充分的论证。
当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抵押物的再抵押比再转让和再出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再抵押(以及抵押权竞存)中,即使适用“403方案”,实务中也不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产生多少不合理的影响,因为在陌生人社会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先权利人(在先者)与第三人(在后者)彼此没有直接联系,只要在先者不登记就应推定在后者为善意,可见,在后者很容易就能成立善意并能对抗在先者。所以,“403方案”在实务中一般也不会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总之,综合考量多重抵押权竞存、在先抵押权和在后所有权及债权的竞存可知,就相竞存权利主体的利益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而言,“414方案”有厚此薄彼、兼顾不周之弊,“403方案”则平衡有道、兼顾周全。所以,在处理动产抵押中的两类权利竞存问题时,“403方案”应该成为“统一的可预测的优先顺位规则”。有鉴于此,在《民法典》第403条中,在先抵押权人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包括:善意且已办理登记的抵押权人、善意的质权人、抵押人正常经营活动之外善意且已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善意且已占有标的物的承租人。(35)参见崔拴林:《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规则的法理与适用——兼释〈民法典〉第225条》,《法学家》2021年第2期。需注意的是,在抵押人不享有处分权时,善意第三人应该对“有在先抵押权人”和“处分人无处分权”皆为善意。(36)如果在后承租人明知抵押人无处分权而仍与后者缔约,则此等承租人显然不属于“债权优先于物权的特殊情形”中的债权人,故其债权不能优先于在先权利人的物权。如果承租人对于“有在先物权人”和“处分人无处分权”皆为善意,则可以类推《担保解释》第54条第2项(因为本项所含“抵押人有处分权”的构成要件与“承租人对‘处分人无处分权’为善意”的情形相类似),认定此等善意承租人可以对抗在先权利人。基于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的“母法”示范效应,在动产担保中,“403方案”也应该成为处理多重担保权竞存、在先担保权和在后所有权及债权竞存时的统一的优先顺位规则。
另外,“403方案”也为确定动产担保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范围提供了一个答案,亦即,此等善意第三人包括在后的、善意且具备公示要件(登记或交付)的抵押权人和质权人。所以,“403方案”在确定此等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 语
《民法典》第 403 条、第 641 条第 2 款、第 745 条确立了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这一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善意的构成”和“善意第三人的范围”这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由于该规则会涉及无权处分,故总体上讲,善意第三人之善意的对象涉及在先权利人和处分人,第三人无重大过失地“不知有在先权利人”或“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权”都构成善意。就后者而言,在动产担保权的竞存中,《民法典》第403条与第414条第1款第2项形成法条竞合,综合考量之下,应该适用前一条,排除后一条;相应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包括善意且已办理登记的抵押权人、善意的质权人、善意且已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但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之买受人”的受让人、善意且已占有标的物的承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