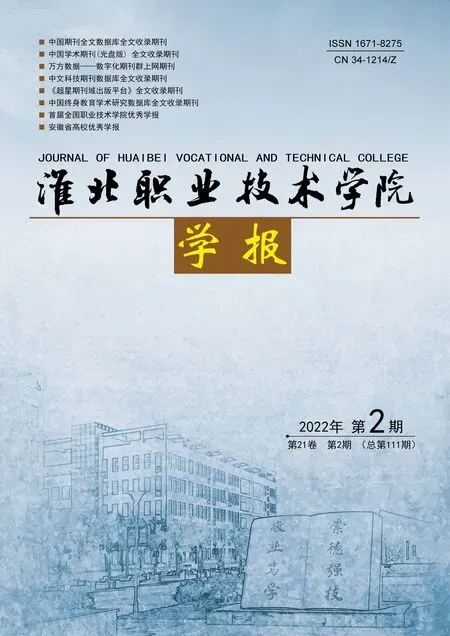千年的邂逅
——论汉乐府对元杂剧之影响
朱云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正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4,元代是我国戏剧的巅峰时代,尤以杂剧称盛,元代杂剧有着独特的美处,“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1]4虽然王国维对元杂剧的文学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如此巨大的成就离不开前代文学的奠基,元杂剧作品中就包含有前代汉乐府的文学基因,元代杂剧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或有意或无意对汉代乐府诗进行了接受。汉乐府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体裁,在两汉时期被发扬光大,呈现出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其诗乐交融、母题重构,以及女性人物形象给予后世剧作家一定的启发,对元代杂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汉乐府和元杂剧的相似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不同文学体裁的相互渗透。
1 诗乐交融,踵武前作
元杂剧以相对固定的音乐形式作为作品的基本框架,一部完整的元杂剧不仅仅包括文本故事,更离不开音乐上的呈现。汉代已经出现了俳优戏剧和角觝等百戏,虽然它们都还不成熟,但都对元杂剧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的“乐”范围十分广泛,郭沫若曾认为:“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2]汉代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机关,自然也和俳优戏剧和角觝等百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汉代乐府诗中就有诸如戏剧演出的例子,据逯钦立记载,《俳歌辞》是一部汉魏年代的作品:“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3]这是一首扮演野兽类的歌词,说明汉乐府诗中确有为诸戏演出的戏词。从一些汉代经典作品中,我们也能窥见诗乐舞交融的影子,甚至有科白的出现,诸如:《西北有高楼》《大风歌》《战城南》等作品,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抒情诗歌,而具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可以说为日后的元杂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除了那些通俗的音乐活动,汉代的乐府诗歌还与祭祀中的雅乐密不可分,而祭祀这一重大活动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也体现出汉代乐府诗与音乐的密切联系。《郊祀歌》云:“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4]4《练时日》《华烨烨》等乐府诗也大力叙写神灵的各种动作,这些诗歌所追求人神共乐场景并非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而是通过演唱、舞蹈具体表现出来,神灵活动与场面舞台兼具,可以说这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雅乐”也具有“戏词”的性质。
以上是从内容雅俗的角度进行解读,从音乐的角度也能看出其对汉乐府的影响,很多汉乐府单纯以乐入诗,相和歌辞中的《上留田行》是因声作歌的范例,有记载曰:“王僧虔《技录》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古今注》有‘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故曰《上留田》’。”[4]563汉乐府中相和歌辞的调式可以分为平调、清调和瑟调,这些调式按照诗歌表达不同情感而灵活运用。在语言方面,汉乐府民歌作品中多有叠词与口语,诗歌声韵和谐,富有韵律美,写景状物更加生动传神,增加了诗歌的连续性与音乐美。汉乐府看似是叙事诗歌,实际上部分作品更接近后世的说唱文本。在汉乐府中,乐的大众娱乐功能和表现情感的特质得到发挥,而后世的元杂剧也是娱情与抒情的结合,这使得元杂剧在后世戏曲创作中体现更为明显。音乐形式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决定音乐的内容,所以,汉乐府足以称得上是乐化的诗歌。
如果说在音乐层面上汉乐府是乐化的诗歌,那么,元杂剧可以算是诗化的戏曲。元杂剧作为戏剧本身就和音乐舞蹈结合,但其又具有诗化的特征,从中我们也能探索出诗乐两者的互动交流。元杂剧自从其诞生就有自己的音乐特色,杂剧中的曲字不仅要求每首每句的句末平仄,甚至在句中字词的使用上都有规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作品中的唱词语言具有音乐美与诗化美。其次,元杂剧的诗化体现在曲词上,有的剧本整部剧几乎就是一首抒情诗,作品中根本没有精彩的情节冲突,但作者的重心放在了抒情曲词上。例如:《单刀会》一剧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但观众都能被作品中主人公的一腔热血所感染,剧中关羽的唱词不仅能让读者体会到演唱者音乐水准的卓越,更能从语言上感受到剧作者诗词功底的深厚。其实,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品中,抒情类型的小曲经常出现,例如:关汉卿代表作《窦娥冤》中主人公窦娥在慷慨赴死前的唱词也和《单刀会》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耍孩儿][二煞][一煞]这三首唱词感情如火如荼,将主人公的三件遗愿如同潮水般涌泄出来,虽是性情的恣意宣泄,但在语言上做到了诗话,达到了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最后,元杂剧在宾白上也体现出诗化的倾向,这些宾白借剧中人物之口不仅对舞台的场景进行解说,增进了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也”[5],更因其文人化的诗句与韵语而让人陶醉。宾白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出其俗的一面,而诗词韵语的雅化语言虽减缓了剧本的发展,但却能增加作品的诗歌属性,从而取得雅俗兼备的效果。
2 袭古而取新:母题的重构
中国的古代诗歌中存在众多母题,胡适就曾谈道:“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枝叶细节……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它们原来同出一个‘母题’。”[6]母题在诗歌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化,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观念的更替以流动的状态展现给观众,甚至跨越不同体裁的文学著作。元杂剧的创作也离不开对前代文学作品中母题的影响,所以,戏剧的审美与母题的重构可谓意义重大,元杂剧中的母题就是剧作家审美情感的结晶,其中采桑式母题最为有名。
采桑母题与汉乐府的《陌上桑》息息相关,元代石君宝的剧作《鲁大夫秋胡戏妻》虽从题目上取自于汉刘向《列女传》中的秋胡故事,但其深受《陌上桑》的影响。尽管二者颇具相似之处,却也有诸多不同,这些差别体现出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对汉乐府《陌上桑》的继承与发展,从中又能看出元杂剧对于汉乐府母题的沿用与重构。首先,从发生地点来看,两部作品中的主要场面都是桑林,桑林成为男女主人公发生冲突的中心,但《陌上桑》的地点只有桑林,别无他处。而《鲁大夫秋胡戏妻》还叙述了戏妻前秋胡与妻成婚的场景,以及戏妻后在家相识的尴尬场面,其舞台的广阔度明显胜于前者,这其实是将桑间调戏这一中心事情扩展了去写,增加了诗歌原有母题的深度与广度。其次,在人物刻画上,《陌上桑》使用赋法极度铺张罗敷衣衫之华美,并通过其他观者对罗敷的痴迷来反衬罗敷之美,但作品中只字不提罗敷的容貌美,这也是汉乐府经常出现的写法——写衣不写人。《鲁大夫秋胡戏妻》在相似的场面下对人物的刻画比前者更进一步,剧作者不仅仅是通过描绘梅英的外貌来刻画主人公形象,而且增加了媒婆、李大户等人物,进一步丰富了女主人公梅英的形象。相对于《陌上桑》中的秦罗敷,梅英个性色彩十足。她认为夫妻应当相敬如宾、地久天长,十年里,她一直在默默等待秋胡的归来,面对李大户的逼婚与父母的施压,她也能够从容应对,表明她自己坚决的态度。但罗敷和梅英还是有差别的,前者更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而后者口语化的表达更具有田间生活气息。在《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三折中,石君宝更用心书写了梅英怒斥李大户后去桑林途中的复杂内心世界,女子的柔弱可怜与黯然神伤跃然纸上,这使梅英这一人物更加真实化、立体化,这是《陌上桑》所不及的。在整部戏剧中,梅英的心路历程一直在变化,她从开始的诧异、到恼怒、再到最后的愤恨,整个情绪波动被刻画得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戏剧的最后,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丈夫,一个独立自强、不受男性支配束缚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塑造出来了。所以,综合以上人物刻画来看,秦罗敷以自己的聪慧取胜,而罗梅英更有泼辣爽直、独立坚强的品质,这不仅仅是因为剧本容量相对较大,还有时代的呼唤。第三,是对采桑母题思想性的再探索。《陌上桑》反映出中国传统女性坚贞、睿智的品质,而石君宝的这部剧作虽对前者有所继承,但意蕴更加深厚,梅英勇于承担生活重担的高贵品格和自我独立之精神是作品的精华,而且她身上的反抗精神也能折射出元代人民对异族统治阶级的反抗,这不仅仅是男女爱情问题,更上升到国家民族的矛盾问题。就《鲁大夫秋胡戏妻》的结尾而言,同样值得深思,曾有学者认为:“《秋胡戏妻》虽然结尾是大团圆,但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喜剧,因为该剧一系列情节都是悲剧性的。”[7]秋胡十年间发生的改变彻底击碎了梅英的梦,他们就算和好,以后的路又能坚持多久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听众思考,这种余味无穷的思想意蕴也是《陌上桑》望尘莫及的。
石君宝对于这部杂剧接受前代母题的原因,与剧作者内心固有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梅英的人物形象与生活观念折射出石君宝根深蒂固的妇女观。“贞烈妇梅英守志,鲁大夫秋胡戏妻”的剧名显然是一种“男子中心论”的体现。元代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但杂剧作家心中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消失,儒家观念在元代社会上仍占主流,梅英的形象源于生活真实,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后人没必要对此过于苛责。《陌上桑》奠定了采桑母题的基本形态,后代文人想要深层次挖掘变得十分困难,大多数人只能对此进行模拟与仿作,这使得采桑母题进一步文人化、雅化,更使其成为一种抒情方式,汉乐府原有的民间气息被彻底抛弃,从俗到雅的过程也就意味着采桑主题的衰亡。但在石君宝的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中,这一失传已久的乡土气息再次出现,作品中的采桑场景并没有以诗化的语言呈现,而是以完完全全的叙事性语言表达,重新回到了汉乐府《陌上桑》世俗的轨道,正可谓袭古而取新,《鲁大夫秋胡戏妻》在传统的母体中汲取了多方面的营养,作品本身富有“元代特色”,既富有历史性,又具备时代性。
3 相似的女性,别样的刻画
汉乐府是诗歌,元杂剧是戏曲,它们虽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通过阅读对比就能发现它们都是叙事性文学,因而离不开作品中人物的塑造。汉乐府与元杂剧都刻画了众多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其中不少人物具有普遍的共性,元杂剧里部分女性形象的刻画神似汉乐府中的人物,这主要包括两种女性:追求爱情类与对抗邪恶类。通过解读汉乐府和元杂剧中的女性人物,品味她们生活中的悲喜离合,可以更好地感受汉乐府对元杂剧的影响。
第一类女性人物包括《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倩女离魂》中的王文举、《金线池》中的杜蕊娘等,她们都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而不懈努力。这些女性都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敢于私下约会,敢于私奔,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她们敢于冲破传统的贞节观念,敢于反抗父母的权威,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真挚爱情,她们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8]为粪土,这类高大的女性人物摆脱了在女子头上的强大的精神枷锁,书写着自己的浪漫人生。例如: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宋引章把从良当作最佳出路,殊不知自己终究被排斥在正统社会伦理体系之外,名正言顺的夫妻生活是她追求的理想目标,可宋的单纯天真导致其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在这部杂剧中,虽然宋引章不是主角,但正因为她的存在才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宋引章是一个奋斗者,可惜的是普遍存在的歧视使她终究不能摆脱被蹂躏折磨的命运。剧本虽以喜剧告终,但如果没有赵盼儿的帮助,宋引章奋斗的结果就是一场悲剧。又如:《潇湘雨》中的张翠鸾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男子的背叛,甚至被棒责一顿之后刺配沙门岛,并差点在路途上遇刺身亡,其悲惨程度不逊于宋引章,相比于崔莺莺、杜蕊娘、李千金等人,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遭受的苦难更大。以上这类形象在汉乐府中已有相似的存在,《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中的刘兰芝,美丽而勤劳却遭到婆婆的一再刁难,不堪忍受而自求遣归,但自求归家只是一时之策,她内心深处还是深爱着焦仲卿。《上邪》和《有所思》更是直接书写女性对于真挚爱情的追求。“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乃敢与君绝。”[4]231对爱情的渴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有所思》中:“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4]230诗中女子原本打算将火热的诚心和纯真的爱意交给远在天涯海角的心上人,但闻知所爱男子居然另觅新欢,女子毅然决定分手,其内心的痛苦何尝不比杜蕊娘等人少呢?元杂剧中追求爱情的女子与汉乐府中的女性一脉相承,只不过前者多以团圆的结局收场,后者多以悲剧收场,但仔细观之,元杂剧中的爱情剧虽结尾套上大团圆,但全剧大部分还是以悲为主,戏曲里的悲剧要素不就是汉乐府里女子悲惨心声的展现吗?只不过元代剧作家在作品结尾实现了团圆,大团圆在很多时候也许仅仅是个形式,那些看似最终团圆的女子其实早就走上了一条悲剧的道路,她们都曾走过了汉乐府中女子的道路。
第二类女性人物是对抗邪恶的正义化身。元杂剧《秋胡戏妻》中的秋胡赴京博取功名,归来之时今非昔比,但他好色专横之心也随着名利而增长,在剧中,已然成为一个邪恶的反派。梅英面对秋胡的调戏坚决反抗,并没有把他视为自己的丈夫,俨然视作一个敌人对待,这体现出梅英勇于面对邪恶的伟大。在贞洁与金钱面前,她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原谅了自己的丈夫,未来的日子在物质上或许很是丰足,但梅英没有因金钱向昔日的丈夫妥协,虽然剧本以大团圆告终,但早已宣布了梅英未来爱情的“死亡”。除了梅英以外,《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为了拯救宋引章而与周舍斗争,《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勇于与黑暗势力决斗的女子,她们都是元杂剧中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女性代表。这些光明高大的形象在汉乐府中就能找到影子,《陌上桑》与《羽林郎》两首即是,罗敷因其美若天仙的姿容很容易引起无赖之徒的注意,于是,招来无耻男子的轻薄言语,对此,罗敷以坚决的态度来回绝,她的乐观与自信也能在元杂剧中的梅英、赵盼儿、谭记儿身上体现。《羽林郎》中胡姬的经历和罗敷极为相似: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拜为大将军,窦氏兄弟专横跋扈、抢占民女、无恶不作。此篇讲述霍家奴调戏胡姬的故事,胡姬以“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4]909婉转拒绝,更通过“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4]909表达自己的忠贞态度。从汉乐府中的罗敷、胡姬到元杂剧中的梅英、谭记儿、赵盼儿,这些女性人物都富有立体感与形象性,这少不了故事中邪恶势力的衬托,以路人的反应衬托出罗敷的美,以宋引章、白士中的张皇无主衬托了赵盼儿、谭记儿的智勇双全,以使君、金吾子、周舍、秋胡、杨衙内的卑劣嘴脸及言语交锋中的尴尬无助衬托出五位女主人公的纯洁高贵、大胆机智。从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们能读到一种乐观主义精神,《陌上桑》和《羽林郎》虽是诗歌,但足以称得上是一出戏剧,两者在故事情节、角色分配、矛盾冲突等方面都符合“机智喜剧”的特征,《秋胡戏妻》《望江亭》《救风尘》更是如此,这五部作品在女性人物刻画上都充满戏谑与俏皮的风格。看似智勇双全的女子的背后也有她们的辛酸,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是男女社会地位悬殊的产物,以致我们欣赏作品时也会产生悲喜交融之感。
4 结语
各类文学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与不同文体间的渗透作用密不可分。汉乐府与元杂剧,这两个看上去相距甚远的文学体裁,它们其实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交流,元杂剧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汉乐府的接受。元杂剧剧作者们写作剧本水平高超,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但是,他们的开拓创新摆脱不了文体交融的历史影响。如果看不到文体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就很难把握文化长河中各种文学的发展方向,也不可能探索出文学现象中有趣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