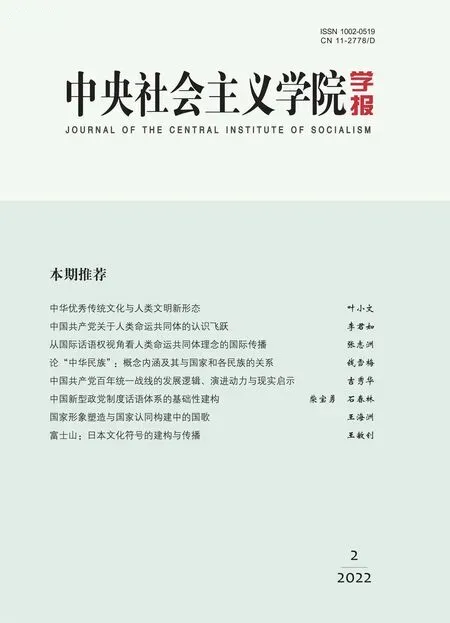从国际话语权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中国带有政治与外交性质的最热门词语之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一个带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虽然2011年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首次使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表达,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逐渐发展与完善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系统化也是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习近平在重大国际场合完成的,即是说,它的提出、完善与系统化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五大要义,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体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于回答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这五大要义所包含的话语创新与国际话语权含义,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基础。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研究者所认同。不过,作为一套系统性新话语,在西方占据国际舆论和话语权主导地位的“西强我弱”总体格局下,它在传播中也遭遇了一定的“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深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的“超越性”话语含义,突破其“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正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话语创新与传播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系统化的丰富内涵,媒体舆论和研究者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各自的阐释,但它首先是一套创新性话语。我们知道,理念的传播首先是话语的传播,理念是通过话语来表达的;而所谓话语创新,其核心的要旨就是理念创新。话语创新和理念创新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非两个不同的事物。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可忽视话语创新的视角。而话语创新的基本动力,一是创新性理念表达的需要,二是价值观传播的意图,三是话语权的竞争。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创新而言,这最终无疑是指向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完善和体系化,有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场合。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①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该句子的完整表述是:“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阐明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题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阐述为五大支柱: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③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544页。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也以此五大支柱性理念为标准式表述。④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含这五大理念的完整表述是:“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多重理念构成的复合概念。
这五大理念无论是合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体来看,如何理解其所具有的话语创新价值和国际话语权含义?当然,这里所指的创新,是与此前既有的理念表达或他者的话语表述相比较而言的。
一方面,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五大理念合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既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关联,与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外交定位相关联,与历史的经验总结与教训相关联,也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关联。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之答”“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套中国创新性的国际话语,每一个理念的表达都是有上下文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的。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创新价值及其作为“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含义。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整语境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主题演讲中都讲得很清楚,这里仅举一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的阐明则更加完整。在这些重要讲话及报告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的对话,无疑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系统化的及时的国际传播,对于克服“传播困境”、促进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从单个理念来说,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似乎都不特殊;其实不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既有理念的超越性正是包含于其中。这五大理念是中国可以有信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终究会赢得话语权的基础。
其一,关于持久和平。当今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虽然不同阶段形态各异,但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冷战的终结看似迎来了世界和平的时代,但很快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如霸权国家美国主导或作为主角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英、法、德、加、澳等西方主要国家也以出钱或出兵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战争。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和叙利亚的内战,以及非洲某些国家的内战与种族屠杀,都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大事件。在许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虽然内因有别,但从外因来说大体都是美国“烹制的一道有毒的菜”。冷战后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了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核不扩散机制遭到严重破坏,核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再看中国,它尽力维护和平,倡议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派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维和部队去一些发生战争的国家。中国深知“持久和平”的重大价值。虽然众多研究都把“持久和平”的理念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和睦、和谐的“和天下”思想,事实上古人并没有做到“持久和平”。在西方思想史上,虽然康德有过“永久和平论”②[德] 伊曼努尔•康德:《论永久和平》,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但那是对欧洲历史上战争频仍的反思,仍然只是在一个哲学家的脑袋中而没有能够付诸实践。而“持久和平”的理念超越了东西方过去所有关于和平的理论,中国推动构建的实践能力超越了纸上谈兵的设想。
其二,普遍安全。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对安全的追求,被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认为是国家的本能、首要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追求安全,即使到冷战后时代,一些强权国家仍然追求“绝对安全”。为了安全利益,某个国家不顾国际道义、以邻为壑的事件就经常发生,“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成为现实主义信奉的圭臬。但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一方追求绝对安全必然会造成另一方的不安全,于是会出现“安全困境”。①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 World Politics, Vol.2,No.2,1950,p.157.就冷战后美国与伊朗以及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例子来说,核问题的出现也与某些国家追求单方面安全导致的“安全困境”有关,而解决方式的理念基础只能是“普遍安全”。各国都能获得安全,才是真的安全。在冷战后安全概念泛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也更凸显,普遍安全的另一层含义应该是各种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普遍安全”。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是最好的说明。可见,“普遍安全”理念才是各国家各民族获得安全的基础,也是解决国家之间走向冲突和战争等许多矛盾的一把钥匙,它超越了西方以“理性自私”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
其三,共同繁荣。全球化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每一个国家都处在全球价值链中,即使有的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独自繁荣,但从长远来说它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国家共同繁荣的背景下保持长久的独自繁荣。这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逻辑,也是经济规律使然。当然,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自然禀赋、管理机制、生产能力和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发展有先后,是否繁荣有差异,但经济和社会繁荣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世界人民谋大同。②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主旨演讲,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求索奋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全文)》,2021年4月20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4/20/c_1127350811.htm。如果没有共同繁荣,当然就谈不上世界大同。但对中国来说,这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一方面,它植根于中华文明“大道不孤,天下一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天下主义”世界观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外交”政策和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方略,有“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大国责任担当和道义。中国也欢迎他国“搭便车”,③《习近平欢迎各国“搭便车”亚洲方式布局周边外交》,2014年8月22日,https: //www.chinanews.com.cn/gn/2014/08—22/6523301.shtml。把自己的发展变成他国发展的机遇。中国虽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种共同繁荣的价值理念是表达得非常清晰的;而回头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它们对于具有“共同繁荣”价值的“一带一路”倡议多有贬损,尤其是第一霸权国为保持“美国优先”政策,不惜“筑墙”“脱钩”。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繁荣”无论在道义上、文化理念上,还是发展政策上都超越了西方。
其四,开放包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明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民主、自由等许多共同的价值,但是没有单一的标准。如果只有单一的标准或单一的文明形态,就像百花园里只有一种花、阳光只有一种颜色,世界就会变得单调。开放才能学习,包容才能互鉴,这不仅是文明和文化的要求,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要求和经济发展形态的要求。但总有一些强权国家自以为是,它们或信奉“西方中心主义”,或将西方经济模式化的“华盛顿共识”推向世界,甚或将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性的文明,中庸的思维方式也有利于采取包容性的政策。即使说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理念还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中国所主张的开放包容无疑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的基本法则。“开放包容”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单边主义”的偏狭、“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与“历史终结论”的虚幻。
其五,清洁美丽。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势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如今,在南北半球的许多城市里连清洁水源、洁净空气都成了稀缺物品。保护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过低碳、绿色、节能的生活,已经是世界潮流的方向。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存的环境为代价,人类在生态危机中不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旦发生,没有谁能幸免。中国作为大国,人口多,碳排放压力大,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但是现在就明白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可以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并行不悖,除了做解决气候暖化问题的积极行动者和榜样外,倡导人类生态文明、把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作为环境和生态的价值理念,这就超越了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共和党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及与世界不合作的碳排放政策。当然,对于仍然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倡导也是一种引领。
概括而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五大价值理念和支柱,实现了对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他国、历史与现实、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多重超越。正是因此,五大理念支柱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从国际话语权的理论视角来看,创新的、优秀的理念是理论的品质,而认同才是理念及系统化的理论赢得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增长与“传播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已经产生了巨大反响,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话语权的快速增长。当我们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困境”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就是其国际话语权增长的态势。因此,两方面都不可偏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及其已经赢得的国际话语权增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众多重大的国际场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理念的国际传播。例如,他于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2017年1月17日,他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1月18日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等等。全球范围的记者和新闻媒体对会议主题的报道和对演讲的评论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包含的理念成为一种“世界话语”。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权威性国际组织的“背书”。例如,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①《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2月11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17—02/11/c_1120448960.htm。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2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安理会决议呼吁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18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17—03/18/c_1120651440.htm。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在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时,明确表示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着手解决许多紧迫问题。③《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7年3月24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4/c_129517029.htm。11月1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被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被纳入联合国安全决议。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日,第21版。2020年11月6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表决通过“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一次被写入联合国外空决议之中;决议序言段重申,应研究和采取切实措施,达成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一次写入联合国外空决议》,2020年11月7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07/c_1126710616.htm。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诸多国际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赞誉。例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现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鼓舞人心,能改善国际治理体系,让各国更好地应对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谷畑勇夫表示:“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全世界认识到每个国家既可以各具特色,也可以和谐相处。”⑥《习近平致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10月7日,第1版。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的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委主席、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鲁罗姆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前瞻性,是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有效办法,应该在多边领域加以推广。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认为,各国只有摒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相信巴基斯坦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受益者。⑦《综述:联合国热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1月2日,http: //mt.sohu.com/20171102/n521268634.shtml。
四是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外交实践相结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多层立体的体系。如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第四届核安全峰会、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领导人气候峰会,集体会见出席中国海军成立七十周年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等场合,分别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中国还在地区层面分别提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盟友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在双边层面,中国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等一系列国家领导人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倡导共建命运共同体。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52—53页。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话语”“世界话语”。话语只有被接收到才可能被认同,只有被认同才会转化为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不断获得认同、赞誉,而且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基础理念和动力的作用。因此,它不是一套空洞的原则,而是赢得认同越来越多、国际话语权日益增长的“中国方略”和“理念软实力”。不过,我们在看到话语权增长的成就时,也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所遭遇的“传播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没有从积极的方面回应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反而经常对之抹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猜忌和疑虑。中国部分邻国甚至也以“国强必霸”的逻辑来看待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践平台“一带一路”,②陈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72—73页。因此常有抵触情绪。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其“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是有矛盾的,拜登政府宁可自己花费更大成本搞新基建,也不愿意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它的一种竞争与不合作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则担心崛起的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使它们被中国所控制,虽然这种误解可能会慢慢消除,但是从目前来说,这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增信释疑”工作。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遭遇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于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民来说,思维方式带有重原则、重理念和保持一定模糊性的特征,而分析性思维则相对不足,这也反映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上。西方的思维方式重个案研究,重逻辑分析,带有分析哲学的特征。因此,中国人的好心与善意,西方人却往往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站在全球问题和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视角来提供的“中国方案”,而西方人对中国倡导的“双赢”“义利观”“天下观”等理念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认为其带有“乌托邦”色彩。③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第202页。还有人认为,中国梦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都只是一种“话语表达”或“道德叙事”。④William A.Callahan, “China 2035: From the China Dream to the World Dream, ” Global Aff airs, Vol.2,No.3,2016,pp.247—258.Jacob Mardell,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 Xi Jinping’s New Era, ”October 25,2017,https: //thediplomat.com/2017/10/the—community—of—common—destiny—in—xi—jinpings—new—era.这种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也反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翻译上。在中文中很好理解的这个词,翻译成英文或其他一些外文,就遭遇到难以找到对应词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仅英文就有多种翻译。如“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等,尽管“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被确定为官方标准,但是“shared future”字面意思是“共享的未来”或“共同的未来”,而汉语中“命运”与“未来”却是相去甚远的概念。时间是流逝的,如果“共同命运”可以被理解为“共同的未来”,那么已经过去的昨天就不是“共同命运”了吗?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存在于不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是很难消除的。
其三,西方对于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存在误解。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颇多研究,他们从“现实需求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动因有五花八门的误解。如有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在保障中国国内稳定和发展,为中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保障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长久性;①Christine R.Guluzian, “Making Inroads: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 Cato Journal, Vol.37,No.1,2017,pp.135—147.或认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的“一带一路”是为了稳定中国的能源补给及资源优化,解决资源分配不均与产能过剩的发展困境;或认为是为了应对美元体系的冲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认为是为了稳定东北亚局势,促进东北亚国家间信任与共同利益;或认为是为了维护海上安全,包含着中国人谋求霸权的动机,等等。②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第198—200页。这种误解就把中国基于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念与和平理念,以及由“以天下为己任”经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大国担当”精神等优秀品质,当成了一种“自利”行为。这样的严重误解,就不免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陷入困境。
其四,“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使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舆论环境往往由西方媒体主导。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有所提升,但是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获得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世界传媒霸权仍然掌握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手中,它们塑造着主流舆论,掌握着带有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形式性质的话语主导性。尤其是与传播相关的议程设置、国家形象塑造能力、叙事结构、修辞应用等,都是它们的“拿手好戏”。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仍然不小。在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当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往往与“一带一路”相钩挂,也就很难获得它们的积极评价和认同。虽然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走出了“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传开没人信”的“认同障碍”。
三、从话语权视角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尽管存在着“认同障碍”与“传播困境”,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具有向国际社会传播的重要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套创新性话语,它的传播是否有效,最终要看是否转化为了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因此,从国际话语权理论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国际传播,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国际话语权理论包含一些基本的关于话语产生权力的原理,或者说话语产生权力的逻辑。依据这样的逻辑,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我们可以树立更强的信心。
话语如何产生权力,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国际关系学学者侧重于国际关系视角的解释,传播学学者侧重于传播理论的解释,语言学学者侧重于语言学的解释,但是话语产生权力的原理是一样的。话语产生权力,不仅在于话语的内涵和本质,而且需要通过传播而获得认同;所以说,认同就是话语产生的关键,而传播必不可少。在话语的国际传播中,人们总是对与自己相同或相近的他国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易于接受并认同,而与之相反的则难以产生认同,话语不能获得认同当然也就不能赢得话语权。话语权就是话语言说者或者话语主体的话语所赢得的权力,因此对话语主体的认知和判别至关重要。形象积极正面可信可亲的国家,其话语更容易赢得认同。形象跟身份也相关联,朋友和伙伴比对手和敌人更容易赢得好的形象。国家的国际形象如何,又在于“自塑”和“他塑”的话语竞争,而话语权强弱结构则不仅对谁的话语能在塑造国家形象中起到决定作用,也直接决定着话语产生权力的关系。思维方式相近者更易于互相理解和认同,思维方式差异大则容易在跨文化中产生误解。道义是话语的内涵本质之一,也是话语赢得权力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寻找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进路,促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应基于国际话语权生产的逻辑并结合当下的“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予以探索,具体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化世界共同价值的认同。目前我们较多地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这固然是必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和思维的烙印,这是不可磨灭的,也是它所具有的“中国性”的根本。不过,今后要更多强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世界共同价值,以便得到认同。其实,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演讲中,就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时阐述了中西方的共同价值认同:“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他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①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页。这样的表述就容易强化国际传播效果,赢得国际话语权。
其二,思维方式上靠近。有研究者指出,既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跨文化传播”常见的话语不对应性。今后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应用于国际问题解决和外交实践的个案上多下功夫,注意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原则性”“模糊性”特征,多在分析思维上下功夫。还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当前存在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传播效果不佳的状况,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外传播过程中话语体系设置缺乏亲和力,叙事语言单一、叙事路径程式化,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全球贡献的质疑与批评,中国媒体通常扮演澄清者和反驳者的角色,缺乏相应的议程设置。①赵文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国际传播》2020年第5期,第39页。换个角度来说,西方的媒体评论重“批评”,而中国的媒体重弘扬“正能量”而对“挨骂”非常敏感,这也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习惯于国内传媒环境的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的大趋势下,要学会更好地适应国际舆论的风格。
其三,塑造中国良好形象。西方媒体经常贬损中国形象,有时候是出于其偏见和“职业习惯”,有时候是出于“不明真相”,还有时候是出于意图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竞争。“增信释疑”是需要去做的,可以消除一部分不必要的负面形象。在对中国形象的“自塑”和“他塑”竞争中,我们可以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树立形象,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和平形象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又如,中国的减贫成就巨大,中国是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减贫榜样,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宣传其实难以有亲和力,需要加强的是个人化的减贫和生活改善的故事。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上有许多误解和质疑,我们可以讲述这一倡议是如何有助于沿线发展中国家某些个人减贫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使“共同繁荣”的宏大理念具有“可感性”。中国形象的塑造,就是中国作为话语主体的形象和身份的塑造,对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国际话语权意识。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复合体,政治话语权是核心,经济话语权是物质基础,文化话语权是根本,媒体话语权是前沿,意识形态是攻防阵地……各领域的话语权形成一个复合结构。一套话语背后包含价值理念,有叙事逻辑和结构,但说到底还是需要国家的发展实力。中国的发展优势要转化为话语优势,这需要思路创新和话语创新,需要有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国际话语权战略。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必然会在国际传播中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和认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套创新话语,也理应在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