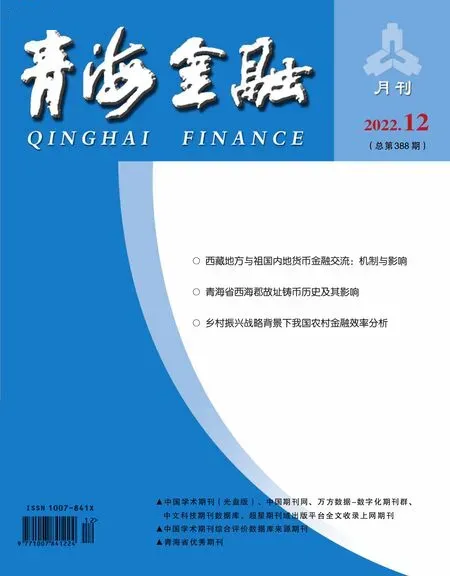青海省西海郡故址铸币历史及其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史研究课题组
一、研究背景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汉武帝经略河湟之前,湟水两岸、九曲牧地、祁连山下和江河源头等地,都是羌人部落游牧之地。《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以产牧为业”“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当时西羌人大都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加强,经过“文景之治”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国力强盛,具备了解除边境威胁的能力,于是开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将赵充国至金城,随后统兵过黄河,深入湟水谷地,大量汉族百姓迁徙至青海。期间,随着汉文化逐渐与羌文化融合,以五铢钱为主的货币也进入了青海。
1944年,考古人员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青海湖东北金银滩草原上发现了一座三角城遗址(实际上其平面呈不规则的四方形)。经考证,这座遗址便是王莽新朝时期所建西海郡郡城的所在地。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西海郡故城内发现了一座虎符石匮,刻有“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的瓦当,以及“大泉五十”“五铢”“小泉直一”“大布黄千”四类陶钱范。其中,除“五铢”钱范之外,“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黄千”都是王莽新朝时期发行的货币。
本文主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青海西海郡故城的数件陶钱范、货币及其他相关文物,结合文献材料,探讨王莽新朝时期在西海郡城铸币的历史及其影响。
二、西海郡出土陶钱范概述
史书中记载的西海郡有三处:一处是东汉末年置于甘肃省的居延西海郡;另一处是吐谷浑王国在青海湖以西设置的西海郡;还有一处便是王莽新朝时期在青海湖附近设置的西海郡,此即本文所述和研究的西海郡。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秉政,力谋开疆拓土,当时,已有东海、南海、北海等郡,“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唯西方未加”。为形成“四海统一”局面,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取西海地区(今青海湖)和盐池(今茶卡),于元始四年冬在治龙夷(今青海省海晏县三角城)设置西海郡,并在环青海湖地区设置五县归西海郡管辖。大约到天凤六年(公元19年),西羌各部纷纷起义,重新占据了青海湖地区,西海郡从建立到消亡其实只存在了大约15年。
钱范是西海郡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铸币的必要之物,目前见诸资料的共有8次,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和王莽新朝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研究员到西海郡故城考察,采集到了五铢钱、货布、货泉等货币及钱范。1972年,西海郡故城内的草地上发现了一件已使用过的王莽新朝时期“小泉直一”的陶范,陶范长11.5厘米,宽7.5厘米,厚5厘米,后馆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1975年,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小泉直一”残钱范一件,上有阳文隶书反书“前锺官工良造第八”等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作人员又在西海郡故城内发现一件陶钱范,疑为今馆藏于青海省博物馆的“大泉五十”叠铸范。2014年,工作人员在西海郡故城采集到五件钱范,均为夹细砂红陶质。
除在西海郡故城发现了王莽新朝时期的钱范和货币之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葬群、互助汪家庄汉墓、民和川口镇东垣、西宁南滩汉墓、西宁陶家寨汉墓群皆有货币出土,这些货币的发行时间大约集中于西汉至东汉年间,出土王莽新朝时期的货币主要是“大泉五十”,但数量并不多。
馆藏于青海省博物馆的王莽新朝时期“大泉五十”陶钱范是西海郡出土陶钱范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它长13.9厘米,宽9.2厘米,厚6.3厘米,夹砂粗陶、呈砖红色。钱范为圆形长方体,层层叠放、底平。范面斜排两行钱样,钱铭为阴文“大泉五十”。在王莽新朝时期的钱币中,流通时间最长、铸量最大的就是“大泉五十”。
王莽秉政时,曾大力推行一系列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币制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王莽实行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货币改革期间大量铸造“大泉五十”、错刀、契刀等货币,与五铢钱并用。第二次币制改革时,废除了流通已久的五铢钱,在保留“大泉五十”的基础上,新铸“小泉直一”。为加快新旧货币兑换,增加新币的供应量,王莽还下放了铸币权,派出谏大夫50人到各郡铸造新货币。后来,经历第三次、第四次币制改革后,全国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最终危及政权。西海郡故城多件陶钱范及货币等相关文物的出土,证明王莽新朝时期的铸币制度已延伸至青海湖地区。
三、西海郡铸币的可能性研判
虽然在西海郡故城发现了多件陶钱范——“五铢”“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共四类,以及“货泉”“大泉五十”“契刀五百”“货布”“小泉直一”“一刀平五千”等货币,但是学术界对于王莽新朝时期是否在西海郡铸币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王莽新朝时期在西海郡铸币的可能性很低。其一,虽然西海郡故城有钱范出土,但是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青海虽有王莽新朝时期的相关货币出土,但是数量并不多。一些汉墓中有货币出土,但是数量较少,也有可能是古人陪葬之用;其二,目前未在青海发现铸炉遗址遗迹或窑址;其三,王莽新朝时期青海地区经济落后,当地游牧民族使用货币的概率很低。王莽新朝之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环青海湖地区的管控。直到明清时期,环青海湖地区还有很多百姓“茶马互市”时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本课题组与以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王莽新朝时期,在中央授权下西海郡曾经铸造过货币的可能性很大。其原因如下:
(一)政治条件
《汉书·王莽传》记载,始建国元年,“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西海郡也是当时拥有铸币权的郡国之一,西海郡出土虎符石匮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虎符就是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大臣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物。西海郡虎符石匮的建造年代为始建国元年十月,正是王莽新政与西汉王朝政权更迭之时,表明王莽政权对西海郡非常重视。据甘肃酒泉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的记载,王莽始建国元年之后,在西海郡任命大尹。《续汉书·百官志》记载:“(郡)皆置诸曹掾吏”。李贤注曰:“王莽时置喜好军,令其吏皆百石亲事”“一曰为四百石,二岁而迁补”,意为王莽新朝为稳固西海郡吏员,故特地给西海郡的官员们以秩四百石的优厚待遇。出土汉简还载:“西海轻骑张海马亖匹、驴一匹”。可知王莽新朝设置西海郡时曾有军队设置,一是为防护西海郡城;二是为了抵御擅长骑射的西羌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由此可见,西海郡建立后,王莽新朝并没有因为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等因素将其不管不顾,而是很重视它,与其他各郡一样,西海郡也有着完善的官吏制度和军事设施。
(二)经济条件
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边政公论》著文中指出:“东西方的交通不是由张骞开始,汉以前即有”。唐长孺先生曾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中谈到:“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与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料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期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接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颇大的作用”。唐长孺先生所说的“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指的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羌中道。
丝绸之路青海道起源于先秦时期,当时青海道是玉石、彩陶、小麦、青铜等物品传播、流布的交通要道之一,因此,学术界以“玉石之路”“彩陶之路”等命名此通道。苏海洋先生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孕育自齐家文化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贸易之路也可能是钱币的流通之路。西海郡故城恰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一个重要节点上,东面连着河湟地区,西面可达西域各国,北面还可以进入河西走廊,是羌中道上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两汉时期,因匈奴的影响,河西走廊阻多通少。但当时羌中道周边却是道路通畅,经济繁荣。所以许多西域和中原的商人都会通过羌中道,进行贸易,这就促进了西海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取道湟水流域。从西域归汉时,途经于阗、鄯善,“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羌中便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到王莽新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早已成为一条国际化通道,承载着氐羌民族与中亚、西亚交流、沟通的渠道。王莽设置西海郡后,自然也获取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管理权。在交通要道处铸币,可以方便来往商旅,从中获得利益。
(三)技术条件
铜器冶炼技术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成为主要通货。考古证实,欧亚大陆最早的冶金技术来自西亚,并以西亚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新疆是我国最早接触到铜器冶炼技术的地区。因为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地区也是青铜冶炼技术传播的重要场域。
在青海省有多处青铜冶炼遗址。考古证实,今格尔木至青海湖之间,都兰香日德地区是羌中道沿线重要的中继站,这里发现了诸多青铜冶炼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采集到铜渣和炼铜用具的残片,还有斧、刀、钺、镞等青铜器,说明这里很早以前就在铸造铜器。除此之外,在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曾出土我国最早的青铜镜——七角星纹铜镜,在西宁沈那遗址出土了长61.5厘米、宽19厘米的圆銎宽叶铜矛……这些青铜器的出土证明,青海地区较早就拥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那么青铜铸币自然也不会有技术上的困难。“结合羌中道沿线的铜器冶炼遗迹,笔者认为,在冶金技术传播过程中,西羌可能借助羌中道将这一技术带到河湟地区,形成这一区域特色鲜明的青铜文化”。
西汉时期制造青铜钱币普遍采用的是范铸技术。铸钱必须先制作钱范,再将融化的青铜注入钱范,冷却后取出钱币的毛坯,最后加工成钱币。西汉时期,我国的铸币技术已经成熟,为了提高铸钱效率,人们开始制造陶土为原始材料的钱范。与铜范、石范相比,制造陶范不仅成本低,而且只要采用模压工艺,将带有钱币模型的工具在半干的土坯上压印,就能制造出比较理想的陶范,减少了铜范等刻制钱腔的步骤。这种浇筑钱币的方法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叠形范。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海郡故城发现的王莽新朝时期“大泉五十”陶钱范,有被人使用过的痕迹。范面上斜排两行钱样,分布着八枚钱形。青海省博物馆保管研究部工作人员曾认真研究了这块陶钱范,发现整块陶钱范是由好几片泥质薄范片层层叠放而成。在钱范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孔。当时,由谏大夫从长安携带颁行的铜母范到各郡国,以金属母范为模,翻制出若干泥质子范,阴干后装窑烧制成陶子范,然后将数块陶子范层层叠加,形成一组,用泥封严,仅留浇注口,将铜液灌注进浇注口,冷却后敲碎陶子范,即可成钱,一次可铸数百枚不等。铜质母范可以反复利用,陶质子范为一次性使用。西海郡故城出土“大泉五十”陶钱范上的小孔便是浇注口,使用陶范有着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甘青地区是彩陶的故乡,广泛分布着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文化类型。在青海,第三纪红土广布,这些红土成为制作彩陶的主要原材料。王莽新朝时期,用红土制作夹砂粗陶陶范也算是一种就地取材。
综上所述,在西海郡铸币,有着极好的技术条件。“青铜冶金术以新疆为中心向东传播,通过甘青地区传播至中原,所以掌握了冶铜技术的西羌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文明成果东移的中介”。
(四)人才条件
王莽新朝设立西海郡之前,青海湖地区多为羌人居,他们本身就掌握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西汉时期,不少汉人从中原迁徙至青海。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是汉王朝向青海移民的前奏。汉宣帝时,青海羌人叛乱,西汉老将赵充国进兵湟中(青海),平定羌乱后罢兵屯田,许多来自淮阳、汝南等地的士兵和驰刑、应募之人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安居在了青海。
王莽新朝时期,频繁的币制改革让百姓民不聊生,国民财富被大量洗劫,很多普通家庭面临破产。强权币改下的普通大众生活困难,最终很多人走向有违法风险但又有暴利可图的盗铸钱币之路。第一次币制改革后,“民多盗铸者”。第二次币制改革后,“及坐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记载,王莽新朝时期建立西海郡后,为扩充西海郡人口,王莽不惜扩大“犯禁”的范围,“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后“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青海,徙者以千数万”。这些“犯禁者”中不乏中原地区为生计而盗铸钱币的手工业者。拥有先进青铜冶炼技术的西羌人与曾盗铸钱币且拥有先进技术的“犯禁者”,无论哪一方都是铸币的技术人才。
(五)资源条件
铸币自然需要铜资源,青海祁连山一带便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西海郡所处的海北地区的成矿区带有赛日图——冷龙岭多金属矿带、达坂山铜矿带……全州共发现各类矿产地431处,探明储量占青海省铜资源的比重达15.1%。《青海矿产资源志·古近代矿业》记载,在距今约2900~2700年的柴达木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炼铜用具的残片及冶炼剩下的铜渣,说明当时的少数民族也已掌握了采矿炼铜的技术。
综上所述,王莽秉政后,为了占据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交通要道,在青海湖边设置了西海郡。西海郡的羌人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再加上王莽徙万民于西海,又谏大夫50人到各郡县铸造货币,使得铜矿资源丰富的青海湖畔铸币有了很大的可能。
四、西海郡铸币的历史影响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王莽政权设置西海郡,下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5县,设炉鼓铸货币,并在西海郡发行、流通货币,这对青海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扩大了汉朝的政治疆域。西海郡的存在虽然很短暂,但它的设置将中央管辖和郡县制延伸到了青海湖地区,对以后整个青藏高原逐步归入祖国的版图,有着深远的意义。
其次,改变了羌人的贸易方式,促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发展。西汉势力进入青海以后,主要管控区域在河湟地区,羌人是环青海湖大片地区的主要聚居人。在青海考古中,虽也发现过一些贝币,但是数量极少,是否被当做媒介用于商品交换还有待考证。西海郡建立以前,羌人大多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商品贸易,这样的交易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西海郡设立后,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正式扩大到环青海湖地区,五铢钱及王莽新币也随之进入。青海文史学者程起骏认为,西海郡成立后的大笔支出,从中央王朝运送钱币,一来是路途遥远,不便运输;二来出于安全考虑,就地取材铸造钱币更为合理。这次铸币,改变了西羌人多年来的交易方式,方便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青海道“玉石之路”“盐道”“青铜之路”“民族迁徙之路”“小麦传播之路”的作用愈加凸显,同时也推动了青海经济社会的文明进程。
再次,促进了青海地区的民族融合。大约从公元2世纪50年代开始,古羌族迁居汉地的越来越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仰慕汉文化而自愿内迁汉地;二是发生战争后被迫迁入汉地。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羌人或自愿或被迫,一直没有停下迁徙的脚步。两汉时期,在羌人内迁的同时,汉人也逐渐迁徙到了青海。羌汉居民交错杂居,在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融和,使当时青海地区的民族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最后,促进了青海地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随着两汉及王莽新朝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徙,农耕文化逐渐传播至青海湖流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一起。汉族人口的迁入,一方面使得青海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青海的人文风貌。随着农耕文化的西进,原本属于游牧文化区的湟水上游和黄河谷地,逐步被开发成新的农业区。中原移民世代习惯于农耕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羌人的生活方式。
西海郡从设立到废弃,虽然只有十余年时间,但是王莽新朝时期在青海设立西海郡,并极可能在此铸币,仍然对青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海郡陶钱范及钱币的出土证实,当时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已扩展到环青海湖地区,西海郡的设置及货币的流通,改变了羌人的贸易习惯,促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发展。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