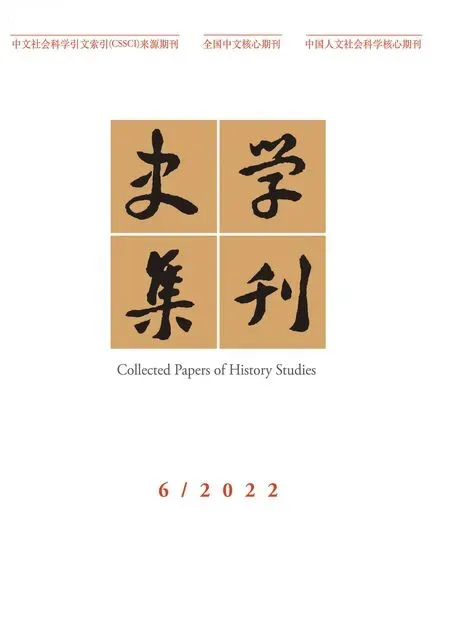重新解读清中前期欧洲来华使团与外交礼仪之争
陈玉芳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马戛尔尼(Goe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开启了中英政府之间的直接往来。学界对清朝与该使团交往方式的解读,是迄今为止研究清中前期中国处理对欧洲国家关系方略的基础。诸多学者认为清朝固守“天朝”礼仪规范、保守自大,并将此作为中英关系未能在当时开拓新局面的根本原因。沿此思路,这一事件进而被认为是中国朝贡体制与西方条约体系正面冲突的开始,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朝廷接待英国使团时表现出的盲目自大、故步自封是英国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基本背景。(1)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2007年版;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前述主张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说。(2)参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还有学者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角度论证清朝对外思想和礼仪规范的历史渊源与合理性。(3)王开玺:《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刘凤云:《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前述研究路径有其意义,但清中前期中欧官方往来还涉及葡萄牙、荷兰、沙俄多次向中国派遣使团,将认识清中前期中欧关系过度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并由此得出的清朝处理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方略特点,难免偏颇。已有学者注意到清朝在对待个别使团的礼仪问题上具有灵活性,但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清朝在与欧洲国家往来时的方略。(4)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冯尔康:《试析康雍乾三帝接受俄葡英三国使节国书礼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版),2018年第5期;Peter C.Perdue,“Boundaries and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Negotiations at Nerchinsk and Beijing,”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3,No.3(2010),pp.341-356.本文以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使团的来华目的、出使结果以及双方发生的礼仪问题为中心,综合考察清朝接待欧洲各国使团的方式,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对清朝的欧洲政略及当时中欧关系格局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荷兰、葡萄牙使团来华期间的礼仪争执与贸易交涉
荷兰在顺治、康熙年间多次为贸易通商之事派遣使团来华。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驻巴达维亚城总督派遣杯突高啮(Peter de Goyer)和惹诺皆色(Jacob de Keyzer)率使团(1655—1657)来华,请求中国朝廷对荷兰开放贸易。经过此次出使,荷兰获准八年一贡,且“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5)《清世祖实录》卷一○三,顺治十三年八月甲辰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4页。康熙五年(1666),彼得·范·霍尔恩(Pieter van Hoorn)又奉巴达维亚总督之命率使团(1666—1668)入华,在京之际向朝廷提出要求:荷兰人可以每年派所需的船只数量来清朝贩运货物;荷兰人可以在广东、漳州、福州、宁波和杭州贸易;荷兰人可以与任何人贸易,并且不用违背意愿被迫买卖商品;荷兰人可以购买运输丝绸、丝织品和除皇帝禁止买卖之外的其他商品,而且需要知道哪些是违禁品,以不违反皇帝的意旨;荷兰船只抵达即可贸易,准备好时即可离开;荷兰人可以购买所有的供应品和其他必需品,并带上船;荷兰人可以花钱购买一处住宅便于储放和买卖商品,并且远离火源。(6)Arnoldus Montanus,ed.,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ing Lipovi and to Konchi,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y,John Ogilby,trans.,London:Printed by Tho.Jonson,1671,pp.328-329.清廷以对荷兰已有八年一贡定例为由,拒绝了其各项请求。(7)(清)梁廷枏撰,骆驿、刘晓点校:《海国四说》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9页。康熙二十四年(1685),宾先巴芝(Vicent Paats)率使团(1685—1687)入华,提出了与彼得·范·霍尔恩类似的请求。(8)VOC 1438:691,Reports by V.Paats,24 February 1687,cited in John E.Wills,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61-162.朝廷针对荷兰使团的这些要求,要么拒绝,要么不做回复,仅允许更改八年一次的贡期为五年一次,且可取道福建:“荷兰国进贡之期,原定八年一次,今该国王感被皇仁,更请定期,应五年一次。……该国请定贡期,以船入广东路近而险,福建路远而稳。部议如所请。”(9)(清)梁廷枏撰,骆驿、刘晓点校:《海国四说》卷三,第210页。自此以后一百多年间,未再有荷兰使团进入北京。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荷兰巴达维亚总督才派遣德胜(Isaac Titsingh)率使团(1794—1795)来京庆贺乾隆八十四岁寿辰。
荷兰使团历次入华,在送往迎来、朝见、宴赉等各个环节,尽遵清朝仪制。第一个到京的荷兰使团成员尼霍夫(Johan Nieuhof)甚至嘲讽沙俄巴伊科夫使团不久前因拒绝遵守清朝礼制被驱逐:“有些人就是那么高傲,使他们为了保持那种自以为是的尊严而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使臣阁下日夜思索如何恰当地完成业已开始的谈判。”(10)[荷]约翰·尼霍夫著,庄国土译:《荷使初访中国记》,[荷]约翰·尼霍夫原著,[荷]包乐史、庄国土著:《〈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86页。此外,清朝接待荷兰使团的礼仪也并非一成不变,至少在乾隆年间德胜来华时,准许使臣在觐见皇帝时亲自将国书呈上,交与近臣,而非遵守将国书置于黄案之上的定例。德胜言:“吾双手捧匣高与额齐平,一大臣由舆前走来,将匣接去。吾人于是免冠行礼,九叩首于地。”(11)MS.Report,cited in J.J.L.Duyvendak,“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1794-1795,”T’oung-Pao,Vol.34,No.1(1938),p.56.不过,尽管荷兰使团尽量遵从清朝礼仪规制,未与清朝之间发生明显的礼仪冲突,但也没有因此获得明显的有利于贸易的殊遇。荷兰人第一次出使清朝后,得到八年一贡的许可。然而,这远不能满足荷兰的对华贸易需求。他们违背清朝的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进行非法贸易。其间,清廷因康熙二年(1663)荷兰助剿“海盗”有功,许其“二年贸易一次”,但在康熙五年范·霍尔恩出使之前,清廷又下令“荷兰国既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1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622册第932页。当范·霍尔恩提出大幅度扩大贸易规模时,朝廷即以对荷兰已有八年一贡定例为由,拒绝了其各项请求。宾先巴芝来华时,清朝并未因其遵从中国礼仪而放宽关于贸易的限制。鉴于使团外交没有带来更为有利的贸易优势,且清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陆续设关开放对外贸易,荷兰人之后未再因贸易事宜向清朝派遣使团。
葡萄牙也多次派遣使团来华。康熙年间,玛讷撒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使团(1667—1670)、本多白勒拉(Bento Pereira)使团(1678)和斐拉里(Onorato Maria Ferraris)使团(1720—1721)均为澳门贸易之事入京。(13)白勒拉和斐拉里使团均由澳门议事会直接派出,并未得到葡萄牙国王或葡印总督的授权。白勒拉在京时提出了一系列请求,包括:允许葡萄牙人出海到故土和有亲属的地方,以寻求生存之路,并且要求其船只可以自由往来,无需支付丈量费用或其他通行费;赋予澳门城在该土地上的所有特权;允许澳门居民在遇到与澳门福祉相关的重大问题时,无需经过广东当地官员便可前往京师向皇帝禀报情况;允许澳门居民自由前往广东买卖商品。(14)Jose de Jesus Maria,Asia Sinica e Japonica,Vol.2,Macau:Imprensa Nacional,1950,p.86.雍正帝年间,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Menezes)奉葡萄牙国王之命来华(1725—1728)。国书汉文译本表明,他来华是为了感谢先前康熙皇帝曾派传教士张安多(Antonio de Magalhaes)出使葡萄牙,并趋朝恭贺雍正登基。(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页。葡萄牙文的国书原文则透露出麦德乐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澳门葡萄牙商人:“盼望陛下像先帝一样能给予我国和其他国家商人优惠权利,以使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16)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7页。除此之外,鉴于雍正帝登基当年即在全国颁布了禁止信仰天主教的诏令,麦德乐来华也带有缓和朝廷禁教的意图。乾隆年间,葡萄牙国王又派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Assis Pacheco Sampaio)使团(1752—1753)来华,意在“培养同中国当朝皇帝的友谊,促进在华各传教团的保存及发展,重建吾王陛下的保教权及其他政治利益”。(17)[葡]巴哲格著,金国平译:《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1752年出使京廷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212页。
与荷兰使团不同的是,葡萄牙使臣多次挑战清朝的外交礼仪和程序。撒尔达聂来华时,广东官员按朝贡定例,令其交出国书和礼物清单以供查验,而他坚持进京面见皇帝时方可呈递。后经数月僵持,双方最终协商同意仅查验国书副本。(18)John E.Wills,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pp.106-107.此外,葡萄牙国王在国书中未向清朝皇帝称臣、称奏,与清例不符。撒尔达聂借口欧洲国王通函无称臣之例,且不知晓中华之礼,对此清廷未再追究。尽管撒尔达聂有不合清朝外交礼仪的行为,但清朝并未因此拒绝使团入京或怠慢使臣。
麦德乐也挑战了清朝既有的接待外国使臣的规则。他抗议广东官员在往来文书中称其为贡使,表示“绝不以贡使身份进入中华帝国,因为他无纳贡义务。他代表伟大的葡萄牙国王来恭贺皇帝登基”。(19)[葡]麦德乐著,金国平译:《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遣中华及鞑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简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02页。广东地方官没在该问题上与麦德乐僵持不休,而是颁布告示澄清麦德乐并非进贡使者:
香山县捕厅吴为传谕事。照得极西大人麦来澳进京恭贺圣主。今访得无知民庶讹传进贡,但西洋国无进贡之例。现奉各宪接请进京。合行传谕。为此,示谕澳属居民等人知悉,凡有讹传极西大人麦系进京进贡贡官者,许地保人等扭禀赴本厅,以凭解赴本府重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一出示议事亭、军营前、市街。雍正四年九月某日。案。(20)Biblioteca Publica de Evora,“Chapa Sinica”,cod.Cx.Vi/2-6,No.11,fl.454,转引自[葡]麦德乐著,金国平译:《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遣中华及鞑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简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03页。
此外,他抵京后拒绝学习觐见礼仪,并要求“像莫斯科的大使那样直接把信交到皇帝手中”。(21)《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法]杜赫德编,朱静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三,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 页。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麦德乐进表庆贺,“仪与康熙五十九年同”。由此可知,清朝最终妥协,允许麦德乐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来华的斐拉里一样“膝行至宝座旁恭进,圣祖仁皇帝受表,转受接表大臣”。(2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礼部·朝贡·朝仪》,《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3页。麦德乐第二次觐见皇帝时,亲自献上葡萄牙国王的礼物,由官员接过,当面呈给皇帝,这也与礼部负责转呈礼物的定例不同。他还拒绝了贡使才会受赐的三百两白银。(23)《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法]杜赫德编,朱静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三,第238 页。麦德乐此行被认为是:“他战胜了一切困难,甚至那些认为无法解决的困难,保持了他的君主及整个欧洲的威望。此行之前,在京廷看来,所有来华的使臣无一不为贡臣。”(24)[葡]麦德乐著,金国平译:《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遣中华及鞑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简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10页。
之后的巴哲格绕开由广东地方官员查验国书之类的程序,径直与京城的耶稣会士联络,而乾隆皇帝得知后,直接派钦天监监副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神父和内务府官员前往广东迎接使臣。此外,在巴哲格的坚持下,广东地方官发告示声明:葡萄牙国王不向中国纳贡,凡对葡使以贡使相称者,将受到严惩。(25)[葡]巴哲格著,金国平译:《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1752年出使京廷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14页。入京之后,他与麦德乐一样,跪奉国书,由皇帝亲手接过:
是日,来使公服候于后左门,恭候皇上升乾清宫宝座。臣部堂官一名员,带领在京居住西洋人一名,令来使恭捧表文,引至乾清宫西阶上,入西边隔扇,由宝座西边台阶上,至宝座旁跪,恭献表文。皇上接,授侍立大臣,侍立大臣跪领,恭捧侍立。仍引来使团由西边台阶降,出西边隔扇,至丹陛上,在西边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由西边隔扇引入,赐坐于右翼大臣之末,赐茶,叩头,吃茶。皇上慰问时,令来使跪听,毕,臣部堂官引出至乾清门外,谢恩。(26)《礼部奏折(移会抄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9页。
巴哲格在第二次觐见皇帝时亲自呈上礼物,而且还声称:“我是第一个获得将进呈的礼物清单不写上‘进贡(贡物)’,而标上‘礼单’(敬送礼品的清单)的人。”(27)[葡]巴哲格著,金国平译:《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1752年出使京廷记》,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36页。
由上可知,葡萄牙使团在使臣身份的认定,国书的查验和呈递,以及方物的进呈等方面多次挑战了清朝既定的外交仪制。萨尔达聂坚持广东地方官仅可查验国书副本而非原件;麦德乐要求广东官府公开表明他并非贡使,坚持亲自向皇帝呈递国书,拒受礼部通常赏赐给贡使的三百两白银;巴哲格声明自己不是贡使,将礼物清单标记为“礼单”而非“进贡”。这些都为清朝所接受。此外,从斐拉里使团开始,清朝也将使臣到礼部呈送国书和礼物的旧制更改为使臣觐见皇帝时亲呈。然而,葡使来华或为澳门问题,或为天主教之事,他们因没有机会或无意陈请,有时也因清朝拒绝,很少实现来华诉求,仅白勒拉的部分请求在次年得到回应,即开放粤澳陆上贸易:“续因西洋国进贡正使本多白勒拉,见岙彝禁海困苦,赴部呈控。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内,准兵部咨为备述岙门界外孤洲等事,议复刑部郎中洪尼喀等,到岙踏勘,准在旱路界口贸易。奉旨依议,旱路准其贸易,其水路贸易,俟灭海贼之日,着该督抚题请。钦此。遵行。”(28)(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二《请除市舶岙门旱路税银疏》,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二、俄国使团来华与中俄交涉
17世纪中叶,俄国先后派遣巴伊科夫使团(1654—1658)和佩尔菲利耶夫使团(1658—1662)来华探查情况,并有意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在开展使团外交的同时,俄国多次侵扰清朝东北边疆,并于康熙六年(1667)年策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叛离清朝。为此,清朝迫切希望与俄方交涉边界和逃人问题,而俄方也继续派使团来华。康熙九年(1670),米洛瓦诺夫使团(1668—1672)来京,提出在华自由通商,清朝皇帝向沙皇称臣纳贡等要求。(29)[俄]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35页。康熙十四年(1675),斯帕法里使团(1675—1677)来华,提出包括允许商民自由往来、释放俄国俘虏,以及向俄国派遣使团等在内的12条要求。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就东段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为探明清朝对《尼布楚条约》和两国未定边界的态度,以及商谈兴建教堂、开展贸易及设立领事馆等问题,沙俄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派遣义杰斯使团(1692—1695)来华。此后沙俄又分别派伊兹玛伊洛夫使团(1719—1721)、萨瓦使团(1725—1728)和克罗波托夫使团(1762—1763)来华。
中俄双方围绕外交礼仪问题也发生了诸多争执。俄国第一次派遣的使臣巴伊科夫坚持亲自将国书和礼物呈递给皇帝,并拒绝习觐见礼,被朝廷遣还。佩尔菲利耶夫来华时,清朝认为俄方国书“不遵正朔”“矜夸不逊”,仅令贡物照收、礼遇使臣,但拒绝召见使臣。(30)《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五,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2页。斯帕法里使团来华时,双方礼仪冲突达到高峰。先是,斯帕法里在嫩江时与前往该地迎接使团的礼部侍郎马喇之间就会见地点和方式产生争执。继而,他不仅拒绝将国书交与马喇查验,甚至不肯出示和说明国书的内容。清朝最后在这些问题上退让,并允许使团入京。斯帕法里到京后,中俄两方就使臣如何呈递国书,觐见皇帝时是否行跪拜礼,接受皇帝赐宴时是否叩头谢恩,以及是否跪受皇帝回赐礼物等问题再度发生争执。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如下与清朝外交仪制不符的协议:使臣呈递国书和礼物时,把国书正本和译本以及礼物带到皇帝大殿,将国书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黄案上,礼物放在另外的桌案上。俄使在殿外觐见皇帝时,在比之前葡、荷使臣离皇帝更近的地方行跪拜之礼,在殿内受召见时,再行一次叩礼。皇帝赐宴时,使臣仅行一次三跪九叩之礼。皇帝回赐沙皇和使团礼物时,使臣站着接受回赐沙皇之礼,但跪着接受回赐他本人的礼物——事实上斯帕法里站着接受了全部回赐。在此次往来中,清朝在礼仪上让步甚多,且没有遣返使团,但也并非一味退让。鉴于斯帕法里对礼仪的挑战,以及沙皇没有在国书中提及根特木尔的问题,清朝拒绝回应他提交的12条要求,同时声明,如果俄国想继续派使臣和商人来华,必须接受3项要求:遣返根特木尔;来华使者必须是通情达理且遵从清朝礼仪的人;确保俄国居民居住的边界地区安宁。(31)[俄]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51页。
到义杰斯使团来华时,朝廷要求使臣按清朝既有的外交定例,向相关官员禀明沙皇国书内容,出示礼单,并将国书和礼物放置在黄案上,由索额图转呈皇帝。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再度出现争执,但俄使臣最终妥协,并按照清朝定例完成了呈递国书和礼物的仪式。不过,由于沙皇的国书里没有对清朝皇帝称奏,朝廷将对方国书和礼物退还,且规定日后俄使臣来华,须先由边界大臣查阅国书,符合体例方可放行,不合体例,则不准奏。(32)[俄]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91-93页。尽管双方有礼仪冲突,义杰斯还是完成了此次出使,并在北京买卖货物后方才返回。到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来华时,康熙帝又打破前述俄使臣须将国书置于黄案之上的规定,亲自接过国书,并对使臣说:
虽然他有一个传统惯例,从不亲自接受任何外国使者和使臣呈递的国书,但因为尊敬俄国皇帝,并把俄国皇帝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朋友和邻居,所以他现在放弃过去的惯例,亲自从使臣手中接受国书。(33)[俄]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13-114页。
而且,他也在外交礼仪上主动变通,不仅允许俄使按欧洲习惯亲吻他的手背,而且决定以敕谕使臣而非沙皇的方式书写回函,如此即避免了两国君主在称谓方面的冲突。敕谕内容如下:
敕谕俄罗斯使臣伊兹玛伊洛夫:尔国君主恭请朕安,愿益敦两国之睦谊,祝中国愈加繁荣昌盛、诸事成功等情之奏书,朕已收阅,贡物皆已收下,凡事皆已当面降旨。着尔恭记朕旨,转告尔主,事竣妥为返回。特此敕谕。(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页。
更为重要的是,俄国使团在北京三个多月期间,双方多次就贸易和商务代表等问题展开了谈判。
雍正三年(1725),萨瓦使团奉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之命来华,他呈递国书和觐见皇帝的礼仪程序,皆如伊兹玛伊洛夫之例:抵京后,向大臣递交国书副本。觐见皇帝时,先行三跪九叩之礼,走近皇帝后,重新跪下,将国书高捧过头,由皇帝亲手接过,交与近臣。俄使团在华期间,双方就边界、逃人、国书形式和互通信函等问题进行谈判,并议定由俄枢密院与清理藩院互通信函,沟通处理相关问题,以避免互通国书和使臣往来时可能出现的争执。(35)[俄]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54-156页。
可以看出,清朝面对俄国使臣的礼仪主张,有时坚持,有时让步,有时主动改变方式,体现出一定的灵活变通特点。俄国使团有在礼仪上向清朝妥协的,也有因礼仪问题遭遣还或未达到出使目的。整体来看,中俄双方寻求的协商谈判并没有因为礼仪争端而被打断或全无成果。
三、欧洲人的中国保守封闭意象与清朝的对欧使团方略
马戛尔尼结束北京之行后,英国各方评价不一,认为此次出使为一次外交失败的看法逐渐占据主流。究其失败原因,有人归咎于马戛尔尼的做法,更多的则是认为清朝官员腐败和中国朝廷的傲慢自大导致了如此结果。(36)Laurence Williams,“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Gaze:Satire,Imperialism,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1792-1904,”Lumen: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32(2013),pp.97-102.而使团成员的看法,直接推动这种言论成为主流。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指出,英国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朝廷的傲慢和狂妄自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管是梁栋材先生(37)梁栋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1736-1812)为法国在华传教士。还是那些相信只要英国使团无条件地卑躬屈膝就有可能取得更大成功的人,他们的推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与此相反,那样做很可能创造一个先例,即奴颜婢膝地遵行这个傲慢的朝廷所要求的侮辱性的礼仪,只能助长其荒谬的狂妄自大之心。(38)[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与这一声音同时甚嚣尘上的是对中国封闭、落后的负面评价。使团另一成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闭关锁国和排外的:
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和排外偏见仍然存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高度的优越感,在他们眼中,其他国家都是蛮荒之地……可清王朝固守着闭关锁国的方针,不愿同外国打交道,也不愿自己的臣民同外国人有来往。(39)[英]乔治·斯当东著,钱丽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他继而指出,这是导致中国无法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原因:“而且因为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他们无从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发明创造。”(40)[英]乔治·斯当东著,钱丽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5-376页。马戛尔尼本人也指责中国停滞落后、盲目自大:
(中国)……至少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而且,尽管在他们和使团交际期间感觉到我们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强,他们仍显得惊奇而不自愧……一个国家如不进步,必定倒退,最终沦为蛮夷和贫困。(41)[英]乔治·马戛尔尼、[英]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1页。
欧洲人的这种看法并非在18世纪末才出现,17世纪时就已经有欧洲人认为中国对外保守封闭。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说过:“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因此闭关自守,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的传教士例外。”(42)《利氏致德·法比神父书》(1608年8月23日),[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曾德昭(Alvaro Semedo)《大中国志》(TheHistoryofthatGreatandRenownedMonarchyofChina)英译本序言说道:“这个国家如此遥远,小心谨慎,避免与外来人交流,不向外人透露他们的事情。”(43)Alvaro de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London:Printed by E.Tyler for John Crook,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Sign of the Ship in S.Pauls Church-yard,1655,“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英国根据荷兰文书籍和旅行日志翻译出版的《中国图志》(AtlasChinensis)开篇提到的对中国的认识是:
中国人拒绝并憎恶与外面的通信联系,严格遵守一条古老的律令,禁止其他国家的人进入中国,除非是邻近地区的或者外国使臣携贡物而来,并把他们的皇帝当作世界之主一样示以敬意,但是许多来华使臣都是借机展开贸易。(44)Arnoldus Montanus, ed.,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ing Lipovi and to Konchi,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y,John Ogilby,trans.,p.1.
不过,17世纪来华的欧洲人虽然提及中国保守封闭,但同时他们也将诸多有关中华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社会繁荣的看法传播到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仍占据主流。此后欧洲人的中国意象逐渐改变,中国停滞落后的形象流行日广。(45)国外有关中国停滞落后认识的研究,参见Guido Abbattista,“At the Roots of the‘Great Divergence’:Europe and China in an 18th Century Debate,”in Mathias Middell ed.,Cultural Transfers,Encounters and Connections in the Global 18th Century,Leipzig:Leipziger Universitatsverlag,2014,pp.113-162.在这种情况下,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根据亲身经历发表的言论强化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贬华思想(Sinophobia)在19世纪成为主流,成为英国人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之一,甚至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学派影响下的中外学者解读清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基本预设。
然而,这种影响深远的看法只是欧洲人在与清代中国政府往来中的单方面体验。他们基于自身与中国朝廷交往的挫折,断定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想与任何外交使臣议事,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做决定”,(46)VOC 1438:684-684v,reports by V.Paats,24 February 1687;Vixseboxse,pp.78-79,cited in John E.Wills 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p.167.忽视了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如俄国,外交往来的情况,也没有看清当时中国处理欧洲使团来华事务方式背后的基本考量。
前文已经表明,葡、英、俄来华使团均在外交礼仪方面与清朝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争执,所涉礼仪问题接近,而出使结果,并非一切取决于礼仪争议的结果如何。俄国使臣巴依科夫因拒习觐见礼遭到遣还,马戛尔尼虽拒习觐见礼,但却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召见和礼遇。而且,清朝面对欧洲来华使团对既有外交礼仪的挑战,有不同程度的妥协和变通,有时面对不同国家使臣挑起的同一礼仪问题,反应也不同。例如,针对对方君主在国书中不称臣、不称奏的问题,清朝廷没有深入追究葡萄牙萨尔达聂使团呈递的国书,却退还了俄国义杰斯使团携来的国书。再者,清朝对各国使团诉求的反应也不一。整体来看,与对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诉求类似,清朝廷对葡、荷使团的请求,多是拒绝,或是没有实质性的协商谈判和回应,而在对待俄国使团时,却有不同。中俄之间虽然在国书的呈递方式、觐见皇帝的礼仪,以及国书格式等问题上争执不休,锱铢必较,甚至爆发过严重的礼仪冲突,但从长时段来看,双方不仅在礼仪问题的交涉和博弈过程中均有妥协,达成了关于如何呈递国书、回函对方等外交礼仪的共识,而且还就关系两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如逃人、商贸、边境、准噶尔等展开了协商谈判。尽管造成欧洲人出使中途被拒或未达到目的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本文对荷兰出使的分析表明,遵行清朝仪制并不一定能实现出使目的,而本文有关葡萄牙和俄国使团的研究又证明,外交礼仪冲突尽管有时会导致出使不畅、遭拒或未达到出使目的,但也不尽然。换句话说,外交礼仪问题不是决定欧洲使团未能达到出使目的并因此被认为出使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么,清朝拒绝马戛尔尼请求的根本原因何在?第一,清朝与葡、荷、英这些距离遥远的西洋国家之间无依存关系,对其出使中国兴趣不大。例如,怡亲王允祥就曾对麦德乐不远万里来华却又执意违反清朝的外交礼仪规定表示不解:
葡萄牙使臣来不来我们朝廷与我们有什么要紧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来是向皇帝致谢,并且祝贺他登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派人去迎接他?(47)《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法]杜赫德编,朱静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三,第233页。经万明考证,引文中语言为怡亲王所说,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467页。
而俄国则与这些西欧国家不同。清朝与之毗邻,双方之间牵涉逃人、划界等重大问题。对这种毗邻关系的注重以及对前述问题的关心,促使清朝与俄国积极展开包括贸易、传教在内的各种事宜的协商谈判。叶柏川也通过简单对比俄国和英国来华使团后指出,俄国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一样,同清政府之间同样发生了礼仪之争,但是,礼仪之争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地缘政治因素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而在当时中英关系缺乏这种推动因素。(48)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7页。
第二,马戛尔尼使团的诉求在根本层面挑战了清朝的立国原则,使朝廷感受到威胁。马戛尔尼呈交给乾隆皇帝的书面请求包括:准许英吉利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贸易;准许他们与以前俄罗斯人一样,在北京设立堆栈用于出售货物;允许他们把舟山附近某个与陆地分离的、未设防的小岛作为仓储地,堆放未出售的货物,以及作为英国人管理货物的居留地;准许他们在广东附近享有类似特权和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自由;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至少减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标准;禁止向英吉利商人榨取皇帝公文规定以外的税款,要求给英吉利商人一份公文抄本,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该文的明确要求。(49)Heelen H.Robbins,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Earl of Macartney,and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1737-1806,Boston: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4,p.333.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要求意味着改变清朝的法度。他回复表示:“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50)《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5页。乾隆帝在逐条拒绝英使所请时,多次提到定制不可更改。他指出,西洋各国来华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51)《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188页。
其实,清朝从英使的诉求中感受到了威胁。乾隆帝对臣下指出,“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其要求留人在京照料沿海贸易,可能“心怀窥测”。(52)《谕军机大臣著长麟速赴粤办理预防英人滋事并将办理情况回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60页。他在下达沿海各督抚的谕旨中,反复提到英国虽然“僻处海外,过都历国,断不敢妄生衅隙远越重洋”,“但观该国如此非分干求,究恐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53)《谕军机大臣著沿海各省督抚严查海疆防范夷船擅行贸易及汉奸勾结洋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63页。“特恐该贡使因不遂所欲与西洋各处夷商勾串齐行,小有煽惑,不可不预为之防”,“总当随时留心,先事防范”。(54)《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八月二十七日廷寄》,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0页。
除马戛尔尼外,清中前期欧洲各国来华使臣,包括葡萄牙使臣白勒拉、荷兰使臣范·霍尔恩、宾先巴芝都向中国朝廷提出过类似要求。尤其是,荷兰使臣提出的开放港口贸易,划地用作仓储之类的要求与马戛尔尼十分相近。清朝廷除了在白勒拉出使后的第二年下令开放粤澳陆上贸易之外,对欧洲各国使臣提出的类似要求均加驳回,原因当与拒绝马戛尔尼的请求一样。这种处置与历史经验相关。清朝因荷兰人曾协助清朝打击郑氏势力,赐其“二年一贸易”的特权。但是,荷兰人于康熙四年(1665)劫掠普陀山,使朝廷上下产生防范之心。福建总督李率泰在临终前也上书提醒朝廷,要对荷兰人加以警惕:“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而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端。”(55)张本政:《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因而,表面看清朝拒绝马戛尔尼等西欧各国使臣要求,却愿意与俄国使臣展开各项谈判,二者差异巨大,但其背后的考量却是一致的。
综上,各种对马戛尔尼使华遭遇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都夸大了中国的保守封闭性。虽然清朝当时并非没有保守性,但这种夸张的中国保守封闭性解读毕竟是一种片面的历史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没有关照到清中前期中国处理与各国往来关系时的差异性,也忽视了中国当时不仅处于全球贸易发展的背景下,同时也处于殖民主义势力逐渐聚拢于周边的国际环境中。中英觐见礼之争没有导致马戛尔尼使团被拒,马戛尔尼未能实现其目标的根源主要不在礼仪冲突,而在于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以及此前其他欧洲国家提出的类似要求,使清朝感受到安全威胁。马戛尔尼即使遵行清朝礼仪要求,该次出使也大概率不能实现其最初目的。此外,清朝在礼仪争执中并非一味固执自我,也具有一定的灵活变通性。外交礼仪之争既然没有决定中俄关系的走向,也就不是决定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走向的根本原因,更不是欧洲国家后来以武力冲击中国的正当理由。而中国并非在欧洲的冲击之下才会做出变通,更非执着于朝贡体制的幻想之中,中国与欧洲之间也不完全是传统朝贡体系和现代条约体系的冲撞。
——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