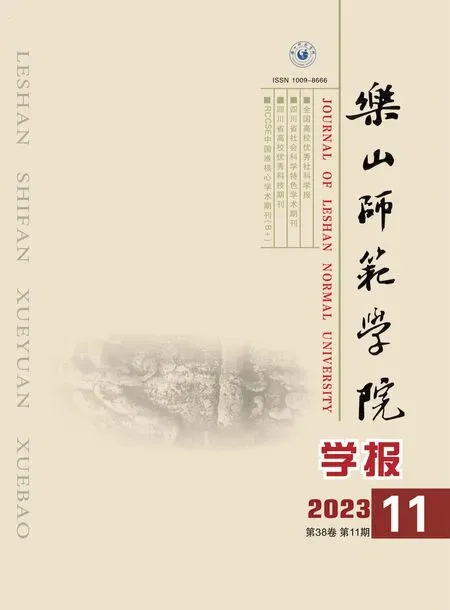宋人对远域国家“拂菻”的想象与认知
王熙雨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宋代,外部大环境多变,北方、西北、西南疆域较唐代缩减许多,难与先前一样通达四方。在这个时期,宋与周边王朝如北方辽、金,西北的西夏,南方区域性政权大理、交趾、占城等都直接接壤或距离较近,与这些国家通过民间交流、朝贡、贸易、战争等方式建立了直接且真实的交往。而在超远距离的域外,宋人由于当时交通的落后与他国之阻碍,难以取得实际意义上的联系。
今人根据宋人留下的绘画与文献才得以了解当时人们的想法。在绘画方面,有关职贡图的讨论是宋人对拂菻看法的热点之一。但以宋代李公麟的《万方职贡图》为代表的描绘朝贡盛况的作品,在地理上并没有描绘真实的拂菻地理风貌与人文习俗,是朝贡体系下对自身的一种“帝国”的想象。在对于拂菻的文献中,其位置考辨则为另一个热点。对于拂菻的著述,今人多站在当下的视角,在语源、宗教文化上对其具体位置进行考证,且至今也无具体之定论。但鲜有人从宋人视角入手,在其文献中寻找当时宋人眼中的拂菻位置的变迁,也少有人从宋人的视角看文献中记载的其他拂菻器物、建筑、文化生活之变迁和异于前代之处。虽然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文献中这种“详实”的描述很难反应当时真实的远域国家,文献中时人的想象与认知也杂糅于文献之中,无法准确区分①。但从这其中,宋人依然提供了时人看待西域、看待世界,甚至是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
一、宋人文献记载中的拂菻地理空间
(一)文献记载中的拂菻方位及其与“大秦”的关系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古人便开始了解西方世界。东汉和帝时期,甘英便被赋予了出使大秦的使命,虽然并未成功,但一个强大而富饶的远方强国的形象却深入人心。随着时间的变迁,对“大秦”这一称谓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黎靬、犁鞬、拂懔、拂菻等。我国史书最早记载“拂菻”②这一名词始见于《前凉录》[1],而后在《隋书》《旧唐书》中,均有与古称“大秦”混用的拂菻国的描述。
以时间顺序从宋人文献中记载拂菻的成书年代来看,较早的为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其载:“大秦国一名犁鞬又名拂菻国,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2]3515。仁宗时代成书的《新唐书》中所载:“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3]6260可见在北宋前中期,宋人对于拂菻位置的描述是比较统一的,认为拂菻就是先代所言的“大秦国”,其位置就在京师四万里外的西海边。但紧接着之后,宋人文献之中对于拂菻的位置描写便出现了分歧,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元丰年间的拂菻国进贡或者其他海外的消息流传入宋。《宋会要辑稿》中提及“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国贡方物,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4]9777,神宗时代庞元英《文昌杂录》之中则载“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5]。可见,神宗之后,拂菻国的位置出现了不同于前代“西海国”的记述。
在此之后的南宋以至于元初,对于拂菻国的记载则更加混乱。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无“拂菻”而只有“大秦”,在其记述中“(交趾西北的细兰海)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古临国,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6]75周去非认为的大秦国位置同北宋初年的一致,也位于西边大海的周边。赵适汝的《诸蕃志》中,其目录中也不存“拂菻国”,但在大秦国的条目中,却引用唐代杜环的描述:“拂菻国在苫国西,亦名大秦。”[7]12元初的《文献通考》之中,拂菻与大秦的条目则同时出现,其所载吸收了《宋会要辑稿》之中的“拂菻国南东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达靼青唐,乃抵中国”[8]9397,又有前人描述“大秦一名犁靬,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从条支西度海曲万里,去长安盖四万里”[8]9377。对于拂菻与大秦同时出现并且地理记载不同的情况,马端临认为:“唐传言其国西濒大海,宋传则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馀界亦龃龉不合。土产风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为一国云。”[8]9397可见由唐到宋,所记载的拂菻国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从围绕着“西海”这一地理坐标向更远的地方扩散。导致作者不敢将其归为一国,但又因为宋之前史籍中确实又指出了拂菻与大秦为同一国家,所以马端临也只得把两种记录都采纳于《文献通考》之中。故由上述材料可知,实际上在宋人眼中,西方强国拂菻的位置是相对模糊的,“拂菻”与“大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认识在宋人之中也不绝对。在这里,西海这一地理意向起到了锚定的作用,所有关于拂菻国的地理描述基本都围绕着西海周围,且拂菻距离宋有四万里左右。
(二)宋人想象中的拂菻位置与周边环境
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具体的位置描写,较抽象的拂菻国位置叙述则是在景教僧人所作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中所示:“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9]186其说法模糊且浪漫,出现了“珊瑚海”“众宝山”“仙境花林”与“长风弱水”等明显不是具体地名的意向,这与此碑作者景教和唐僧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德认为,这些拂菻僧人为更好的传教而重新提及大秦国名[10],这暗合了中国古早史书之中的记述,方便其行动也增加了神秘感与知名度,同时还浪漫化了他们的所出生的土地。再加上从汉代以来对于大秦国多珍宝的描述,混同于一,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宋人赵适汝的地理著作《诸蕃志》中就体现了对拂菻位置的浪漫描述:“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11]13宋人眼中的拂菻国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虽然说法众多,但由此可知的是,拂菻国确实是一个对于当时的宋人来说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在极西且接近大海的日落之地。
在宋人的认知与想象中,拂菻确实为一个西方大国。时人给予其“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11]13的极高评价,并且其“小国役属者数十”[8]9397,可见拂菻对周边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其周边的何国之中,“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画拂菻诸国,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8]9350。也有当时宋人认为其是大国天竺国的宗主,“天竺国其(大秦)属也”[6]95、“天竺国隶大秦国,所立国主,悉由大秦选择”[11]13,虽今日也无见拂菻其控制佛教国家的其他说法,但可见其在宋人眼中的强大。史料也载“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8]9398这种见到来使便给予优待的政策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也有些许神似,展现了其大国风范。更加具有想象力的则是拂菻周边“存在”的附庸西女国,“西女国,在葱岭之西。其俗与东女略同,种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子不举。”[8]9391以今人之眼光来看,女儿国只是存于文学等奇幻故事之中,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周边关系、交通条件、知识水平,宋人无法对各种传说与记载作出有效的判断。在赵适汝的记述中,称西女国传说的由来是“有一智者,夜盗船亡命得去,遂传其事”[11]21。可是实际上有关拂菻派遣男丁去女儿国的记载在梁代《供职图》中便存在,具体描述为“去波斯北一万里西南海岛有西女国,非印度摄,拂懔年别送男夫配焉”[12]。通过这些拂菻国附属的西女国史料不难发现,对于这些超远距离的域外国家,宋人对他们的认知是真实与想象杂糅在一起无法区分的。他们虽然可以认识到,那个从汉代发现的西方大国一直存在,而且影响着其周边的很多国家。但是对其具体位置、其周边国家的实际情况却只有非常模糊的理解,其中还不乏很多当时人们的杜撰想象。可正是这些地理上的正史与故事、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才令我们得以窥见宋人对当时遥远国度的看法。
二、宋人文献中的拂菻国生活及物产
(一)城市居住环境
宋人对于拂菻这个国家的想象不仅体现在宏观上强大的西域影响力,也体现在微观上的精美高超的建筑器物,这些器物经过了多次的朝贡方物、使节叙述,再加上宋代拂菻国与宋并未形成连续的交往,其记载的“物”的意象很多与唐代相似,但充满了西域国家的奇幻风情。首先是城市建筑,宋人有关其城市占地面积的记载见于《经行记》中“王城方八十里”[7]12,其城市不可谓不宽广豪华,北宋都城汴京也只有“方圆四十馀里”,而旧京城更只有“方圆约二十里许”[13]19对于拂菻王宫“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3]6260,“王所居舍,以水精为柱、以石灰代瓦,多设帏帘,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11]13其中较引人注意的是“水精柱”与“石灰为瓦”这两个意象,《太平御览》载“水精谓之石英”,同时指出其原产地,“水精出大秦、黄支国”[2]3593。水精也是珍贵的朝贡物品,如西域诸国向中原朝贡之时便进贡此物,“开元初献锁子甲、水精珠”[14]2815,“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玻璃状若酸枣”[14]2844。对于石灰,在宋人眼中,其是做瓦的材料,即“瓦作用纯石灰[15]”。而这种无瓦却直接用石灰为顶的建筑,在宋人的记述看来,也其并非简陋,而是拂菻国民俗与建筑独特的建造方式,这与《旧唐书》中对于拂菻国建筑的记载较为相似,且为一种较有技术含量的装饰。不仅是王室,民间也亦是如此,“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16]同样的《太平寰宇记》也载其民“無瓦,以白石塗屋上如白玉焉”[2]3515。像白玉的评价体现了宋人对其建筑技巧的称赞,在记载周边国家时,天竺国也受拂菻影响“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11]13。不同与其他国家的贫苦“官民悉编竹覆茅为屋,惟国王镌石为室”[11]4,或“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铺板覆茅”[11]5。也不同与强国大食王之奢华,且王与民贫富差距极大③。拂菻王宫除了水精柱外也与民居无大差别,拂菻王的建筑在精巧的同时十分可能也体现了其王室低调简谱的特点,可能与宋人认知中的其佛教信仰相关。
除了以灰代瓦外,在拂菻人的屋顶之上还有两种奇物。第一种为利用某种机械装置汲水上房的机械装置,可使水流沿房而下如瀑布。此记载可能最早出现于《旧唐书》,拂菻国人“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17]。而宋人也载拂菻人“至于盛暑,人歊烦,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18]。可见这种装置是安装于屋顶之上的一种引水避暑装置,其能让水沿墙而上,并从房顶淋下降低房间温度。这种装置在唐宋皆出现过,名为自雨亭“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鉷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19]。说明在唐代,自雨亭属于上层人士才能享受的奢华装置。从宋代著名词人秦观《再赋流觞亭》中的诗句“仙山游观甲寰瀛,不比人间自雨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拂菻国这一机械装置颇为赞赏,认为其能制造人间之仙境。而对于自雨亭这种中原存在但数量稀少的奇物,据宋人记载其遍布拂菻,可见在其国人能工巧匠众多。第二种奇物为其城楼之上的黄金大钟,此物也在宋人的著作中也被提及。“第二门之楼悬一大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有声,金人即应声引唱以记日,时毫厘无失。”[2]3516金人不知用何种矿石所制,但“其大如人”同时又可以“应声引唱以记日时”,可见在宋人认知与想象之中,拂菻人建筑上有着独特的风俗,且机巧玄妙众多。
(二)丰富而独特的物产
关于拂菻宝物众多的描述史籍中屡见不鲜,早在三国时期便有记载④,宋时也载其有“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缦布、红马脑、真珠”[6]95,“土多金银,其宝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龟、白马、朱鬛、瑇瑁、元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2]3515,是名副其实的“重宝之乡”。
而在其中,珊瑚便引起了宋人的特别关注,在宋代珊瑚的使用被看做是一件非常奢侈之事,英宗时期知太常礼院李育便奏言痛斥当时的奢靡之风,其中言道:“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馀,岂足为圣朝道哉!”[8]3464而正是这种中原王朝很少获得的宝物,在拂菻国则可乘船用大铁网直接从河中捞出,唐时的景教僧人就称其国“南统珊瑚之海”[9]186,《新唐书》中便详细地记述了拂菻人“种植”与采集珊瑚的过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敢即腐。”[3]6261而在《文献通考》中,对种采珊瑚也有相近描述,而在种之前,还特别提到需要有人先潜入水下观察有无珊瑚苗这一情况,“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在养殖阶段则记录了珊瑚头年到第三年的变化,“初生白,而渐渐似苗坼甲,历一岁许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极三四尺,大者围尺馀,三年色乃赤好。”[8]9398成语“铁网珊瑚”便是出自拂菻人捕捞珊瑚的这一采集行为,比喻搜罗珍奇。
可见在宋代,人们对于拂菻宝物众多的想象是持肯定态度的,而这种想象往往源于唐代的史籍记述,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在《宋会要辑稿》当中,拂菻的物产则只有“产金、银、珠、胡锦、牛、羊、马、独峰、杏、梨”这几样,而在其贡献的方物之中,则只有“贡鞍马、刀、剑、珠”[4]9777。考虑到宋代特别的政治形式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记载的宋代拂菻来使的真实性也难以考证⑤,这也是马端临在对“大秦”与“拂菻”两个条目之间是否真是一个国家产生的怀疑的原因之一。可以见得,这就和宋人整体对拂菻物产的认知与想象一样,充满着对当时史籍的描述信赖与对当时实际情况不符的矛盾。
三、拂菻人的生活和风俗文化
(一)拂菻人的相貌与服饰
相比于较为模糊的地理描述,宋代之前对于拂菻人的了解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出使西域后,虽然没有到达,但是带回只言片语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经历数百年之后也变得更加符合当时人的逻辑范式。其描述始见三国时期曹魏郎中鱼豢所作《魏略》⑥,《后汉书》中则提及其人相貌与其国名称由来“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21]。在《晋书》中,大秦人穿着胡服与类似华夏相貌的记载也均被继承。而在《魏书》之中则出现了“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22]的描述。可见在东汉到唐前,人们认为其国被取名“大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人长相与华夏相同且服饰礼仪可能同中国类似,并且在时人看来,战国时期的强国秦在西方,故称其为大秦。
第二阶段始于唐代,随着唐代大量佛教僧人不畏险阻前往西域求经,唐人对拂菻的认识又较之前有所变化。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描述,如“(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23]”,“男子翦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17],这些唐之后的史料认为拂菻人有着与邻国波斯人大致相同的长相,而穿衣风格也非“类同中国”。这些观点为宋人所接受,但也对其造成了困惑,在宋代对于拂菻的记述明显的分为“拂菻”与“大秦”两种。如《文献通考》中记述的大秦国,依然沿用了前唐的大秦人长的类似汉人的看法⑦,而在其后的拂菻国则记述为“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贵人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紫褐,并缠头跨马”[8]9398,《宋会要辑稿》之中也有拂菻王“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首领皆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亦各缠头”[4]9777的记载。同时也都并没有对于拂菻人相貌身材的描写,但从缠头这一行为来看其应该是异于中原而更加倾向西域的文化。而在《诸蕃志》中的“大秦国”依然记载“其人长大美晰,颇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髦头而衣文绣”[11]14。同样以“大秦国”为条目的《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十里一亭,三十里為一置,一如中土”[2]3515。由此可见,虽然在宋人眼中,虽然“大秦”与“拂菻”有时混用,但宋人对于“大秦”这一国家的认知更加趋向于这是一个有着汉人长相且带有某种胡风的文明,甚至其国还存在“官曹”与“簿领”这些中原官职意象,而其名为“拂菻”时,这一国人的外貌认知则更像是域外的波斯诸国。
(二)拂菻人以农业为基础的风俗文化
首先,对于宋人来说,拂菻应是一个有着农业文化的西域国家。《魏书》中便记载拂菻如中原一般“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22],《文献通考》虽无记述拂菻农业情况,但在记大食国时说“土多砂石,不堪耕种,无五榖,唯食驼、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面”[8]9393。由此可见,在宋人眼中拂菻依然是农业国家,或种稻或种麦,也许兼而有之,而其作物产量高,国家富裕,“其谷常贱,国用富饶”[8]9378。故在宋人的记述中,拂菻人也有农耕民族的习俗,“多工巧,善织络”[11]14。而织布的原料则来源于其本地奇羊“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3]6261。这说明了他们同中原一样有畜牧业,但是“地多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为所食”[11]14。这明显是继承了前代拂菻记述中多狮子的印象,为此,宋人认为其畜牧业需要筑围墙保护,“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墙护之,恐兽所食也,其脐与地连,割之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遂绝,逐水草,无群。”[8]9377所以在文献中看来,拂菻依然是一个类似中原的农业国家,可能也有“男耕女织”的样貌,有“脐与地连”的奇羊,但因为狮子猛兽多,故放牧十分凶险,需要圈养。
其次,对于拂菻国社会民俗的记述的内容较少,史料中只可窥见一二。在中原人看来,拂菻是一个娱乐活动发达的国度,拂菻舞蹈在宋人眼中评价便颇高:“裾翻庄蝶,翩翩猎蕙之风,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善睐睢盱,偃师之招周伎;轻躯动荡,蔡姬之詟齐公。则有拂菻妖姿,西河别部,自与乎金石丝竹之声,成文乎云韶咸夏之数。”[24]同时民间艺人技艺也相当高超,拂菻有能吐火的奇人是自三国时代便有的记述,《魏略》中载有“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20]860而在后世则将其取名为“幻人”,凸显其奇特,《后汉书》中则有记载域外藩国进贡幻人,“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25]。尽管自后汉书后,再无进贡幻人的文献记录,同时对幻人的记载也逐渐变少,但唐人的《隋书》中却记有“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26]。至宋代,幻人已经不再只是口中吐火,成为了“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3]6261的样子,也有“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幡眊乱出”[8]9377的记载。
从开始的“口能吐火”到宋代“能额上为炎烬,手中作江湖”,其变化可能是宋代发达的民间娱乐,即瓦肆勾栏的发展所致。宋代中原民间便有许多民间艺人可表演吐火,他们“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同时更有甚者从事危险性极高的表演,每当有社火时,民间艺人们“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13]758。高超的宋代艺人表演使得时人对于异域的民间表演想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从文献中窥探异域表演的提升也恰恰反映了中原本土的民间表演艺术之进步。以上种种零碎的文献记载拼凑了一个宋人认知与想象中经济发达、娱乐繁多的农业国拂菻的社会文化图景。
(三)拂菻人的政治与宗教信仰
对于其政治与宗教文化,古人对拂菻的认知与想象也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且以宋代为分界。宋前之人对拂菻的印象多是一个贵族共和制的国家,且一般没有讨论其宗教信仰,可能认为其为世俗国家。如早在三国时期的描述“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20],到唐代“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17]。而到了宋代,虽然在宋初依然有如唐人大秦为世俗共和国的描述⑧。但随着时间流逝,之后的宋人则认为其为是一个绝对的佛教国家。
对于“成为”了佛教国家的拂菻,拂菻王变成了一名宗教君主且再不可随意罢黜,其“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11]14,因为国王每日诵经念佛,固定的时间前往佛寺拜佛,所以“国人罕识王面”[6]95,拂菻君主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另有记载拂菻王参加其国家重要的佛教仪式“每岁遇三月入佛寺烧香,坐红床,人升之”[4]9777,这与宋之前的认识大不相同。其次,拂菻作为一个宗教国家,其货币正面均为佛教意象,“以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名,背凿国王名,禁私造”[4]9778,也有说法为“面凿弥勒佛,皆为王名”[8]9398,这种说法更加的体现了宋人想象的其君主专制的特点。
另外,多部地理著作记载了拂菻为佛教大国天竺国的宗主,如“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6]74、“天竺国,隶大秦国,所立国主,悉由大秦选择”[11]14。由此可见,在宋人的想象之中,拂菻彻底的变成了一个佛教国家,这种变化可能源于唐代对于西域的发现与了解。因为之前古人便认为拂菻可能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强大中心,而佛教又是从西域传入的,天竺是西边的一个佛教大国,掌控它的国家自然而然也会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宋代因为地理环境阻隔与南北对立的环境也使其注意力多放于北方,即“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27]。故对于西方的世界,其继承并改造了唐人对于拂菻国的想象,使其成为了一个充满佛教文化色彩的君主专制国家。
四、结语
葛兆光先生曾指出,虽然对于远域国家的认识随着古代王朝的对外交往变得越来越丰富,可这对于古代的文人、史官来说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古典的历史文献依然是他们知识的重要来源,他们依然会选择百年前,甚至更古早的记述原封不动的继承。“提供异域知识的所谓‘古典’主要是古代的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对于异域的记载,常常是后来想象的基础,而且这种记载以‘历史’的名义享有‘真实’,以至于后人常常把这些本来记载于文史不分时代的文字,统统当做严谨的历史事实。”[28]但通过宋人对远域国家拂菻的描述,却可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在地理与周边环境的记载中,宋人因为对西域的掌控较前代大幅减弱。一方面,拂菻的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宋人文献中变的模糊不清。他们也并没有完全以史料为准,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对“拂菻”是否就是“大秦”产生了疑问。但另一方面,因为交通阻断,许多前代的瑰丽想象,如西女国等,则被宋人文献继承了下来。
而在拂菻的工巧与物产中,唐代出现的,而非更古老的描写则被宋人文献广泛记载。这可能与宋人较为相信四通八达时的唐人叙述,如自雨亭、“石灰代瓦”、“铁网珊瑚”等。另外较前代不同是,其也出现了“拂菻”与“大秦”两国物产不同之记载,其都为宋人呈现了一幅独特的远域国家景观。
在对其国人的记载中,书有依循古人的“大秦人”时,其国人样貌与制度则多有中原痕迹,这便沿袭了早于唐代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但宋人在记“拂菻人”时,其相貌则更加偏向当时的西域人。另外,在“幻人”的表演技能与拂菻国家的政治制度上,在进入宋代之后其文献内容发生了许多变化,可见宋人对文献的认知与想象是根据前代的文献或实践与本国认知的变化相叠加而成的。
总的来说,文献之中的远域国家的记载与同时期的绘画有较大区别,是保有理性、不少赞美且尽量中正平和的论述。虽然文献的记载有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之弊端,但宋人文献中对超远域外国家的想象有异于同时代的绘画作品,图画多以朝贡图的形式对域外国家之人进行描写,其本质是通过域外遣使来贡凸显中国之强大,是宋人“天下观”的某种体现。而对于远域国家的文献中情形则不太相同。对于域外国家的富饶、器物之精致都有详细的描写,对不同国家的珍宝、工巧也有详尽描述,这些域外大国是强大且自信的。另外,关于域外国家的文化描写则颇具矛盾与趣味,同时加上来使夸张的叙述和坊间传闻,对于宋人来说,拼凑出了一个既有继承前代,又有本朝特色的超远距离域外国家的想象与认识。
注释:
①关于对宋代有关拂菻的绘画的讨论,林英的《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 年)第四章通过比较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拂菻图指出,由于五代以后东西文化交流的衰退,中国画史中的拂菻形象也完成了由实向虚的擅变,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三期)对宋代人矛盾的天下观与不同于欧美近代的民族主义雏形作了探讨;林英(《唐代拂菻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85 页。)对职贡图的真实性作评价时说“笔下的拂菻没有承载真实的地理知识,其成为遥远而又神奇的西方世界的代名词,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度。”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三期)他认为李氏画作象征着“中国在收缩的时代,却想象自己在膨胀”,且“在有限制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的‘帝国’想象。”对于拂菻位置的具体著述之猜想与考辨,今人著作有夏德《大秦国全录》(大象出版社,2009 年)、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 年)、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 年),期刊论文有张绪山《“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述评》(《历史研究》2009 年第5 期)、徐家玲《拜占庭还是塞尔柱人国家?:析<宋史·拂菻国传>的一段记载》(《古代文明》2009 年第4 期)、武鹏《<宋史>中的拂菻国形象考辩》(《贵州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等,其主要内容基本为对史籍中所载拂菻相关的钱币、人名、地名、国名进行考证。故本文中所指的“想象与认知”为一个整体,其为宋人看待外部世界之方式。
②原文为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三》,“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③《诸蕃志》,卷上《大食国》,第15 页。其原文“其居以玛瑙为柱,以绿甘为壁,以水晶为瓦,以碌石为砖,以活石为灰……民居屋宇,与中国同”。
④魏晋时代所记载物产则更为丰富,见《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4 册,第861页)。其载有“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可见其珍宝丰富。
⑤详见张绪山《唐代以后所谓“拂菻”遣使中国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6 期)其认为《宋史》中“拂菻”为一个塞尔柱人国家。
⑥原文为《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4 册,第858 页。“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⑦原文见《文献通考》卷339《四裔考十六》,第14 册,第9377 页。原文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曰本中国人也。”
⑧原文为《太平寰宇记》卷184《四夷十三》,第9 册,第3515 页。原文为“贵臣十二共理国事,其王无常人,简贤者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