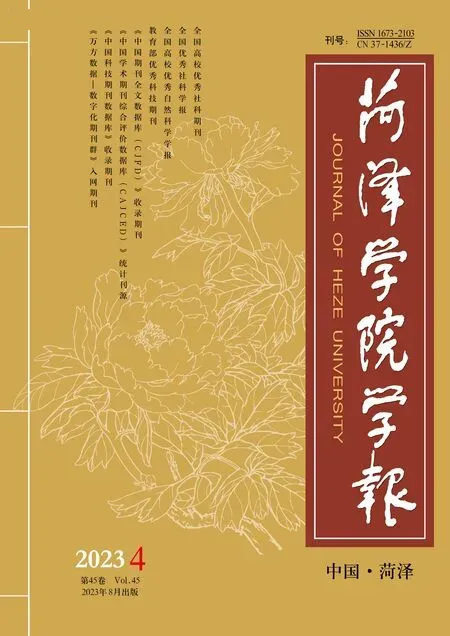英国早期女权主义的局限性之省思
——以《简·爱》为分析中心
周 琦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英语文学史上的名著之一。正如学者埃尔希·米基所形容的那样,这部小说中“第一人称女主人公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将维多利亚文学界卷入了一场风暴”[1]。《简·爱》中所体现出的追求女性独立和性别平等的诉求是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而其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人民生活方式的描写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女性视角,这部小说也因此成为英国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小说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其女权主义思想的探索,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几个彰显女性追求的主要情节,比如简·爱选择独立工作、简·爱的出走以及简·爱对于圣·约翰婚姻的抗拒等。对于文章的对话、角色的内心独白等细节,则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其实,从小说的情节、对话和角色形象中,我们可以追索隐藏在简·爱的女权主义追求背后的种种局限性:女主人公简爱对于宗教信仰的诉求、对罗切斯特的精神依赖体现了其人格独立的不彻底性;她的自卑心理和等级意识也与其对平等的追求相冲突;她潜意识里对男权的服从进一步削弱了其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已经从一个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家中天使”,一个需要依靠男人和家庭来获得生命意义的女人。因而,我们不仅应该揭示这部小说的女权主义意蕴,而且应对《简·爱》中女权主义的局限性进行省思,以升华小说的主题。
一、简·爱的精神依赖性
(一)简·爱对上帝的精神依赖
《简·爱》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贯穿于小说始终的强烈的宗教色彩。每当女主人公陷入困境,上帝的超自然的力量就开始在她的睡梦中和幻觉中闪现,给予她心灵上的抚慰和鼓励。许多被认为“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情节都是通过上帝的频频出现而推动的,正因为在进退两难时有着上帝的指引,简·爱才能通过宗教信仰的“外力”来对抗她内心中的踌躇不决和作出决定时的重重顾虑,最终走上追求独立和平等的道路。
在小说中,当简·爱被内心的焦虑和迷茫所困扰时,上帝就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出现了。当罗切斯特与简·爱的婚礼因为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的存在而取消后,罗切斯特恳求简·爱留下来陪伴他,这让简·爱在精神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渴望留在爱人身边的强烈欲望和拒绝做没有名分的情妇的自尊自爱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正当她遭受着抉择不定的煎熬时,“上帝帮助我!”[2]这句话从她的嘴里脱口而出。这句求助般的呼声将她的脆弱、犹豫不决、精神的依赖性清晰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在做出离开的决定时,她依靠的并不是个人的信念,而是求助于上帝的指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她的女权意识其实并不足以说服她依靠自身的独立思考来做出“出走”的决定。
在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前的最后一晚,简·爱梦到了一个从云中而来的白色身影,那个身影向着简·爱的灵魂低语道“我的女儿,离开诱惑”,而简·爱回答道:“母亲,我会的。”[3]梦中的这位“母亲”的身份给予了简·爱出走的信心,也以“神”的身份为她的行为赋予了正当性:出走是为了离开“诱惑”,是正当之举,是不应该犹豫的。这个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的身影无疑是简·爱内心踌躇不定的反映,因此她需要梦中的“他者”来劝说自己,以神灵和长辈的名义为优柔寡断的自己作出离开的决定。
当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开始了她漫无边际和艰难困苦的游荡之时,对于上帝的信念再一次抚慰了她的心灵,给予了她生活下去的信念。因为出走而被读者看作是“追求独立平等”的简·爱,此时其实充满了对罗切斯特的牵挂,但是当她感受到了上帝的“无边无涯”“万能”和“无处不在”,她坚信“罗切斯特先生是安全的……会受到上帝的保护”[4],从而摆脱了悲哀的情绪。宗教的力量又一次在小说中显露,在简·爱为了自己的决定而痛苦时抚慰了她的情绪,帮助她彻底接受出走的决定,推动了情节的进展。
在文学史上,简·爱的出走往往被看作她女性意识觉醒的宣言。但在上述三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简·爱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并非是从个人的信念中汲取力量,而是常常求助于宗教信仰,将自己所作出的决定看作是神灵的旨意,以神灵的全知全能性为自己追求独立的行为“正名”。由此可见,简·爱的女性意识并未强大到可以主宰她个人行为的程度,她对独立和平等的追求其实是脆弱的、不坚定的、需要外力支持的。这无疑体现了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二)简·爱对男性的精神依赖
简·爱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她对于经济独立的追求,例如,她坚持家庭教师的工作,拒绝做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家庭主妇。但尽管如此,在精神层面上,简·爱依然习惯全然依赖于男性,甚至在爱情的希望渺茫、自身在爱情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依然将罗切斯特看作生活的全部追求,缺乏爱情之外的生活寄托。
在修道院中长大的简·爱,是自尊、自爱、自强,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于挑战毫不胆怯的,她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做教师的资格,并且渴望冒险,不安于生活的一隅:“我为自由而殷切祈祷……恳求变化,恳求刺激。”[5]然而在遇到罗切斯特之后,她立刻屈服于他的男性魅力之下,完全忘记了真正的世界是一个“广袤无垠,充满各种希望与忧虑、激动与兴奋的天地”[6]。相反地,罗切斯特已经成为了她的世界的全部:“我的未婚夫正在变成我的整个世界,还不仅仅是整个世界,而且几乎成为我进入天堂的希望。”[7]其实,二人之间的财富、相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已经预示了这段感情是不公平的、婚姻更是阻碍重重的,与其说简·爱的心情是甜蜜欣喜的,不如说她经历的苦痛更甚于此。当她注视着罗切斯特时,她觉得自己就如同一个绝望的快要渴死的人,为了最后的一丝快乐去心甘情愿的饮用有毒的水,这种卑微的依赖让她陷入到了无尽的自我折磨中,然而,她依然无法从这种痛苦的爱情中解脱出来:“我们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鸿沟——可是,只要我一息尚存,还能思维,那我就不能不爱他。”[8]
更重要的是,当简·爱得知了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依然存活的消息后,她对他的依赖不减反增,甚至于在罗切斯特恳求她留下作一个没有名分的地下情人时,她也无法对他生出怒火或者怨言,反而感到“我的良心和理智都背叛了我,指控我犯了反抗他的罪过”[9]。显然,罗切斯特在婚姻状况上对于简·爱的刻意隐瞒和欺骗,早已经被她无条件地原谅了。虽然她最终决定离开,但这个决定仅仅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名誉,而并非来自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从后续的情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出走后的简·爱“一刻也没有忘记”[10]罗切斯特,她对于后者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精神依赖。
最终,简·爱嫁给了因意外而变成盲人的罗切斯特,每日照顾他的起居,陪伴他的生活,就已经成为了她“最甜蜜的愿望”[11]。对于罗切斯特的精神依赖已经成为了她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仿佛那个曾经对生活充满激情、渴望拥抱广阔世界的简·爱逐渐离开了读者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陷入爱情而不能自拔、在精神上完全依赖男性的传统女性。这也体现了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二、简·爱自相矛盾的平等观
(一)简·爱的自卑情结
在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独白:“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地位平凡、长相平庸、个子矮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嘛?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也有灵魂以及一颗充实的心!……我是在用自己的灵魂与你的灵魂对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离开了人世,穿过坟墓,一同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而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12]
这段文字,因为明确提出了“平等”的概念,往往被视为简·爱的女权主义宣言。但这段愤慨的呐喊,其实不是出自她内心中“人人平等”的信念。在小说中,简·爱之所以说出这段话,是由于罗切斯特故意显露出对于贵族小姐英格拉姆的倾恋,这深深地刺痛了相貌平凡、身份低微的简·爱,也使她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种种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她对于“平等”的呼声,与其说是出于内心的自信自强,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卑情结的掩饰。
简·爱之所以产生自卑的情绪,是因为她一直用英国传统的女性观来评价自己。在19世纪的英国,美丽的外貌和纤细的身材一直都是评价女性的主要标准,而简·爱更是常常因为自己的相貌,将自己摆在卑微的地位。当她第一次听闻英格拉姆小姐的美貌时,她的反应是克制自己对于罗切斯特的爱,因为简·爱认为相貌的差距已经决定了她在爱情中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在她的独白中,我们更可以清晰的看出她深深的自卑和消极的自我否定情绪:
“那么,简·爱,听着对你的判决:明天,把镜子放在你面前,用粉笔如实地绘出你自己的画像,不要淡化任何一个缺陷……并在画像下面写上‘贫穷孤苦、相貌平庸的家庭女教师肖像’。”[13]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她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这其中也有顾虑相貌差距的因素:“而我呐,长得那么平庸……我们绝对不般配。”[14]显然,她将相貌当作评判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于因为相貌平凡而主动否定了自己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可能,这种观念无疑仍是一种传统女性观。
简·爱自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贫穷和低下的平民身份。在小说中,当罗切斯特给她购买衣物和珠宝时,她并没有感到惊喜和幸福,反而产生了“恼恨和堕落感”[15];罗切斯特的微笑,在她看来也变成了“对一个他刚刚赐予金银珠宝的奴隶微笑一样”[16]。尽管此时罗切斯特已经向她求婚,她却依然觉得自己的贫穷和低微是低人一等的。如果简·爱真的对自己充满自信、认为自己与罗切斯特是平等的,又如何会因为几样礼物,就如此敏感不安呢?正是因为她强烈的自卑心理,将自己的人格摆在了卑微的地位,所以她在收到未婚夫的礼物后,才会产生这种“被施舍”的愤怒和羞恼,才会以强烈的躁动来展现被自卑情结深深压抑的自尊。
所以,简·爱追求“男女平等”背后的动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女性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我否定的自卑情绪。正如她对罗切斯特的质疑中所说,“跟一个配不上你的人结了婚……我才不相信你会真正爱她”[17],她其实是自信不足的。一方面,简·爱有自己的主见,热爱知识,勤奋工作,不贪图荣华富贵,是一个优秀的女性。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简·爱将相貌、财富和身份作为评价女性的主要标准,这就使她完全忽略了自己人格上的诸多优点,反而否定自身,认为自己配不上罗切斯特。正是因为简·爱认为自己和罗切斯特在现实条件中不是平等的,所以她才要坚持“灵魂上的平等”,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来填补二人的差距。因此,她强烈呼吁的“灵魂上的平等”,是爱情中弱势方的自我保护以及对于自卑情结的遮掩。这也体现了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二)简·爱的等级意识
一方面我们肯定,简·爱以倡导“灵魂的平等”而成为维多利亚小说中独树一帜的主角,但同时也需要指出,简·爱所呼吁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指爱情中双方感情付出程度的平等。在小说中,简·爱在很多场合下,依然表现出了强烈的等级意识。
在小说中,简·爱对于平等的追求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她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平等的重要性;而面对低等阶层的社会成员,她在潜意识里依然是存在着阶级优越感,不愿意将自己看作是与对方平等的人。从她的童年开始,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她就将贫穷和堕落相联系,当她离开罗切斯特、到一所乡村学校教导乡下儿童时,她认为自己又一次堕落了:“我感到有失身份……我怀疑我跨出的这一步不是使我在社会生活的等级上提高,而是降低了。我在我的周围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有无知、贫穷、粗俗,我隐隐有点沮丧。”[18]在面对和自己幼年时十分相似的下层的儿童时,她没有感到同情,而是感到“有失身份”,虽然她认为经过几个月的教学后,她对这些儿童的“讨厌也就会被渐渐满意而取代”[19],但这种内心的挣扎证明了她有轻视穷困人民的嫌疑。在经历过桑菲尔德庄园得体的生活和与贵族们的接触后,简·爱在潜意识里已经将自己看作了一个“上层人”,也忘记了在面对贵族成员罗切斯特时所喊出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的话语。从简·爱的所思所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平等”虽然是她心中所坚持的普遍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等级观念在她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从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称呼中,我们也或可看出她有等级观念的一面。在桑菲尔德庄园时,她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受聘于罗切斯特,所以称呼罗切斯特为“主人”,这在二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罗切斯特成为了她的未婚夫后,她依然时不时地自然地称呼他为“主人”。例如,在小说的第37章中,“主人”的称呼就出现了五次。当她第一眼看到罗切斯特时,她认出了他:“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主人”[20],而在之后的交谈中,她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语:“我亲爱的主人,我是简·爱”;“我亲爱的主人,只要我还活着,绝不会留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本能地更加紧紧依偎着我那失明而深爱着的主人”;“……我的主人继续说”[21]。此时,作为未婚妻的简·爱对于她和罗切斯特的等级、地位差距依然有着潜意识中的认同,也因此才会自然而然地使用“主人”这个有着自我贬低意味的称呼。正如学者罗伯特·B·马丁所说,尽管这部小说被誉为最早的女权主义小说,但在小说中却看不到在政治和法律等层面上对男女平等的诉求[22]。面对拥有强烈的主仆等级意识的简·爱,我们又仿佛看到了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三、简·爱对男权的潜意识服从
(一)男权的压制
在小说中,男权对于女性权利的种种压迫,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女权主义色彩。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就是传统男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严厉、专断、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在爱情中往往不能顾及女方的感受,这从他对待妻子伯莎的态度中就可以判断出来。虽然罗切斯特辩解说,伯莎和她的家人是看中了他的贵族身份,才让伯莎来讨好他,但他也确实沉迷于伯莎的美貌和魅力:“我发现了她是个美人……她恭维我,还卖弄姿色和才艺来讨好我。她圈子里的所有男人似乎都崇拜她,嫉妒我。我眼花缭乱,激动不已……我以为我爱上了她。”[23]出于被女性讨好的虚荣心,出于对伯莎美貌的恋慕,他娶了她,却在婚姻变质后将责任都推到了他人的头上:“她的亲戚们怂恿我;情敌们激怒我;她引诱我……我从来没有爱过她,敬重过她。”[24]罗切斯特显然是十分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没有爱过和敬重过伯莎,同意结婚仅仅是因为贪恋她的美貌,渴望享受迎娶美女的虚荣。但面对简·爱的质疑,他却将伯莎形容成了一个媚俗、虚荣、与自己不相配的女人,将自己的过错轻描淡写地形容成“幼稚无知,没有经验”[25],将他们婚姻的失败归咎于伯莎精神错乱的病情,企图为自己脱罪,毫无承担婚姻后果的责任感。因为娶了伯莎而后悔、自觉“有失身份”的罗切斯特,将发疯的伯莎软禁在了阴暗的阁楼里长达十年之久,剥夺了她的自由,更剥夺了她接受治疗和被人照料的权利——因为伯莎是他年轻时的污点,将她永远藏在庄园中的一隅、抹杀她的存在,才能维持他作为贵族的体面。罗切斯特通过残酷的男权压制,在物质上彻底剥夺了伯莎作为一个人的所有自由、权利和尊严,在情感上彻底否定伯莎作为一个妻子的存在价值。这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制,体现了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的权利是如何微不足道、而婚姻中女性的低位又是多么地可悲。
为了娶简·爱为妻,他欺骗了她,隐瞒了他已有伯莎这个法律上的妻子的事实,这使简·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差点成为他的情妇——因为伯莎的存在,简·爱无法获得任何法律上的名分,一旦真相暴露,她最终收获的只能是社会舆论对她不贞的指责。罗切斯特的自私和欺骗将简·爱推到了名誉扫地的边缘,正如后者所想的那样,如果她留下来继续做他的情妇,“他有一天会以此刻回忆时亵渎她们的同样心情来看待我”[26]。简·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罗切斯特的所作所为看来,他对于前任妻子确实没有肩负起任何责任,对于简·爱这个“后继者”也并非是抱有十足的诚意的,维多利亚时期两性的权力之不平等也就可见一斑了。
与罗切斯特相比,小说中的第二位男主人公——圣·约翰,虽然没有对简·爱造成任何心理上的伤害,但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依然是十分专横的。圣·约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遵循着宗教正统和社会习约的男人。他从来都没有对简·爱产生过爱情,他请求简·爱嫁给他,仅仅是因为她适合做一个牧师的妻子。在他的印象里,简·爱是一个“温顺、勤奋、无私、忠诚、坚定、勇敢”[27]的女性,是可以帮助他在印度进行传教工作的“无价之宝”[28]。为此,圣·约翰还以上帝的名义来压制简·爱的个性:“上帝和大自然要你做一个传教士的妻子……你生来就是为了操劳,而不是为了爱情。你是属于我的……为了我主的事业而奉献。”[29]他将简·爱视作男人的附庸和可以利用的工具,将自己的事业追求和生活方式强加到她的身上,认为这就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所应有的归宿。有学者认为,圣·约翰是“简·爱的身体和心灵的潜在谋杀者”[30]。如果简·爱嫁给了圣·约翰,她就要终身面对毫无爱情的婚姻和铁石心肠的丈夫,在环境陌生、条件恶劣的异国他乡生活,更要一辈子进行她毫无兴趣的传教工作,这无疑是一种另类的精神囚禁。圣·约翰的所作所为,虽然不包含任何自私和欺骗的成分,却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了男权的运作方式——将女性打入一个黑暗的精神世界,剥夺她们的追求、自由和对爱情的渴望。遭受男权压制的伯莎和简·爱,虽然生活境况不同,但却面临着共同的精神困境。
(二)简·爱的顺从
在维多利亚社会,男性的优越地位和男权的强势是被默许的社会成规之一。正如学者哈默顿所指出的那样:“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法律是十分守旧的,反应了人们对于婚姻中男性处于优越地位、而女性顺从的状况,是广泛接受且深信不疑的。”[31]遭受着法律和成规的拘束的女性,根本无权在婚姻中要求平等的对待,而简·爱在婚姻中受到男权的压迫时,因为潜意识里受到男权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也是更多地采取了顺从的姿态。
在小说中,简·爱亲自见识到了因发疯而不成人形的伯莎的悲惨生活,在恐惧之外,她却没有对伯莎产生同情;尽管罗切斯特试图隐瞒伯莎的存在,但经过他的自我辩解,简·爱接受了他的说辞,将他的婚姻惨状归咎于伯莎的精神错乱,而不是罗切斯特自身的冷漠无情。她对于伯莎悲惨现状的无动于衷,是因为在潜意识中已经默许了伯莎被囚禁、被冷落的事实,默许了罗切斯特对于伯莎的态度。罗切斯特的所作所为处处都体现着男性沙文主义的专横和冷酷,简·爱最终还是嫁给了他——这是她对男权主宰婚姻、女性无条件顺从的现实的无声的认可。
面对圣·约翰的求婚,简·爱清晰地知道这段婚姻并不包含任何爱情,而仅仅是为了维持两人在传教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而设立的一种法律枷锁。但从文中可以看出,与其说简·爱反对这项提议,倒不如说她其实是在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甚至流露出了软弱的情绪:“我感到他的影响已经深入我的骨髓——他的控制已经束缚住了我的手脚”[32]。虽然她严词拒绝了他,但当圣·约翰暂时退步并允许她再考虑结婚的提议时,简·爱又产生了一种类似愧疚和自责的情绪:“作为一个男人,他可能想要强迫我服从,但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才这么耐心地容忍我的执拗,给我那么长时间思考和忏悔。”[33]简·爱将自己拒绝求婚的行为理解成了一种需要“忏悔”的罪过,而提出无理请求的圣·约翰反倒成为了宽宏大量的一方。这足以说明,在简·爱的潜意识中,男性依然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他们的要求是不容拒绝、必须顺从的。也正因如此,圣·约翰的些微妥协,在简·爱看来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高尚和宽容了。而当圣·约翰收起他冰冷的态度、露出温柔的一面时,简·爱的顺从就更加明显了:“我能抵御圣约翰的怒火,但在他的温情下,我像芦苇一样柔顺。”[34]显然,简·爱拒绝这段婚姻的决心,其实是不坚定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简·爱虽然在行为上总是试图逃脱男权的掌控,但她对于伯莎境况的默许、对于拒绝圣·约翰求婚时的愧疚和踌躇,都体现出她在潜意识中依然将女性的权利置于男权之下。正如陈姝波所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简·爱已经不再那么反抗和叛逆,也不再是那个“为了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而义无反顾的人”[35]。每一次与男权的碰撞,都使得顺从的心理更加深入她的骨髓,使她逐渐失去摆脱男性、追求独立的决心和勇气,这也体现了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四、传统婚姻观和传统女性价值的回归
(一)传统婚姻观的回归
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如愿以偿地嫁给了罗切斯特。在女权主义的视角中,这是简·爱通过追求独立平等的抗争而取得的回报,是女性勇于追求跨阶级的爱情而取得的胜利,更是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象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他们结婚前,他们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简·爱获得了来自亲戚的一笔遗产;罗切斯特遭遇了一场大火,失去了妻子和家产,自身也失明且残疾了。如果没有这些出人意料的“意外”,当贫穷的简·爱回到桑菲尔德时,面对的依然是那个英俊富贵的已婚贵族,两人之间的种种差距又一次展现在读者面前时,恐怕小说结局就只能是简·爱的第二次“出走”了。
作者关于遗产和大火的巧妙设计,填补了简·爱和罗切斯特在物质条件上的种种差距,这才是两人得以顺利成婚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上,简·爱是幸运的,突如其来的财富使她得以真正地独立起来,这就为她自由追求爱情而提供了前提;而罗切斯特却在一夜间失去了宅邸,搬到了贫苦的农庄,成为了一个落魄的无产贵族。在社会地位上,简·爱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女性,脱离了为生计而奔波的劳动者身份;罗切斯特不但失去了财产,其疯狂的妻子纵火伤人的丑闻,对他的名誉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其贵族身份已经名不副实。在相貌上,简·爱虽然长相平庸,却拥有健康人的身体;罗切斯特却失明断肢,彻底地成为了残疾人,连普通人也不如了。两人之间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相貌的差距,在此消彼长之下,已经基本持平;在此前提下,两人的婚姻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又一次占了上风。
对于传统婚姻观的认可,在简·爱对待罗切斯特境遇的态度中也可以体现出来。虽然罗切斯特变成了一个残疾且落魄的男子,简·爱在他面前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我兴致勃勃……和他在一起,毫无恼人的拘束,不需要压抑高兴和快活,因为我知道我合他的意。”[36]曾经自卑敏感的简·爱,为何不再像以前一样,因为爱情而患得患失、疑虑重重,反而变得如此自信呢?显然,因为两人在物质条件上的种种差距已经消失殆尽,简·爱才能把自己摆到与对方平等的地位,更是因为两人终于“般配”而感到如释重负。由此可见,这场看似美满的“跨阶级”的爱情只是一场空中楼阁,在背后运作的,依然是两人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相貌上的暗中博弈。传统的门当户对的阶级观,在简·爱心中依然拥有重要的地位。
简·爱对于传统的反叛,实际上掺杂了一种“对于特定社会传统的坚定遵守”[37]。当我们在探讨小说中女主人公勇于追求平等爱情的女权主义意蕴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简·爱的成功实际上更多的依靠的是戏剧性的“意外”而非是自身的努力。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和罗切斯特终于在物质条件上达到了平等,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婚姻观的妥协。
(二)传统女性价值的回归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古芭和吉尔伯特提出了出名的“天使与魔鬼”的女性形象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遵从男性的需求则为“天使”,反之则为“魔鬼”。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小说末尾就变成了一个为了罗切斯特而存在的“家中天使”。对于罗切斯特的失明、残疾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事实,她甘之如饴:“我愿当你的邻居,你的护士,你的管家……为你读书,陪你散步,坐在你身边,服侍你,做你的眼睛和手。”[38]简·爱此时已不单单是罗切斯特的妻子,而是如同帕特摩尔的诗中所说的“女仆和妻子”[39]一样,丈夫的需求,就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为此,简·爱也放弃了她家庭教师的工作,因为她的“全部的时间和精力”[40]都要用来照顾她的丈夫,这固然有罗切斯特残疾的原因,但同时也代表着,在婚姻和家庭之外,简·爱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社会身份。在小说的结局处,“家庭教师简·爱”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是“罗切斯特的夫人”,一个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家庭的传统女性。
“社会训练女性,使她们只为一个功能而生,这个功能就是婚姻。”[41]简·爱的归宿也正是如此。那个为了独立而发奋自强、为了世界之广大而兴奋不已的简·爱仿佛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她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依靠亲戚的遗产而生存、依附于丈夫、为了家庭而存在的“家中天使”。简·爱形象的转变无疑削弱了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而这部小说的主旨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女性观:“女性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对爱情和婚姻的奉献。”[42]
长期以来,《简·爱》被视作世界文学史上彰显女权主义的代表性著作,而简·爱的出走、拒婚、独立工作等等行为,也被当作是女性追求独立平等的范例。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意识到,《简·爱》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几个主要情节就可以概括的。在一个“出走”行为的背后,有着无数的文本细节在填充,其中所体现的简·爱的内心挣扎和矛盾心结,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在这部小说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一方面,简·爱展示理性、冷静、充满斗志、激烈反抗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她又显得十分虔诚、顺从和保守[43]。在简·爱的出走的背后,是神力的相助以及她的依赖、软弱和不舍;在她呼吁独立和平等的同时,内心的自卑和对下层人的蔑视也体现出了她强烈的阶级观和等级观;反抗男权控制的她,在面对欺骗她的罗切斯特和冰冷的圣·约翰时,却依然几度动摇自己拒绝求婚的意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了简·爱在其女权主义追求上的“二律背反”。
简·爱在行动和思想上的种种不一致,体现了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内心思想与时代观念的激烈冲突。因此,在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种种矛盾特质的集合体:智力和感觉,热情和理性,反叛和守礼,侵略和自守,都融为一炉[44]。在传统女性观和女权主义观中摇摆的简·爱,一直都受到作者所设计的种种宗教、机遇和巧合的外力的推动,这才做出了一系列彰显女权主义追求的行为。然而,为了简·爱最终能够得偿所愿、不负之前的努力,勃朗特设计了“遗产”和“大火”的双重巧合,让平凡而贫穷的简·爱在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中获得了华丽转身,却也变相否定了她之前的种种努力。显然,在勃朗特的内心深处,女性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女性观依然根深蒂固。
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勃朗特的妥协是一种时代的必然。简·爱在爱情中的挣扎就是她在压抑女性的社会泥潭里的挣扎。在研究《简·爱》时,我们不仅应该揭示这部小说的女权主义意蕴,而且应该将其放入本文所揭示的种种矛盾和悖论之中进行省思:它依然接受了维多利亚价值观对女性的定义,即女性存在的意义依靠其丈夫而得以体现,女性生命的意义在于其对家庭事务的投入和对其丈夫的利益的关注。对《简·爱》中女权主义的局限性进行省思,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英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而且对于我们观照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疯女人”的反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