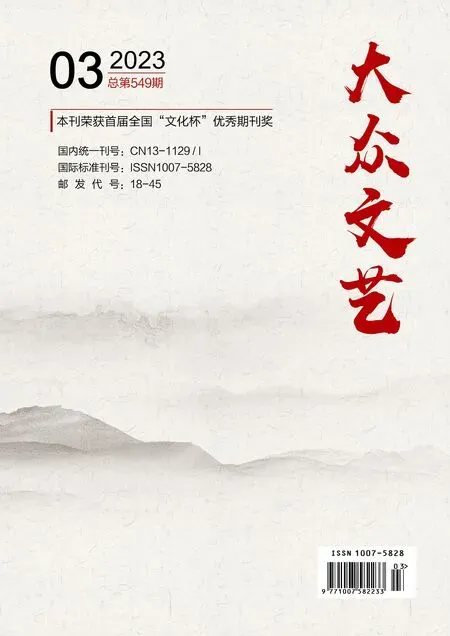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域下小说《装台》解读
李元嘉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欧美,它的产生和出现与欧美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关系密切,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与反思女性问题,它是对“厌女主义话语”的反动,它侧重于从女性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文本,展现女性历史生存的境况,并挖掘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期望借此唤醒公众对女性群体的重视,与此同时,也对固有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强烈批判。[1]陕西作家陈彦立足于自身生活的陕西大地,根据其多年在文艺团体中的生活经验,描绘了他眼中以装台人刁顺子为代表的一批生活在西安底层的普通人,小说以他们的装台生涯为主线,刻画了围绕在刁顺子周围的刁菊花、蔡素芬、韩梅等女性角色。在小说中,作家用了大量笔墨去描绘这些女性角色,人物形象鲜活饱满,但与此同时,对女性角色性格、外貌和相关空间的刻画,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因此,下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小说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的生存境遇进行剖析。
一、男权社会中的他者
自古以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女性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其主体性都被男权社会瓦解,广大女性生存于男性的集体压迫之下。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传统,女性的地位始终处于一个被社会、被男性凝视且被剥削的状态。当今虽然女权主义运动不断,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底层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女性相对于男性仍是边缘性的存在。[2]女性群体被社会和男性定义,接受男性的“观看”,承受男性的压迫。小说《装台》中所描绘的部分女性角色正是处于此种境况,她们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中,由男性定义,成为男权社会中的他者。
(一)被凝视的女性
凝视理论由西方“视觉至上”原则逐渐发展而来,通过凝视展现欲望机制。针对凝视,西方许多理论家对此进行过探讨研究,例如,拉康认为人的眼睛是欲望的器官,凝视的过程是幻想的投射,是实现自身欲望,寻求欲望满足的过程。而福柯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凝视与权力的关系。在凝视过程中,凝视的主体完成了对客体的统治,置于男权社会中,女性则是在被“看”的过程中,感受到男性凝视的权力压力。[3]劳拉·穆尔维将凝视理论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将之用于电影镜头的分析中,认为当今主流电影站在男性中心的视角上,以男性的视角拍摄女性,展现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常作为刺激男性视觉欲望的角色而存在,成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劳拉·穆尔维等人有关凝视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当代电影批评,同时在当代小说的解读中,也可找到论证其观点的影子。
《装台》中,主人公刁顺子总共有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田苗生下女儿刁菊花后离开刁家。第二任妻子赵兰香带着与前夫生下的女儿韩梅,嫁进刁家,但不久后便病死,独留继女韩梅。小说便从刁顺子将第三任妻子蔡素芬娶进门时展开叙述。全书十分注重对女性的刻画,书中大量存在着从男性视角出发对蔡素芬、刁菊花等女性角色身体的刻画和评价。男性往往将自身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投射于女性身体之上,这在小说中有鲜明体现。蔡素芬是小说中所谓的“漂亮女人”,这是从顺子等男性的视角得出的,顺子认为蔡素芬是他三个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蔡素芬脸上还是油光水滑的。除了眼角,脸上几乎还看不到一点皱纹。”[4]“一群心闲下来的男人,突然发现阳光下的蔡素芬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楚楚动人…可此时的蔡素芬,跟她们哪一个比起来也都毫不逊色,长发飘飘的,简直美极了”。[5]而作为与漂亮女人蔡素芬相对立的反面——“丑女人”刁菊花,其外貌同样也未逃过男性的凝视。刁菊花毫无疑问是个丑女人,这一点甚至得到了与她关系亲密的两个男性即父亲刁顺子和大伯刁大军的认同。在刁顺子看来,自己的女儿“人长得丑些,随了他的相貌,脸上到处都显得有些扁平……尖额头咋都拉不宽展,短下巴也抻不长”[6],就连刁大军也同样如此认为,因此,刁菊花一直单身。在小说中,女性外形始终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中,成为男性评判的对象,被男性消费和获得视觉上的满足。在男性看来,蔡素芬、韩梅、年轻的杨桃花是漂亮的,因为她们的皮肤光滑少有皱纹、身材曼妙、五官立体。而刁菊花是丑陋的,因为她五官扁平,脸型奇怪,皮肤也很粗糙。美、丑皆由男性而定,男性对于女性外形的凝视,正是其审美观念强加于女性的过程。行走于男权社会的女性,无论外形如何,其评判的权力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更甚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之中,长久以来,已围绕男性形成了一套观念和价值判断。并且在千年之中,它们已深刻嵌入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不仅仅潜藏着对女性外形的定义标准,也包括对女性价值的衡量和认定标准。什么样的女人是男性眼中的好女人?男性又是基于哪些维度对此做出判断?这些在小说《装台》中便有所显现。刁顺子虽有三任妻子,但让他满意和难忘的是第二任妻子赵兰香和第三任蔡素芬。小说中,针对刁顺子对赵兰香的怀念做了大段描述。在刁顺子看来,赵兰香长了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自从把赵兰香接回家后,那个‘烂猪窝’才算有了彻底的改变。她是把家里打理得利利朗朗的,几乎把他和菊花原来穿得变了形的衣服,全淘汰了。”“那时家里也特别和顺”,[7]赵兰香毫无疑问是勤劳、贤惠、体贴的,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而在蔡素芬后来被刁菊花逼得离家而去之时,刁顺子也怀恋过蔡素芬,首先在他看来,蔡素芬“太漂亮,靠不住,”“比自己有文化,说啥跟人都不太一样”,但她“能下苦,能背亏,不计较,不是非”,无论菊花如何难为她,她都“忍气吞声地跟着自己往下过”。[8]在小说中,刁顺子从男性的视角审视自己过往的妻子,在以刁顺子为代表的男性看来,妻子应该漂亮但不过分漂亮,最重要的是贤惠、体贴、不多事,料理好家庭,维护家庭和谐安稳。在男性眼中,对于女性本身的价值判断往往不具多元化倾向,男性对女性的价值衡量与评判,往往来自女性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社会框架中“主内”能力的显现。这意味着,女性众多其他超出此框架的价值被严重忽视和低估。可以说,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在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标准和框架下动弹不得,女性在身体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维度上被男性评判和定义,接受男性的凝视。
(二)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自我认知
在波伏娃看来,女性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形成的,因为女性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充斥着男权观念的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必然影响着女性的成长与独立。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而女性作为被凝视的一方又是如何进行选择与判断的呢?存在主义学者萨特认为,“注视”是一种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他人是注视者,是“注视”的主体,被注视者也就是“我”,是客体。处于被注视地位的“我”处于被动状态,这意味着“我”有可能被他人“异化”。[9]而这一点,正是在分析女性生存处境时,最应该担忧的地方。当女性长久地处于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时,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接受着男性对自身的评判和衡量,自塑为男性眼中的“他者”,以男性标准评判自身、建构同性。
小说中,男性公认的“丑女人”刁菊花便是这样一种存在。她“十分忠诚”地接受着男性的评判标准,以此衡量自己的同时,也衡量身边的同性。她怨恨自己长相平庸、皮肤粗糙,并深刻地认为这是她感情不顺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她把男性的标准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她看来,蔡素芬“比上一个女人更年轻、更漂亮、更风骚”,这个漂亮女人进家门,成了她“人生中一件不能轻易退让与放下的事”。[10]刁菊花原本与继妹韩梅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但自从继妹把“长得颇有几分高仓健意味的”男同学领回家后,两人的关系瞬间破裂。她审视韩梅的外貌,对其酷似奥黛丽赫本的高挺鼻子嫉妒不已。而刁菊花远不仅仅从外形上审视自己和同性,更是依照男性的标准审视同性的性格和风格。在刁菊花看来,自己的闺蜜乌格格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但风格上远不是男人喜欢的类型,她“高大肥美魁”,属于女汉子类型,因此在乌格格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对象时,她内心难以平衡。在男性标准的压迫之下,她对外貌的执念越来越深,甚至不惜委身与自己最初瞧不上眼的谭道贵在一起,赴韩国做整形手术,终究彻底丢失了自我。从刁菊花眼中看到的女性难以摆脱男性目光,女性本身多元化的价值和发展空间也皆被同为女性的刁菊花亲手抹除。
刁菊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自塑为他者的缩影,她可怜、可悲也可恨,她的结局值得警醒。
二、女性的空间博弈
在小说《装台》中,家宅空间是十分重要的空间。它是刁顺子一家家庭生活日常上演的场所,而刁顺子一家作为重组家庭,此家宅空间也是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博弈的场所。对于女性而言,家宅除了是满足她们生理需求的居所外,更是她们的归属地和栖息地。事实上,依据传统来看,男性与女性的活动空间往往存在差别,女性活动空间往往具有“向内性”,而男性的活动空间往往具有“向外性”。女性往往不像男性那样拥有充裕的社会活动空间。[11]而刁顺子一家的三个女性,正是传统意义上女性的最佳写照。家宅这个狭小的空间,涵盖了她们一生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从传统观念上来看,男性为当家人。因此,在刁顺子的家宅中,刁顺子是一家之主。三个女人中,其亲生女儿刁菊花因与刁顺子的血缘关系,便具有了占据这个空间的名正言顺性。她年近三十岁,仍未嫁出去。因此,对于她而言,即使她对这个家庭颇有不满,认为它贫穷,对父亲颇有怨恨,认为他的职业上不了台面,这个家宅仍是她唯一的栖息地,是她在偌大的西京城里唯一的归宿。因此她要牢牢把控这个家的控制权。相比起刁菊花,韩梅与蔡素芬都具有了相比较而言的“外来性”。韩梅是刁顺子第二任妻子带进刁家的女儿,与刁顺子并无血缘关系。因而,亲生母亲赵兰香死后,在她心中,哪怕继父待自己不错,自己与继父终究“隔着一层了”。而她的房间,虽占地仅十四平方米,于她而言“这就是她作为西京人的立足之地了”“这里牵连着她另外的人生希冀和梦想”[12],对她来说,这也是她存在于西京城的唯一确证,她得守住。而对于蔡素芬来说,丈夫刁顺子本身便是她在西京城唯一的依靠,其自身技艺有限,便只能生活在丈夫的“半径”中。因此,不管是刁菊花还是韩梅和蔡素芬,在她们眼中,这个家宅虽然贫穷,却都是她们在西京城唯一的栖息地。
但三个女人共享一个家宅空间,这一点让刁菊花难以接受,于她而言,这个家姓“刁”,韩梅和蔡素芬皆是外来者,因此,她不断给她们难堪,威胁她们离开刁家这个空间,以便自己成为唯一的女主人。三个女人性格各异,而性格泼辣、善妒、蛮横不讲理的刁菊花占了上风。
对于刁家这个家宅空间而言,刁顺子作为刁家的一家之主、家宅的直接拥有者,其本该在此空间中具有第一权威性。但与其他以往的家宅空间不同的是,刁顺子本身性格软弱,在每一次刁菊花挑起家庭纷争之时,都企图以求饶、示弱以换取短暂的安宁。刁顺子的个性,使其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大大削弱,这也导致其亲生女儿凭借血缘优势,在整个家宅空间中变本加厉地挤压另外两位女性的空间。最终致使韩梅与蔡素芬在刁菊花的压迫之下,离开此空间,另寻容身之地。
这看似是三个女人的博弈,而实际上她们的“砝码”和与刁家这个空间产生关联的底气,皆来自刁顺子这个刁家唯一的男性。刁菊花是刁顺子的亲生女儿,紧密的血缘联系让她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地位。而韩梅与蔡素芬因其各自与刁顺子的关联,本不至于被挤兑至此。然而,刁顺子的性格使其在整个家宅空间的话语权严重旁落。当刁菊花在刁家的权威凌驾于刁顺子之上时,纵使刁顺子主观上并不情愿她们离开,仅靠情感与刁顺子关联的韩梅和蔡素芬,便也终究丧失了守住这个空间的底气和强有力的庇护。而若细究,刁菊花肆无忌惮的资本只不过来自与刁顺子更加紧密的血缘关联。因此刁家的家宅空间中,看似是三个女人复杂激烈的博弈,但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留存着男性权威的影子。
三、现代女性光芒的闪现
正如前文所言,在小说《装台》中,部分女性或者成为男权社会中的他者,接受男性的“凝视”,并形塑自我认知;或者依靠男性的庇护,生活在男性的“半径”中,寻求一片生存空间。然而,在小说塑造的众多女性角色中,剧团女导演靳导的存在却显示了与绝大部分女性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
依照小说的描绘,靳导身材肥胖,完全不符合男性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但她全然不在乎男性的评判,于她而言,男性与他人的评价皆不是她所需关注的,她不是男性衡量标准中的“漂亮女人”,也不是贤惠持家的贤妻良母,面对三段失败的婚姻,她皆是淡然视之,心境豁达而非满腹怨言。她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无须通过男性获取栖息的空间,这意味着她拥有对自己人生方向的掌控权和自己空间的支配自由。
作为一名女导演,她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认真对待每一部舞台戏,无论是演员还是灯光、造型、剧情,她都力求做到完美而不留一丝遗憾。她爱戏到痴狂,是别人眼中的“戏虫”“戏疯子”。刁顺子等一众工作人员一方面对她的一丝不苟颇有怨言,一方面,也敬佩她对戏剧事业的认真和严谨。
除了对靳导工作、生活和外貌的展现,小说也通过刁顺子的手下猴子因工受伤而讨要补偿一事展现了靳导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剧团这类组织中,靳导作为导演,毫无疑问处于上层的位置,然而自身的位置却并未抹杀她对底层人民的悲悯和关怀。她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同情底层人民的遭遇。即使与自身利益并不相关,在猴子手指因工受伤时,她却站出来不计回报地为猴子争取更多补偿。身处高位却仍存体谅他人的慈悲之心。她违背了男权社会中一切的衡量标准,但其对事业的专注和高尚的品格精神,同样为她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理解。
靳导是一个闪现现代女性光芒的角色,她的存在如小说中的一个光点,揭示着现代社会中“新”女性应有的模样,也藏匿着作者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怀,和对女性独立发展的期望。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