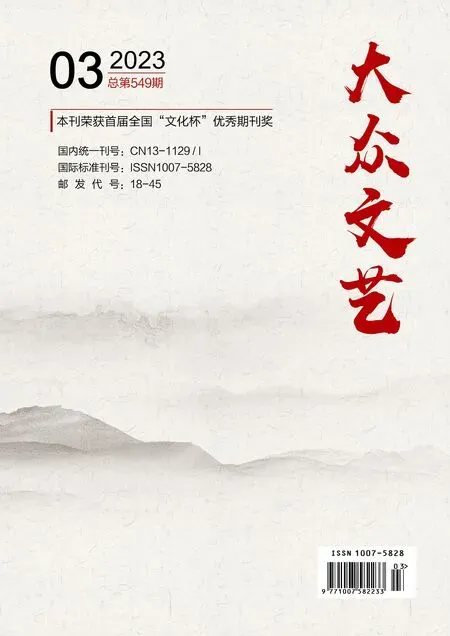论《纵横交错的世界》中的老年书写
王沛然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阿莉·史密斯(Ali Smith,1962-),英国后现代小说家,曾多次获得英国金匠文学奖、《卫报》年度小说奖,多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被认为是值得期待的未来诺贝尔奖得主。她的小说多具有浓厚的实验性质,采用多视角叙事策略,使得“每部分既独立又彼此相连”[1],独树一帜。《纵横交错的世界》(There But For The,2015)以巧妙的叙事结构讲述了麦尔斯作为“闯入者”在晚宴过后将自己锁在主人客房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对曾与之有交集的四人的回忆进行厚描,将看似割裂实则紧密相关的故事线索加以串联,在描摹众生百态的同时逐渐揭开麦尔斯的神秘面纱。
小说自问世以来,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有学者就其中的在场、缺席、时空复杂性等进行论述,亦有学者从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及文本虚构层面分析其非自然元素,但较少关注到《纵横交错的世界》中老年书写这一主题。史密斯通过对以马克、梅为代表的英国当代社会中老年群体的多维度描写,将衰老所带来的创痛情景化、具体化,呼吁对边际化老年群体的关注与倾听。本文将从老年书写角度对《纵横交错的世界》进行解读,分析史密斯何以借助老年人这一独特的文化身份反思个人与社会如何面对衰老进程,进而提倡个体从意义客体到意义主体的转向。
一、无法掌控的身体
在与麦尔斯有交集的四个人物之中,马克是一名年近六十的同性恋男性,梅则是一名年逾八十、生活无法自理的女性,二人分别处于老年学意义上的“第三年龄”(the Third Age)及“第四年龄”(the Forth Age)阶段,在生理及心理层面或呈现一定程度的衰退或残障,被大众普遍视作老年群体、边缘群体。史密斯通过对二者的身体书写,将衰老所致的无力感融于生活图景,折射出英国社会中老年群体的生存困境。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引发各界关注,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应运而生。“纵观人生命的自然发展历程,呈现出中间‘强’两头‘弱’的态势,幼儿与老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柔弱的特质”[2],而老龄这一概念似乎已被符号化,通常与衰弱、疾病、死亡等相关联。年近花甲的马克尽管具有完全行动能力,却发现自己“行动渐渐迟缓、大脑转速变慢、皮肤薄如纸片、视力急剧下降”(82),记忆中不甚陡峭的格林尼治公园实则亦令他走了很久,需要在半路调整呼吸,感叹“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段路相当陡”(76),再不似过往那般健步如飞;年逾耄耋的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腕上戴着“塑料的手镯形状的东西”“粗糙干枯的手腕从一件睡衣袖子里伸出来”(179),连试图做出触摸手腕上异物的动作亦需花费较长时间颤抖摸索、拼尽全力,然而在面对便溺失禁时却毫无掌控之力,“她突然有所感觉,只是那些东西都悄悄溜了出来,她根本无法阻止”[3](230),全力与无力对比之下尽显苍老之态。
除身体机能衰退外,小说中的马克与梅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残障”。世界卫生组织将“残障”界定为生理残损、活动受限、参与受限三个维度,包含肢体障碍、语言障碍、精神障碍等。[4]梅被诊断为“全面崩溃、精神错乱、高烧、泌尿系统感染”,被其子女与医院协商认定为“需要‘临终关怀’的病人”(184),被“囚禁”在病房中接受医学观察的同时亦要接受来自不认识的探视者的凝视,几乎与死亡画了等号,将老人自身的意愿与价值统统抹去。无论是在格林尼治公园还是在李氏夫妇的晚宴,马克皆因其精神障碍被大多数人所孤立:带着年幼孩子的夫妻有意地将孩子抱得离马克远一些;晚宴宾客大都不情愿坐在马克旁边,在李太太提及马克时,除“同性恋”之外便是用“年龄较大的男子”进行指代,似乎这两个词汇便足以描绘马克其人,无须像描述麦尔斯一般极尽辞藻,将这位老人标签化、扁平化。伴随生理衰老与多维残障而来的则是心理层面感知功能的强化,即“在身体实践退化的情境下,依然在心理与精神层面赋予主体稳定的领域把握”,从而构成“非年龄化自我”,使得老年群体“总感觉自己年轻(feeling young),而且比同龄人状态良好”[5]。59岁的马克认为自己“顶多三十岁”“好像三十岁的自己困在一匹老马的身躯里”(82),日渐衰老的外表难掩其充满活力的心灵,能够发现并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拍下冬日里鸟儿在阳光中恣意歌唱等自然中生机勃勃之景;梅·杨永远年轻(May Young will be forever Young,此处Young具有双关含义),她意识清醒、思维活跃、妙语连珠,只在大脑范围内将感受与回忆讲起,对自己苍老的躯体颇为陌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现实、对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认知”,更能通过“观察身体的境遇,了解生命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6]。而正如看护梅的一位爱尔兰护士所说,“一副苍老的身躯并不是他们的全部”(200),即便生理衰老不可避免,却可在心理层面追求更为细腻的感性体验,实现身体实践的心理转向。
二、如影随形的幽灵
根据德里达的研究,“幽灵”指涉一种“处于在场和缺场之间的存在状态”,具有“在现实世界无法抓住或触摸但会留下印记的特点”[7]。小说中除马克已故母亲这一显性幽灵外,梅的幼女早逝一事亦成为其心中挥之不去的隐性幽灵,而“幽灵”所带来的情感创痛似乎亦在代际之间传递,不断唤起过去的记忆。《纵横交错的世界》一文着重刻画了伴随两位老人的幽灵,展现他们在记忆中寻求慰藉的动态过程,以幽灵为介折射老年群体的怀旧之态及精神创伤。
幽灵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创伤的复现,是“压抑的情感之外化,它神秘可怖的气质、破碎的语言、缥缈的身影、来去无踪的行动都将人内心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压抑感外化为具体的形象”[8],反映了主体内心对某种情感的渴求。小说中最显而易见的幽灵即为马克已故的母亲。章节开篇即向读者表明这一幽灵的在场:“马克的母亲费伊已经去世四十七年了……她平常说的话会比今天早上的这句要物理、残忍的多”(75)。马克自十三岁起便能听到母亲的声音并时常能与之对话,甚至会故意出言激怒母亲争吵斗嘴,以此回忆幼时为数不多与母亲相处的时光、弥补母爱缺席的遗憾。此外,尽管马克曾“因为他母亲的自杀感到很生气”(153),母亲的死亡并未给他带来较大的实质性伤害,童年在姑姑家的缄默反而更像是造成其内心孤独、缺爱的诱因,促使母亲的幽灵出现聊以慰藉。自此,马克便游走于割裂的两重空间:“第一重是当下熟悉而真实的世界;另一重是创伤幽灵时时造访的隐秘的空间”[9],两重空间相互交织、纵横交错。正因马克可随时随地与幽灵对话,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导致在现实世界中被误以为是自言自语的疯子,使得他总是无法融入当下社会,却亦无法从与幽灵对话的世界中脱离。梅的幼女詹妮弗虽未以类似费伊的形式存活于世,却也成为小说中隐性存在的幽灵,反复出现在梅的记忆之中。84岁的梅仍清晰记得詹妮弗“1963年4月4日生,1979年1月29日亡”(191)于心脏疾病,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六岁。丧女之痛是梅生命中的巨大创伤,女儿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又似乎如此遥远,故而在心中建构一个“秘穴”(crypt),“想象或失去的个体被隐蔽起来,使自我对创伤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10]。对幼女的愧疚与怀念使得梅错将发生在大女儿埃莉诺身上的事嫁接于詹妮弗身上,甚至因为“回忆的内容不恰当,把埃莉诺弄哭了”(190)。此举非但不能弥补已逝亲情的遗憾,反而在无意识中将这一遗憾接续转移至生者心中,致使大女儿抱怨“总是詹妮弗”,形成创伤的代际传递,陷入亲情缺失的创伤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诸如非自然叙事、内视角与外视角的转换等多种后现代叙事技法来描绘主体的创痛与修复,将马克母亲的押韵词句与梅断断续续的诉说记录在案,使得幽灵的复现在唤醒创伤的同时模糊了真实与虚构、过往与未来、生存与死亡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结构,为过去与未来建立了对话的桥梁,帮助情感缺失群体重拾温暖记忆,在重整记忆碎片的同时逐渐与过去和解,恢复生活信心继续前行。
三、难以言说的话语
作为一名后现代作家,史密斯善用文字游戏传达多重含义,而双关作为小说中各大主人公所偏好的文字游戏,在梅的篇章中亦有所体现。梅被塑造为患有失语症的老妇人形象,而“失语”一词既指涉生理层面老年群体的疾病表征之一,亦暗示了这一群体处于话语边缘的现状,呼吁人们关注老年群体内心的声音,在尊老爱老的同时鼓励他们从意义客体到意义主体的转向。
失语症从病理上讲指涉由于各种原因损伤大脑半球后所导致的语言交流能力障碍,兼具生理及心理因素,使得患者无法清晰准确地表达自身意愿及诉求。自从重症监护室转出以来,梅再未说过一个字:“现在不会再有人大声讲话了,而且以后也不会有了”(179);即使偶尔张嘴,说出的话却“根本不是她本来想说的话”(212)。正是这种无法表达的状态使得梅被穿上了粉色这一“永远都不会原意穿的颜色”、被戴上“写着她出生日期的塑料东西”(179-180)而毫无办法,甚至会在情况好转后被送至她极度反感的港湾之家。尽管梅有着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可有些是为了学校课题而来,有些则是为了完成探望老人的任务,并以此拿到徽章而来,戴耳机的造访者似乎也暗示着鲜少有人真正关注梅等卧病在床的老年人内心声音的境遇。即便是乔茜将梅从医院中带出来后,梅可以用支离破碎的语言讲述她的回忆,却也遭到乔茜男友的埋怨与嫌弃,“让她别再唠唠叨叨地说下去了”(230),不愿倾听她们的遭遇。同时,因价值缺失而处于权力话语底端的老年群体亦患有“失语症”,他们“生活在人生的边际空间,他们的生活节奏、他们的语言表达都与主流社会价值存在很大的距离”[11],无法融入社会话语甚至被剥夺了发声的机会,这便是失语症这一双关的第二重含义。老年群体往往无法快速掌握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鲜事物,梅会将互联网错当作“挚友网”,对于电话的使用亦令人啼笑皆非,这也限制了他们用新型社交媒介为自己发声的能力。无独有偶,马克亦面临着失语的境遇:在李氏夫妇的晚宴上众人高谈阔论、把酒言欢,却无人关注马克不喝白酒且渴望红酒的意愿,以致主人在“给每位客人的杯子里都斟上红酒”时“唯独没有给马克倒”(121),而马克因想不出该如何要求红酒而无以表达内心诉求;在麦尔斯事件成为全国热点,媒体想要采访马克这一曾出席宴会、与麦尔斯有交集的宾客时,被李太太一口回绝,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和您谈什么”“我想他们需要的信息我们都提供得差不多了”(167),再次令马克失语。
不同于世界传统文学中的“智者”“先知”“神明”等积极正面形象,现代社会往往因老年群体失去社会价值而将其边缘化,甚至出现“道德败坏的老男人”“疯婆子”等污名化词汇,使其处于道德伦理劣势地位。马克在格林尼治公园仅仅是看了一眼讲解队伍中调皮的男生,就被男生用尖刻的声音指认为“看那边的那个老头,你们看他,他喜欢我”,仿佛一个道德败坏的恋童癖;李氏夫妇“每年邀请一些平常不太接触的人参加”,认为“扩大交际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20),实则将他们视作他者,构成凝视。当马克邀请麦尔斯一同参加晚宴时,众人自然而然地将麦尔斯当作马克的新伙伴(new mate);席间关于同性恋的种种偏见不绝于耳,被理查德戏谑地称为“参与过的同性恋倾向最浓的交谈”(125);在谈及艺术及死亡时,马克作为他者中的他者,其同性恋身份以及自杀的犹太籍艺术家母亲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的笑声很大,好像他们找到了一个笑柄”(145)。梅尽管在日常交流中鲜少开口,却会在发病时疯狂寻找“在任何一个人家里都不可能找到的东西”(188)、絮絮叨叨地讲述他人都听不懂的话语,被认定为疯癫难缠的老婆子。不同程度的失语使得老年群体成为衰老的客体,与其说是在与话语搏斗,不如说是在与生命的意义搏斗,亦是让老年人“成为生活的主体,以求新的心态,追求将生命的意义定格,以叙述、描写的形式不断地生成生命意义”[12]的过程。
结语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史密斯以独特细腻的笔触将老年问题融入文学创作中,将衰老所带来的躯体残障、创伤复现、价值缺失等问题具体化、情景化。阿莉·史密斯本人也于本年踏入60岁这一第三年龄阶段,其创作与表现手法的创新似乎也向老年群体传达着意义给生命带来的前进张力,而对于文学老年学的研究“既是一个现实命题、社会命题,也是一个情感命题、哲学命题,在多个层面上凸显出重要意义”,以期通过对老年人生存境遇及心理模式的刻画反思个人与社会如何面对衰老进程,呼吁对边缘化老年群体话语的关注与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