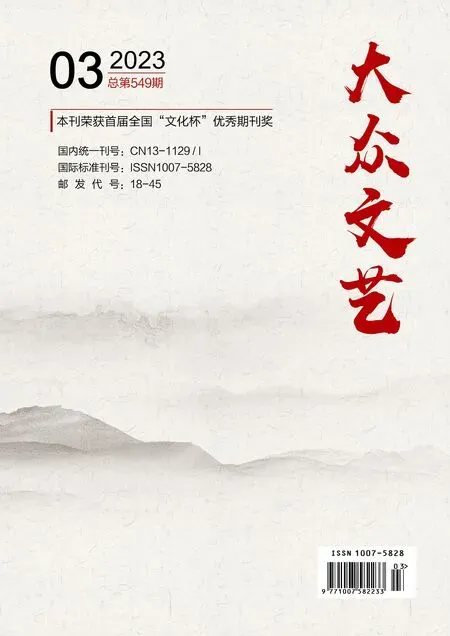古雷茨基第三交响曲的接受视域和音乐话题研究
程婉君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00)
西方艺术哲学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接受问题的关注明显上升,特别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以解释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作品与接受大众的关系后,掀起了研究接受美学的热潮。波兰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萨(ZofiaLissa)、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 Danuser)等学界大师均对音乐接受问题进行批判性论述,这些理论为研究波兰作曲家亨里克·古雷茨基(HenrykGórecki,1933-2010)《第三交响曲“悲歌”》(Symphony No.3,Op.36 Sorrowful Songs,1976)的“神化”事件提供了丰富的模式。笔者将通过接受问题中的“视域”“作者意图”和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中提出的音乐“话题”(Topoi)等概念,解读古雷茨基第三交响曲的接受问题。
一、接受史中的“古雷茨基第三交响曲神话”
古雷茨基是波兰“音响主义”先锋派作曲家之一,他精通十二音序列技术,是波兰现代音乐的领导人物,一度被视为“后韦伯恩序列音乐的波兰继承人”[1]。第三交响曲创作于1976年,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共三个乐章,其波兰语副标题为“悲歌”。第一乐章是寂静如歌的慢板,运用了古老的教会调式,以低音提琴缓慢演奏的定旋律为基础,由女高音演唱15世纪波兰祈祷文《圣十字悲歌》;第二乐章的文本取自盖世太保集中营中的少女在墙壁上刻下对圣母的祈祷;第三乐章是如歌而单纯的慢板,源于西里西亚暴乱时期的波兰民歌,讲述了战争中母亲对爱子的哀悼,宛如摇篮曲一般宁静。这部缓慢平稳、简单纯净的交响曲完全背离了先锋派序列音乐,回归到富有情感的传统创作方向。
第三交响曲在首演时曾受到先锋派批评家们各种锋利的负面报道,但随着之后的演出,特别是80年代发行的三版唱片,使它两次成为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排名最高的作品,销量超过了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的专辑,在全世界掀起了古典音乐屈指可数的现象级流行热潮。除了音乐本身独特的创作风格外,社会和情感因素也促使这部作品广为流传,而这场转变被誉为“古雷茨基神话”(Górecki myth)。[2]
二、第三交响曲的“接受视域”对“作者意图”的反叛
“接受视域”即为接受者的“目之所及”,由于接受者的语境存在差异,不同的接受者有着有不同的接受视域,因此就一部音乐作品而言,同一部作品的接受问题在不同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群体中的接受视域截然不同,但这些接受者的视域均与古雷茨基的原始创作意图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
(一)幼稚的“保守派”——先锋派评论家的视域
1977年第三交响曲首演于法国鲁瓦扬举行的国际当代艺术与音乐节,首演过后有六家德语音乐期刊先后批评了这部作品的“保守”风格,海因茨·科赫(Heinz Koch)在期刊《音乐》(Musica)中写道,这部交响曲“在三首古老的民谣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中拖拉了55分钟。”而期刊《奥地利音乐》(OsterreichischeMusikzeitschrift)的评论家迪特马尔·波拉切克(DietmarPolaczek)声称“古雷茨基严重偏离了已经被证实和确立的先锋风格,而这部作品只是包围先锋派顶峰多余的垃圾”。[3]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古雷茨基的这部交响曲中不存在任何“新式”的创作手法,完全不具有先锋的特点。然而鲁瓦扬音乐节是当时最重要的先锋音乐节之一,信奉的是德法先锋派,这部交响曲就当时的评论家们而言无疑是幼稚、保守、倒退的,但古雷茨基却表示“对我来说,这是我在那里(鲁瓦扬音乐节)听到的最先锋的作品。”[4]而事实证明,在20世纪70年代后,激进的先锋派也逐渐成为一种“过时”的风格,音乐创作朝多样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甚至出现回望历史的趋势。
(二)战争的“安魂曲”——英美音乐市场的视域
20世纪80年代,大众对冷战格局、纳粹暴行和共产主义瓦解等重大政治事件掀起批判的潮流,1989年在德国布伦瑞克为悼念德国入侵波兰五十周演出了第三交响曲,将交响曲与战争直接相连,自此,这部交响曲逐渐变成二战时期所有受害者的悼歌,象征着几十年来东欧经历的所有苦难。1992年第三交响曲的出版商美国埃莱克特拉公司(Elektra-Nonesuch)对唱片的包装和营销策略直接促成了这部交响曲的广泛流行。埃莱克特拉在灌录唱片时邀请了嗓音温柔、平和的女高音演唱家道恩·厄普绍(Dawn Upshaw)演唱,唱片封面使用了一位正在祈祷的少女剪影,柔焦镜头像一层面纱遮住这位无名少女,以此隐喻三个乐章中的女性主角,而少女身旁还有一个十字架组成的围栏,架在一个圆形拱门上,这与古雷茨基设计的母性和宗教主题紧密相连。唱片内页的音乐说明强调了1989年在布伦瑞克的演出,更加暗示了第三交响曲与战争的关联。这张唱片的销量极其可观,使第三交响曲的商业价值堪比热门流行音乐。但反观这一时期的评论文章,对第三交响曲的结构、音色和风格等审美问题的关注明显减少,评论家们的关注集中在“战争安魂曲”“大众化”的实用功能和商业功能。
然而古雷茨基从未将第三交响曲作为纪念战争受害者的作品,他曾否认到“交响曲不是关于奥斯威辛。也不是关于斯大林战争后波兰人所遭受的可怕政权。它甚至不是关于团结的斗争……”[5]古雷茨基也多次拒绝了以战争为主题的创作委托,因此单纯地将第三交响曲视为纪念战争受害者的挽歌是一种误解。然而乐曲的第二乐章中关于集中营的背景不容忽视,古雷茨基成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战争带来的阴影是他创作第三交响曲时至关重要的情感背景。
(三)“神圣简约主义”——音乐学者的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分析研究第三交响曲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些音乐学者和评论家将古雷茨基与当时以阿沃·派尔特为代表的“神圣简约主义”(holy minimalism)联系在一起。[6]首次将古雷茨基与神圣简约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位纽约的音乐制作人,当他在1991年听到了第三交响曲在波兰的录音时认为它能够利用派尔特“神圣简约主义”的名气,或者利用“新世纪”(New Age)音乐的裙摆效应获取公众的关注。[7]而神圣简约主义的主要研究学者之一泰瑞·乔特(Terry Teachout)更是认为第三交响曲具备神圣简约主义最典型的特征。[8]在那时的音乐风格史分类方式中,古雷茨基甚至被视为“神圣简约主义”这一流派的代表,英国音乐学家威尔弗雷德·梅勒斯(Wilfred Mellers)将古雷茨基、派尔特和约翰·塔维纳(John Tavener)并称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简约主义者”。
然而古雷茨基强烈反驳了这种风格标签,并始终与简约主义保持距离。尽管第三交响曲的自然音阶、旋律重复使它形似于简约风格,但古雷茨基当时并不熟悉简约音乐和简约主义作曲家们,并且在第三交响曲首演后的数年中,从未有任何一篇文章或者评论指出古雷茨基与“神圣简约主义”之间的关联。当然,以这一术语统称东欧使用简洁音乐材料且具有强烈宗教精神意识的作品和音乐家们明显有失偏颇,他们彼此的创作灵感和宗教背景有着极大差异,因此现在学界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常带有批判性,更多使用“精神性”或“沉思作品”等词语来突出此类作品的特点。
(四)更加多元化的“接受视域”
在已经背负了二战安魂曲这样沉重的情感包袱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导演和编剧又以全新的角度赋予第三交响曲更加深刻的意义。1990年制片人安娜·盖尔斯(Anna Benson Gyles)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电视版的《凡·高传》(Van Gogh),并用这首交响曲描述了天才画家凡·高在法国阿尔勒的乡村找到创作灵感的场景;美国编舞家莫里萨·芬利(MolissaFenley)曾为交响乐的第一乐章编舞,献给因阿拉斯加石油泄漏而亡的野生动物;1993年澳大利亚电影导演彼得·威尔(Peter Weir)执导的灾难剧情电影《空难遗梦》(Fearless)用第三交响曲渲染因飞机失事引发的救赎故事;1996年美国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的电影《轻狂岁月》(Basquiat)以第三交响曲表达了一位不为人知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巴斯奎特辛酸而艰难的一生。[9]第三交响曲从作为对大屠杀受害者、战死者的安魂曲,到为环境、艺术、音乐和哲学哀悼的挽歌,不断发挥着与古雷茨基创作意图相反的功能。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交响曲接受人群的视域大相径庭,但均与古雷茨基的原始意图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尽管自古以来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是理解音乐作品最有效的途径,但它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接受史观恰恰挑战了作者意图,重新审视作者的话语权。同时,接受的历史还呈现出人们是如何通过“裁剪”作品实现对作品意义的期待。那么当接受视域与作者意图都不具有权威性并且相互抵牾时,音乐的本真体现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第三交响曲的真正内涵?
三、“悲痛”情感——第三交响曲中的音乐话题
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提供了可供音乐接受史选择的研究课题,研究作品的“话题”(Topoi)问题就是其中一种。达尔豪斯强调“音乐接受史一定程度上受固定的、不断出现的母题观念决定。这些母题观念的存在和影响都相对独立。”[10]以“话题”的方式解读第三交响曲,能够在尊重古雷茨基创作意图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吸纳接受者的多元解读。第三交响曲的接受史表明,它的话题展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悲痛”情感。
(一)超越母性与宗教主题的悲痛情感
第三交响曲的三个乐章都是由女高音安宁的嗓音叙述着母亲对孩子的爱,这位母亲的形象还象征着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古雷茨基信奉罗马天主教,第三交响曲的灵感也源自中世纪宗教音乐,除此之外还有一首波兰民间小曲,然而艾德里安·托马斯(Adrian Thomas)认为“古雷茨基已经超越了基本的宗教神圣和爱国情怀,进入另一种理解的层面。他所超越了(他曾拒绝描绘的)丑恶的死亡和战争。”[11]古雷茨基没有针对一种特定的冲突或悲剧元素,他将这首作品塑造成一种普遍的悲鸣。例如在第三乐章中,诗歌所描述的是她的儿子尚未归来,但母亲推测她的孩子可能已经死去,使死亡的阴影伴随着女高音的吟唱笼罩在每个人心中。因此,这三首歌曲的悲剧性并非源于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带来的失去感,以及失去亲人伴侣、纯真希望等一切美好事物的悲痛感,是历经苦难的人的痛苦感受。这与古雷茨基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历经战争、大屠杀、疾病、痛失母亲,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而这些苦难在第三交响曲的每一首“悲歌”中回荡。
(二)简约音乐风格传递的悲痛情感
第三交响曲以人声和管弦乐队的创作模式探索了死亡、天堂、童真、悲痛与救赎等主题,这些主题都指向对古雷茨基影响最大的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马勒的《悲叹之歌》(Das klagende Lied)、《亡儿之歌》(Kindertotenlieder)、《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以及第二、第四和第八交响曲等作品都是第三交响曲音乐形式的先例。然而与马勒不同之处在于,古雷茨基使用了简明的主题旋律、简洁的织体结构、简单的和声进行,以简约的三首歌表达了人类最沉重而悲痛的情感,而这种悲痛情感也使其与美国简约主义的形式极简背道而驰。洛杉矶时报乐评人马克·史维德(Mark Swed)认为,第三交响曲“通过重复将简单的事件放大为具有纪念性的事件,将个人的不幸放大为大规模毁灭,也许是理解大屠杀的唯一途径。而这首交响曲告诉我们,必须从墙壁上最小的裂缝中找到美,惊奇的美,才能超越苦难。”[12]我们能够透过速度缓慢、宁静如歌的旋律感受到面对残酷现实的祈祷者的坚定信念,第三交响曲带来的冥想和沉思效果是抚平悲痛感的一剂良药。
借助符号学的理解方式,第三交响曲的话题本身是由“悲歌”主题与简约风格(能指)和“悲痛”情感(所指)构成,然而在接受的过程中音乐话题又转变为“能指”,而各种接受视域在“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中形成“所指”,赋予音乐多重意义。第三交响曲作为一个广义的悲痛情感“符号”,未被局限在其宗教和母性音乐文本中,史蒂文·温盖特(Steven Wingate)总结了这种悲痛情感“(第三交响曲)创造了一个容器,使人类的痛苦能够跨越世代、距离和信仰得以分享。”[13]古雷茨基以这首“简单”的交响曲传递无法用言语直叙的复杂情感,使人们得以窥见他的灵魂、分享他的苦痛,第三交响曲超越了语言和文字表达的障碍,提供了一种创造式的音乐体验。
结论
一些分析第三交响曲的文章认为第三交响曲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应运而生,在现在这个对战争强烈批判的和平年代,这种风格的作品只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于是产生了质疑研究第三交响曲意义这样的争论。面对这些评价不置可否,因为接受者的推动力对这部作品的“知名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第三交响曲是当代为数不多集艺术性、大众接受和社会需求为一体的作品之一,于这类作品而言,研究其接受史是至关重要的,若以完全客观的音乐批评视野对第三交响曲的音乐形式结构进行分析,那么它正如古雷茨基所言,是一部由三首相对不具有联想意义的“简单”歌曲组成的交响曲。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第三交响曲背负了众多情感包袱,时至今日它依然在感动、激励和抚慰着大部分接受者,接受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三交响曲是人类悲痛情感最深沉的表达,接受视域也将继续赋予其新的含义,这也是这部交响曲至今仍能保持新鲜活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