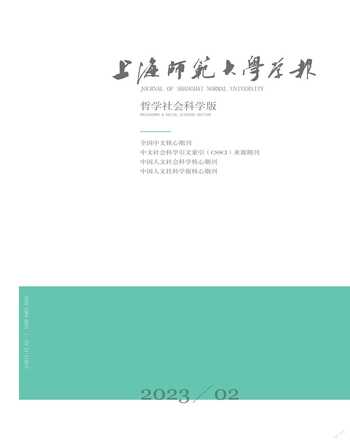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中日丝绸贸易
孙立祥 刘燕
摘 要: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东海丝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日丝绸贸易则是东海丝路中的核心贸易。文章从中日丝绸贸易尤其是日本丝织业发展轨迹的视角切入,回答了曾给东北亚各国带来巨大贸易红利并持续千余年的东海丝路,为何在明清之际由盛转衰,以至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亦即,通过对“中国丝织技术和制品的单项东输与日本丝织业的不断进步”“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本丝织业的奋起直追”“中日‘丝银贸易的展开与日本蚕丝业的快速赶超”三个具体问题的探讨,大跨度、纵向考察中日丝绸贸易的得失,尤其是日本丝织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并从中总结出五点启示性的结论。
关键词: 中日丝绸贸易;东海丝路;东方外交;中日关系;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48;F7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2-0131-(06)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2.014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无疑是东方外交史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而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又是海上丝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南海丝路具有打通不同文明圈联系的地理和文化意涵,东海丝路仅具有沟通儒家文明圈内各国贸易联系与文化交流的功能,故在人们传统意识中一提起海上丝路,首先想到的是南海丝路,而较少将东海丝路纳入视野。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认识误区。实际上,同南海丝路相较,将中国、琉球、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区域四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东海丝路并不逊色。这条持續千余年的海上贸易航线,不但缩小了区域内四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而且为东北亚区域儒家文明圈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甚或可以说,中、日、韩三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某种程度上与持续千余年的古代东海丝路不无关联。因此,对东海丝路在整个海上丝路中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应给予充分的评估和恰当的评价。
不过,本文在此拟重点研讨的问题是,这条曾给东北亚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发展“红利”并持续千余年的东海丝路,缘何在明清之际由盛转衰,以至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换言之,大跨度、纵向考察在东海丝路上曾长期扮演主角的中日丝绸贸易的演变轨迹及其经验教训,尤其是对日本丝织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当是一个可以管窥乃至一探究竟的切入点。
一、中国丝绸和丝织技术的单项东输
与日本丝织业的持续进步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丝绸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其交通路线,一条是从朝鲜半岛最南端越过对马海峡直抵以福冈为中心的日本北九州地区,另一条是横跨日本海到达日本其他地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9年至前210年,命徐福率“男女三千人”,远赴烟波浩渺的东海深处遍寻长生不老仙药。然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1 可以肯定的是,徐福到达的“平原广泽”即今日本,这不仅有史籍所载和两国传说作为证明,而且有徐福迄今被日本人尊奉为桑蚕神和丝织神加以祭祀和膜拜为佐证。若徐福所到之处果系日本,那么他便是中日东海丝路的开拓者。
如果说徐福是中日东海丝路的开拓者,那么弓月君就是将中国养蚕和机织技术东传日本的重要人物。《日本书纪》记载,283至285年,自称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自百济来归”,2 日本人据此将弓月君视为养蚕织绸的第一人。而这些能生产出“服用柔软,温煖如肌肤”3 丝绢的秦氏子孙,被仁德天皇赐予与织机的“机”字日语发音相同的“波多”(“秦”意)姓氏,这些人可谓日本丝绸业的奠基者。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罗织品和罗织技术已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38年卑弥呼女王向魏国所献的贡品中就有“班布二匹二丈”。而魏明帝除册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外,还回赠了“绛地交龙锦五匹”。4此乃中国丝织品传入日本最早、最确切的文字记载。
步入中国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日本雄略天皇在位期间,为学习中国丝绸技术,曾于464和468年两次遣使到“吴国”(南朝刘宋)聘请中国工匠传授技艺。472年,雄略天皇诏令“宜桑国县殖桑”。5 可以说,雄略天皇在推动日本丝织技术进步和丝绸文化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唐朝中叶,东海丝路除北方航线外,还辟出一条由日本博多港向西南横渡东海直达明州(今宁波)的南方航线。尤其在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200多年间,随着中国高级丝绸制品被遣唐使带回日本,日本匠人很快仿制出了。在日本正仓院中,迄今藏有赤地鸳鸯唐草文锦等珍贵的唐朝丝织物品,以及兼具唐代风格和日本本土特色的大量丝织品,从中不难看出日本织匠们的模仿学习能力。中日丝绸文化交流随之走向高潮。赴唐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也学习中国的丝织工艺,与鉴真一起东渡的“绣师”们也将中国的丝绸刺绣技术带到日本,以致日本上流社会无不以穿戴唐式礼服为荣。
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则成立了大藏省织部司,有组织地组织工匠生产出绫、罗、锦、纱等各类高档丝绸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要,日本丝织业由此获得长足进步,以致其丝绸生产地从以京都西阵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向全国扩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开始向中国输出水织絁、美浓絁等本土丝织品,甚至能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6 字样绣在袈裟的边缘上,足见当时日本丝绸生产技艺之水平高超。
尽管从894年终止遣唐使派遣起,日本进入了“国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日本上流社会对中国精美丝绸的需求和热衷并未随之减退。到9世纪中期,原以新罗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改变为中日直接贸易,其中明州成为东海丝路上最重要的港口。唐诗“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古籍所记“唐人商船来着之时,诸院诸宫诸王臣家等,官使未至之前遣使争买”7 等,当能反映以丝绸为主的“唐货”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至宋元两朝,东海丝路走向兴盛。北宋时期,中国商人成为东海丝路的主角,有宋商一年中几次往返于两国之间,1 足见中日丝绸贸易的繁忙程度。到南宋时期,由于日本平清盛废除出海禁令、整修博多港、疏通濑户内海、奖励商人出海贸易,以致出现“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的繁盛景象。2 迄至元朝,尽管官方关系因忽必烈两次征日和日本海盗犯边而步入低谷,但两国民间贸易仍在继续,以致元末六七十年间成为日本商船来中国最多的一个时期。3 在中国丝绸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巨大影响下,日本的丝织技术不断进步,“博多织”“唐绫”“大宫绢”等便是最好的体现。
综上,在上自秦朝下迄元朝的中国丝绸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丝织技艺获得了长足进步。不过,此间日本全国性的丝织中心只有京都西阵一处,其丝织业总体上还谈不上繁荣发达。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丝绸作为昂贵的奢侈品还仅供日本上层社会享用,市场需求十分有限;二是日本上流社会更喜欢中国的精美丝绸,致使日本本土丝织业备受挤压而难以发展。
二、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本丝织业的奋起直追
明初,在日本,南北朝战争中失败的南朝武士入海为寇,开始对中国扰边犯境;在中国,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战败的张士诚等余部亦逃往海上与倭寇勾结。这一内忧外患的形势,严重威胁着国祚初立的大明王朝的统治。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数度下达“禁海令”,旨在斩断元末反叛势力与日本倭寇之间的内外勾结,甚至严到“片板不许下海”的程度。这无疑阻碍了东海丝路贸易的开展,也因之影响了日本上流社会的生活。直至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数度遣使入明,并确立起宗藩关系,大明朝廷才下旨颁发朝贡勘合文册,使中日贸易以“勘合贸易”形式恢复起来。
不过,大明朝廷对“勘合贸易”做出了种种限制,以致“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4 诸如,“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初,……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5 这样一来,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便无法满足日本上流社会的需求。加之后来“勘合贸易”渠道亦被堵死,走私贸易遂成为中日贸易唯一渠道,致使明朝中日贸易整体受阻。其结果便是,尽管中日贸易渠道不畅,导致日本上流社會生活不便,但为日本仿制替代性丝绸产品创造了机会。换言之,大明朝廷“禁海令”的频繁出台,倒逼日本丝绸、瓷器等行业发展起来,这便是这些相关行业的本土规模生产几乎均从室町幕府时代开始的原因。
日本战国时代,各藩大名无不奉行“富藩强兵”政策以求自保和壮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白银冶炼技术从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大森、生野、相川等地银矿的发现,日本的银矿开采业发展起来。日本在16世纪后期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产银国,至16与17世纪之交日本的白银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6 这为日本带来了巨额财富。因此,丝绸制品不再作为奢侈品而仅供上流社会消费和享用,逐渐成为商人甚至普通市民的日常消费品。恰如西班牙商人阿拉比·希隆所言,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来,不但每年“大约消耗掉3000匹到3500匹生丝”,而且“以出色的技巧”将这种“纯白细腻,质地极优”的生丝加工成“非常完美”的素绢,“年年销售一空、消费殆尽”。7
明朝的海禁政策可谓为日本丝织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日本国内掀起的新一轮技术学习热潮,又为日本丝织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日本人运用从中国广州学到的丝织技术改进“博多织”制法,结果竟能成功生产出质地厚实、纹线优雅的“博多带”(高档和服腰带)。到16世纪后期,“西阵织”不但恢复起来,而且出现了勃兴态势。丝绸品种,在绫、锦等既有制品外,又增加了丝绒、缎子等诸多新品种。到安土桃山时代末期,日本丝织品的质量已与中国同类制品不相上下。
时至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丝织业进入空前繁荣和发展阶段。不仅京都西阵一处就有机屋1177家、织机7000余台,1 博多、堺、仙台等其他地方也都发展成为丝织品制造中心。时至此时,尽管日本丝织技术和生产规模均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但其学习和吸收中国丝织技术和丝绸文化的脚步从未停止。与此同时,日本的织匠非常重视本土丝织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西阵织匠筒屋濑平发明的“织锦机”便是典型案例。由此,中国丝绸不但逐渐淡出日本市场,到18世纪中期甚至已被视为劣品而不再进口。2 时至德川幕府末期,日本丝织业已进步到可与中国丝织业一较高下了。
三、中日丝银贸易的兴衰与日本丝织业的
快速赶超
从植桑、养蚕到缫丝、丝织,是丝绸制品生产必不可少的几个步骤。明末,中日丝银贸易之所以能够展开,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桑蚕业状况即原材料生丝产量满足不了其丝织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缫丝技术还无法生产出高级白丝,只能产出劣质黄丝。这样,从中国输入质优货足的白丝便成为日本维持丝织业运转的唯一渠道。恰值中日贸易因明朝廷实施海禁而陷入困境之时,葡萄牙武装商船适时填补进来,成为东海丝路主导中日生丝贸易的主角。
葡萄牙商人早就想染指中国的对外贸易。他们1554年获得在广州通商贸易的权利后,继而又于1557年获得在澳门居留和贸易的权利,逐渐成为远东国际贸易尤其是东海丝路贸易的主角。其实,早在1542年葡萄牙商人便因“种子岛奇遇”而开始同日本进行贸易。当他们发现中日生丝贸易有巨利可图后,便将收购于广州的生丝进口到日本长崎再行销全国。
而就在中国以白银为货币出现庞大需求之际,日本随着银矿开采业的发达而呈现白银供过于求局面。例如,17世纪30年代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7或1∶8,而日本的金银比价却为1∶12至1∶13。3 如此一来,将日本的白银输往中国同样可获巨利。于是,葡萄牙商人便将日本的白银输往中国澳门收购中国的生丝,再将中国的生丝运回日本换取白银。这便是他们经营并掌握主导权的往返均可获巨利的中日丝银贸易。当时,每年葡萄牙商人从日本输往中国的白银有100万两左右,从中国运往日本的生丝则多达1500至3000担,以至中日丝银贸易成为16世纪中叶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东海丝路最有利可图的贸易。自此,生丝取代丝绸成为中日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大宗商品。
1603年建立的日本德川幕府,为了从葡萄牙商人手中夺回对华贸易控制权,特颁发“朱印状”开展中日贸易,日本的“朱印船”便应运而生。在明朝廷推行海禁政策的背景下,“朱印船”只好绕道琉球、东南亚地区等,通过第三地贸易购买中国的生丝和其他商品。截至1635年,“朱印船”每年从日本输出白银约3万至4万公斤,自中国进口生丝1400至2000担4,这同葡商控制的中日丝银贸易规模大体持平。
与此同时,江户幕府或遣使中国游说,或请琉球和朝鲜居间调停,试图通过恢复两国邦交直接开展中日丝银贸易。在均未获得明廷回应的情况下,德川幕府还以允许在日本自由交易等为优惠条件鼓励华商赴日贸易。中国商人尽管早就知晓经营中日丝银贸易可获“十倍”甚至“百倍”5巨利,但畏于明廷禁令而不敢贸然趋利。直至17世纪初大明王朝海禁渐弛,中国走私商船才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冒险前往日本直接贸易。
葡萄牙商人从中日丝银贸易中所获的丰厚利润,引起西方其他殖民主义者尤其是荷兰商人的眼红。荷兰人继1596年抵达爪哇岛的下港、1602年于此成立东印度公司、1609年设立平户商馆、1622年进攻澳门未果之后,最终在1624年侵占我国的澎湖和台湾。自此,我国台湾、澎湖遂成为荷兰商人经营中日丝银贸易的基地。据统计,仅1636年一年,荷兰商人就将1422担生丝输往日本,又将70余万两白银运往中国。1 这样,在17世纪早期的东海丝路上,呈现出中、日、葡、荷四国商船百舸争流,从事中日丝银贸易的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
中国生丝的大量进口虽然为日本丝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导致日本白银大量外流,因此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对中日丝银贸易加以限制,以遏制白银继续外流。结果,1685年“贞享令”、1715年“正德新令”等的先后颁布,在遏制住日本贵金属外流的同时,也导致从中国进口的生丝数量逐年下降。不过,这虽然使日本丝织业深陷原料不足的困境,但也为日本发展本土蚕丝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本国蚕丝业的发展,包括幕府中央命令各藩为养蚕农户提供桑苗、蚕种、资金和技术,而仙台、土佐、博多各藩则自行采取奖励措施鼓励植桑、养蚕和生丝生产。在朝野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桑蚕业迅速发展起来。到江户幕府晚期,随着缫丝生产技术大幅提高,日本国产生丝不但在质量上不亚于中国生丝,而且在产量上也基本能够满足其本国丝织业生产的需要。至19世纪初,中国生丝已被完全挤出日本市场。而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丝织业更是做好了同中国同行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高下的准备。
四、五点启示性结论
纵观中日丝织业的逆转发展历程和两国丝绸贸易、东海丝路由盛转衰的演变轨迹,我们至少可从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性的结论:
第一,日本丝织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赶超先进的正面经验。在东海丝路的东端,孤悬于万里波涛中、丝织技术几乎零起点的“弹丸岛国”日本,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学习追赶和创新求变。当丝绸作为奢侈品仅限于上流社会而市场狭小之时,日本就一边从中国进口丝绸,一边虚心学习丝织技术。当丝绸由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普及为百姓的日常用品而市场迅速扩大之时,日本就通过虚心学习和贪婪引进中国的先进丝织技术,制造出优质的国产丝绸。当大量进口中国生丝造成白银外流而危及国本之时,日本便果断通过发展本国的蚕丝业以遏制白银继续外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然一直根据需要通过东海丝路进口生丝、丝绸和技术,但始终把重点放在丝织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上,未曾中断,从而为其本国丝织业弯道超车即追赶先进提供了不竭动力。结果,日本最终摆脱了对中国丝绸制品和丝织技术的依赖,构建起自己完整的“植桑”—“养蚕”—“缫丝”—“丝织”生产链。
第二,中国丝织业的演变轨迹提供了由盛转衰的反面教训。与日本丝织业“向上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东海丝路的西端,本来从秦汉时期起就拥有先进丝织技术的中国,由于既不与时俱进改进,提高自己的生丝及丝绸生产技术,又缺乏掌握中日贸易主导权的竞争观念即商战意识,导致中国丝织业呈现“向下走衰”的演变态势。因此,一旦丧失丝织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丝织品最终被挤出日本市场也就只是时间问题,在劫难逃。
第三,中日丝绸贸易史留下了双边贸易值得总结和汲取的一大历史教训。尤其是在中日丝银贸易中,中国有生丝、缺白银,日本有白银、缺生丝,这一互补性极强的双边贸易却因大明朝廷的一纸“禁海令”和德川幕府的“贞享令”等自我削弱,乃至阻断了中日贸易往来,致使本应由中日两国独享的贸易利润多被葡萄牙、荷兰等第三国商人席卷而去。
第四,中日丝绸贸易史还留下了国际贸易护航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中日丝银贸易中,葡萄牙商船与荷兰商船均自我配备武力组成武装商队进行贸易,日本的“朱印船”也有幕府提供的武装力量随船护航经商。而唯独中国商船,不但缺乏武装力量保护,且还需要在内躲避官府追查,在外受葡萄牙与荷兰武装商队欺压,只能在内外挤压的夹缝中求利,其艰难性和危险性可想而知,值得后人反思和铭记。
第五,积极进取的日本赶超墨守成规的中国的过程就是中日丝绸贸易乃至东海丝路兴衰的过程。纵观中日丝绸贸易的全过程不难发现,中国始终扮演了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老师”角色,而日本一直在扮演一个与时俱进、勤奋好学、锐意进取的“学生”角色,以致千余年来形成单向东传而非双向互学、共同进步的交流格局。其结果必然是,墨守成规的“老师”迟早被好学上进的“学生”赶超。日本能在明治维新后尤其是在20世纪初从中国手中夺走世界第一生丝出口大国的地位,当与日本在千余年来通过持续学习和不懈努力夯实技术基础密不可分。今天,中国正大踏步走在重振海上丝路的征程上,历史上东海丝路尤其是中国丝织业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值得汲取,而日本丝织业持之以恒赶超先进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借鉴。可见,东海丝路尤其中日丝绸贸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应是东方外交史领域不宜忽视的重要课题。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in the Field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SUN Lixiang, LIU Yan
Abstrac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The East China Sea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is the core trade in the East China Sea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especially from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Japanese silk weaving industry, this paper answers why the East China Sea Silk Road, which once brought huge trade dividends to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changed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d even disappeared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 single export of Chinas silk weav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o the East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Japans silk weaving industry”, “the ‘Sea Ban policy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atch-up of Japans silk weav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ilk-silver trade and the rapid catch-up of Japans silk indust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especiall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Japans silk weaving industry from scratch and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summarizes five enlightening conclusion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East China Sea silk road; Oriental diplomac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責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