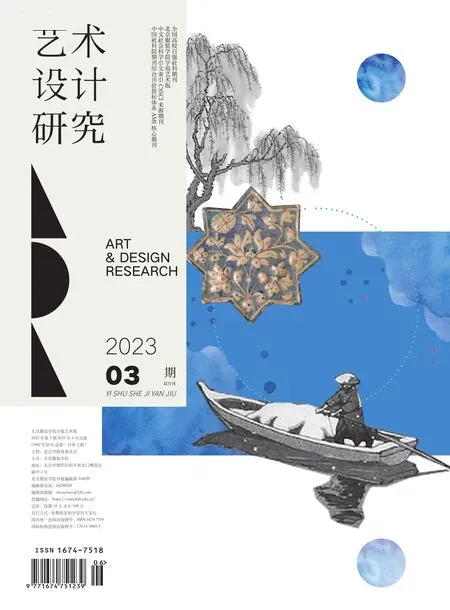《绘因果经》与插图佛经溯源
刘 晨
文字与图像的伴生及其关系是各文明中常需涉及讨论的问题。就佛教文本而言,现存最早的插图佛经乃是日本奈良时代(710 ~794)的《绘过去现在因果经》(本文简称《绘因果经》,图1)。尽管中日学界对于这件插图佛经应该是受到中国祖本影响而绘制的这一观点都广泛接受,但由于相关材料的缺乏,目前为止对其祖本和同期及更早插图佛经的面貌仍缺乏讨论。本文将从《绘因果经》入手,通过其图像细节、视觉叙事模式和上图下文形式与中国现存壁画和卷轴画实例的比对,来确定该插图佛经之中国祖本的具体时间。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从中印两国的图文传统及其书画材质入手,讨论插图佛经可能具有与纯文本佛经不同的渊源。

图1:《绘过去现在因果经》(局部),奈良国立博物馆,8 世纪,纸本着色,26.4 厘米 x 115.9 厘米,乘海旧藏
一、《绘因果经》及其中国祖本
《过去现在因果经》是梵文佛经LalitavistaraSutra(以下简称《因果经》)的至少第五个中译本,南朝宋时,由天竺入华僧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394 ~468)译成(《大正藏》编号为189)。①该经讲述了释迦牟尼从兜率天降世到成佛后于鹿野苑第一次说法的前半生,涵盖了一般称为“佛传”的前一多半佛陀生平事迹。《因果经》本为四卷,插图本将每卷扩充为上下两卷,共绘制抄写成八卷本的《绘因果经》。不过,目前只剩下与其中四卷相关的部分(仅一本为全本,其余为残本),分藏于日本的数家机构:上品莲台寺、奈良国立博物馆、醍醐寺、出光美术馆、旧益田家及东京艺术大学。由于现存残卷各段在绘画与书写风格、技巧等方面存在差异,且醍醐寺本与出光美术馆本所绘制书写的是同一部分经文,即均为绘卷五、经文卷三讲说佛陀修行至得道的经历,可以推知这些现存片段至少应为两套《绘因果经》的残卷。不过,通观这些绘卷片段,其在各个方面仍然有着极高的一致性。从材质和装裱上看,它们均为纸本着色,纸质类于唐代流行的“硬黄纸”,高度在26.5 厘米左右。②其在接纸抄经完成以后,以中国特有的手卷形制装成八卷。这些插图佛经残卷几乎是讨论日本美术史时必然提及的作品,数十年来引起了日本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的较高关注。专业论文往往聚焦个别残本,通过对其中图像细节、书法特色等展开分析讨论,尤其是与中国同期及早期同类作品的对比,来确定作品的绘制时间。近年来,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可见于坪井みどり的《絵因果経の研究》。③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绘制抄写于公元8 世纪中叶的奈良本《绘因果经》乃是依据中国的更早祖本绘制而成,尽管后者早已不存。
通观《绘因果经》上的绘画,均以中国传统的线描来造型,且赋色较为鲜艳,主要使用朱砂与石绿、石青等对比度较大的颜色。其中部分图像细节呈现出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绘画一脉相承的关系。如奈良国立博物馆本最后一个场景“太子请求国王恩准其出家修行”,其对应的下部文字为:
尔时太子年廿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时。而便往至于父王所,威仪庠序,犹如帝释往诣梵天,傍臣见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来大王所。(王)闻此言,忧喜交集。太子既至,头面作礼;尔时父王即便抱之,而敕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爱集会,必有别离,唯愿听我出家学道。一切众生,爱别离苦,皆使解脱。愿必……
在相应画面中,我们看到净饭王身着蓝袍端坐于矮榻之上,面对着跪伏在他面前的太子抬起右手,似令其起而就坐之意(图2)。

图2:《绘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请求”
此部分描绘与传为东晋顾恺之(约348 ~409)所作《洛神赋图》中的一个局部非常相似。《洛神赋图》表现的是曹植所作《洛神赋》的内容,描绘了作为男主人公的“余”或曹植在返回自己属地的途中,与洛水女神“神会”并互生情愫,但却因“人神之道殊”的疑虑而失去洛神的经过。其中,表现洛神离去之后,男主人公“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的部分,与上述《绘因果经》局部极为相似:二者以几乎相同角度的斜线和同样近边短、远边长的台面绘制出与人物比例相近的坐榻;且主人公以相似的姿态、右手上举,面左坐于榻正中;近旁侍者顾盼的姿态和身后侍者所持的伞盖都甚为相近;其画面结构均为前景有山石、背景有树木,从而框定出人物活动的户外空间④(图3、图4)。人物与树木、山石的比例关系也很相近,正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述及此一时期绘画风格时所说的“人大于山”的面貌。《洛神赋图》现存至少九个相似版本,陈葆真通过比对考查,认为其共同的祖本约创作于6 世纪,很可能是在560 ~580 年间。⑤也就是说,《绘因果经》的中国祖本应该与创作于6 世纪晚期的《洛神赋图》祖本这类作品大致同时或稍晚。

图3:《洛神赋图》局部,约12 世纪初期摹自6 世纪的祖本,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4:《绘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请求”局部
在视觉叙事模式方面,《绘因果经》上部的绘画是对应着下部的佛传故事、以多幅场景顺序表现的。例如,奈良国立博物馆本仅存的62 个竖行文字,上部就对应描绘了从北门而出的悉达多太子问答比丘、太子骑马归城、优陀夷向国王禀报太子与比丘会面之事、太子与太子妃观赏艺伎奏乐歌舞、太子请求国王恩准其出家修行等五个情节。这些情节均以相似的树木和从前往后斜向缩进的山坡等图像自然地间隔开,再在前景中以小块山石或灌木将每幅场景框定为较为独立的空间,从而形成多幅连环叙事的表现模式。这种表现模式正与南北朝时期绘画中所见的视觉叙事模式相类。⑥除了《洛神赋图》,在敦煌的多幅壁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连环”的模式。⑦例如,绘制于北魏中晚期的第257 窟西壁《九色鹿王本生故事画》,以及绘制于北周时期的第428 窟东壁南侧《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5)本生故事画等。⑧以树木作为场景间隔的模式可见于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至唐代甚至发展成为一人一树、一般被称为“树下高士”或“树下美人”的模式。但是这种以小山坡和树木一起作为场景间隔的叙事模式,目前却只在南北朝时期的叙事性画作中可以见到。⑨事实上,按照经文表述,奈良国立博物馆藏残卷部分所描绘五个情节的后三个——优陀夷向国王禀报太子与比丘会面之事、太子与太子妃观赏艺伎奏乐歌舞和太子请求国王恩准其出家修行——应该为发生在净饭王宫殿中的室内情节。然而在《绘因果经》中,这三个画面呈现的仍然是与其他场景一致的、由树木山石环绕的户外环境。显然,这种以树木山石分割场景并组成连环叙事的表现模式作为《绘因果经》的基本构图,应为时人所自然运用和接受,这对他们来说并无任何不妥。

图5:莫高窟第428 窟《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壁画
从形式上来看,《绘因果经》均为纸张上半部分绘图、下半部分竖行抄经,即所谓的“上图下文”。在图文并置的作品中,图与文可存在多种位置关系。⑩例如,纪年为唐咸通九年(868)的木版印本《金刚经》,是在扉页配上一幅图像的“前图后文”形式。⑪此外,明清时期各类宗教或世俗题材印本中还流行一种多幅式全页插图,形成文图穿插的形式。不过,从《绘因果经》及其同时和稍后的现存佛经写本来看,似乎“上图下文”是中国早期插图写本中图文关系的主要形式。事实上,现存的可能为唐代的插图写本佛经——浙江博物馆藏《佛说阿弥陀经》写本残片和敦煌遗书p.2683《瑞应图》写本等——也具有比例关系非常类似的上图下文形式(图6)。⑫唐及唐以前这类带插图的佛经写本,虽然尚未在我国发现,但从敦煌藏经洞中数件10 世纪的写本佛经来看,似乎也都是沿用这种上图下文的范式。例如,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伯希和敦煌遗书p.4513),就是这一时期一件典型的上图下文的写本插图佛经(图7)。⑬这种上图下文的形式便于观者同时兼顾图文,其用途可能为其拥有者诵经之用,尤其是对于文字不熟悉的妇孺或对图画感兴趣的读者。这与敦煌遗书P.4524 那种正反面分别为图与文的长卷不同,后者经梅维恒(Victor Mair)等前辈学者讨论,很可能是用于某种佛经展演的活动之中。⑭

图6:《佛说阿弥陀经》写本残片

图7:敦煌遗书 p.4513《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局部,2728 厘米×674.8 厘米,10 世纪,法国国家图书馆
由以上讨论可见,图像细节及视觉叙事模式都支持《绘因果经》更接近南北朝时期艺术形式的结论。不过,其人物衣饰已从褒衣博带和笼冠、梁冠变成了唐代流行的圆领窄袖袍和软脚幞头,经文抄写的体例等也体现出鲜明的唐代特色。唐代佛经传抄活动保持了相当活跃的状态。就官方抄经活动而言,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机构和相当成熟的流程。在写本的行文格式上,严格以“乌丝界栏”规范,在纯文字本标准佛经写本中,为一竖行抄写17 个字。同时由于有严格的审校管控体系,书写中甚少出现错漏的情况。《绘因果经》中下部的经文正是以唐代流行的抄经“正书”(即正楷)写出,并以淡墨勾画出“乌丝界栏”规范;因在上半部插入了绘图,通行的每竖行抄写17 个字就折减为八个字,其他抄写规范不变,除少量缺字、红笔更正和注解之外,行文规范合度,几无错漏。⑮也就是说,《绘因果经》乃是基于南北朝后期约公元6 世纪的中国祖本,并以8 世纪衣饰和抄经习惯绘制而成的。
二、印度的早期佛经抄写及插图写本状况
《绘因果经》的图像细节、多幅连环叙事模式及其“上图下文”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插图佛经的可能面貌。如若追溯插图佛经的渊源,不免会让人想到其是否也与一般文字佛经一样,是从印度传来的呢?早在佛陀生活的时代,印度人就已将贝叶(即贝多罗树叶Tāla-pattra,一种棕榈科热带植物)作为书写材料。⑯例如《佛本行集经》中讲到,佛陀为了证明自己出家前所娶妻子耶输陀罗(Yaśodharā)及二人所生儿子罗睺罗(Rāhula)的身份,经毘沙门天王用多罗叶写下了文字证明:“于时而有毘沙门天去佛不远,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陀罗叶,往诣佛所。尔时,世尊手自作书。”⑰尽管已有贝叶可作书写,但是佛经在印度佛教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依然主要是以口述的方式流传,并未有文本传世。直至公元1 世纪贵霜王朝(约公元1 ~4世纪)时期,在迦腻色伽(Kanishka,约127 ~150 年在位)王主持下,才对佛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结集,并组织人员以梵文和巴利文等进行抄写和传播。⑱因为贝叶是如此广泛地应用于早期佛经抄写中,因而佛经常常又被称为“贝叶经”。此外,古代印度也有使用树皮尤其是桦树皮作为书写材料的。例如,于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发掘出土的著名的“吉尔吉特写本”(Gilgit Manuscripts),就是书写在桦树皮上的。⑲
20 世纪以来,陆续发掘出一些保存状况较好的早期印度佛经写本实物。不过,这些早期佛经写本均为纯文字无插图本。例如挪威斯奎因收藏(The Schyen Collection)的从公元2 世纪至公元6 世纪的数件写本残页,均只见文字、不见图像(图8)。此外,目前被认为是5 到6 世纪制作的“吉尔吉特写本”,1931 年于一座可能是坍塌的佛塔之下的木盒中被发现,因而保存状况良好。这套写本有三对绘有图像的木质封面、封底,被认为是具有“保护功能”和作为“还原图像”来绘制的,并非与写本中的内容有对应关系。该写本约有423 片,均抄写于较大的桦树皮上,尺寸为12 厘米× 66 厘米,由于字体偏小,因此每一片能抄录很多文字。写本中的400 余片内页均布满文字,仅见以较大的圆圈标识出每段律(vinaya)的结束,例如今编号为f.53a 的一页,右下有两个较大的圆圈占去了大约三行的位置(图9)。⑳除此之外,早期写本中并未见其他图像。㉑

图8:《大众部——说出世部经》,贝叶梵文,印度,4 世纪

图9:吉尔吉特写本,编号f.53a,5 ~6 世纪,桦树皮
真正带有图像的写本大约在公元1000 年左右才在印度出现。㉒不过这些图像多为与文本不甚相关的各种神祇的小像(miniature),与吉尔吉特写本的封面、封底图像一样,其目的旨在强化写本的神性并对其施以保护。㉓图文相关的插图写本在印度出现得更晚,现存最早的实例是定为公元1288 年绘制抄写的、带有23 幅小插图的Subahukatha——一部关于耆那教神祇Parsvanatha 的故事。㉔其插图所以晚于文字如此之多,主要是受制于贝叶较为狭窄的幅度。㉕上文所举斯奎因收藏的数件早期贝叶经,每页高度仅在五厘米以内,连书写文字都相当局促,更遑论插图了。
三、中国的图文并茂传统
可以看到,插图佛经显然并非渊源自印度的传统。㉖相较而言,我国却有着极其悠久的图文并茂传统。继甲骨与金石这两种使用和阅读范围都较为有限的书写载体之后,中国出现了简和帛这两种更为便利且易于运输的书写媒材。文献记载,简的最早使用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帛用于书写则大致在春秋;而据考古出土文物来看,竹木简及缣帛作为书写媒材在战国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㉗缣帛较为宽裕的幅面,为图文并置提供了可能。中国现存图文并置最早的实例,是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的帛书《四时令》(图10)。㉘东汉末年纸张已经基本取代简牍,成为书籍抄写的主要媒材。㉙这一取代过程在西晋(266 ~316)时期最终得以完成。㉚仰赖纸张的流行,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图书”。例如《隋书·经籍志》提到“梁有《毛诗图》三卷、《毛诗孔子经图》十二卷,《毛诗古圣贤图》二卷,亡。”㉛基于这样的图文传统,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逐渐兴盛,为佛经配插图这一做法也就应运而生。在图像和形式上与《绘因果经》相近的插图佛经,应该流行于南北朝至唐代之间。这些抄本可能也较大地影响到了10 世纪以降的写本和刻本佛经。

图10:子弹库出土帛书《四时令》摹本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将奈良古本《绘因果经》中的个别图像细节、连续视觉叙事模式和上图下文形式与中国实例的比对,判断其祖本大致出现于中国南北朝时期。通过爬梳印度写本佛经及带有图像的文本发展史,本文认为《绘因果经》所代表的南北朝和唐代插图佛经,并非如纯文字佛经一样传自印度,而是基于中国悠久的图文并置传统而发展出来的。
注释:
① 在该本译出前已有的至少四部同经异译中文本分别为: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竺法护译《普曜经》和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参见Richard B.Mather,”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Buddhist Life: Wang Jung's (468-93) "Songs of Religious Joy" (Fa-le tz'u),Journalofthe 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07,No.1 (Jan.- Mar.,1987),pp.31-32.
② 关于唐代盛行的抄经用硬黄纸的制作和使用等,参见刘仁庆:《论硬黄纸——古纸研究之七》,《纸和造纸》,2011 年第4 期,第65-69 页。
③ 坪井みどり:《絵因果経の研究》,东京:山川出版社,2004 年。
④ 关于这一时期的伞扇研究,参见刘未:《魏晋南北朝图像资料中的伞扇仪仗》,《东南文化》,2005 年第3 期,第68-76 页。
⑤ 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35 页。
⑥ 相关研究可见于Julia Murray,MirrorofMorality:ChineseNarrativeIllustrationandConfucian Ideology,Honolulu,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p.38-49。
⑦ 不过,针对这些不同的连环方式,陈葆真更将它们区分为“连圈式”“半连圈式”和“残圈式”等类型。参见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02-111 页。
⑧ 莫高窟第290 窟窟顶人字坡东、西两坡的北周《佛传故事画》也属连环的多场景叙事画,但其87 个场景主要是以建筑屋檐的斜线分隔,中间绘以树木。虽然同为佛传故事画,但《绘因果经》所存残卷部分有些290 窟未画出,例如本文讨论的“太子请愿”场景,同时,《绘因果经》与290 窟均有绘制的部分相似度不算高。因此,这两本看来应出自不同祖本。
⑨ 关于树木作为场景分隔的全球艺术史考察,参见Zhang Hanmo,“Searching for the Origin of an Art Motif: The Tree as a Universal Seperating Device in Early Indian,Iranian,Etruscan and Chinese Art”,Xiao Li edit,StudiesontheHistoryandCultureAlongthe ContinentalSilkRoad,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2020,pp.121-176.
⑩ 例如,朱凤玉将敦煌遗书中出现的图文关系分为上图下文、左图右文及正图背文这三种。朱凤玉:《论敦煌文献叙事图文结合之形式与功能》,见《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556-573 页。
⑪ 这些“前图”现通常被称为扉画,相关研究较多。例如,张建宇:《“中唐至北宋〈金刚经〉扉画说法图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 期,第24-32 页。
⑫ 关于《佛说阿弥陀经》的更多讨论,参见邱忠鸣:《“浙藏插图本〈佛说阿弥陀经〉写本年代初考——兼论传世写本的真伪与年代问题”》,《敦煌学辑刊》,2014 年第3 期,第104-118 页;关于p.2683 的近期讨论,参见陈爽:《“‘秘画珍图’——敦煌绘本长卷P.2683〈瑞应图〉再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 年第9 期,第77-94 页。
⑬ 图片源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官网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8641g/f1.item.zoom,2023 年3 月15 日获得。
⑭ 参见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上海:百家出版社,2011 年。(英文原作Vcitor Mair,Paintingand Performance:ChinesePictureRecitationandIts IndianGenesis,Univ of Hawaii Press,1997.)
⑮ 关于奈良《绘过去现在因果经》的颜色颜料问题,可参阅秋山光和:《繪因果經、紫式部日記繪卷、金棺出現圖のx 線による》,《美術研究》第168 号,1953 年,第131-138 页。
⑯ 梵文中Tāla 多罗是树名,pattra 贝多是叶的意思。
⑰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 册第190 号(T03n 0190),《佛本行集经》卷51,[0888c25]。
⑱ 关于印度佛经文本早期状况,参见李学竹《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载于《中国藏学》,2010 年第1 期,第53-62 页。
⑲ Jeremiah P.Losty,TheArtoftheBookinIndia(《印度书籍艺术》),London: British Library,1982,p.29.
⑳ 佛教训诫通常分为经、律和论三种。
㉑ 关于这些彩绘木质封面及其功能的讨论,详见德波拉·金伯格·萨特撰,贾玉平译《吉尔吉特写本封面书本崇拜》,《藏学学刊》,2009年刊,第283-293 页。
㉒ Jeremiah P.Losty,TheArtoftheBookin India,London: British Library,1982,p.24.
㉓ Sagarmal Jain,EncyclopaediaofJainaStudies Vol01JainaArtandArchitecture,Varanasi HO: Parshwanath Vidyapeeth,2010,p.377.
㉔ 同上,第22 页。
㉕ 同上,第20 页。
㉖ 中亚与东南亚的佛经插图出现的时间更晚,因而未在此文中论及。
㉗ 参见马静静:《简牍:作为媒介的历史属性及其功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 年第3 期,第69-73 页;刘蔷:《帛书述略》,《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 年第5 期,第77-80 页。
㉘ 本文以李零命名称之为《四时令》,参见李零:《子弹库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
㉙ 关于印度和中亚早期写经的情况及纸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参见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77-182 页。
㉚ 参见陈静:《西晋通行纸诏考》,《齐鲁学刊》,1999 年第1 期,第126-128 页;陈静:《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 期,第62-65 页。
㉛ 笔者不赞成一些学者将这些“图”都理解为图文并存的插图书籍,即这些“图”完全可能是图解文本的单行图绘。例如,《中国古代插图史》就将这些“图”不加区分地归为图文并茂的插图写本,参见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