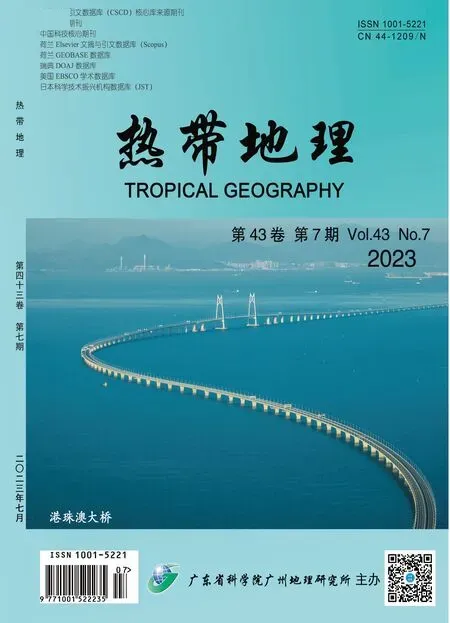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
——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陈洁莹,刘云刚
(1.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2.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城镇化是农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或就地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可以划分为传统和新型2个阶段。传统城镇化过度强调城市化率的提高,一味强调城镇用地的扩张及城镇居民数量的增长,忽视了城市内各主体间生活品质的提升(杨环,2020)。而2014 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及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Su et al., 2020),强调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也需积极帮助更多人均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在身份上从农民转变为市民(齐勇,2019)。
城中村是被城市景观包围的原有农村聚落(闫小培 等,2004),其改造过程符合新型城镇化路径。在外部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城中村的改造过程需首先实现居住空间的“村转居”、接着再逐步推动居民身份的“市民化”(陶伟 等,2015)。城中村居住空间的改造使得村民们面临户口、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乡土特色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改变,但部分村民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行为习惯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仍未达到市民水平(刘亦舒,2018),存在经济地位较低、身份认同模糊、再就业困难、思想文化素质偏低等市民化滞后问题(刘晔 等,2012;黄文炜 等,2015;王娟,2015)。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进程缓慢,容易激发村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潘卓林等,2020);年轻村民的不就业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形成城镇发展新格局的重点任务(阳盼盼,2020),有利于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改善目前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高善春,2019)。
杨箕村具有广州市村落变迁的典型特征,能反映广州市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多数典型问题,且互联网、教育的日益普及和城中村改造机制的日益成熟,给杨箕村村民市民化带来更多机遇,村民的市民化特点与较早回迁的城中村(如猎德村)相比会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着眼于更长的时间尺度,结合杨箕村的变迁历史,从身份、经济、文化市民化3个角度对村民的市民化过程和结果进行剖析,着重探讨杨箕村的变迁和村民的市民化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城中村村民存在的市民化滞后问题,进而对城中村村民身份转变现象进行深层次探讨。以期为优化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进程提供建议和参考,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 综述
市民化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素质、价值观点等方面逐步向城市市民转变,也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获得与城市市民均等权利的过程(宋蔚 等,2020;丁百仁,2020)。对于市民化的研究,国外倾向于采用文化融合、社会认同来分析移民的迁移和流动(罗利佳等,2020),认为社会资本、流入地的政策、社会网络等会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Goldlust et al.,1974)。发达国家的市民化和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而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壁垒,城市市民和农民存在身份差距,市民化进程滞后于城市化进程(Solinger, 1999)。目前国内对市民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 个方面:1)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为经济、制度、社会、政策、心理等多个方面,或者分解为市民化意愿(王玉君,2013;刘于琪 等,2014;罗其友 等,2015)、市民化能力(陈俊峰等,2012;李练军 等,2017)、外部环境3个层面,构建市民化进程测算的指标体系(李亮 等,2018),得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测算结果,对研究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张建丽等,2011;刘松林 等,2014)。2)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王桂新 等,2010;申兵,2012),包括公共成本、个人成本和企业成本(刘锐 等,2014;李小敏 等,2016)。3)针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黄锟,2011),如个体资本、心理融合、就业情况、公共服务、户籍制度等(王成利,2020)。另外,已有对市民化的研究也探索出一些新的理论视角,如地方依恋理论(邓秀勤 等,2015;谷玉良,2016)、空间正义的理论(王瑞雪,2021)、场域理论(唐云锋,2019)。
目前市民化研究尺度以宏观角度为主,微观尺度的研究较少。宏观角度包括全国(戚伟 等,2016;朱纪广 等,2020;王凯 等,2020)、省域(李练军,2017)、市域(林赛南 等,2019;王慧等,2020)、县域(刘思辰 等,2020)等尺度。微观角度有市民化的代际影响(刘思辰 等,2020)、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佟伟铭 等,2019)、外部城镇化进程与内部居民市民化的现状与困境(魏后凯 等,2013)等。另外,市民化的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乡-城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梁梦鸽 等,2014;应婉云 等,2015),这部分群体的数量庞大,是市民化的首要对象(罗峰 等,2020)。随着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的大范围开展,学术界也开始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城中村改造后失地村民、城郊村民的市民化问题(叶裕民,2015),但相关研究仍相对较少。城郊失地农民和城中村农民2类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大多数拥有城市户口,受到城市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与城市市民没有明显隔阂,但有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还保留着农民的特征,如自我满足的小农意识等(甘丹丽,2019)。
市民化具体的研究维度有生产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4个层面的转变(解丽霞,2019),也有经济融入、市民权获取、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的逐步推进过程(张海娜 等,2021)。另外从时空2方面进行解构,市民化的空间转换视角可以归结为“生存空间转换、社会身份转换、生活意义转换及生存境界转换”4 个层次,市民化的时间演进角度可以划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阶段、农民工群体形成阶段、“民工荒”与农民工回流阶段、农民工全面市民化”5 个阶段(王孝莹 等,2020)。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应包括身份、经济和文化市民化3个方面。其中,身份市民化指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后以市民身份这一社会角色参与到城市治理中;经济市民化指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从农业职业向非农职业转变,从而提高收入、达到城市市民消费水平的过程;文化市民化指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思想理念、生活习惯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
市民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王桂新 等,2010),市民化的过程是农业转移人口经历从农村退出、进入城市、城市融合3 个环节(李练军 等,2017),逐步在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方面转变为市民(王孝莹 等,2020);市民化的结果研究是测度现有条件下区域内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魏后凯 等,2013)。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不仅受到外部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也有村内自身的发展机遇,村民个体能动性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问题更为复杂。当前研究大多是对城中村改造村民市民化进程现状、困境及原因的分析。如刘晔等(2012)对于猎德村村民市民化的研究认为,村民只是被动接受改造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没有对自身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做出相应调整。较少研究会通过被研究者自身的经历来再现城中村的变迁。因此,本文着眼于将村民命运与外部城镇化进行关联,希冀可以深入解构城市村落变迁历程对村民市民化的影响。
2 案例地及研究方法
广州市越秀区杨箕村位于珠三角冲积平原,总面积约11.51 hm²,东面为广州大道,南面为东兴北路,北面是中山一路,杨箕涌在西面绕村而过,现村内有泰兴直街、雄镇大街、杨箕大街等街道(图1)。杨箕村毗邻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珠江新城,区域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城中村和外来人口集中地,村内主要有李、姚、秦、梁四大姓氏(陈俊峰 等,2012)。

图1 杨箕村区位Fig.1 Location of the Yangji Village
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访谈以及新闻、网络文章。由于杨箕村租户及住在杨箕周围但常到杨箕的居民(下称“其他人群体”)对杨箕村民的市民化有间接影响,因此,除了村民,也对这2类群体开展调研。问卷调研时间为2021 年1—7 月,调查内容有个人基本情况、自身对杨箕村改造前后的感受对比、户口、身份认同、价值理念等,重在了解杨箕村群体的市民化结果。访谈主要了解杨箕变迁过程中村民个体扮演的角色、对杨箕村改造的看法,重在了解杨箕村村民群体的市民化过程,同时也对位于广州中心地区但尚未改造的城中村之一——程介村选取村民进行访谈,以此对城中村市民化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把握。最终共获取有效问卷132 份、半结构访谈14 份,还有部分问卷填写者的随机访谈。具体访谈对象及属性如表1所示,问卷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则如表2所示,受调查者中村民以60岁以上、已婚、且在广州超过10年并住在杨箕村的人群为主;租户和其他人群体则以20~40岁、且在广州超过10年的人群为主。

表1 杨箕村村民市民化重点访谈对象基本特征及访谈时长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iew duration of key interviewees of villagers' citizenization in the Yangji Village

表2 杨箕村问卷受调查者的基本特征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to the questionnaire in the Yangji Village %
3 杨箕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分析
3.1 村落时代的杨箕村
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从事生产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的村落是一个靠血缘维系的自治社会。杨箕村发迹于北宋天禧三年(1020 年),从宋仁宗嘉祐年间开始(1034 年),姚李秦梁四大姓氏移民从陕西、河南、江西、闽浦等地南迁到杨箕村。经过九百多年的发展,直到解放前,杨箕村的范围东至石牌、林和交界处,北至现沙河街、体院、动物园一带,西至达道路口,南至珠江河畔,拥有190.67 hm2良田①https://wenwen.sogou.com/z/q827867243.htm。当时杨箕村是广州主要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但政府统购统销政策导致村民月工资仅为3元多,远低于工人月工资的30多元,因此杨箕村村民直至改革开放前一直相对贫困。综上可知,村落时代的杨箕村村民是典型的农民身份,受制于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3.2 城中村时代的杨箕村
改革开放给杨箕村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村落也在慢慢终结。从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到1987年创办鞋厂、酒楼等企业及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杨箕村固定资产增至1亿元。另外,20 世纪80 年代,广州要发展五羊新城,杨箕村五羊新城一带的7个生产队所属土地被东华实业公司等单位所征收。政府征地的同时,也安排不少村民转为城市户口以及提供城镇就业指标,如广州钢瓶五金厂等,这批原来拥有五羊新城土地的农民(即7个生产队)也因此转为城镇户口,且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作。另外7个生产队的村民土地尚存,继续从事农业活动。
“当时45岁以上的男村民和40岁以上的女村民可以获得政府补助6 000 元而不用进厂,大概300人,其他年轻人必须做工人,田地都没了,村民也没有别的选择。”——《杨箕 广州城中村风情画》采访村民姚长杰(文珍,2011)
村落变迁是在工业化、全球化等多种现代性因素对传统村落的侵袭下,村民逐渐脱离传统农村生活秩序的过程。20 世纪90 年代,广州政府因发展珠江新城而对杨箕村另外7个生产队进行征地,至1995 年,杨箕村155 hm2耕地全部被征完,村内保留的约8.33 hm2自留地被村民用于修建出租屋出租给外来人员,杨箕村逐渐发展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集聚地,呈现非城非乡的复杂空间形态,而长期的违规加建也使得杨箕村建筑质量、采光条件较差。与其他城中村类似,杨箕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集体收益分红以及个人劳动收入、房屋出租3方面。此时村民的收入水平相比五六十年代有了大幅提高,以2008年为例,全年村民个人年均净收入为3.16万元,高于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25万元(陈易,2019)。
综上可知,第二阶段的杨箕村先出现村民主动“非农化”过程,而后村民在“城市化”的客观浪潮中被动地不再从事农业活动。也即在改革开放到90年代,农业活动的薄利驱动大量村民开始从事工业生产活动,走向非农产业;之后在90年代政府规划建设珠江新城的过程中,杨箕村由于外部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带来内生空间的重构,杨箕村因政府的征地而变得无地,且广州的城市化浪潮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迁移,杨箕村民加盖楼房出租。该阶段的村民大多住进小平楼,户籍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职业从务农转向务工,外出务工过程中与城市市民的接触机会也相应增多,加上与外来庞杂的租户群体的接触,村民的人际交往网络在悄然发生变化,村民的经济收入、思想观念等方面逐渐向市民身份转变。
3.3 改造后的杨箕村
广州“三旧”改造加快了杨箕村用地功能和空间结构的重构,实现土地价值的释放。2009年,杨箕村开始撤村建居,其改造沿用猎德“拆一赔一”的改造模式,并在2016年5月实现回迁,回迁前后的杨箕村如图2所示。结合实地调研可知,杨箕村改造后,村民的生活空间变为现代化小区,回迁房中大约1/3 村民自己居住,剩下2/3 约2 600 户由租客居住,租金相比城中村时代也有了大幅提高。一些保留农村户口的村民还有集体分红,年轻村民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状况良好。整体上,杨箕村的改造提升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推动了杨箕村村民的经济市民化。在现代化的核心环境下,改造后的杨箕村还保留着祠堂供村民们活动,并保留着端午节划龙舟等传统民俗,但村民在接触与高素质及高消费水平外来人员(如在珠江新城上班的白领阶层)及通过网络媒体感知现代化思想理念的过程中,促进自身观念的现代化,整体上,杨箕村的改造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杨箕村村民的文化市民化。

图2 改造前(a)和改造后(b)的杨箕村Fig.2 The Yangji Village before (a) and after (b) reconstruction
4 杨箕村居民市民化结果分析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分割,从制度设计上阻碍了农民向城市流动,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过程;改革开放给村落变迁带来大量发展契机,都市文明的侵袭推动村民不断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多维互动中,杨箕村民不断适应城市生活,实现身份、经济、文化市民化。除此以外,村民也呈现社会融合度高、适应新环境速度快,在杨箕社区长期居留意愿强烈的特点,说明总体上杨箕村改造对于推动村民市民化进程是有利的,杨箕村受调查者身份、经济、文化市民化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杨箕村居民市民化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citizeniza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ji Village %
4.1 身份市民化结果
从户籍看,目前杨箕村的村民以城市户籍为主(65%),但仅有约36%的村民、33%的租户和其他人群体倾向城市户口,反映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户口的吸引力在逐步增强。通过访谈得知,杨箕村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对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差异,农村户口能有集体分红的红利,因此村民对农民户口的倾向性明显。事实上,当年政府征地时转为城市户口的那部分村民,由于从事非农职业,且与城市市民有较多接触,他们整体上的市民化程度比仍为农村户口的村民要好,思想观念上更为先进。
“当然农村户口好,农村有地嘛,我们没有地了,要有地才好,有地就有得发展了。”(60多岁杨箕村民)
“按照杨箕这样,当然是农村户口好,农村户口经济方面挺好,有红分、有屋租,城市户口只能靠退休金那份。……教育方面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没啥区别,(读书)都是靠自己。”(60 多岁杨箕村民)
从身份认同情况看,分别有约41%、9%、27%的村民认为自己是市民、准市民、农民身份;其余的受访村民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模糊。由此可见,村民对自身的市民身份认同度不高。改革开放后杨箕村民顺应外部城镇化变迁带来的机遇,逐渐走出村落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并出租房屋给外来人员,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中,老一辈村民认为自身的市民身份和村民身份的界限在慢慢淡化,而年轻村民会更认可自己是市民身份。另外,针对尚未改造的程介村村民的访谈可知,老一辈的程介村村民更认可自己是农民身份,有作为农民的优越感,且在思想格局上相对落后,主观上不愿意改变过去的传统看法。
“我没有什么村民的概念,不会说我是这个村的我就怎样,没那么传统吧,就可能老一辈他们就还会觉得自己是村民。”(20多岁杨箕村民)
“大部分人改造后还是同化啦(跟城市人一样),是市民还是村民,现在这个概念都很淡化了。”(60多岁杨箕村民)
“(身份认同模糊)是农民吧,但是又没田分;是城市人吧,但是又没工作,给你自己来说,你觉得是怎样嘞。”(50多岁杨箕村民)
“没有(自己又像农民,又像市民的)困惑的,像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农民,很有优越感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井底之蛙吧,就是看事情还是太落后了,还不懂得外面现在世界变成怎么样了,就好像传统那种生男生女思想还是有。”(30多岁程介村民)
从改造对受调研者的社会地位影响看,有44%的村民、22%的租户、31%的其他人群体表示杨箕社区改造能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中部分受调查者认为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由此可知,杨箕村改造对村民的社会状况的影响最为显著。但年轻村民群体认为城中村改造对自身社会地位影响不大,提高社会地位需依靠自身奋斗。
“这里的环境的对我自身的社会地位没什么影响,这个还是靠自身的,不是说你住在那个杨箕村就会比别人的社会地位高。”(20多岁杨箕村民)
4.2 经济市民化结果
从月工资水平看,仅有22%的受调查者月工资在6千元以下,剩余55%的受调查者月工资水平在1 万元以上,说明受调查者总体工资水平较高。有48%的村民、37%的租户、32%的其他人群体认为杨箕村改造能提升自身的经济状况,有一位村民表示目前月收入比改造前增长了1万元,也即杨箕村的改造对村民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事实上,包括杨箕村在内的城中村,早期村民都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失去土地后主要的经济来源为集体分红、出租屋收益及工资收入,之后的回迁显著提升了房屋的出租价格,且年轻一辈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因此村民的经济收入整体上是在逐步提高的。
尽管快速的城镇化改变了一些村民的价值观念,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以及社区缺失职业培训等原因,促成部分失地农民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保留知足、求稳的小农意识。目前中老年村民仍常会在祠堂内进行娱乐活动,这部分村民以分红和房屋出租为主要收入,缺少外出工作来提升收入的意愿,容易满足现状,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现今社会大多数工作都要求学历,而村民的学历水平相对较低,政府虽然改造了杨箕村的外观环境,但没有帮助一些就业困难的村民解决就业及社保问题,和猎德村相似,这种“征地不管人”的策略导致这部分村民处于“准市民”的社会地位(刘晔 等,2012)。
“搞到现在好多村民都没有社保,工作跟不上。因为社会都要求学历,你应该政府把一部分钱留下来,帮助他们再就业嘛,保证他们生存的。……其实征了这么多地啊,我可以说是毁了一代青年啊,不是个个都要求上进啊,老是要在这打麻将啊,一点文化气息都没有,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啊,拿着租金分红就不去做了,也没心思去管孩子的培养,下辈的人发达都有限了。”(60多岁杨箕村民)
4.3 文化市民化结果
从学历的调查结果看,村民群体低学历人群(大专及以下)的比例接近51%,高学历人群(本科、硕士或以上)比例接近49%;租户和其他人群体低学历人群比例约为37%,高学历人群高达63%。由此可以看出,村民群体的学历水平相对较低,租户和其他人群体高学历人群数量较多。54%的受调查者都认为杨箕社区改造后附近人的文化素质有变好,其他受调研者则认为变化不大。整体上,虽然部分村民旧有的农民、小市民惯习仍然没有随着杨箕社区的改造而改变,但大部分杨箕村的人都在慢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更好地融入新的社区生活。而这种文化素质的提高也不仅仅只是因为在城中村改造这一外力作用下,也有整体社会氛围、自身想要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观意愿等方面的影响。
(村民现在的素质有没有变好?)“那肯定有啦,就是随着整个受教育水平提高,但我感觉还是整体上会差一点,跟企业上班那种的感觉还是差一点。”(30多岁程介村村民)
从改造对村落文化的保护看,有57%的村民、59%的租户和其他人群体认为政府对村落文化是合理、非常合理的。有一半的村民、42%的租户、45%的其他人群体认为保持以前生活习俗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总体上,各主体均对以前习俗的认同感一般,认为传承文化是重要的,但要与时俱进。相对于租户、其他人群体,村民对生活习俗的认同感最强,传承意识最高,这与杨箕社区拥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村民的耳濡目染有重要关系,村民一直在潜意识中保留着宗族观念,并希望能一直传承。
“(保持以前习俗)肯定重要啦。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嘛,所以我带他(孙子)来这里(祠堂边),你只有知道你是杨箕人,你的祠堂就在这里啊,让他从小就有这个意识。”(60多岁杨箕村民)
大多数受调研者认为自己的生活习惯、教育观念、养老观念、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差别不大,说明大多数受调查者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向市民身份转变。虽然改造能促成杨箕村村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科技、媒体的发展使得村民在网络信息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以及社会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另外,早年外出务工的村民群体与市民的隔阂相对较小,而当初保留村民户籍、在村内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思想观念则较为滞后,由此可知村民内部存在观念的分异。
“我们是征地时候出去了,出去受到社会氛围影响嘛,接触到一些人。……观念改变的话和城中村关系不大,跟社会接触、媒体传播,他们会受到教育,肯定会有提高的,现在手机这么发达。我是工作关系,跟他们(保留农民户籍的村民)还是不一样的啊。”(60多岁杨箕村民)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不可逆转的城镇化浪潮中,城中村村民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必要的社会工程。城中村村民市民化遵循的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并在与外界人员的互动中逐步实现市民化。以杨箕村为例,改革开放前的杨箕村是典型的岭南村落,村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改革开放后,政府因发展五羊新城和珠江新城而对杨箕村进行征地,村民开始在政府安置或村集体创办的企业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并修建房屋用以出租,此时村民的收入有了较大提升,外出务工的村民获得城市户口,且与城市市民有较多接触,推动杨箕村村民身份市民化、经济市民化和文化市民化的进程。2009年杨箕村的撤村建居进一步推动村民的市民化进程,回迁后的小区有2/3 的房屋由外来高素质人群居住,房租水平也大大提高,此时村民的收入、文化水平都有较大提升。在身份认同上,年轻村民相比中老年村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为开放,因此更认可自己是市民身份,这与猎德村(潘卓林 等,2020)相似。但从本研究也可以看出,中老年村民实际上也可以划分为2个群体,在上世纪外出打工获得城市户口的村民思想更为开放、文化素质水平较高,更认可自己是市民身份;一直在村内的村民受教育水平低,再就业困难,有自我满足的小农意识,更认可自己是农民或准市民身份。
职业的“非农化”、居住地域的“城镇化”及身份的“市民化”理论上是一体的,实则“市民化”进程落后于“非农化”及“城市化”进程。本研究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村落时代的未市民化、城中村时代的开始市民化以及回迁小区时代的加速市民化(图3)。村落时代的村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思想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较低,此时的村民未开始市民化;城中村时代,大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于务工、房屋出租和集体分红,少数村民来自务农,职业开始非农化,并有大量村民获得城市户口,在与城市市民的接触中提高了思想文化素质,此时的村民开始市民化;到了回迁小区时代,村民的收入集中在务工、房屋出租和集体分红上,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入、文化素质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此时的村民加快了市民化进程,且市民和村民的概念界限也在淡化。而整个过程中,外部城镇化是重要推动力,推动城中村从村民职业的非农化到居住地域的现代化再到身份的市民化。

图3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过程Fig.3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in urban villages
5.2 讨论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中村表面上是游离于城镇化进程以外的特殊空间场所,实质上其内部环境的变迁却恰好是城镇化进程的见证,从传统村落到城中村再到现代化小区的嬗变历程映射大城市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张,由此带来内部的社会空间生产,其中既有村民对融入城市社会的向往,也有村民满足于现有条件,多因素影响下使得城中村成为复杂的社会空间。中国城乡长期的二元结构是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关键,已有关于猎德村的研究认为,城中村改造改变了人居环境和人口构成,为村民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转变创造机遇,但无法触动制约村民市民化的制度框架,无法改变村民的思维习惯、个人素质(刘晔 等,2012)。而从本研究认为,城中村的改造总体上能推动村民市民化进程的,但村民的市民化动力不仅仅只停留在改造背后带来生活空间转变这一层面,还有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在过往研究中,户籍的取得被视为市民化的关键所在,而对于城中村村民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拥有城中村农村户口的居民由于能均等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甚至还能获得村集体的分红,提高个人收入,因此大多数村民都更倾向拥有农村户口,在此情况下,以是否想要城市户口衡量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意愿是不合理的,而应从主动进行社会融合、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的意向等其他角度进行衡量。另外,针对程介村村民的访谈可知,即使城中村改造能显著改善人居环境,但有部分本身在城中村时代就有较高收入和较好居住环境的村民主观上不愿进行改造,认为改造只是有利于自己这一代(“征了我只是我这一代富了,我下一代就不富了。不征的话那块地永远是我的,我这条水就细水长流的”——程介村村民),从这个层面来说,推动城中村市民化进程不能仅仅依靠改变户籍,而应着力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增加村民的就业机会、并在改造中兼顾村民的安置和未来发展问题,由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进程及市民化进程。
综上,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外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进程。本研究也有部分群体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市民化,处于“准市民”或“农民”状态。市民化的完成需要村民真正拥有市民意识,转变生活方式,摒弃过去不合理的传统思想观念,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水平:1)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帮助失地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包括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培训和指导平台以帮助村民再就业。2)引导失地农民接受新的文化。外部城镇化浪潮下,城中村是岭南文化的喘息之地,在保留村落传统文化习俗的同时,政府部门也要通过举办一些社区活动或者借助现代化媒介来帮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村民理解城市文明的制度规范,助力提升其思想素质及在城市生活中的公共服务意识,促使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