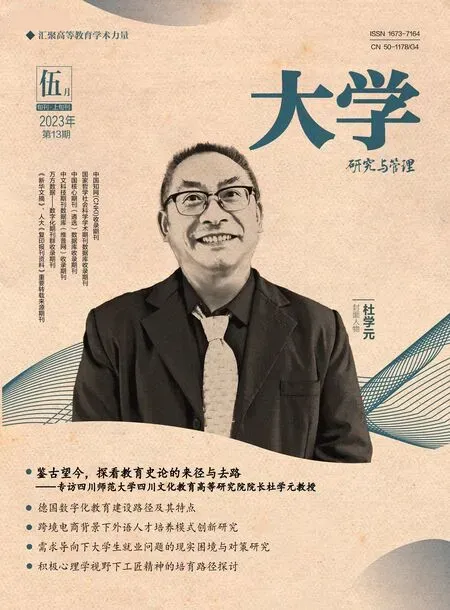青海“花儿”与高校卓越师范生培养的思考
——以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例
王金锐
(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花儿”是一种民歌,又名“少年”,产生于青海,流行于青、甘、宁、新等地区,其唱词浩繁,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1]。它孕育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原始文明,“花儿”不仅饱含着音乐艺术性,还有文学意蕴和民俗学价值。在西北,“花儿”不只是一种悠扬的山歌,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和男女传情的方式,从侧面也反映出了西北人的浪漫。青海“花儿”在西宁及周边地区流行甚广,在近十多年的发展和传播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卓越师范生培养的过程中,积极邀请青海“花儿”演唱家走进校园,为学生开设讲座、进行演唱交流,让青海“花儿”与师范生培养融合,为学生走上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岗位做好铺垫。本研究结合青海师范大学卓越师范生培养的实际和青海“花儿”教育传承培训的做法,提出几点意见。
一、青海“花儿”的艺术价值与传承模式
“花儿”流传的省份较多,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和宁夏。其他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地也有不同风格“花儿”的散落。主要由汉、回、土、撒拉、藏、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传唱。“花儿”曲调丰富,有200 多种,主要用“令”在称谓不同的曲调。可用衬词、地名、行当、民族或曲调特点等方式命名。如用衬词命名“白牡丹令”“大眼睛令”;用地名命名的“孟达令”“马营令”;用曲调特点命名的“直令”;用民族命名的“撒拉令”“土族令”等等[2]。“花儿”的艺术价值尽显在唱词中。“花儿”的唱词大多用“比兴”的手法写作,以物托情。“比兴”“夸张”“押韵”“开花调”等是“花儿”常用的写作方法。青海“花儿”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各民族对“花儿”都进行了不断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在理论传承、自然传承和网络传承上都有了新成果。
(一)青海“花儿”的理论传承
“花儿”是大西北的魂魄,承载着西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其非遗价值也在歌唱、文学、风俗和传承上得到了认同。西北歌唱家、音乐家、教育家等人员纷纷投入“花儿”研究中,如青海师范大学李昕教授的《青海“花儿”的音乐特征及其继承与发扬》,对四个民族“花儿”的音乐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特别是对土族“花儿”的旋律、音程,演唱中的气息与滑音等方面做了细致研究[3];宁夏大学王薇薇教授的《“花儿”传承与文化生态链构建》《传西北“花儿”之魂士承中华文明之脉——西北“花儿”当代传承发展刍议》等文章对“花儿”的传承发展类型和模式做了很好的梳理;新疆艺术学院马成翔教授的《我对多声部“花儿”合唱作品创作的探索和实践》、杨生顺老师的《河湟“花儿”综论》等文章和专著,为“花儿”的传唱与传承创新发展提出了新思路,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是“花儿”在传承传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也为“花儿”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思路。
(二)青海“花儿”的自然传承
自然传承一直是“花儿”600 多年来经久不衰的最基本的形式。从最原始的口口相传,到政府支持或协会帮扶的“花儿”山场,源源不断的滋养着西北人民的心灵。如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的创建,使青海民和七里寺“花儿”会、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乡“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等更加活跃,更加繁荣,这种以区域为单位的“花儿”山场以崭新的面貌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呈现出与现代社会水乳交融的局面。今年是丹麻乡土族“花儿”连续举办的第十五届,也是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的重要站点。在演唱会期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业界专家、“花儿”歌手、“花儿”爱好者等汇聚单麻乡,“花儿”研讨、美食娱乐、农副产品推广、民宿旅游等,激发了当地的消费潜力,活跃了乡村消费氛围,赋能了美好生活,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青海“花儿”的网络传承
近些年,随着各类网络直播平台的出现,极大拓展了“花儿”传唱和传承的新方式、新路径、新空间。传统的传唱和传承的模式通过网络实现了转变,微信群、QQ 群、快手、抖音等语音、短视频的功能,为没有文字书写能力的“花儿”传承人和“花儿”唱家们提供了较好的传承和传播的条件[4]。青海79 岁的国家级“花儿”传承人马明山、73 岁的省级“花儿”传承人祁永秀都能通过手机,在微信群传播自己的声音。省级“花儿”传承人祁永秀,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酸奶奶奶”。因她自制酸奶每天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售卖,并自编了歌词,用“尕吾令”进行演唱,她把卖酸奶的奔波生活用“花儿”演唱了出来:“卖个酸奶真辛苦,翻山架岭走了,脸上的堂土身上的汗,只为了穷光阴了,”很多人来吃一碗酸奶都是为了听她演唱“花儿”。如今,“酸奶奶奶”有10 个“花儿”爱好者微信群,群里人数最少的53 人,最多的260 人,每天她都会在微信群里应邀演唱“花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青海“花儿”传承人或爱好者在各类直播平台开展短期或定期直播的人数约为300 人左右,直接“花儿”受众达27 万余人,很多“花儿”唱家不仅利用网络直播传播了当地的民俗文化,网络流量、点赞、打赏等为他们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益,增强了“花儿”爱好者的文化自信,为乡村文化自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花儿”教育传承在青海师范大学的积极尝试
(一)青海“花儿”研培活动的民族传承
2018 年获批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项目——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花儿’”培训活动连续三期(三年)在音乐学院开展,每期按照项目要求培训40 人,来自青海西宁及周边地区120 余名“花儿”爱好者走进高校,参与为期一个月的学校和交流活动。参加培训的学员最小的17 岁,最大的56 岁,有的是非遗项目的持有者,有的是“花儿”演唱的从业者、爱好者,当他们再次行走在校园,和高校学生同吃同住同学,每一个人都有了不同的感慨和收获。青海“花儿”传承人培训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青海“花儿”代表性非遗项目为培训工作重点,以传承性保护、活态化利用为实施路径,以尊重“花儿”艺术的原生态性、地域文化特点,保护“花儿”艺术的多样性为原则而举办,使“花儿”传承人群与高校教育资源深度融合。培训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演唱方法与表演技术、多形式的交流研讨与实践,增强了培训学员的基础素养,拓宽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了文化自信和“花儿”演唱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青海“花儿”研培活动的文化传承
为提高青海“花儿”研培的系统性、规范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反复研讨、多方面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了“花儿”研培计划咨询专家库和师资库,其中很多“花儿”传承人都被遴选到专家师资库中。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的嫡系弟子马俊、国家级花儿传承人78 岁的李明山等拥有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走进培训课堂,为学员普及理论知识、教授花儿演唱技巧、传唱不同的“花儿令”,用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教学习方式,打开“花儿”培训学员向上向美向善的通道。培训课程设置为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三大类,共240 个学时,在教授花儿培训学员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对“花儿”理论和花儿价值的认知,提高民族自信,精进演唱水平、拓展创作视野。学员不仅增强了表演的能力和水平,也具备了一定的教授传播技能。除此之外,研培汇报、外出考察等,让学员分赴非遗传承基地,与当地的非遗项目传承人交流演唱和表演技艺,学习非遗传承模式与管理,大家通过竞技、交流、观摩,使研修研培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从一定意义上说,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担了青海“花儿”爱好者音乐素养提升的重任。在后期的调研和反馈中,这些学员在各自的学习和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起到了文化传承与传帮带的作用。
三、青海“花儿”教育传承与卓越师范生培养
2017 年开始,青海师范大学按照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成果申报青海师范大学卓越师范生培养项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搭上了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的快车,并于2019 年获批了青海省一流专业。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学校卓越师范生培养计划,保持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的优势,主动适应青海当地乃至周边省市对中小学校师范生的要求,强化师范生对音乐各类课程的理解和把握,提升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培养学生教学实践能力和跨专业学习的能力,造就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卓越师范人才,学院建立了由高校、政府、中小学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在培养过程中不断修改培养方案,力求让学生通过四年的音乐教育学习中更加适应社会需求。为此,音乐教育培养方案中每学期增加了一门卓越师范生培训课程,课程内容由学院根据学生需求和本地资源情况,安排16 周32 节课程。每一周一个专题,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师范专业技能训练。内容涵盖教师语言与训练、书写训练、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实操、班级管理与学生发展、学科教学论与教学技能训练、卓越提升课程等。在卓越提升课程中,学院按照中学阶段高中课程及教材的要求,在奠定音乐鉴赏、歌唱、演奏教学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学生对音乐与舞蹈、音乐与戏剧等的把握,学院增加了京剧、青海花儿、扎捏、尤克里里等戏曲、地方音乐及打击乐等内容。其中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安排了三周的青海花儿鉴赏与教学,聘请当代“花儿王子”马俊、青年“花儿”歌手马全等知名“花儿”专家到校为音乐教育专业师范生授课。“花儿”唱家们介绍花儿的发展和传承历史,演唱学生比较熟悉的作品,如《上去高山望平川》《雪白的鸽子》《尕老汉》等曲目,也会逐句进行教唱,引导学生增强对地方音乐的兴趣,从青海方言的特点、“花儿”演唱的技法等方面与学生进行交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近年来,青海招生政策对青海生源的保护逐步加强,音乐学院每年招收120 名新生,其中70%的学生是青海生源。青海生源数量的提升,为学生学习“花儿”和传唱“花儿”奠定了语言基础,但在实际的调研和教学中发现,目前大学生多是“00 后”,他们对地方方言的掌握很有限,兴趣不足,推进青海“花儿”进高校、进课堂、进年轻人的心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一)存在师资引进和经费不足的困难
随着高校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及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引进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学校对人才引进的要求都是博士。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广人稀、经济困乏,引进艺术高层次人才相对困难。青海“花儿”艺术人才来校授课,学校能给予外聘教师的授课费为教授每节课50 元、副教授40 元、讲师及以下30 元。学校目前的位置与主城区的距离相对较远,省内的传承人和“花儿”唱家到学校长期开展教学活动也很困难。这些因素为学院聘请花儿传承人、花儿兼职教师或花儿讲座教授等带来了不便。
(二)青海生源与青海“花儿”教育传承的标准不匹配
从数字上看,青海生源的数量近十年有了近30%幅度的提高,占学院全部生源的70%以上。但是,这些生源60%以上来自青海西宁及周边地区,在全国语言规范化推进的影响下,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父母都不再会讲青海地方语言,“00 后”大学生缺乏基础的语言环境。因此对青海“花儿”缺乏感情,对“花儿”演唱和研究不感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容易产生共情,并没有地域优势。虽然每学期聘请了“花儿”唱家进校开展讲座或授课,但青海籍学生难以起到带头或示范作用,所以教学安排中的“花儿”课程难以在短时间内与卓越师范生产生共鸣,收不到预期效果。从2017 年开始,已实施近6 年,做到了学生了解“花儿”、学习“花儿”,但让青海“花儿”在学院卓越师范生中积极传唱和传承还有一定的难度。
(三)青海“花儿”的文化内涵在高校教育传承认同上仍存在分歧
青海“花儿”的内容一类表达男女爱情婚姻,另一类描写社会情感内容。描写社会内容的作品数量不多,主要是揭发暗黑丑恶、歌颂社会生活和感悟人生哲理等三种。但总的来说,青海“花儿”是情歌,传统的“花儿”唱词内容主要以言情为主,“花儿”主情,是灵魂,情是“花儿”表达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表现[5]。虽然近些年通过“花儿”会等活动的推动,以开阔的视野创作的新词很多,如歌颂党、歌唱新时代等新作品不断涌现,在歌唱和歌词中有所突破,但高校一些学者认为“花儿”是一种民间歌曲,有选择地开展鉴赏十分必要,如作为专门的声乐课程进校教学。一是“花儿”的歌唱技法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专业老师去学习研究;二是“花儿”的内容需要精选和甄别,有些内容不适合作为专业课程进行教授。目前,适应新时代的“花儿”唱词的编撰没有形成规模和团队,新创作的歌词在充分表达传统“花儿”的意境和情感上尚待研究。
四、青海“花儿”教育传承与高校卓越教师培养的对策
(一)争取政策和经费的支持
学院要积极与政府和地方文旅局、文化馆进行衔接和合作,在争取资金支持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创作团队的作用,策划一些成熟的“花儿”项目,如长期开展“花儿”研修研习的培训,为青海“花儿”的高质量传承获取必要的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持。
(二)积极遴选并开办卓越师范生能力提升创新训练营
学院要通过遴选,组织一批具有语言基础或对青海“花儿”感兴趣的学生建立青海“花儿”能力提升创新训练营,把青海“花儿”作为专门的声乐课程,聘请省内“花儿”唱家,每月进行专门的授课,帮助学生涵养教育情怀,寻找文化认同,为青海“花儿”真实落地青海师范大学,走进卓越师范生的课堂、走进卓越师范生的内心做好第一梯队工作,再由这些具有青海“花儿”演唱技术和演唱情怀的学生去进行传唱和传播,从而不断扩大青海“花儿”在高校的影响。
(三)积极参与“花儿”的教育传承与保护
高校是地方音乐传承和保护的生力军。西北地区的高校具有地方音乐保护的人才优势,同时也具有信息技术的优势。青海“花儿”教育传承需要有一套规范的“花儿”人才培养机制、结构体系、人才智库等,学院要组织一批有研究能力的年轻人,通过数字化形式对青海“花儿”的传承进行保护。只有这样,通过教育接续传承和数字化传承两种形式,让青海“花儿”的教育传承和保护有更强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高校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做些事情。因此,要打破时空的界限,打通高校与地方合作办学的壁垒,积极谋划,克服困难,为青海“花儿”传承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