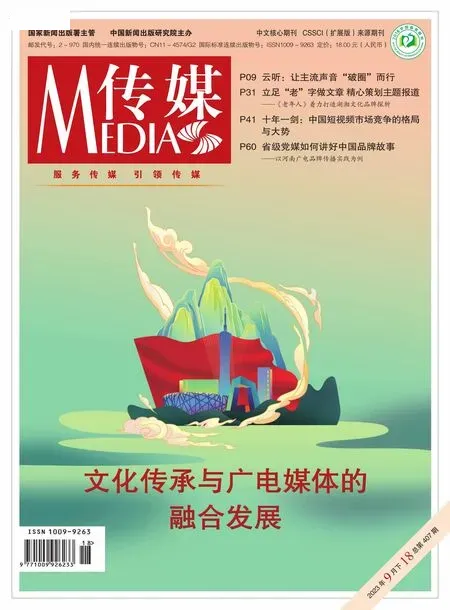构建与嬗变:国产儿童电影中儿童银幕形象的更迭研究
文/范小玲 王艳芝
儿童电影是一种电影题材,也是一种电影类型,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作为电影艺术表现的重要对象与核心,其角色塑造与表现手法,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富有特色的艺术形态,也映衬出时代的烙印。
随着时代的变化,国产儿童电影中儿童银幕传播形象不断更迭,成为特定时代的一种记忆。从时间轴线来看,儿童电影整体朝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儿童银幕形象从较为单一的色彩演变为“五颜六色”,儿童银幕形象塑造与呈现,在不同时期有着鲜明的特征,归纳起来看又带有明显的共性。
一、作为底层苦难记忆的见证者:社会道德教化与价值引领
国产电影真正将儿童作为主要银幕形象表现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了“彰显儿童本位、塑造儿童经典”的创作观。随着社会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的涌现,儿童作为独立的生命体,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由家庭本位的附属且被忽视的对象,发展为“儿童本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最痛恨旧时代、旧传统对少年儿童的压榨与伤害,在作品中疾呼“救救孩子”,彰显了其对儿童的重视与期望。
由此,从文学到电影出现了一批把儿童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塑造了多种儿童艺术形象。1922年,由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顽童》成为中国儿童电影的萌芽。“《顽童》是一部无声的黑白短片,表现一个6岁的孩子在花园里玩耍的片段。有情节,由演员扮演,表现儿童情趣,是有故事色彩的影片。从儿童故事片的角度看,《顽童》算是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短故事片”。

图1 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
中国电影从起步之初就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实现教化社会的目的,以写实主义影像风格揭示城市底层流浪儿童生活之艰辛,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大多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他们大多生来不幸,没有任何选择地被迫生活在社会底层。儿童电影通过真实刻画孩子们的生活境遇与艰辛,展示的是当时悲惨的社会图景。
1923年,明星公司出品了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片。电影不仅再次将焦点放到儿童身上,而且塑造了余璞单纯、善良的典型形象,为同时期儿童银幕形象塑造奠定了整体基调。余璞一出生就被迫失去父爱,被人排斥,艰难地生活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余璞是不被人接受的苦命孩子,但是他最后挺身而出救下祖父,展现的是一个可怜儿童经历苦难后的成长。电影触及社会实际,揭示当时的社会矛盾,将新思想与传奇故事结合起来,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涵,最后三代人圆满结局也起到了道德宣教的作用。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苦儿弱女》(1924年)描述了小慧卖身葬母,有容卖身还债,孩子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展现了黑暗社会中残喘生存的孩童所经历的磨难。张石川导演的《好哥哥》(1925年)表现了在社会动荡背景下,作为孤儿的大宝背着二宝受苦受难的故事,电影首次塑造流浪儿的形象,是当时纷乱社会的真实写照,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控诉。另外,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小朋友》(1926年)塑造了流浪儿唐小棠的电影形象,他被叔父遗弃,后被乔氏夫妇为还赌债卖给剧团被迫卖艺,揭露了当时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之后由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1936年)延续了这类受难者儿童形象,影片成功塑造了小三子这位孤儿形象。小三子失去了父母,被收养又遭抛弃,流浪成为他的宿命,揭露对旧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
电影《三毛流浪记》(1949年)根据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通过孤儿三毛在旧上海的悲惨遭遇与苦难挣扎,展现了旧社会广大城市底层儿童的不幸命运。电影塑造了三毛倔强、正直、机智活泼的形象。三毛虽无衣无食,但不贪恋富贵,虽到处碰壁,但不灰心丧气,他不向黑恶势力低头,顽强地生活着。电影拍摄跨越上海解放前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映的国产故事片,关注度与影响力极高。导演赵明、严恭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拍摄这部电影,用喜剧的风格演绎悲剧的人生,用喜剧作为揭露黑暗、针砭社会落后现象的有力武器,让观众含着眼泪笑。三毛富有特点的人物造型以及从社会现实中提炼的行为动作,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银幕形象。
电影工作者接连塑造出儿童电影中最触动人心的流浪儿、孤儿等儿童形象群体,成为最能体现社会底层的形象。这些苦难社会的受害者除了成为艺术典型之外,还承担着教化社会的作用,也成为儿童银幕形象的最初形态。

图2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
二、作为肩负革命重任的小英雄:主流意识形态个性化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描写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成为当时的主要题材之一。儿童电影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了一系列小英雄形象。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不仅表现儿童自身的悲惨遭遇,还展现了关于儿童在战争危难下的成长与变化。这类题材中的儿童形象年龄大小不同,身份不一,但他们都是战争背景下肩负重任的小英雄。这些小英雄的艺术形象或来自真实事件中的真实人物,或通过艺术创作形成的人物形象,都十分典型生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石挥导演的《鸡毛信》(1954年)中,小海娃经历重重磨难,最终成功地将鸡毛信送到了八路军手里。电影塑造了抗战背景下儿童电影中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小英雄形象。电影对小海娃心理活动的刻画,既丰富了人物形象,也增加了戏剧张力。“影片根据儿童特有的思想感情、语言行为刻画人物,从内容到形式都富有儿童情趣,浅显易懂,易为小观众接受。片中扮演小主人公的蔡元元,将海娃的机灵勇敢塑造得十分生动。继三毛之后,海娃成为中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又一难以忘怀的形象。”
这个时期有一批儿童电影突出地塑造了许多肩负革命重担“小英雄”形象。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兵张嘎》(1963年)作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儿童影片,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作品,“嘎子”这一儿童形象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影片中的“嘎子”虽然是一名抗日小英雄,但并没有因此被神化。影片通过大量的细节塑造人物,分别展现了在敌我斗争中嘎子经历的一系列波折,穿插“三次咬人,四次落泪”等经典情节,最后摆脱危险成长为小英雄,电影将嘎子这个形象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人物形象也比较丰满。
说到儿童形象不得不提《闪闪的红星》(1974年),这是“十七年”后到改革开放初,这个阶段较有影响力的一部电影。电影塑造了“潘冬子”这个家喻户晓的儿童人物形象。带着满腔仇恨的潘冬子“一夜长大”,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肩负起游击队交给的革命任务:筹盐、搞情报、破坏搜山计划,最后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很显然,电影儿童形象的塑造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大多与战争题材结合,这些影片塑造的儿童形象多是肩负重担的小英雄,他们在战争的环境中历练成长,展现了儿童敢于抗争的精神,具有一定的历史教育意义,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图3 电影《我的九月》中的安建军
三、作为“叛逆者”,在寻求自我中成长:时代特征的彰显与浓缩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儿童电影节的举办以及中外电影交流的日益增多,为国产儿童电影生产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宽松的环境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儿童银幕形象由原来集体主义基调下产生的小英雄形象逐渐转化成了关注个体命运,他们找寻自我突破。电影表达了他们从依赖到独立,从懵懂躁动到身心成长的历程。
电影《苏小三》(1981年),塑造了抗战时期,在江南水乡一个叫苏小三的孤儿不甘束缚从杂技班逃离,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电影赋予苏小三能变魔术会耍杂技的技能,这样不仅增加电影娱乐性、观赏性,也使得人物的行为以及情节发展具有合理性。
电影《大虎》(1981年)刻画了调皮、顽劣的李大虎在陈娟老师耐心细致地教育下,成为爱学习、守纪律、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好孩子。电影《候补队员》(1983年)的主角刘可子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他生性好动,喜爱武术,自称“姿三四郎”,学习成绩不好,又不守纪律,进不了校武术队。后来,在黄教练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成为一名正式队员。电影由孩子身上体现出的问题,引起观众对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反思。《扶我上战马的人》(1983年)中塑造以狗娃领头的人称“八大金刚”的野娃娃们,为实现骑上高头大马的愿望,由原来的“野”孩子,而转化为认真读书,积极上进的好孩子。
《多梦时节》(1988年)中小主人公罗菲刚步入青春朦胧期,陷入少女的遐思与幻想。电影对她的个性、理想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尤其十分到位地把握了她的心理特征。电影片头电子音乐如梦如幻、朦朦胧胧的气氛,奠定电影基调与风格。象征意味鲜明,挂满鸟笼子的大树下,罗菲与梦中老人的对话,揭示出罗菲精神世界、生活状态以及成长的烦恼。《霹雳贝贝》(1988年)是第一部国产儿童科幻片,手上带电的小男孩贝贝与众不同,生来具有“超能力”。贝贝欲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甘愿放弃“神奇力量”,渴望能够融入集体,与家人和小朋友能够亲密接触。
电影《我的九月》(1990年)贴近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电影以北京亚运会到来为背景,表现了生活在北京普通家庭的小学生安建军从胆小害羞到自强独立的成长变化。安建军不善言辞,被人称为“傻子”。电影通过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折射出儿童性格的差异,提出家庭和社会对孩子成长影响的深层思考。
另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涉及儿童以及青少年的问题也有许多,如犯罪,早恋等。此时的少年儿童在找寻自我中更多地充当“叛逆者”的角色,试图在与社会的对抗中确认自己的地位,表达自己的思想,电影不仅将这个时期少年儿童的个性与诉求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同时也真实自然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理特征,使得其银幕形象更加多维立体,电影也具有了更加深远的社会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逐步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明显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或是个性迥异,坚持自我;或是尝试突破,随性不羁。在塑造这些儿童银幕形象时,电影既做到贴合时代背景,也遵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银幕上的儿童形象也给观众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引导作用。
四、作为渴望家庭关爱的留守者:乡愁的表达与同情效应的阐释
进入新世纪后,农村留守儿童成为儿童电影关注的焦点,涌现出了大量的留守儿童题材的电影。这些影片重在展现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无论是他们贫乏的生活条件还是渴望能得到关爱的内心世界,都使得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国产儿童电影的儿童形象也再一次地结合社会实际更迭到留守儿童的身上。
在刻画留守儿童这一形象时,有很多不同的侧重角度,有部分电影着重描述他们的生存状况,表现了由于父母长期不在家,留守儿童无人看管教育变成了“问题孩子”。比如,《留守孩子》(2006年)中的王小福、杜小苇和月月等留守儿童,他们合伙偷钱去网吧玩游戏,因抢占座位跟别人发生冲突,多次被带到派出所,体现出了孩子们因缺失家庭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春风化雨》(2009年)中,十岁男孩蓝金宇和八岁女孩金悦等一群性格各异的留守儿童打架逃学,在别人的教唆下闯下不少祸。
电影对于留守儿童的表现更多地还是聚焦于呼唤“缺失的爱”的回归。《空巢里的孩子》(2009年)中父母寄回来的信件成了留守儿童的精神寄托。电影中,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代号:北京、青岛、深圳、广州、苏州。片尾“北京”全身贴满收集来的邮票,站在邮筒边,想把自己寄给父母,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推到大树上的鸟巢,隐喻意义明显。《天堂的礼物》(2010年)中,小虎的父亲外出务工身亡,母亲离家出走。为了不让孩子的心灵遭受打击,村长给他找了一位临时妈妈,并且隐瞒真相,大家共同编织善良的谎言,定期会有一本小虎喜欢的《哈利·波特》书邮寄到家里当作爸爸送他的礼物。电影表现了性格孤僻的留守儿童小虎对父母的思念。
《空火车》(2012年)中小女孩月月,时常跑到山坡上远望驶过的火车,期盼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过年,在她身上反映出大山里留守儿童寂寞、孤独、敏感的内心世界和时刻盼望与父母团聚的美好心愿。电影《早安!小树》(2013年)刻画了五年级学生李小树所遭遇的困境,三次寻找父亲,表面是找钱,实质上是寻找爱,表现了孩子们对于爱的期盼。
《千里送鹤》(2022年)中多杰和格桑幼年丧母,跟父亲情感疏离、有隔阂,和奶奶一起生活。他俩救助了一只因受伤又失去父母呵护而无法迁徙越冬的小黑颈鹤,决定将小黑颈鹤从青海草原送到云南香格里拉过冬。善良的姐弟俩跨越千里送鹤,最终盼来了父爱的回归与陪伴。
一般而言,儿童和老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把他们作为表现对象能够唤起观众较大的共鸣,特别是儿童具有天真、稚嫩的特点,能够获得观众较多的“同情度”。儿童电影将留守儿童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不仅表现孩子们的生活状态,更多在于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留守儿童银幕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丰富电影内容、传递世间真情,还是呼唤社会关注都具有现实意义。

图4 电影《早安!小树》中的李小树
五、结语
国产儿童电影走过百年历程,儿童身份与处境的转变,透过银幕形象广泛地传播,体现出社会的现实状况,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变革,也反映出电影艺术创作观念的转变。
曾经一段时间,面对种类繁多的娱乐形式,特别是动画片井喷式的发展,传统儿童电影受到空前的挑战。尽管当下儿童电影创作从题材、手法和风格都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儿童电影数量也不断增长,但是影院中却存在高品质儿童电影缺席的尴尬局面。儿童电影面临着市场份额占有率低和社会影响力偏弱的现状,如何实现艺术、商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电影从业者必须再思考的问题。
当今,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电影观众,他们对通过影像与声音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这种形式,有着与生俱来的挑剔,这给电影创作者提出更大的挑战。儿童银幕形象的塑造应捕捉凝练现实生活中儿童富有“童趣”的行为和言语,情节发展要符合儿童的思维逻辑。儿童电影创作也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历史传统,敏锐捕捉时代变化气息,结合新时代语境,拓展探索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