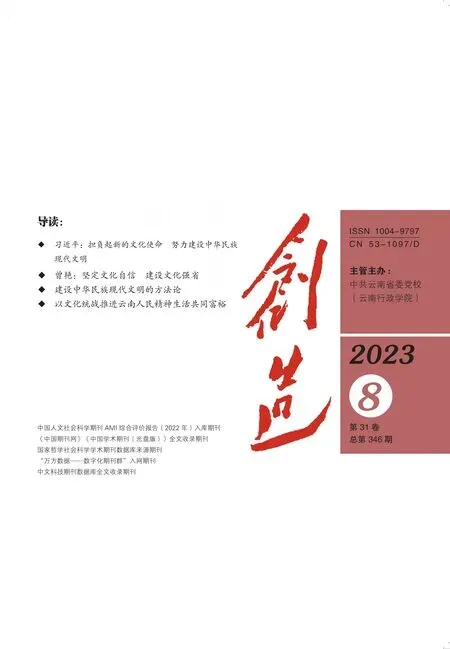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 祁永超
独龙族是云南世居的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在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之间的独龙江河谷地带。受特殊生存环境影响,其在与自然生态长期交互的物质实践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以神话史诗、民间信仰等观念文化为内核,物质生计为载体,禁忌习俗与习惯法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精粹,呈现出鲜明的地缘生态特征,展现出独龙族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今天,着力挖掘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和智慧意蕴,并将其同现代文明相融合,在去粗取精中实现现代化转型,可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一定助益。
一、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其族群同自然生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殊适应过程的产物。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独龙族,通过与自然生态的亲密接触,孕育形成了调适族群与独龙江河谷相互关系的传统文化,对维护“三江并流”区生态文明和物种资源具有重大影响。从民族生态学视角来看,其传统文化既蕴含着独龙族物质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凝结着朴素的生态智慧,是维持本地区生态面貌长期稳定的精神力量。
(一)和谐共生的天道观
“神话是一个民族变形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现实的积淀与反映。”在漫长的原始农耕社会中,通过对自然界的接触与观察,独龙族逐步萌发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源于自然”“人神兽同源”。基于此种认知,独龙族开始对万物的起源做出各种猜测和构想并由此形成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天道观。例如,独龙族神话史诗《人类的起源》,就传达出“人与动植物同为自然母亲的儿女”的观念。而《嘎美嘎沙造人》则将自然力量抽象化、神秘化,把万物的诞育归结为超自然神秘力量——天神嘎美嘎沙的功绩。它赋予嘎美嘎沙灵魂和智慧,使其具备人的声音、情感和职能,成为具有社会意味的“人格神”。即“远古时代,天神嘎美嘎沙用泥巴造出一男一女,并赠送粮食给他们,让他们到人间生活。同他们一起到人间的,还有不同形态的动植物。它们都是天神的杰作。”透过独龙族神话史诗不难发现,其认知蕴含着独龙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感知。人与自然是平等、互补、共生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人征服自然或自然凌驾于人的“主奴关系”。自然环境所孕育的一切生灵,并非是人类可以无限制随意利用的物质,它有其灵魂和意志。人类在利用这些物质维持肉体存在和族群延续时,必须怀揣崇敬感恩的情绪,自觉保持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荣关系。受其影响,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独龙族形成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为友的生态观念,并由此对独龙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在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早期,出于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独龙族人民根据既有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思维意识,形成了对生活世界的另类感知。他们将自然界万事万物神圣化、人格化。由此,独龙族基于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开始诞生并长期主导其人民的精神世界。在独龙族人的认知中,自然界的神灵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其一,“属我”的自然神灵。其二,“异我”的自然神灵。其三,“护我”的自然神灵。此三类神灵均是“独龙族人从谋生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其不发达的意识里形成的灵的幻想,使得他们对于能经常向自己提供饮食的动植物,多是怀着异乎寻常的感激或屈从的心情来对待它们、膜拜它们”。这种膜拜和敬畏意识,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积淀着独龙族人对自然生命追索和宇宙万物思考的智慧,彰显其敬畏生命、感恩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独龙族人民根植血脉的环保意识与生态道德发育成长的“敬畏之域”。
(三)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生活在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河谷地带的独龙族,在社会生活的早期,低下的生产力导致其“依赖自然就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采集、狩猎的族群生活,使其萌发节制、感恩的生态实践思想,他们将自身的活动控制在适度范围,由此既满足族群生存延续的需求,又维持生态健康,促进生物多样性存续。例如,独龙族通常是在粮仓即将告罄才会采摘林果和野菜,而不会事先大量收集储备。同时,在采集过程中,他们一般只采摘植物的嫩茎、嫩芽以及成熟的林果,从不破坏植株。这是其“节制”生态实践思想的一种具象表现。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和族群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独龙族开始摆脱自然束缚,进入利用自然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独龙江流域地形复杂,少量完好的狭小冲积扇或山前平台无法满足族群物质资料的需求。基于此,独龙族人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出一套包括根据森林砍伐难易与林地肥力、严格制定休耕轮歇制度与人工栽种水冬瓜树、保护土地肥力等举措在内的不同于其他山地民族的另类刀耕火种生计模式。从表面上看,这些生计方式都带有破坏自然、危害生态的意味。但是,站在客观立场不难发现,采集与狩猎所秉持的是一种节制、适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它在维持族群发展的同时,又以人为形式促进物种的自然选择和进化,从而间接实现地区生态与物种资源的发展;而根据土地肥力和森林砍伐难易划分土地类型,并由此人工种植水冬瓜树进行有节律的烧山开荒、轮耕抛荒,则以最小的自然代价获得最大的物质效益,同样对独龙江河谷地带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
受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制约,生活在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人长期奉行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念。他们认为,获取食物只是为果腹,建筑屋舍只是为保暖和防范野兽侵袭。受此种认知影响,独龙族人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诸多生态实践行为都体现出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意识。例如,在日常饮食中,独龙族人的饮食结构十分简单,“山里有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从不挑剔。同时,封闭孤立环境,使其饮食连基本的盐、油等调味料都无法保障。故而,其饮食偏于清淡,且每餐必定吃完,绝无浪费。而在房屋选址、用料、建筑上,独龙族人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念更是显露无遗。与其他民族不同,独龙族人很少将房屋建在交通便利的独龙江河谷缓坡地带,他们更喜欢在山中居住,目的就是为更好照看土地、采集和狩猎。得益于独龙江流域茂密的植被和丰富的森林资源,独龙族人很少利用铁钉、水泥等材料建造房屋,其建筑材料主要是自然界常见的草、藤、树、竹等植物。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独龙族人秉承简约、实用原则,任何材料必定物尽其用,绝不因奢侈美观而有所浪费。房屋建成后,其通常会在客厅中央设置一个巨大的火塘,它既是家庭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也是连通祖先和鬼神世界的通道,发挥着照明、烹饪、取暖、祭祀等多项功能。
和谐共生的天道观、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使得独龙族人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萌发出独特的生态环保意识,对推动独龙江流域生态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二、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受高山峡谷地形地貌的制约,独龙族人根据族群发展需求创造出一种蕴含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体现了对自然敬畏与感恩情绪的原始山地族群文化。其渗透到独龙族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颇具特色的生态保护思想。
(一)独龙族禁忌习俗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没有信仰、禁忌和秩序的人们是不可能和睦相处的。”信仰、禁忌与秩序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信仰是禁忌与秩序的精神支柱,禁忌是基于信仰和宗教产生的观念和习惯,而秩序则是信仰和禁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族群发展历史中,独龙族人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萌发出自然神灵崇拜和万物有灵意识,并由此形成原始民间信仰。在其形塑、约规下,又创造出一系列反映原始民间信仰的禁忌习俗。它们以强制或半强制的形式指导个体活动,调适族群与自然关系,进而构造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神圣秩序”。
“在独龙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禁忌对于独龙族的社会成员由‘自然’之人转为‘文化’之人,对于其社会新成员的社会化和内在化,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其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物质实践活动中。独龙族人认为,整个世界都被鬼神所包围,人从事一切活动都必须征求鬼神意见或避开恶鬼威胁。基于此种认知,独龙族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禁忌习俗。例如,生产禁忌:“畸形动物不能打,万一打到要祭鬼;自然死亡的动物不能吃,否则家里要死人;巫师说有鬼的地方,众人不得开垦耕种……”生活禁忌:“男子不能吃家禽及野兽的脚和肠子,否则不能获得更多猎物;播种剩下的籽种不可以再煮食,否则玉米等粮食会被野兽吃光……”上述禁忌习俗,看似荒诞无稽,但却是独龙族人对自然深刻感知和“自然神圣事物”的观念、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明确了个体与自然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订立神圣契约,进而自觉规范个体行为,主动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构造出一个以超自然神秘力量为主导的“生态保护场域”。
(二)独龙族传统制度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独龙族社会将生态保护作为制度要求的主要内容自习惯法时期就已经开始。据王四新等学者考证,独龙族习惯法是在超血缘的公共权力机构尚未出现前的漫长社会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它主要以“神判”、当事人和解、头人调解等形式,协调人际关系。其中,“神判”又称神裁或天罚,独龙语称为“克尔大”,意即由神灵裁判人间是非善恶。它主要是处理族群生活中诸如违背禁忌习俗、不正当两性关系及严重危害生态健康的行为。而当事人和解、家族头人和解等形式,则以自治意味协调个体与自然、族群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同自然始终维持良性互动状态。例如,独龙族的生态习惯法就明确规定,“尼勒”(父系氏族集团)成员不断增加和扩大形成“克恩”(村寨)组织后,“克恩”必须在其生存发展地域范围内以大自然中的巨石、河流、山沟等事物作为标识,并告知周边其他“克恩”。他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生存的范围内进行刀耕火种,而不能到其他地区去毁林开荒,违者将会遭受其他“克恩”的共同审判。在具体进行采集、狩猎及刀耕火种等物质生计时,可以采摘什么植物、捕杀什么动物以及如何进行轮耕抛荒等,也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否则便要遭受“克恩”组织惩罚,若拒不认罪则要接受“神判”。
依靠一系列详细的习惯法规及严密的习惯法规执行组织,独龙族人建立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生态习惯法。其毁林开荒、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对生态的破坏也维持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由此使得独龙江流域在满足人类延续发展需求的同时,又能健康持续发展。这是独龙族人“与自然签约,与自然立法”的结果。至今,在贡山县独龙江乡辖区内仍保留的大片原始森林即是例证。
三、独龙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满足当代人发展需求的同时秉承科学、节制意识,以确保后代子孙有满足其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其核心观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物种的存续与生态系统的稳定。二者缺失其一,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单纯依靠法律、行政的强制手段,经济的利益引导手段抑或是道德的约规,都无法完满实现生态系统的维持和物种资源的保护。基于此,就必须回归到民族生活的历史,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环保意识的挖掘、激活,来引导人们生发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环保意识和平等对待万物、与自然建立伙伴关系的心向,从而在意识层面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进而在实践层面自觉推进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物种的保护开发,最终达成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协调统一。
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渗透在其创世神话史诗、民间信仰、物质生产、禁忌习俗、习惯法规及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生活于其间的独龙族群众,受浓厚的生态环保氛围熏陶和感染,无意识地萌发约束个体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建立伙伴关系的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由此推动独龙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二)维持生态平衡的价值
独龙族生态文化是独龙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晶和智慧精粹,是独龙族人物质生产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抽象化表达,也是被历史和现实确证的能促进生态保护的特色文化。在漫长的原始农耕文明社会中,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着独龙族人的生存发展,通过同自然的亲密接触,独龙族人形成了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他们明确认识到,“人源于自然”,世间万物与人都是平等共生的,彼此是伙伴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权奴役对方。在这些认知的主导下,独龙族人在日常行为活动中,牢固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自觉将族群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控制在“度”的范围,由此维持地区生态平衡。
自然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异己的东西,而是维持人类肉体存在和族群发展必不可缺的物质资料的唯一来源。人与自然之间既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独龙族传统生态文化借助禁忌习俗、习惯法规等带有神秘色彩的“非成文”制度,形塑、约规族群成员的实践活动,使得自然生态遭受破坏保持在可控范围。而基于神鬼意志的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更是强调依靠自然力恢复生态面貌。这些理念和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独龙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对实现地区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在的精神意蕴和思维意识值得传承和弘扬。
(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同当地生物多样性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依托自然生态场域发展起来的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物质文明演进的基础,正因自然界丰富物种资源的存续,人类才得以在维持肉体及族群延续的情况下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不同族群依托其生存繁衍的自然条件发育、成长的民族传统文化则是生物多样性存续的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族群成员在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塑、约束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环保实践,从而无意识地促进物种发展。因此,“生物多样性与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多样性生物创生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文化存续着多样性生物”。
独龙族生态文化建立在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建立亲密友好伙伴关系的生态伦理观念基础上。千百年来,其依托本土自生的传统文化,形成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它以神鬼意志为面纱,自然环保理念为内核,禁忌习俗与习惯法规为内容,物质实践活动为载体,渗透到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保护独龙江流域生态环境,进而保护地区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独龙族世代传承的传统生态文化,是其在漫长原始农耕文明社会中同自然交往互动产物的精华,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确证能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产生重要作用的优秀文化。但是,独龙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采取的是直接过渡的方式,因而,在其传统生态文化智慧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蒙昧落后的意味,他们的某些具体生态保护实践在当代也有待商榷。新时代,深入挖掘独龙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蕴,传承弘扬其生态智慧,要在突破时空与地域限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其内容和形式与现实、与科学文明相融合,从而在超越和转换传统生态理念智慧表象与载体中实现现代化转型,最终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提供助益。
——独龙族纹面女
——人间天堂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