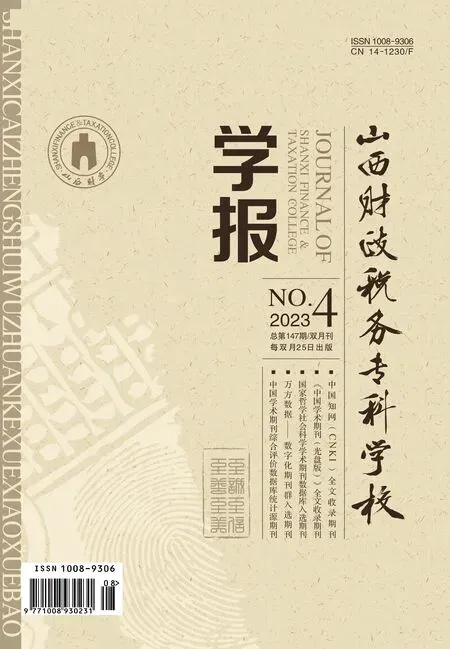交强险免责条款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陈志斌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山西 太原 030024)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依据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22条等法律依据;二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交强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以受害人并非第三者为由进行抗辩等其他事由。本文主要针对第一类法定免责事由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一、交强险免责法律条款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交强险责任法条的“正向适用”问题
1.法律条款解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交强险条例》第21条均提到: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此法条在适用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交强险赔偿的前提是否仅仅限定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失”。对此,部分学者、原告律师等从文义解释角度,得出主张“交强险应当赔偿”的结论——这是该法条的“正向适用”。但笔者认为此结论与交强险立法精神不符。一是在大量司法判例中,绝大多数法官认为此法条并未明确机动车因何种原因发生何种事故,因此系“原则性”规定,甚至是相关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顺序性规定,不能简单地直接适用。二是作为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该条规定是基于现实中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情形而制定的。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非交强险赔偿的必要条件。
2.相关法律条款的分歧。很多学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与《民法典》第1213条存在矛盾。笔者认为,第76条的法理逻辑是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应当先由交强险赔偿第三者损失,之后对第三者损失不足的部分再依第三者是否为机动车以及事故责任划分具体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民事赔偿责任确定方式,即第76条核心在于对事故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分配作出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第1213条则是规定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各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先后次序: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关于责任保险的立法精神,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的前提是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责任,所以笔者认为这两条法律规定在根本上不存在矛盾,只是规制的侧重点不同,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是争议焦点。
(二)交强险责任法条的“反向适用”问题
1.法律条款解读。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于2003年,历经三次修改,但第76条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一直未曾变更。由此可见,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从颁布伊始,就规定了在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免除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这也是民法过错责任基本原则的体现。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务院于2006年制定了《交强险条例》,其中第21条第二款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作出的一致性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强险不予赔偿。从上述第76条到第21条,其法理逻辑是当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则在“理论”上界定为责任保险的交强险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引申出一个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形的交通事故(如意外事故)中,当法院认定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则交强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定论,大多数法院对此法条采取“反向适用”,即因为第三者的损失并非由第三者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而发生,从而判定交强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处,法院之所以采用交强险承担“赔偿责任”的表述,是基于被保险机动车一方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并非是基于机动车与第三者之间给付责任的法律性质。
进一步明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的“反向适用”是指当人民法院认定交通事故的损失并非由受害人故意造成时,或者无证据证明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时,则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引起的交强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我国《交强险条例》第2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出现“无证驾驶、醉驾、车辆被盗期间肇事、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情形时,交强险对第三者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三者人身损害的抢救费用仅承担“垫付”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条款的具体内容本身无争议,但对此条款未明确规制的第三者死亡伤残赔偿金等其他人身损害交强险是否赔偿有一定争议。因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认定交强险应当赔偿,同时赋予了保险公司向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向责任人的追偿权。
(三)交强险免责法条在理解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在不同法条中,“交通事故”一词的具体含义有所区别。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交强险条例》第21条中,“交通事故”共出现6次,如果对每一处“交通事故”均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作相同解释,则会导致无法正确适用该法条。因此,应当结合上下文根据各法条不同的规范内容,对“交通事故”的主体、造成事故的原因、事故性质等进行区分,以解决原、被告双方的争议,正确适用法律。
2.原、被告双方对上述第76条和第21条中的“故意”理解不一致。在某些案件中,对于受害人(第三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免责法条中的“故意”,直接关系到机动车一方、受害人以及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交通事故可分为因过错导致的交通事故和意外型交通事故。其中行为人的过错在法理上又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如图1所示。此处的故意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违反交通法规是故意,但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是过失——这不同于交强险免责法条中的“故意”,后者是受害人(第三者)主观上对事故造成自身的损失持积极追求的故意心态。即便如此,在认定免责法条中的“故意”时,是否需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与动机?如果考量,则是否将其作为行为认定的必要条件?行为人主观上是对行为的故意还是结果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准确理解法条的基础上,才能正确适用法律。

图1 机动车交通事故原因分类
3.对于特殊的机动车侵害案件的法律条款适用问题。如果事故当事人涉及到故意犯罪,则在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中是否可以适用前文交强险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款?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较为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件,如“胆小鬼博弈”、事故侵权方与受害方故意的并存等。本文将在深入剖析相关法条的基础上,将此类案件正确适用法律条款,并得出相应司法认定结论。
二、关于交强险免责法律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分析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内容:“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1.交通事故的“主体”,应当限制解释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第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关于“车辆”“交通事故”的释义进行推理,依照当事人主体性质不同,交通事故可以分成五类,如图2所示。 第二,基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归责于非机动车或行人一方,所以“交通事故”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之间两种类型的交通事故,即图2中的②、③。第三,这意味着对于“B机动车故意碰撞A机动车,并导致B方损失”的案件,不能直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但能否以“举重以明轻”的法理逻辑而扩展适用此法条?或者能否直接适用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制——该问题将在后续的相关案例进行研究。

图2 依主体性质对交通事故进行分类
2.“交通事故”的碰撞类型,应当是A机动车与S非机动车车身或与骑行人、S行人的躯体之间直接发生物理碰撞的事故。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仅从文义解释角度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也应当适用于此类特殊的连环案件——“在行人S故意碰撞A机动车时,A为躲避而撞向其他受害方C”,或者“行人S从天桥故意扔石头砸中A机动车,A失控进而撞向C受害方(国内已有多起案件)”,由此造成C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如果适用此条款,意味着A方对C受害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继而交强险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此时如果S方逃逸或无力赔偿,则C受害方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将难以弥补,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关于这一问题:一是如果S方逃逸或无力赔偿,则承保A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仍需向B受害方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享有向S的追偿权;二是如果A车的避险措施不当,造成C不应有的损失,则依《民法典》规定,A车对C受害方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赔偿责任。
3.“损失”是指事故导致非机动车或行人一方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当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一方也可能产生损失(包括车上人员的伤亡),但鉴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可确定此处的损失专指在碰撞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人或非机动车一方的损失。补充说明一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对“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此类案件中无任何过错的机动车一方的损失赔偿责任主体、方式作出规定,这也有悖于一般常理认知(已有司法判例)。
4.关于“故意碰撞”的理解。一是主体要件:行为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实施的故意碰撞行为不适用此条,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一方至少在无过错责任情形下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二是客观行为要件:行为人积极实施了与机动车的碰撞行为(不包括实施“预备行为”之后的被撞情形)。例如,张三出于自杀或其他原因,明知有风险而躺卧在城市道路中央,随后被通行的机动车碾压导致伤亡——首先,张三躺卧道路中央的行为并非“故意碰撞机动车”的直接实害行为,而是准备被机动车碰撞的预备行为;其次,机动车一方仍可能会承担部分事故责任(至少可部分归责于驾驶人未尽谨慎驾驶义务)。因此,此案不能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免除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三是主观因素:行为人无论是寻求自杀(可能已投保巨额人身意外险),还是碰瓷(通过诈骗、敲诈勒索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此时行为人并不追求造成自己人身实害后果),机动车一方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自杀案件中,如果受害人(行为人)已经死亡,则主要依据其“故意碰撞”监控视频等证据进行认定,辅之以受害人生前相关的自杀证据;如果受害人未死亡,则只能依据其“故意碰撞”监控视频等证据进行认定。在碰瓷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必然不承认是诈骗,则同样只能通过客观证据进行认定。
综上所述,行为人是否构成“故意碰撞”,主要从其客观行为角度进行评价,而主观因素并非必要条件。
5.认定受害人“故意”的举证责任。当原告(受害人)主张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当向其赔偿损失时,如果被告(保险公司)依《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主张免除责任,则被告需要举证证明是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其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行车记录仪、监控影像、证人证言等证据。如果被告一方无法举证或人民法院依法对证据不予采纳,则被告将承担赔偿责任。同理,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中,亦需要由机动车一方举证以证明自身无过错。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应限制性地解释为: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非机动车骑行人或行人一方,为实现自杀、诈骗、敲诈等目的,主动以自身躯体或非机动车车身直接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进而导致自身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继而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内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1.本条中的“交通事故”包括两大类:一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图2中的②③);二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图2中的①)。对于后者,设B机动车因为某种原因故意撞击A机动车,则必然造成双方车辆的财产损失,也可能造成双方车上人员的人身损害,当然也可能造成其他受害人C的损失。依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承保A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B方的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
2.依《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一款可知,受害人是指作为车外人员的第三者,受害人可能是行人、非机动车骑行人、机动车驾驶人等。“损失”是指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这意味着受害人的损失是由其自身造成的,即受害人的故意行为与其自身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对“故意造成”的理解,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而非条件因果关系说),即第三者所实施的故意行为会合乎规律、较高概率地导致自身人身损害,自己既是致害方,也是受害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故意造成”一词较为抽象,所以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故意碰撞、打砸车辆等实害行为。
综上所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和《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中,关于“损失”、“故意碰撞/故意造成”的用语含义可作相同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交通事故”包括图2中的②③,《交强险条例》第21条的“交通事故”包括图2中的①②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受害人只能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交强险条例》第21条的受害人包括“行人、非机动车骑行人、机动车驾驶人等”。
三、特定类型案件的司法认定
(一)B机动车故意碰撞行驶中A机动车案件的司法认定分析
1.案件类型。一是B方与A方开“斗气车”,升级为B方故意撞击A车(B方行为可能构成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二是B车碰瓷,如在酒店附近踩点后故意碰撞酒后驾驶的A车,以报警威胁实施敲诈(B方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等);三是B车出于报复、泄愤或其他非法目的而故意撞击行驶中A车甚至其他不特定车辆(B方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在以上案件中,B车故意撞击A车造成A方损失的同时,也必然会造成B方自身车辆损失,也可能导致B车驾驶人、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
2.案件分析。在不考虑车上乘客的情况下,涉及到可能产生赔偿责任的主体有A车、a保险公司、B车、b保险公司四方当事人,如图3所示。鉴于本文研究目的,现在仅讨论B车的损失问题。

图3 B机动车故意碰撞A机动车案件当事人架构
第一,依照《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规定,B车的损失是由B方故意造成的,所以承保A车交强险的a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关于本案,人民法院能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对B方损失由有过错的B机动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一)项中的“过错”所包含的“故意”情形,是指行为人故意违反交通法规,但对造成事故仍是过失心态。而本案属于故意造成交通事故,因此不适用此法条。
第三,关于本案,能否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为依据免除A方对B方的赔偿责任?此处法理逻辑是:当B方主张由承保A车交强险的a保险公司对B方损失进行赔偿,而a保险公司以“A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规定对B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进行抗辩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解决此疑问需要明确两点:
一是能否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扩展适用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案件情形?从文义解释上该法条只是针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的情形,但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此条应当可以扩展适用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案件情形。具体逻辑是:设B故意碰撞A机动车,并造成B方损失,既然依照相关规定当B为碰撞弱势方(行人或非机动车)时,A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当B为碰撞强势方(机动车)时,更应当免除A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二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的适用是否为《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同向适用”的前提?即是否存在“依《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正向适用),但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A车一方仍应赔偿或者不能认定A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反向适用)”的案件?假设B在公路上抛洒钉子,以观看过往车辆爆胎取乐或维修营利,A车途经此处时,爆胎、失控进而撞向路旁归B所有的机动车,导致车辆损毁。此时,依《交强险条例》第21条,B车损失是由受害人B故意造成的,承保A车交强险的a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扩展适用),B车损失并非是由B主动“故意碰撞”A机动车造成的,所以不能“仅依此条”而免除A方赔偿责任,但可依《民法典》第1174条而不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在B车故意直接碰撞A车事故中,可间接扩展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以免除A车的赔偿责任。应当直接适用《交强险条例》第21条以免除a保险公司交强险赔偿责任。在上述B方“故意造成但非故意碰撞”的事故中,依《交强险条例》以免除a保险公司责任,依《民法典》以免除A方责任。
3.在醉驾事故中,B对醉驾是故意,但对事故是过失,整体上评价为过失性的交通事故(交通肇事罪的性质是过失犯罪),而非以上法律条款中的“故意”。此时的法律关系是:如果A车无事故责任、B车全部责任,则A车交强险对B车的各项损失应当在“无责任”的各分项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B车交强险对A车人身损害在分项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肇事方B追偿。如果双方均有事故责任(一般为B车主责),其区别仅仅是A车交强险对B车损失应当在“有责任”的各分项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B车借酒壮胆,故意撞击A车或以不特定对象为目标,则是纯粹的故意犯罪行为。依前文分析,A车一方及其交强险对B车一方的损失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4.对于被阻挡车辆B撞击处于静止状态的阻拦车辆A的案件,因A车并非处在交通状态,所以不属于交通事故,行为人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此本文不作讨论。
(二)B非机动车或行人故意碰撞A机动车案件的司法认定分析
1.基本案情。行人或自行车骑行人B,以自杀或碰瓷目的故意碰撞A机动车,可能造成B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B方可能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财产损失要求A方赔偿)。对于A方,碰撞导致的A车损失一般较小,但可能由于A车急刹时车上人员受伤(对此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2.案情分析。自杀或碰瓷责任事件树如图4所示。在B方故意碰撞A车时,如果A车驾驶人处置妥当,则B方不会产生损失,进而不会产生由A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如果B方受伤、残疾或死亡,则此时如有证据能够证明B方“故意碰撞”行为与其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规定,A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照《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规定,承保A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不予赔偿。如不能证明,则A机动车一方与保险公司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图4 自杀或碰瓷责任事件树
3.交强险免责法条的正反向适用问题。案情改编,设B在公路上抛洒钉子,A车爆胎、失控进而撞向B致其伤亡。此时,依《交强险条例》第21条,B的伤亡是由受害人B故意造成的,承保A车交强险的a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但是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B的伤亡并非是由B“故意碰撞”A机动车造成的,所以不能依此条而免除A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三)“胆小鬼博弈”案件的司法认定分析
1.基本案情。A机动车与B行人之间,因为争吵、纠纷等原因,B以身躯挡在A车前方或钻入车轮下,以阻拦A车离开。对B而言,其理性的策略是如果A真的启动车辆则必须躲开;对A而言,其理性的策略是如果B真的不躲开,则一定不能启动车辆——此称之为“胆小鬼博弈”。此时,如果B方选择的策略是只要躺卧在车前A即不敢开车,同时A方选择的策略是只要一启动车辆B就会避险躲开。此时,A启动车辆,B继续阻挡,则必然造成B重大人身伤害。
2.案情分析。第一,B客观上实施的是较为消极的阻拦行为(而非“故意碰撞”机动车),主观上并不追求自身伤亡,所以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机动车一方的免责规定。第二,客观上A启动车辆的行为与B人身损害后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论A本人主观上是否规避损害结果的发生,但从社会一般观点看,其主观心态至少是间接故意,即对B损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解释》)第15条,承保A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享有对致害人A的追偿权。
(四)“A驾驶人故意+B受害人故意”并存案件的司法认定分析
1.基本案情。A车一方主观上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实施危害行为,同时受害人B也故意碰撞A车,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结合,最终造成B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假设,几日前A酒后驾车时被惯犯B碰瓷、敲诈,虽未造成B损害,但A权衡得失后选择赔钱了事,并怀恨在心。某日,A再次看到B碰瓷时,为报复而开车撞向B,B按往常情形以碰瓷故意与A车相撞,最终造成B伤亡。此类案情极为罕见,但基于法理仍有研究的必要。
2.案情分析。第一,此案情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交通事故,A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依时速、撞击力度、部位进行综合评价),B涉嫌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若B死亡,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整体来看,A、B双方的故意行为共同造成了B的人身损害,但基于碰撞强弱对比因素考量,机动车A方的故意撞击行为“贡献度”或作用力明显更大,因此不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规定以免除A方的赔偿责任;同理,也不能按照《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二款以免除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此时,应依《交通解释》第15条,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当在有责任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在赔偿范围内向A方追偿。交强险赔偿后,对于B方损失不足的部分,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进行责任分担。
(五)B基于违法阻却事由而故意阻拦A车并造成B损害案件的司法认定分析
1.基本案情。例如,交警拦车案,交通警察B在盘查涉嫌酒驾的A车时,A欲驱车逃离,B阻挡于车前,A加速冲撞导致B伤亡。再如,母亲拦车案,B的女儿被拐卖或绑架致A车内,B阻挡于车前,A为逃逸而故意撞击B导致其伤亡。
2.案情分析。交警的盘查是业务行为,其站在车前也是相对消极的阻挡行为,即便交警以警车或摩托车等机动车撞击违法逃离的A车,也属于在权力范围内的执法行为。如果造成交警受伤或死亡,则不适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免责条款,A车一方应承当全部赔偿责任;对于承保A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不适用于《交强险条例》第21条的免责条款,应按《交通解释》第15条承担赔偿责任。母亲拦车案同理。
四、结语
总体而言,本文所分析的交强险是否免责的各类纠纷案件在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争议。这就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中既要保护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一方(第三者)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又要依法保护机动车一方及相应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做到公平、公正。因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公布相关案情的指导案例或参考案例,以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类案同判”,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