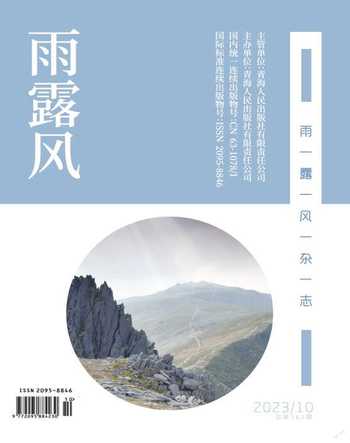传统题材与现代手法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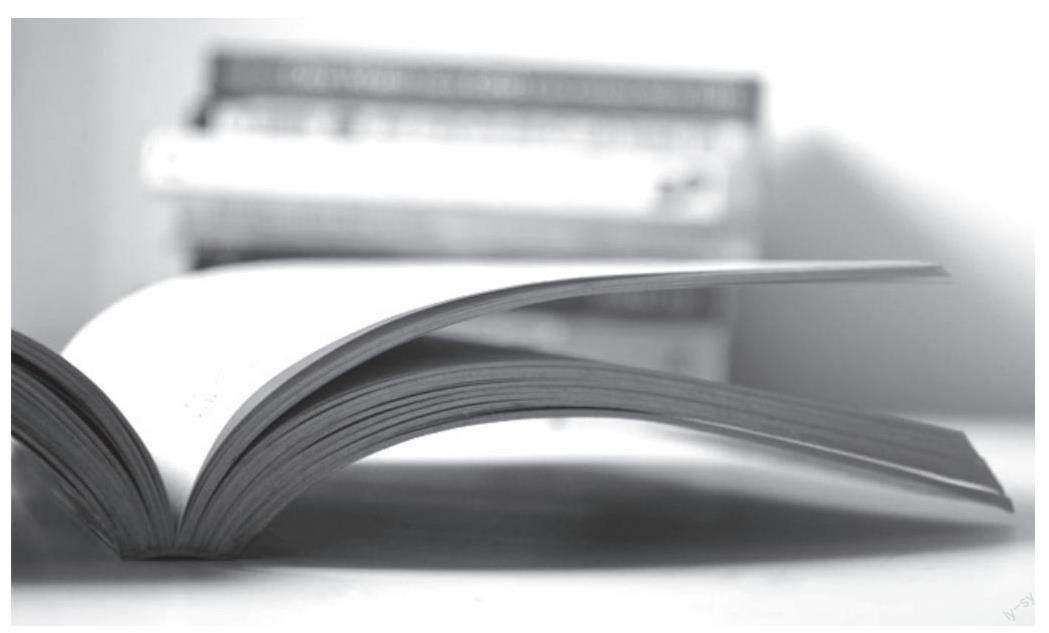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现实主义虽仍是文坛主流,然而身处动乱中的作家们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施蛰存便是其中之一。1928年至1932年,施蛰存先后联合刘呐鸥、戴望舒、穆时英等人,共同创办了一系列现代文学刊物,诸如《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属于中国文坛较早介绍西方现代文学、刊登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刊物,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作家、学者,都受到过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影响。
在传播和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的过程中,施蛰存也主动进行了多番实验性创作,他通过广泛地汲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阅读大量显尼志勒与霭斯里的心理分析作品,再结合上海十里洋场的文化生活体验,触摸到了当时都市大众的心理脉搏,创作了不少有关都市生活的心理小说作品。施蛰存的独创性在于,他将这些从西方获取的现代主义理论融合到现实主义写作之中,自然地就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派那种尖锐、彻底、反叛的内涵,又不同于同时期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形式。这种东西碰撞的融合使得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文学界广泛的关注,他本人也似乎找到一个现实主义创作桎梏中的突破口,加紧了这类作品的实验性创作,留下了诸如《石秀》《将军底头》《鸠摩罗什》《春阳》《梅雨之夕》等经典作品。
“施蛰存小说的现代描写体现在其笔下对于现代都市、心理有条不紊的细致抒写”之上[1]149,他要表达的是现代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所经历、所体会到的情感,他在创作的不同时期对于作品主题的把握有着不同的侧重,展现出不同时期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与改造程度的差别。
一、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手法的本土化试炼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传统文化功底的作家,浓郁的古典文化给予了他细腻含蓄的情感,这也就使得他在进行破旧立新的创作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文学之法,而是有意识地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手法融入到他所熟悉的中华传统中,将新鲜的现代主义融入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尝试对西方文学创作方法进行“本土化”的实验性创作。“他要挖掘被文明的超我所压抑了的力比多的力量”[2]177,其目的是要“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轨道”。[3]3
施蛰存在苏州、松江、上海等城镇的生活体验,使其早期创作带有一种伤逝的情调,同时,其自身所拥有的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以及对都市娱乐生活的积极参与,也天然提供了将文学审美同消费文化紧密融合的创作背景,再加上其对西方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手法的汲取,共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趣味。
(一)古典感伤风格“意识流”的结合
这种实验,最早体现在他小说中古典诗歌感伤情怀与现代文学意识流写作手法的结合上。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施蛰存的第一本小说集《上元灯》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风格富有江南情调,部分篇章里已经能显露出作者擅长描写情绪和心理变化。以《周夫人》为例,其风格在感时伤怀的同时还兼有心理分析小说的色彩,从“我”少不更事的少年视角审视和阐明周夫人隐含的欲望和“我”内心的活动。虽然整篇风格上还是属于现实主义作品,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作者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到了一些意识流手法,例如大段的内心独白、对心理活动流动的描写等,在其后更为成熟的作品《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中则将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加自然。
在《上元灯》之后,施蟄存扩大了西方心理分析小说及相关理论的阅读范围,包括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欧美意识流小说,尤其是奥地利心理小说代表作家施尼茨勒等,除了翻译和介绍此类作家作品,他自己也开始创作心理分析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先后收录于《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品》等小说集中。相较于之前《周夫人》里心理分析的初露端倪,施蛰存后期的《黄心大师》西方现代派色彩更重,运用了心理分析、潜意识、性心理等手法,不过施蛰存对此也有困惑。他在《关于〈黄心大师〉》中提到:“欧式小说中的一部分纯客观的描写方法,有时未免使读者感到沉重和笨拙。”[4]153因此他在小说中大量铺陈一些古典文献的记述,用中国传统故事形式,将评话、传奇演义等文体相融合,其风格依然保有古典叙事和感伤情怀,但字里行间渗透出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作者对历史人物自觉地省视与对其心理的大胆揣摩,显示出一种“纯中国式文体”[4]153的写作实践。
(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的融合
施蛰存的另一篇作品《梅雨之夕》,更能体现出作者对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融合的尝试。《梅雨之夕》的笔触带有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感伤情绪,小说结构依旧是遵循现实主义小说的框架。施蛰存本身受古典诗文的影响较大,因而他对于情绪的处理才会如此地感伤而不颓废。这种细腻、暧昧的氤氲之气又夹杂着主人公大段的心理独白和流畅的、不无跳跃感的潜意识流动,传统的写法加上现代的表现手法,使文章颇有新意。
与前几篇相比,施蛰存的《春阳》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体的精湛功力。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客观地、冷静地观察与描写现实生活,而“表现‘诚实的意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5]180,
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春阳》描写了主人公被压抑的情欲并叠加了心理分析,周遭事物在“强烈的主观意志下沾染了主人公的情绪”,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但这作品本身并不能被归类为一部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春阳》的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很完整的片段,不同于西方现代作品的无逻辑和支离破碎,故事有头有尾,逻辑清晰,这都深深打上了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烙印,“施蛰存很有意地选择描写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微妙诱惑力”[6]188,且巧妙地运用了中外优秀资源,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现实主义传统之上。施蛰存利用这些外来的文化改造中国传统,为现实主义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
二、对传统故事的现代解构
施蛰存还有一类很有特点的作品,那就是对传统故事的现代改写,典型代表是《鸠摩罗什》《将军底头》和《石秀》。这三篇作品都运用了精神分析的观点去叙事,也是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施蛰存通过现代的眼光观照古人,尤其是被历史传统认为的英雄人物,透视历史光环之下他们隐蔽的人性欲望和真实的心理状态,打破那种不食人间烟火、正义凛然、无欲无求的英雄形象,并试图还原某种历史真实。
这类作品虽然很大程度地借鉴和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手法,但仍然保持了作品“本土化”的描写叙述。例如施蛰存在试炼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同时还注重了对故事和人物本身完整性的描写以及保持传统的语言叙事,同时也注意尽量避免逻辑混乱,这样就使得中国的读者在被其中前卫的解读震惊的同时,并不会觉得有太大的语言陌生感和阅读障碍,以此做到将西方现代派技巧融合到传统题材中去。
(一)用西方现代派手法改写中国传统故事
这一部分作品虽题材取自传统故事,手法则多注重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大量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来对他们的动作行为、人性欲望、思维状况进行心理解剖。传统小说一般少有心理描写,施蛰存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更往深处探究根源。为了实现这种心理解剖,施蛰存往往为其小说人物设置各种心理的矛盾冲突。例如《石秀》《将军底头》《鸠摩罗什》三篇小说主人公都遭受着性欲的煎熬,不断的冲突与压抑最终引发人物迷乱的幻想和心理异变。
施蛰存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运用到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中并借由其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对西方现代理论巧妙的化用是施蛰存的特色。小说的整个构架都没有脱离传统小说的主要情节范畴,但这种不同的解读和描写,使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脉络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延展,这些古人具有了现代人的气息和情绪,在长期的性压抑下出现情绪、人性的异变。除了大量描写人性、人欲的冲突,施蛰存通常还会大量描写主人公的幻想,他们被压抑、被克制的欲望通常都能在幻想中得到释放和满足,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关于“白日梦”的解释。
审视其整体创作,施蛰存在创作上对西方意识流手法和相关理论的吸收与应用是有所取舍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例,弗洛伊德理论认为“性本能”是一种根本动力,社会关系和个人本体很难左右这种性之本能。施蛰存并没有这么极端,他的心理小说兼顾了都市人心理、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被欲望驱使,又被感情和其他生活影响,进而呈现出一种对现实的观照,这也就显露出他的心理小说通常呈现的现实主义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特点,通常是调用“各种感官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描写十里洋场里的都市人不宁静的个人情绪、神经质等带来的心理创伤和感觉聚焦,这一写法有着现代派的深深烙印。
(二)多重内涵的解读
与传统叙事不同,施蛰存对他的历史心理小说进行了多重内涵的解读。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很难得出一个确切、单一的主旨,一些意象似乎具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但是每个人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详观这几部历史小说作品,我们不难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在这几部小说结尾的处理上和对人类身体的关注上,施蛰存是别有用心且异于他人的。《将军底头》似乎最受显尼志勒“爱与死”这个主题的影响,小说中将军最终以一种诡异的身体死亡与意识弥留不同步的方式,完成了一系列的幻想,對于将军死去的身体提着头,在河边与少女对话的情节,不同的读者可以获得不同的启发。这个结尾充满歧义和被多重解读的内蕴,可以理解成一种将军的自我惩罚,也可以理解成爱欲对理智伦理的胜利,而结尾处少女的嘲笑也意味深长,这似乎是对弗洛伊德“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场合,比在这种变异里,更能显示出爱情的法力无边来”[7]41这一说法的回应。
而《石秀》的结局则更加触目惊心。《石秀》这篇小说不仅展示出了女性身体被虐待的极端描述,展现了对于人的疯魔、变态行为的冷静,且在更深的内涵中表现出一种隐含的人的“未满足”——需求的失衡导致的性变态,也使这部历史小说作品充满了现代感。
三、结语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是独特的,它的独特性来源于作者丰富的创作实验和广泛的阅读,既有从中国传统所汲取的影响又有来自西方文化的感染,种种的因素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气息,两者无法割裂也不能合体,但却各自绽放着光彩,充满了诱惑力。
施蛰存本人也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自己的写作受施尼茨勒、弗洛伊德、艾里斯的影响很大,他的心理小说里对人物心理和意识流动的描写来自施尼茨勒,对性心理和性变态的描写来自弗洛伊德和艾里斯。[8]175施蛰存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可以展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吸取和整合,从最开始的浅尝辄止到其后剑走偏锋的实验性创作,再到最后对中外优秀资源的完美融合,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所获得的成果都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都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些创作背后,是作者的用心良苦,同时也使得后继者有了一个可供参考与发扬的典范。
作者简介:叶凌宇(1990—),女,汉族,湖北宜昌人,助教,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注释:
〔1〕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2〕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N].文汇报,1983-10-18(3).
〔4〕施蛰存.文艺百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5〕周毅.西方文化历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6〕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2.
〔7〕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