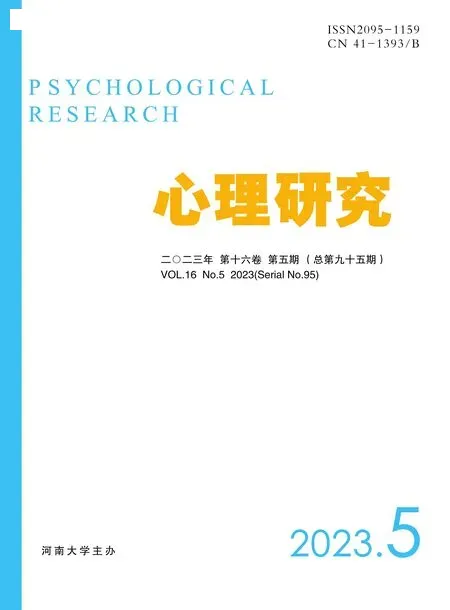领导力研究的中国化:CPM 领导理论的探索与启示
李 明 凌文辁
(1 上海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上海 200233;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
1 引言
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呼唤具有更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领导者, 领导心理学也因此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一方面,领导心理学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开展领导理论研究并进行总结和回顾;另一方面,领导心理学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现实,思考并解答领导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这些都需要汇聚研究者们的智慧,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共同探讨我国领导力研究的相关议题。 而作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理论研究本身也应该来源于实践,并最终反馈服务于实践。从20 世纪初开始,国外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切入点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领导理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凌文辁突破并发展了国外领导行为理论 “工作取向”和“人员取向”的两维结构模型,将领导者的“个人品德”作为文化特异性因素纳入到中国领导概念中来,提出了CPM 领导理论。 CPM 领导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国外领导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自身文化特征,运用行为科学方法所建立的新的领导理论架构,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化研究的特征。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需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些特征恰恰是CPM 领导理论提出和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开展中国化领导力研究,就是要以中国的人、中国的领导现象、中国的发展阶段为研究对象,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思想遗产,总结中国经验和吸收外国先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采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凌文辁, 方俐洛, 2000)。本文对35 年来的CPM 领导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CPM 领导理论的中国特色及其创新价值,展望领导力研究中国化的未来方向。希冀能够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新时代中国领导力研究中来, 探索和扩展我国本土领导力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2 CPM 领导理论研究的探索与回顾
回顾CPM 领导理论35 年的研究探索,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是理论的提出和验证阶段;二是21 世纪的前10 年,是理论的再验证和补充讨论阶段;三是2010 年之后关于CPM 领导理论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的探讨。
2.1 CPM 领导理论的提出和验证阶段
2.1.1 CPM 理论的领导概念及其动力学原理
凌文辁于20 世纪80 年代早期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CPM 领导行为模式假设:中国的领导行为评价模式应该是由C 因素(character and morals,个人品德)、P 因素(performance,绩效达成)和M 因素(maintenance,团体维系)三方面的因素构成。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收集评价项目并编制了CPM 问卷, 从1984 年到1986 年间进行多次反复预试和修改, 并在国内最早采用因素分析等行为科学实证方法来检验这些项目。最后,获得了信度和效度都比较理想的CPM 量表(凌文辁 等, 1987)。 P 因素和M因素反映着与西方类似的管理共性,而C 因素则反映着管理中的个性,即文化特异性(Ling, 1989)。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时代背景下,CPM 领导理论突破并发展了领导行为理论的“任务取向-关系取向”两维度模型, 将个人品德因素作为一个文化特异性因素纳入到领导概念中来,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李明, 毛军权, 2015)。
1991 年,凌文辁应《中国人·中国心:人格与社会篇》(迈进中国本土心理学新纪元研讨会论文集)主编杨中芳的邀约,对CPM 领导理论的动力学做出了解释。 CPM 领导理论的动力学意义就在于它推动了组织机能的执行,即实现组织目标,维系组织的生存与发展。P 因素是完成团体目标的机能,反映着领导者的工作能力;M 因素是维系和强化团体的机能,反映着领导者的人际能力。 P 和M 可以看作是领导者执行领导职能过程的直接影响力,而C 则是领导者的间接影响力。 三者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P针对的是工作,M 针对的是他人,C 针对的是自己。一个领导只有正确地处理好对工作、对他人、对自己的关系,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领导作用 (凌文辁,1991)。 C 机能对P 机能和M 机能起着一种增幅放大的作用,它们之间不是相加的关系,领导效果(E)应该是C×P×M(凌文辁, 2000)。 当然,这种动力机制只是当时的思辨性推理, 并未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证明。
2.1.2 中国人内隐领导理论对CPM 模式的验证
外显的行为理论是基于对领导者外部行为的观察和经验所进行的研究, 而内隐领导理论则是来源于人们内心中关于领导的概念化。对于“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往往是人们头脑中的内隐印象。 1988 年,凌文辁等研究者开始探讨中国人内隐领导理论的因素结构,并考察它与外显理论的CPM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无论在因素结构还是在内容上, 中国人对领导特质的概念知觉与美国人都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内隐领导理论区分了四个领导特质因素:个人品德、目标有效性、人际能力和多面性。其中,前三个维度与CPM 理论的C,P,M 三个因素是非常吻合的。 即使是第四个维度“多面性”的内容,也被P 因素和M 因素所包括,即“多面性”特质既有助于组织目标的达成,又有助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 内隐领导理论的结构与外显领导理论的领导行为评价CPM 模式的三因素十分吻合(凌文辁 等,1991)。可见,无论是外显的领导行为评价模式,还是中国人内隐领导概念的研究,都证明CPM 领导行为模式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对领导进行评价的有效模型(Ling et al., 2000)。
2.2 CPM 领导理论的再验证和补充讨论阶段
2.2.1 中国人内隐领导理论的再探讨
21 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外来的管理思想和文化也进入中国,中国人关于领导的概念和看法是否有所变化,对领导行为的评价模式是否发生了改变? 中国人内隐领导理论的再探讨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领导概念或者说中国人对领导行为的评价模式并没有变,仍是由个人品德、目标有效性、人际能力和才能多面性四因素构成。 说明在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领导者的评价模式并无根本性的改变(林琼等, 2002)。 但是,每个因素中的项目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更替。 这说明,中国人的领导概念在“不变”中又有“变”。 “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心理编码”,即领导概念的结构模式,而“编码”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2.2.2 其他相关研究的补充探讨
在CPM 领导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研究者们还开展了关于德行领导、 破坏性领导、 领导者的执行力、中国人的追随特征等相关议题的研究。
2008 年,凌文辁等人开始了“德行领导与破坏性领导”课题研究。 “德行领导”是对CPM 模式中C因素进行的更深入的探讨。 而破坏性领导则是德行领导的对立面,从一个反面的视角证明了C 因素的重要性,其核心是“恶德”。 一个品德坏的领导者,能力越强,破坏性就越大。 这就表明,C 因素在领导模式中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领导者执行力的相关研究(柳士顺, 2007)对P 因素和M 因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而有关追随力的研究则获得了同CPM 理论相对应的“领导者品行”“团队维系”和“个人绩效达成”三维度追随动机模型(原涛, 凌文辁, 2010)。 领导与追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形象,应该是追随者所要追随的目标。这就从一个逆向的角度证明,CPM 模式是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的领导力理论。
2.3 CPM 领导理论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探讨阶段
CPM 领导模式的提出,主要是服务于定量考核领导干部这一实际需要, 加之当时国内统计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并未对CPM 理论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开展更深层次的探讨。 思辨性理论的提出有待实证研究来支撑和证实。
2.3.1 CPM 领导理论的动力机制研究
研究者通过情境模拟实验探讨了CPM 模式三个因素对下属行为态度的影响及其动力机制。 结果显示,在对下属的追随意愿、上司承诺、工作动机及对领导的满意度产生影响时,C 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大。 而且,在P 因素和M 因素影响下属行为态度的过程中,C 因素确实发挥着增强型的调节作用(李明等, 2013)。 具体而言,在对追随意愿和上司承诺的影响上,C 机能对P 机能起到了增强型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对追随意愿、上司承诺和领导满意度的影响上,C 机能对M 机能起到了增强型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领导者C 机能较低的情况下,即使P 机能增强,对下属的追随意愿和上司承诺的影响变化并不大;而在高C 机能情况下,随着P 机能的增强,下属对领导者的追随意愿和承诺会有较大的提升。 同样地,在领导者C 机能较低的情况下,即使P 机能提高,对下属的追随意愿、上司承诺和领导满意程度的影响变化并不大;而在高C 机能情况下,随着M 机能的增强,下属对领导者的追随意愿、 承诺和满意程度就有了较大的提升。研究结果验证了CPM 领导理论的动力学原理,为“C 机能对P 机能和M 机能起着增幅放大的作用”这一思辨性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
2.3.2 CPM 三因素影响作用的比较研究
李明和凌文辁(2011)研究表明,C 因素在对下属行为态度产生作用过程中发挥了最强的影响作用。在对和谐组织的影响上,典型相关分析和因果关系判断的认知图式结果全面解释了CPM 领导行为对和谐组织的影响作用,以及C 因素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李明等, 2012)。 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领导者的品德魅力确实发挥着最强的影响作用。
2.3.3 CPM 领导行为对下属行为态度及和谐组织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明和凌文辁(2012)得出了CPM 领导行为通过信任上司和情感承诺对员工利他行为和工作投入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研究还分析了情感承诺和组织心理所有权在CPM 领导行为与和谐组织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及其影响路径(李明, 2015)。 这些关于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的探讨,将CPM 领导理论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描绘得更加完整和全面。
3 CPM 领导理论的中国特色
3.1 CPM 模式是领导行为评价的中国模式
CPM 领导理论提出了新的领导概念,并对CPM概念的动力学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探讨, 检验了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性。 CPM 领导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国外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文化背景而建立起来的, 是领导理论研究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CPM 领导评价模型的构建是从外显领导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领导行为评价模式。而两次内隐领导理论研究则探讨了中国人内心中关于领导特质的概念。这就从内外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品德”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评价领导者的一个关键因素,CPM 模式是领导行为评价的中国模式。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崇尚“修己以安人”“内圣外王”, 在管理实践中强调领导者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德治家、以德治企、以德治国。在选人用人实践中,更加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对组织、对国家尽“忠”,对长辈行“孝”,对同事行“仁”和“义”。 所以在中国人的领导风格上,就尤其强调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做魅力型的“德行领导”。
3.2 CPM 模式体现了中西方领导评价模式的差异
任何领导理论的提出都不可能脱离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人的管理上强调“法治”,而中国在对人的管理上则更加注重“德治”。 这首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影响的。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刚正不阿、公私分明、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倍加称颂,而对“缺德”之人深恶痛绝。这种道德伦理观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和评价标准。
另外,中国人对领导者道德品质有独特的要求,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开明的领导者身上,期望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做领导,从而抵消可能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带来的一些弊端。这就使得领导行为评价的中国模式同西方模式具有明显的差异。而CPM 领导理论恰恰反映了领导行为评价模式的中国特色,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
4 CPM 领导理论研究的创新价值
4.1 CPM 模型对领导概念的突破
CPM 领导理论突破并发展了领导理论的任务取向-关系取向两维度模型, 并将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因素作为一个文化特异性因素, 纳入到领导概念中来,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CPM 领导模式的模型建构及两次内隐领导理论的检验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人品德” 是人们评价领导者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这就是CPM 领导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创新和突破。 领导力不仅是领导者所代表的组织机能的表现, 而且也是领导者个人品德的外在表现。 而在21 世纪之前的西方领导理论中,几乎看不到领导者个人品德的影子。
2000 年,樊景立和郑伯壎提出了家长式领导的三元论,即“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两个领导理论,CPM 理论和家长式领导都强调道德品质是中国文化背景下有效领导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这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 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领导方式上的相似性。 进入21 世纪后,国内有关领导力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 一是将国外一些新的领导理论概念引进国内进行本土化的探讨(李超平, 时勘,2005),另一方向是关于管理者和领导者胜任特征的探讨(王登峰, 崔红, 2006)。 这些关于领导力的探讨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非常重视“个人品德”因素。这已成为国内领导理论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并逐渐形成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领导新理论——德行领导理论(务凯, 2014)。 在CPM 领导理论提出35年后的当下,我们仍然认为,在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实践中,必须对领导者“个人品德”方面的特征给予极大的重视。
4.2 探索了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路径
在20 世纪80 年代行为科学开始传入我国时,CPM 领导理论研究最早在国内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来开展领导学实证研究。本文对CPM 领导理论系列研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这些实证研究综合运用了量化研究中的心理测验法、 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情境模拟实验和认知地图技术等研究方法。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 有效地弥补了单一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高了CPM 领导理论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使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更强,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领导力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思辨性的推演和论证上, 而是要将质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使得相关研究议题“扎得下根、 立得住脚”。 通过行为科学的微观数据研究,帮助人们从一个新的科学视角来理解“为政以德”“德才兼备”等政治学和哲学命题。 这一系列领导理论研究新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范本,希望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可借鉴的研究经验。
4.3 彰显出中西方领导理论中的一些共性特征
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管理哲学的多样性,CPM领导理论承认管理模式的特异性, 主张在不同文化和国家中,领导方式既有共性的成分,也有个性的成分。前者是由社会生产活动管理的共性所决定的,后者则是由其所属的文化(国情)的差异性所决定的。进入21 世纪后,随着西方社会和企业中一系列道德丑闻和弊案的曝光, 美国学界开始重视领导者的道德问题, 于是出现了诚信领导 (authenticity leadership)、道德领导(moral leadership)、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 和破坏性领导(destructive leadership)等领导新概念的探讨。 这一新动向正是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揭示领导者品德对于领导效果的影响作用。西方领导理论终于开始重视和填补之前“品德因素”研究的缺位。 基于文化差异性提出的CPM领导理论,反而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共性特征。作为中国特异性因素的领导者个人品德, 逐渐被国外领导理论所重视和吸纳。由此以来,领导理论研究便开始出现了特异性学派和普适性学派的折中融合,即无论是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者, 还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者, 都需要正确地处理好对工作、 对他人、对自己的关系,不仅仅要发挥直接影响作用,更要重视间接的影响作用。
4.4 CPM 领导理论是综合性的领导力理论
纵观领导理论的发展轨迹, 大致呈现出从个别论到综合论,又从综合论向分解论发展的态势。这也许就是西方科学研究的思维逻辑, 即先从分门别类的个别问题(现象)进行分析,再将它们综合起来探讨。 领导力理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外扩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该理论不断实现要素整合、不断系统化的过程(柴宝勇等, 2021)。而当综合的东西没有新意时,又去探讨一些新的个别问题。针对领导现象的探讨,也是先从特质论、风格类型论发展到行为论、权变论等综合论,现在又向探讨领导模式的某个侧面的分解论回归。 西方国家的学者缺乏综合的整体观,习惯于分门别类的科学思维来探讨问题。因此, 他们所提出的领导理论往往只探讨领导的某一个方面特质或某一部分的行为风格。
而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从宏观到微观, 从整体到个体,从综合到分解。 CPM 领导理论的领导观就是综合论。因为领导力就是影响力,领导效能是综合力量的作用结果。无论是单一的直接影响力,还是间接影响力,都不能发挥完整的领导效果。 不过,对于研究而言, 为了探讨某种影响力在领导活动中是否发挥影响效果, 则可以控制其他影响力的作用而单独对其某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出现一些分解论(如诚信领导、德行领导、破坏性领导等),也是可行的。但在应用领导理论去指导实践时, 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力。 CPM 领导理论不仅强调领导执行力方面的内容,还突出了更具影响效果的品德魅力因素,是将行为理论和特质理论有效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领导力理论。
5 对中国本土领导力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5.1 不断丰富本土化领导构念的探讨
现有针对中国情境下领导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情境提出的领导理论,如变革型领导、真诚型领导、公仆型领导等,而对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领导行为的探讨和研究较少(王辉等, 2023)。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沉淀了丰富的政治、社会、经济管理经验和领导模式。 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重视关系(guanxi)”“辩证思维”“以德为先”“中庸之道”和“无我状态”等领导理念值得深入挖掘。 因此,要继续扎根中国情境进行嵌入式情境研究, 探索实践中那些被现有主流理论解释不了甚至相悖的现象, 更新理论以解决管理困境和领导现象, 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张志学等, 2016)。 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时代背景下,以及充满变革的组织情境下,包括CPM 理论在内的不少领导构念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 因此,将中国文化理念、既有领导构念嵌入到当下管理情境中来,将以扎根理论、案例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同以量化测评、实验研究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可以为领导现象提供更为丰富、准确的内涵界定和测量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当下最典型的“中国特色”。 中国本土化领导构念的探讨,必然要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资源, 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下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的治理理念、领导方略、领导制度、执政方式、领导者人格品质和精神涵养等。加强领导干部领导力的研究, 可以有效拓展以企业组织领导者为研究重点的西方领导力研究对象范畴(陶好飞等,2022)。通过构建体现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的党政干部领导行为评价模型和工具, 可以有效丰富和发展中国本土领导理论模型。
5.2 重视领导理论的多元文化比较研究
凌文辁等(1991)开展了内隐领导理论的中美差异研究,发现中美之间在内隐领导的因素结构、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之所以开展中美之间的比较, 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的思维模式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中美之间的对比能够集中反映中西方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上的差异(王辉等, 2023)。如西方语境下提出的“伦理型领导”,同中国情境下领导的德行垂范 (morality)及其衍生的德行领导(moral leadership)虽然语义接近,但也要注意概念的区分(孙健敏等, 2017)。中西方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在解读西方伦理领导、道德领导理论时,需要考量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公平正义、利他主义、正直等领导品质的特定内涵。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德行领导, 需要同儒家思想中的仁政、 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利他价值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结合起来,这些都凸显了道德领导的鲜明特征。在开展本土领导力研究时,需要加强国别、文化的比较,对相关的文化构念进行提炼与总结(段锦云等, 2020)。需要进一步增强多元情境对比意识, 深度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特定领导概念可能产生的不同建构,在充分对比检验的基础上形成本土化领导理论。
5.3 多侧面探索领导行为的前因后果变量
关于领导有效性的探讨,除了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被广泛关注的经典结果变量, 近年来创新创造及员工建言行为、工作投入等研究显著增多(杨朦晰等,2019)。 实际上, 作为实施方(actor)的领导者和接受方(receipt) 的下属或团队共同构成了领导过程, 但多数研究往往关注员工个体层面的结果变量, 少见对团队产出和领导自身方面的关注。 今后可以多侧面探索对新的结果变量的影响, 如领导者行为对自身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对团队和组织层变量的影响等。此外,还要关注对领导行为前因变量的探讨。将领导行为的变化趋势作为因变量,探讨哪些因素会导致领导行为的变化情况 (董小炜 等,2021)。如从个体特质、互动关系、组织文化等角度出发,对领导行为的前因变量进行探究和揭示,可以丰富对领导过程的认知, 有助于理解领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近几年的一些研究也开始揭示正面领导行为对员工、组织乃至领导者自身的负面影响。如研究者们对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授权型领导等正面领导行为的消极效应展开了研究 (凌茜等, 2022; 王震等, 2019)。 考察德行领导等积极领导风格对他人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消极效应,提供了一个探究领导有效性的新视角, 可以更为全面地评估领导风格的作用,丰富和深化领导理论研究。
5.4 深度揭示领导作用发挥的机制“黑箱”
CPM 领导理论作用机制的探讨,特别是三因素动力机制的探讨, 深刻揭示了领导行为有效性发挥的内在动力机制,证明了个人品德、绩效达成和团体维系三因素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鉴于此,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领导作用发挥机制的探讨,不仅要考察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也可以尝试关注领导行为产生作用的内生动力机制, 深化领导作用产生的驱动机制及边界条件,更加准确、全面地揭示领导作用的发挥过程。在具体调节效应的考察上,也可以重点关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典型情境变量的影响,如权力距离、面子导向、传统性、中庸思维等边界条件,这样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而在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领导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对于变量间关系的解释,可以采用更为严格的实验法和纵向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影响机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王雁飞等, 2021)。也有研究者建议关注领导行为的趋势研究和波动研究,用动态的视角来研究领导行为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McClean et al., 2019; 董小炜 等, 2021)。 未来领导理论研究也应关注领导活动的复杂发展过程,根据研究主题采用多层次、多方法、多数据来源的研究设计,提升作用机制研究的解释力和生态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