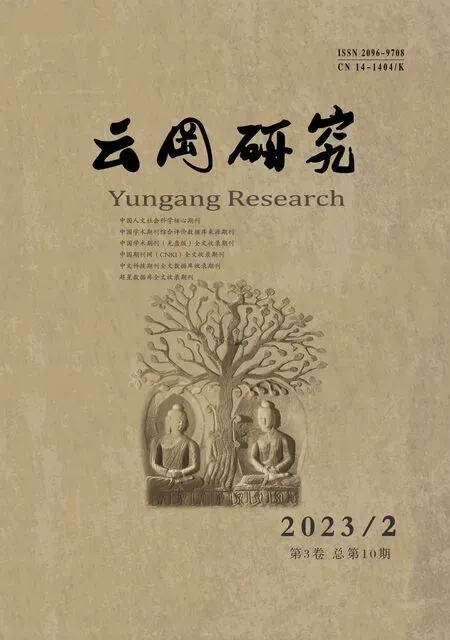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与北魏佛教的中国化
刘世明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艺术杰作,也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北魏民众许愿祈福,于造像的同时在石壁上留下了大量的发愿文字,我们将其称作“造像题记”。1938-1944 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 次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51-1956 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根据调查资料写出《云冈石窟——西历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窟院考古学的调查报告》,其中载有北魏造像记28条。之后,又有几则题记被世人发现。2014 年5 月,员小中先生出版《云冈石窟铭文楹联》一书,收录北魏造像题记共35 条。①本文所用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的第一手资料来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二卷·附录·云冈金石录》,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后来新出或补正的题记材料出自员小中《云冈石窟铭文楹联》、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等著作。这些题记记述了1600 年前的民众生活与宗教信仰,是北魏佛教中国化的真实写照。现在,就从以下三方面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儒释合流
北魏佛教相当盛行,自君王至庶民,大多对其信仰尊崇。人数“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卷114《释老志》,P3048)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曾说:“佛教成了北魏的国教”,[2](P536)诚为的论。只不过,印度佛教来到中国,就要适应中国。《魏书·释老志》言:“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1](卷114《释老志》,P3026)此借用儒家理念比附译释佛教词汇,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格义”之法。于是,西来佛教逐步儒学化。从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孝”观念的延伸与拓展。印度佛教讲求出家、出世,这与我国儒家伦理不合。《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3](P292)《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4](P4)而僧人削发毁身、弃家绝后,实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北魏主簿李玚就说:“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1](卷53《李孝伯传附玚传》,P1177)他认为佛教是弃家绝嗣、堙灭大伦的鬼教,因此有违于中国的孝道。所以说,佛教要想在中国谋发展,就需要从“孝”字上做文章。而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恰恰能够看出这种改变。如《佛弟子惠奴造像记》言:“弟子惠奴□将父平安到京,愿愿从心,所求如愿。”[5](P6)佛教徒祈求父亲平安,是一种现实功利的愿望,当然也是儒释调和的表现。除此,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最引人注目的“孝”文化现象,是对七世父母的关心与祈祷。如“愿义诸人、命过诸师、七世父母、内外亲族,神栖高境,安养光接”[5](P4)、“弟子王□为七世父母发心”[6](P46)、“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愿托生西方”[5](P5)等,皆是。七世父母,在佛教中指的是现在世和过去六世的父母。这样,祈愿者所孝敬的对象与时空都在发生迁移。由现世父母,推向七世祖先,实在是一种革新的大孝。云冈石窟第38 窟窟口上方有一则《吴氏造像造窟记》,其言:“寻吴氏家先,忠和著□,□孝并举。至子孙兴茂,绍隆家嗣。”[5](P6)从往世祖先到后嗣子孙,都成了信徒刻石祈福的对象。而这里所说的“寻吴氏家先”,乃是追孝供养,体现了北魏民众认祖归宗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根祖文化。将“孝”观念延展至此,佛教初传之人,恐不敢想象。另外,云冈石窟还有一处特殊的造像题记,也值得关注。此题记位于第11 窟明窗东壁,上刻“道俗七妻,同为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原、亡男思颜、亡女阿贲,造释迦文佛石像三区”[7]的字样。“道俗七妻”,不仅说明出家人可以结婚,也从侧面展现出北魏一夫多妻的社会风俗。《魏书·临淮王传》曰:“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1](卷18,P423)由此可推,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中的“道俗七妻”现象,是北魏阴教、继嗣的缩影,反映了彼时存在的一种佛教孝礼文化。于是,借佛言孝、据佛行孝,便成了北魏佛教的信仰常态。
其次,忠于朝廷,服从王权。佛教初来,僧人对帝王双手合十,不行跪拜之礼。东晋朝廷曾于此事,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尚书令何充以为“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治也”,[8](P1641)“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9](P667)对此,车骑将军庾冰持反对态度,并认为沙门应尽敬王者。之后,太尉桓玄又与僧人慧远展开论辩,南朝于此之争,从未有过停歇。而北方,则不然。十六国时期的道安就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0](P241)到了北魏王朝,皇帝更是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权威,决定着佛教的存亡。诚如沙门法果所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卷114《释老志》,P3031)其以拓跋珪为当世如来,拜帝即是礼佛。可见,佛教欲在北方推行,则必须依靠皇权、接受国家的管制。纵观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到处都是信徒们对皇室成员的赞颂以及对北魏朝廷的忠诚。如“皇上圣历穹宇,化超唐虞”[6](P40)“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下及七世父母”[5](P5)“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踰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5](P3-4)等等,皆属此类。他们称颂君王、忠于朝廷、为国兴福,不仅是爱国情感的外露,更希图依靠政权的势力来保障佛教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北魏君王也要借助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来治理天下。《魏书》言:“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1](卷114《释老志》,P3036)“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1](卷114《释老志》,P3037)据此可推,云冈石窟的第16-20 窟(昙曜五窟)属于皇家工程,其中的佛像乃北魏帝王的化身,百姓们朝拜大佛,即是参拜君王。佛体帝身,帝佛一体,成了佛教中国化最好的见证。故而北魏一朝,国家以佛治政,佛教服从王权,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最后,以慈树善,依德定制。原始佛教讲究“慈悲”,以“慈”予众生快乐,以“悲”来拔除痛苦,似乎并不着重强调“善”与“德”。而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却对此多有描述。如《为吴天恩造像记》“含生有识,莫不兴慈以树善,积福以资常”[6](P40)、《佛弟子造像记》“发心造多宝像一区,善愿从心”,[6](P46)等等。由慈到善、以善积福,体现了北魏宗教儒佛融通的情形。儒家孟子主张“性善”,其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3](P331)佛教来到中国,以“因果报应”之说与之附合,讲求善恶有报,劝人弃恶从善。北魏君王拓跋弘信仰佛教,曾捕获鸳鸯鸟一只,闻其悲鸣之声,竟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1](卷114《释老志》,P3039)魏收将此事记载于《释老志》中,以明佛教“不伤生”之义。除此,中国儒家思想也特别看重德行。《尚书·洪范》言:“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11](P465)其将“攸好德”视作“五福”之一,形成了中华文化“五福临门”的幸福观念。云冈石窟第11 窟、第17 窟的东壁刻有“德合乾坤”“造像功德”等字样,以说明行善积德合于天地自然之规律。君王有德行,国家方有德政,这是千年不变的事实。北魏沙门统惠深曾对宣武帝元恪上表曰:“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1](卷114《释老志》,P3041)宣武帝立刻应允。可见,德性不仅是僧人修行的目标,也是僧制拟定的准绳。以德定僧、依德行法,是北魏政治与宗教共有的特点。
在北魏,祈愿不离忠孝,性善即是慈悲,德合乾坤,政教一体,最终形成儒释合流的宗教模式。当时信奉佛教者,如高允、杜弼、李同轨、卢景裕、刘献之等,大多为儒生。儒佛会通之事实,可见一斑。从北魏一朝历史来看,佛教始终服从于王权,也遵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因为中国的土壤与印度不同,佛教要想在中国生存,就必须适应中国。
二、佛道混同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汉人信汉教,胡人信胡教,被视作常理。但之后,作为东胡一支的鲜卑拓跋氏,却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无比地尊崇。于是,北魏时期的佛教,又有了道教化的印迹。这里,暂从两方面对其进行阐释。
其一,语词共用。纵览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处处都有佛道混用的词语。如《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中的“道教天下”“道心日隆”“道风堂扇”等。其它诸如“道玄”“玄者”“道人”等词语,也在题记中频繁出现。而最引人注目的,还要说是一个“灵”字。陈寅恪先生说“‘灵育’与‘道育’‘灵宝’之类,皆是天师道之教名。”[12](P123)此字,在云冈石窟现存35则造像题记中共出现七次,分别记作“灵征”“光灵”“灵福”“灵虑”“□灵”“灵姿”“灵相”。除此,云冈石窟第6 窟后室南壁的一则题记,也值得关注。该题记现只存“道昭铭记”四字,见者不知何解。多数人认为,此是北魏诗人、书法家郑道昭所留。若真如此,我们又可见到云冈石窟的佛道混同现象。因为郑道昭信奉道教,其所作之诗,如“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云路沉仙驾,灵章飞玉车”“郑公乘日至,道士投霞归”[13](P2206-2207)等,皆求仙访道之句。其刻字于云冈石壁之上,可见当时士人佛道并尊之信仰。
在北魏时期,还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即佛教来源于道教。太武帝拓跋焘曾说:“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1](卷114《释老志》,P3034)其以佛法为老庄附益而成,并非实有。此说虽不符合事实,但却是那个时代某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例如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中就有七首《化胡歌》,所谓“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刚身。”[13](P2249)彼时民众,确有多人认同“老子化胡”的传说。这里的“化”,亦可释作“庄周化蝶”之“化”,即“变化”。《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屠”,[14](P1082)就是此义。老子化为浮屠,佛教源于道教,是格义之法,而非贬低佛教。从另一角度来看,佛教还须借用“化胡说”在中华大地上进行传播。因此,佛教的道教化,曾在一定时期帮助其融入中国,这一点不容忽视。
其二,观念混同。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刻有“证悟无生”“生死永毕”“生生之处”等有关“生死”的语句。此类观念与道教“不生不灭”“生死齐同”“返本还元”理论,相近相通。除此之外,《吴氏造像造窟记》中的“真容冲隐”“卷舒待时”“真容之在于虚空”[5](P6)等,皆具有道教意味,兹不赘述。正如孙昌武先生所言,“北方少数民族国主支持的佛教,注重神通、预言、巫术等,还带有浓厚的‘道教化的佛教’性格”。[15](P171)《魏书》将“释”“老”归入一“志”,并言“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1](卷114《释老志》,P3052)可见,北魏佛道混同观念之深入人心。然而,观念相融、信众相通,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信奉天师道的拓跋焘,以帝王之力坑杀僧人、焚烧图像及佛经。虽主要原因在于崔浩的怂恿,但其以道灭佛、指斥佛教为鬼道的行为,亦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以中原统治者自居,将鲜卑帝国视作正统的王朝。其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极力推崇中华本土的宗教,当然也是鲜卑汉化的标志之一。
于是,北魏佛教与道教在相融相斥中逐步发展,加之儒学观念的强力渗入,终于形成了“三教一体”的中华宗教模式。楼宇烈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16](P152)这其实也可视作北魏宗教的总体特征。
三、入世实行
北魏佛教不空谈义理,而是重视现实精神、讲求入世实行。这一点,与南朝佛教有本质上的区别。从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着眼,北魏佛教的实践性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教化功效。佛教本是净化心灵、提升道德的一种宗教,民众信仰佛教大多希望能够离苦得乐、摆脱烦恼。而我们遍读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则会发现“道教天下”“利润当时”等文字。即以佛教为教化之道,通过佛法的实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利益。这一点,《魏书》有明确的记载。如“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1](卷114《释老志》,P3035)“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1](卷114《释老志》,P3030)等,皆如是。这样,佛教就发挥着辅助王化、教导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从内心修持到服务社会,这种功能的转变,正是北魏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因为拓跋鲜卑帝王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要想在被征服地区扎根立足,就必须对当地的百姓实施羁縻怀柔政策。于是,其选择佛教来消解对抗、安抚民心,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当然,佛教虽是北魏统治者治理天下的精神利器,但百姓也确实需要依靠它来广种福田,希望将来得到福报。于是,北魏王朝佛教的教化功能充分展现,其效果正如《魏书》所说,“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1](卷114《释老志》,P3030)
第二,戒行合一。戒行,即“恪守戒律的操行”。[17](P183)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就常将“戒”与“行”合而为一,来表达民众对佛教理论的恪守与践行。如《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中的“道心日隆,戒行清洁”[5](P4)、《比丘尼惠定造释迦多宝弥勒像记》中的“现世安稳,戒行猛利”[5](P5)等,皆属此类。这是北魏佛教戒行观的特征,即重视凿窟、造像、立塔、建寺等实践行为,将心中虔诚的信仰落实到宗教活动之中。云冈石窟,便属于北魏造像的代表。清王昶在《金石萃编·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说:“造像立碑,始于北魏……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18](P657)而造像之人,或为帝王、官吏,或为僧尼、大众,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这种通过造像实践来宣扬佛教经义的行为,被称作“像教”,在北魏可说是风靡一时。如《洛阳伽蓝记》所载:“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景明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19](P99)如此规模庞大的行像队伍,难怪“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而“戒行合一”的另一大表现,则是禅修。云冈石窟本是习禅僧昙曜率先开凿,故佛像中有许多跏趺造型。如第17窟交脚弥勒的莲花跏趺坐,第19窟东、西耳洞的善跏趺坐以及第20 窟露天大佛的结跏趺坐,等等。除此之外,云冈石窟还有许多用于坐禅的小型洞窟,都是当时信众的禅修场所。而禅修的戒行方式特别简单,一是观想,二是口诵。即通过瞻仰佛容、口念佛号,达到清心入定的境界。此由1956 年云冈石窟第20 窟附近出土的《比丘尼昙媚碑》,即可见得一斑。碑文曰:“思恋灵福同,拟状金石。冀瞻容者加极虔,想像者增忻悕。生生资津,十方齐庆。”[6](P51)所谓“瞻容”“想像”,即为禅修。可见,北魏时期的佛教已不再被繁琐的教义所束缚。口念心想而成佛,更容易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又如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中的“善愿从心”“正觉之悟”等词语,都是在强调“道由心悟”的佛理。于是,重心性的简易化佛教,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发展。今天的我们,普遍将禅宗视作中国化的宗教,而其“明心见性”的核心理念,实则在北魏已经开始萌芽。
第三,末法抗争。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曰:“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5](P3)这里的“末代”,是指佛教衰弱的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情淡薄,戒律废止,贪、嗔、痴等欲望横行,佛教徒们不知何去何从。于是,一些信众就要起来抗争,希望“像法”仍可以传承、延续。通过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我们能够看到邑义、比丘尼等集体造像的频繁。《比丘尼昙媚碑》曰:“灵虑巍凝,悟岩鉴觉。寂绝照周,蠢趣澄浊。随像拟仪,沾资懿渥。生生邀益,十方同沐。”[6](P51)员小中先生认为这样的倡议书即是“对当时朝廷限制立寺造像和度僧的‘景明之禁’的一种抗议。”[6](P52)朝廷因何要限制立寺、造像和度僧?其本质原因依旧是要维护帝王的统治。北魏王朝,佛教大盛,不仅有道人统、沙门统、都维那这样的僧官,还有僧祇户、佛图户等大量的民户。寺院自己的僧制、僧律,甚至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管辖。于是,为了逃避徭役和租调,众多百姓选择了出家。一时间,犯罪者皆逃入沙门,僧人借赈饥之粟大谋私利、大发横财,终于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也正是由于出家者暴增,寺院不断地和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帝王才开始下令抑佛。太武帝如此,宣武帝也是如此。当然,他们抑佛、禁佛时都以中华帝王自居,斥佛陀为胡神。限制佛教,就是要恢复“羲农之治”,从而彰显北魏王道的正统。此为当时信众末法抗争的历史背景,即佛教无论如何盛行,也绝不能损害政教的利益。这大概便是北魏佛教“中国化”最直接的表现了。
第四,弥勒信仰。云冈石窟有《常主匠造弥勒七佛菩萨记》《比丘尼惠定造释迦多宝弥勒像记》两处铭文,题目中都出现了“弥勒”字样。另有一篇《妻周氏为亡夫造释迦文佛弥勒二躯记》,文中明确写道:“为亡夫、亡息、亡女,生生□值,庆遭三宝,弥勒下生。”可见弥勒下生信仰,已在北魏民间流行开来。此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是信、愿、行,即通过断疑、发愿、实行来抵达弥勒净土,于龙华树下受法成佛。这一信仰的独到之处在于强烈的入世救世精神,以实行走向净土。佛教的教义是超越生死、涅槃重生,而北魏弥勒信仰却在追求实有的“净土”,并希望得到永远的幸福。如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所言:“托育宝花,永辞秽质”[5](P4)“为亡儿生生遇佛,长辞苦海,腾神净土”。[20](P218)离别秽质,走向净土,这种实有的存在,是北魏弥勒信仰中国化的一大特点。同时,秽土成佛,也得到了更多平民的拥护。只不过,寻常百姓并未深究佛典,常将弥勒与弥陀混同。弥勒在兜率天,为天上净土;弥陀在极乐世界,乃西方净土,二者实有区别。龙门石窟《尼法庆题记》曰:“因缘敬造弥勒像一躯,愿使来世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21](P72);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同样也说:“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5](P5)可见,二者已然混为一体。中国化的佛教信仰就是这样,只要可以救济现世、有利民众,那么统统都可以为我所用。另外,弥勒是未来佛,有意造反者常打着“新佛出世”的口号进行作乱。如《魏书》所载:“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1](卷19上《景穆十二王列传》P445)之后,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也以“新佛”的名义,服素衣、持白幡而起,利用弥勒的未来主宰特性谋乱朝廷。这便是北魏弥勒崇拜的现实反抗精神,即从信仰走向实行。
第五,民族交流。云冈石窟有一则造像题记十分特别,即位于第18窟窟门西壁的《大茹茹可敦造像记》。大茹茹,是柔然族的称谓;可敦,全称“可贺敦”,是对柔然皇后的称呼。清人厉寿田说该题记“每行约十余字,共约二十余行”。[7]今可辨识者虽仅有“谷浑”“以兹微福”等不到20 个字,但也可说明柔然君主来到云冈雕像求福的事实。这则题记,是北魏时期利用佛教活动进行民族交流的实证,确属难得。当然,佛教之活动除了在北方进行外,还在南北之间大量地开展。最典型的事件便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由梁入魏,成为了中国禅宗的初祖。而作为鲜卑族的北魏统治者,也逐渐从崇拜天地、山川、鬼神、巫觋的原始信仰中走了出来。诸多民族一起从事造像活动,共同信仰着同一个中国化的佛教。于是,他们之间的理想信念与生活方式逐步趋同,佛教便成了北魏时期民族交流的精神媒介。可见,无论是教化戒行、末法抗争,还是弥勒信仰、民族交流,都是以“入世实行”的特点推动了北魏佛教的中国化。而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则成为这一过程重要的历史见证。
孙昌武先生说:“中国石窟中,气势恢宏的首推云冈石窟。”[22](P1481)其造像粉本或来自凉州,或来自西域,或来自中亚,最终在拓跋鲜卑族的推动之下,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魏书》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1](卷114《释老志》,P3043)可见,云冈石窟是龙门石窟的模本。宿白先生更是说:“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23](P163)以云冈石窟作参照,北魏民众在改造、消化外来宗教的同时,已然将中国化的佛教作为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这里的“化”,并非是完全抹去与消失,而是各民族在佛教信仰上的包容、理解与融合。无论是儒释合流、佛道混同,还是入世实行,都使得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基础。由外来到本土,从鲜卑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佛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构成。有学者认为:“真正的中国佛教形成于北魏一朝。”[15](P188)而作为北魏佛教象征的云冈石窟,本属中国技巧与中国创造,自然也就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风貌与中国气象。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宗教史上,云冈石窟与北魏佛教的研究仅是冰山之一角。但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与执着热情,或许真的可以为新时代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些资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