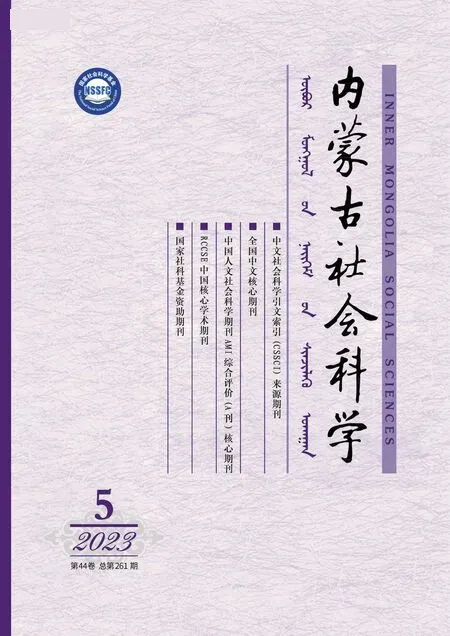从部族到王朝国家:契丹族群早期政治生态演进模式的道路抉择
高福顺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辽朝是以契丹族群为核心,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由汉、奚、渤海等贵族参与,于古代中国北方所建立的王朝国家。辽朝重新构建了东亚社会秩序,“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1](卷37P.495),“东西朔南,何啻万里。视古起百里国而致太平之业者,亦几矣”[1](卷70P.1241),尤其是元末所确立的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2](卷上P.44)的修史方案,进一步肯定了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古史谱系的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3]。契丹族群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地位,学界多有论述,但从政治生态演进视角剖析契丹族群如何与当时中国北疆社会相适应,又为何抉择由部族到王朝国家这种政治生态演进模式,却鲜有专文讨论。本文拟就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演进模式的选择略述管见,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肇基王迹:契丹始祖源流的历史记忆
专属契丹族群的历史始见于《魏书·契丹传》(1)契丹名号之初见,大体有三说:一为始于元魏说;二为契丹国名必自汉以来即有者;三为契丹之名当先于元魏建号。参见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第14~20页。,而有关契丹族群的起源神话则见于《辽史》。《辽史·地理志一》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卷37P.504)剖析此契丹族群起源传说,实与蒙古族群起源传说有相似的历史情境,契丹始祖传说之“神人”“天女”与蒙古人“两男两女”起源传说具有相当程度的耦合性(2)参见拉斯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1页;于默颖、李岭《古代蒙古族政治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21页。,其揭示的是以青牛、白马为标识的两个互婚的契丹氏族共同迁徙至永州木叶山一带(即潢河之西、土河之北)繁衍生息,渐盛后以“族属”为核心析置出“八个部落”。契丹族群的繁衍历程,与人类学家摩尔根所提出的“每个氏族中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个女性婚级”的理论不谋而合,“因为只有规定的婚级才许互相通婚,所以当原先还只有两个氏族的时候,这一个氏族中一半的女子在理论上都是另一个氏族中一半男子的妻子”,“在婚级之上,很自然地产生了作为更高一级组织的氏族组织,氏族组织并没有改变婚级制而只是原封不动地包括于其内”。[4](P.47,55,53)据经典作家的理论概括,早期契丹族群无论是“部落外婚制”[5]、“氏族外婚制,部落内婚制”[6],还是“胞族外婚制”[7],均是以氏族之间的通婚而非氏族内部通婚为基础而繁衍的,具有人类学上所认同的自然繁衍的显著特征。契丹族群的青牛、白马两个氏族的被迫远徙,为早期契丹族群脱离其原始母族羁绊而衍生出新的专属契丹族群的氏族组织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神人、天女“配偶”后“生八子”的故事,进一步揭示了契丹族群已由青牛、白马两个原始氏族繁衍出更多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新氏族,甚至出现属于同一母族的胞族。唯独与经典作家理论不同的是,繁盛后的契丹族群成功主宰了古代中国北方社会而被契丹族群赋予了“天神”之政治色彩,这与古代中国王朝国家统治者所秉持的“天命观”一脉相承。总体看来,早期契丹族群的政治生态演进与世界上其他族群并无二致,仍然是沿着由氏族组织向部族组织的路径而自然演进的。
契丹族群的氏族组织生发于何时,学界尚未有明确的说法,据现有资料推断,当于魏文帝青龙(233~237)年间。《三国志·鲜卑传》载:“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8](卷30PP.831~832)《三国志》的说法,得到了《辽史·世表》的印证:“青龙中,部长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黄龙之北。”[1](卷63P.1053)据此观之,“制御群狄”“稍桀骜”的鲜卑大人轲比能遭害后,鲜卑种落离散,而“散徙潢水之南,黄龙之北”的鲜卑族群之活动轨迹,恰与早期契丹族群祖先青牛、白马两个氏族分别由潢水、土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永州木叶山一带繁衍生息之传说相当类同。《三国志》《辽史·世表》的描述亦得到《新唐书·契丹传》所载“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湟水之南,黄龙之北”[9](卷219P.6167)以及《辽史·营卫志中》所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1](卷32P.428)的叙事文本的支持,可以说契丹始祖的传说与鲜卑“种落离散”密切关联,而且鲜卑某支“散徙”的地域亦与契丹族群早期活动地域相吻合。故此,有理由相信早期契丹族群来源于离散的鲜卑族群,更有理由相信离散于永州木叶山一带的青牛、白马两个氏族此时尚未有契丹名号。
确切知晓青牛、白马两个氏族所繁衍的后裔有契丹名号,乃始于前燕政权早期。元末史官修撰《辽史》时说:“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盖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1](卷63PP.1051~1052)元末史官的看法,在《周书》《辽史》均有印证痕迹,如《周书·文帝本纪上》载:“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10](卷1P.1)《辽史·世表》载:“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1](卷63P.1053)侯豆归,即《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载之“逸豆归”“宇文归”。[11](P.4)依据上述记载推断,契丹名号之出现,当为前燕慕容皝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二月,“率骑二万亲伐宇文归”[12](卷109P.2822),“战于昌黎,归众大败,奔于漠北”[12](卷7P.186)之际。也就是说,青牛、白马两个氏族自东晋康帝建元二年从鲜卑宇文族群析分出来后,才开始独有契丹之名号,且为世人所知。至于《新唐书·契丹传》所载“至元魏,自号契丹”[9](卷219P.6167)则稍嫌“概言性”说法,没有确指。总体说来,早期契丹族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在北魏道武帝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13](卷100P.2408)之后,经慕容皝之伐与登国变乱,早期契丹族群已由依附他族的氏族组织政治生态模式演进至具有独立状态的部族组织政治生态模式,契丹族群具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号,这是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模式演进的初次重大转折。
二、意识脉动:辽建国前契丹部族体制的演生
早期契丹族群的部族组织大约始于北魏建国初期契丹族群与库莫奚族群“分背”之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以来,求朝献于北魏,“岁贡名马”,此时出现了“古八部”之号,即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絜、黎、吐六于等部落。[13](卷100P.2408)对契丹族群的古八部,《辽史·营卫志中》《辽史·世表》均有载记,唯《世表》将“悉万丹部”误为“万丹部”。契丹古八部名称为王朝国家所熟知,当在北魏献文帝之际。献文帝皇兴元年(467)二月,“高丽、库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尒、于阗诸国各遣使朝贡”[13](卷6P.154)。皇兴二年(468)四月,“高丽、库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尒、叱六手、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13](卷6P.155)。《通典》则承袭了《魏书》的说法:“魏太武帝真君以来,岁贡名马,于是东北群狄悉万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14](卷200P.5486)上述载记表明,早期契丹族群的部族组织至少在献文帝皇兴二年(467)之前就已然成熟。此与经典作家所言“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15](P.92)的族群政治生态演进模式基本类同,但从古八部“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13](卷100P.2408)观之,此时契丹族群所形成的诸部落组织尚有独自活动之自由,无论是政治、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似乎尚未结成部落联盟组织,互不统属,无完全统一的步调。
隋初,契丹族群诸部已生发出部落联盟组织之意识,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五月,“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16](卷1P.22)。此则故事,《隋书·契丹传》叙录为“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16](卷84P.2116)。无论是“契丹主莫贺弗遣使”“率诸莫贺弗来谒”,还是“悉其众款塞”,均昭示应存在一个部落联盟长来主导契丹族群诸部与王朝国家之交往。不过,从《隋书·契丹传》所载“(开皇)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16](卷84P.2116)来判断,此时契丹族群的部落联盟长并非契丹诸部落组织中强有力的主宰者,甚至难于制止契丹诸部之间或契丹族群诸部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相互攻伐,以至于被隋朝遣使“责让”。由此观之,此时契丹族群部落联盟组织形式是相对比较松散的,联盟长所能做到的亦仅是遣使谢罪而已,联盟长的权力还相当有限。
隋末,契丹族群“别部寄处高丽者曰出伏等,率众内附,诏置独奚那颉之北。又别部臣附突厥者四千余户来降”[1](卷32PP.428~429),导致契丹部落“渐众”后出现了与隋初大不相同的情形,契丹族群虽仍“北徙逐水草”,却已衍化而“分为十部……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16](卷84PP.2116~2117)。由此不难想象,契丹族群的部落联盟组织之意识空前增强,“至少在个别场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15](P.154)。契丹部落联盟组织的政治生态模式已然初步形成,有征伐,则需要诸部落酋帅商议后而行之,且有“符契”。很显然,契丹族群诸部落虽然在经济活动上有独立性的自由权力,但在政治、军事上必须服从部落联盟长的统一调度,不得擅自为之。“符契”的出现,标志着契丹族群部族体制政治生态模式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契丹族群由诸部族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组织开始逐渐联合成“永久性”的部落联盟组织。
唐初,契丹族群的“永久性”部落联盟政治生态模式已逐渐清晰起来,“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17](卷199下PP.5349~5350)。契丹族群不仅具有强有力的大贺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长,而且大贺氏所统领的八部组织名称也被记录下来,即达稽、纥便、独活、芬问、突便、芮奚、坠斤、伏八部。与《魏书》所载“古八部”相比,已有较大差别,此为被离散的古八部之析分重组,仅藉以八部之名而已,也就是文献所云之古八部“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万余口。继为突厥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故古八部“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1](卷32P.426)。实际上,大贺氏时代契丹总为十部,作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即部落联盟联盟长的窟哥所在部落和作为玄州刺史即部落联盟军事长所在部落,均别出于八部之外,即《辽史·营卫志中》所云“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1](卷32P.429)。在我看来,大贺氏十部是在“隋开皇四年,诸莫弗贺悉众款塞,听居白狼故地。又别部寄处高丽者曰出伏等,率众内附,诏置独奚那颉之北。又别部臣附突厥者四千余户来降,诏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徙逐水草,依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逸其名”[1](卷32PP.428~429)的基础上,于唐初在唐朝的干预下进行再次析分重组构建起来的。
唐初契丹族群析分重组的部落联盟与隋时契丹族群部落联盟的政治生态模式相较已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质变,契丹族群的部落联盟长之世选权已固定在大贺氏部落内部而非契丹八部之中[18](P.20,54,63),进入到“具有一种贵族统治性质的集权趋势和世袭的等级地位排序,但没有武力压迫的正式法定机构”的契丹部族的政治生态模式,导致“亚洲流动的游牧者有时以酋邦形式组织起来,特别是一起参与劫掠或战争时”。[19](P.15,328)在我看来,此时契丹族群部落联盟长的权力还相当有限,仍局限于“战”而非“猎”,但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出现却标志着契丹族群的部族体制政治生态模式已由部落联盟政治生态模式阶段演进至酋邦政治生态模式阶段。
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1](卷32P.430)。正因契丹族群的外患与内乱,“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1](卷34P.449),导致契丹族群诸部落再次析分重组,以大贺氏仅存五部为基础,契丹族群由大贺氏八部嬗变为遥辇氏八部,即旦利皆、乙室活、实活、纳尾、频没、纳会鸡、集解、奚嗢等部,也就是说,“遥辇氏承万荣、可突于散败之余,更为八部”[1](卷32P.426)。遥辇氏时代,契丹部族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是,“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20](卷72P.1002)。不过,此时契丹族群部落联盟与大贺氏时代的部落联盟一样,世选联盟长的遥辇、世选联盟军事首长的涅里所在部落仍别出八部之外,即所谓“遥辇、迭剌别出,又十部也”,“涅里所统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1](卷32P.427,430)不管契丹族群部落联盟如何析分重组,如何重新构建,遥辇氏时代契丹部族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仍未摆脱酋邦阶段的政治生态模式,然距国家政治生态模式的出现已经不远了。
总体说来,无论是大贺氏时代还是遥辇氏时代,尽管契丹部落联盟长的世选部落由大贺氏所在部落转换为遥辇氏所在部落之中,但契丹诸部落所凝结成的“永久性”的部落联盟组织(部族体制)却一直是此时期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模式演进的内核,且与世界上的其他族群的繁衍变迁并无二致,基本上按照经典作家所抽象出的人类学上的政治生态模式而演进。不过,随着迭剌部的崛起,契丹部落联盟长的世选权由遥辇氏所在部落又转换到迭剌部之世里家族。(3)日本学者松井等先生认为“阿保机是代大贺氏而建国的”。参见松井等著、刘凤翥译《契丹勃兴史》,《民族史译文集》第10期,1981年。苗润博先生认为:“开元时期可突于率众迁至潢水流域后,后来的辽朝统治者阿保机、述律平两家族方才真正加入契丹集团,逐渐产生契丹认同,此前的契丹历史可谓与之毫无关涉。阿保机建国后,并未改易‘契丹’之名号,而是以自身的家族史作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历史。”参见苗润博《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载《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契丹部落联盟长的世选权由“部”转移至“家族”,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导致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模式再次发生重大转折,介于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的酋邦阶段的政治生态模式逐渐瓦解,具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特征的政治生态模式渐次上位,太祖阿保机成功实现了“变家为国”[21](卷23P.221)的夙愿。
三、变家为国:辽初契丹部族体制的改造
唐末,“天下盗兴,北疆多故”[9](卷219P.6172),契丹“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22](卷345PP.2701~2702)。唐天复三年(906)十二月,“痕德菫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1](卷1P.3)。对此,王朝国家史官也多有载录,标志着遥辇氏退让而世里家族上位。
世里家族取代遥辇部落成为契丹政治体制的核心,与太祖之六世祖涅里(雅里、泥里)相阻午可汗有莫大关系。涅里虽“让阻午而不肯自立”,但却以唐朝“都督”的身份,职任遥辇氏时代部落联盟组织的夷离堇,即契丹早期统率军马的部族官[23],导致涅里所在的迭剌部落权威势重,为遥辇氏部落联盟主宰契丹族群的军务。涅里为了削弱大贺、遥辇部落的势力,利用夷离堇的身份,对遥辇氏初期析分重组的契丹十部再次进行析分重组,在保留原遥辇初期的契丹八部的同时,将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之三耶律皇族分为七部落,将国舅二审密乙室已、拔里分为五部落(4)据肖爱民先生研究:“《辽史》中记载的组成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的‘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不是阻午可汗在耶律涅里(雅里)辅佐下重整部落时的事情,而是《辽史》修撰者们误把辽朝分皇族耶律氏为七个族帐、后族萧氏为五个族帐的事情移到了遥辇氏阻午可汗时,因此所谓的‘阻午可汗二十部’确实是子虚乌有,为元朝修《辽史》者的杜撰。”参见肖爱民《“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辨析:契丹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研究之二》,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形成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即“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1](卷34P.449)析分结果是“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剌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1](卷32P.431)。这既与世里家族“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菫,执其政柄”密切关联,更与先祖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1](卷32P.427)、“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的部族制度建置密切关联。尔后,诸世里家族成员在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治国策略上均有突出表现,如玄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太祖之父德祖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德祖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故有“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之水到渠成的壮举。[1](卷2PP.26~27)有关太祖“变家为国”纪事,亦得到宋人王钦若《册府元龟》所载“有别部酋长阿保机自称国王”[24](卷967P.11347),以及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庄宗列传》所载“及钦德政衰,阿保机族盛,自称国主”[25](卷266P.8677)的印证。至此,太祖阿保机“变家为国”成为契丹族群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太祖阿保机“变家为国”后,一改契丹族群原有的游牧族群的部族体制统治模式,确立与中原内地农耕族群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同的统治模式。太祖元年(907)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1](卷1P.3)“设坛”“燔柴告天”是中古时期古代中国王朝国家改朝换代“即皇帝位”的礼仪仪式。太祖阿保机的这种政治行为已完全透视出太祖阿保机开始有意识地对契丹部族体制进行改造。神册元年(916),太祖阿保机又于龙化州举行了古代中国王朝国家中央集权体制下所具有的给皇帝上尊号之仪式,且建元“神册”,更加明确了太祖阿保机对契丹族群统治方针与政策之鼎革,彻底导致契丹部族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标志着契丹部族体制政治生态模式演进又出现一次重大转折。
太祖阿保机之所以于中国北疆社会实施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除其早已意识到契丹族群唯有施行此种统辖模式才能保障契丹社会长治久安外,当然还与唐朝于中国北疆社会设置羁縻府州所提供的先决条件有重大关联[9](卷43下P.1127),“遥辇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1](卷37P.496)。唐朝羁縻府州统辖模式为太祖阿保机实践部族体制改造、加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以至于元末史官评论说“(辽朝)分州建官,盖昉于此”[1](卷37P.496)。唐朝羁縻府州制度为太祖阿保机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改弦更张”铺平了道路。
《辽史·营卫志中》在叙录契丹部族体制演进时说:“阻午可汗析为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辽太祖,析九帐、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1](卷37P.427)“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其分部皆未详;可知者曰迭剌,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曰突吕不,曰捏剌,曰突举,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1](卷32P.431)对勘遥辇二十部与太祖二十部就不难发现,太祖二十部与遥辇二十部既有相当大的关联,又存在较大差别。遥辇二十部从耶律、审密等皇族(三耶律)、后族析分重组的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突吕不、捏剌、突举等八部仍被太祖二十部所承袭,只不过太祖阿保机一系的皇族势力依托的迭剌部则析分为五院部与六院部。至于右大部、左大部,应指的是后族国舅某帐。《辽史·外戚表》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拨里,曰乙室已。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1](卷67P.1135)而《辽史·述律后传》又云:“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1](卷71P.1319)《辽史·地理志一》“仪坤州”条亦云:“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以所生之地置州。”[1](卷37P.505)
综上三条史料信息不难推断,右大部当为淳钦皇后述律氏所在的部落。据冯永谦、杨若薇等先生研究,淳钦皇后述律氏的父族乃为拔里国舅帐之少父帐。(5)冯永谦先生认为:“阿古只为拔里国舅帐之少父房,其后世是辽史中最显赫的一支……阿古只为淳钦皇后之弟,其父为月椀。”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杨若薇先生认为:“述律皇后的父族即为拔里族,其中分为大父、小父二房;述律皇后的母前夫之族则为乙室已族,其中又分作大翁、小翁二房。”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6页。由此看来,右大部至少是国舅拔里族少父帐当时的称谓,而左大部于《辽史》《契丹国志》以及相关墓志中仅《辽史》一见,按契丹族群命名习惯推测,左大部很可能是对应国舅拔里族少父帐之大父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舅拔里族大父帐与少父帐概称为右大部,则左大部对应的就应是国舅乙室已族的大翁帐与小翁帐。无论如何,太祖六世祖涅里所析分重组的右大部、左大部,至太祖时,以“二国舅升帐分”,提高了国舅后族诸帐的地位,与太祖一系皇族相虢别出,故太祖时析分重组的部落实际上只有十八部,其中以迭剌部“强大难制”将其析分为五院部、六院部,同时又将征服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重组为奚部。其余诸部如突吕不室韦、涅剌拏古、迭剌迭达、乙室奥隗、楮特奥隗、品达鲁虢、乌古涅剌、图鲁等部均为太祖征战时所俘室韦、奚、达鲁虢、于骨里等户重组。但吊诡的是,太祖六世祖涅里所析分重组之遥辇二十部时所承袭的旦利皆部、乙室活、实活、纳尾、频没、纳会鸡、集解、奚嗢等部族称谓均不见于太祖二十部当中,而见于太祖二十部之中者均为遥辇析分重组的“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的部族称谓。由此推之,遥辇时的旦利皆等八部族均非契丹族群之贵族,他们虽然仍以“部族”的形式存在,但已不构成单独部落存在,被太祖有意识地析分重组到“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的部落当中,“被纳入契丹王朝的管理体制之内”[26](P.157)。由此可以想象,这种析分重组的契丹部族肯定为太祖施行王朝国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清除了不必要的障碍。
太祖析分重组的二十部的管辖与治理,最初仍沿袭建国前遥辇氏时代所设置的夷离堇之契丹部族政治生态模式。如由皇族所在的迭剌部析分的五院部、六院部,“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营。阻午可汗时,与弟撒里本领之,曰迭剌部。传至太祖,以夷离菫即位。天赞元年,以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各置夷离菫。”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曰乙室部。会同二年,更夷离菫为大王”[1](卷33PP.436~437)。所谓夷离菫,“统军马大官。会同初,改为大王”[1](卷116P.1690)。据此可知,夷离菫仍具有部族体制特征。当部族体制改造平稳完成后,太祖便开始推进部族首领官僚化的进程,“更诸部夷离菫为令稳”[1](卷33P.437),这由萧海璃“其先遥辇氏时为本部夷离菫;父塔列,天显间为本部令稳”[1](卷78P.1396)的记载以及统和十四年(996)四月条所云“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1](卷13P.160)的举措得到印证。因太祖时“更诸部夷离菫为令稳”是夹叙于《辽史·营卫志下》“品部”条内,故元末史官主张的很可能是指品部以下的小部族,而大部族仍设置夷离堇,这亦与太宗官制改革的内容相一致。所谓令稳,《辽史·国语解》解释为“官名”[1](卷116P.1700)。在笔者看来,太祖将“统军马”的夷离堇改称为具有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性质的令稳,表明太祖在中国北疆游牧社会遍设具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性质的州县外,更有将部族首领官僚化的趋势。正如李锡厚先生评价的那样:“北面官系统的形成也使得各部族首领变成了朝廷命官,各部族组织形式虽然依旧,就其性质而论却已经变成了契丹王朝统辖下的行政单位。北面官虽然主管部族事务,但它本身并不是在原来的部族联盟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南面官一样,也是依照中原王朝的设官制度建立起来的。”[27](P.81)
太祖对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模式所做出的不同于匈奴、突厥等族群政治生态的道路抉择,使契丹族群的政治生态演进再次发生重大转折,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北疆游牧社会政治生态的演进走向,使古代中国北疆游牧族群与内地农耕族群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四、驶入正途:圣宗朝部族体制的再改造
太宗即位后,绍太祖之遗志,不仅对后晋高祖石敬瑭曰“宜受兹南土,世为我藩辅”[1](卷3P.41),灭晋入汴视朝时,“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俛首不敢仰视”[20](卷72P.1013),而且在中国北疆社会内,在按照太祖既定政策仍持续有序地设置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下州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还在太祖改造部族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太祖时所施行的部族首领官僚化的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太宗天显十年(935)四月,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以萧缅思为尚父领之”[1](卷3P.39),对后族部落予以重组调整,使之更加适应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会同元年(938)十一月,“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菫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1](卷4P.49),正式拉开太宗官制改革的大幕。太宗在擘画州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诸部族首领的官僚化,将皇族所依赖的迭剌部之北院、南院以及“三耶律”皇族乙室部之夷离堇改为大王,将“诸部下官”的梯里已改为司徒,将“县官”的达剌干改为副使,将“县官之佐”的麻都不改为县令,将南北府、国舅帐的“官府之佐吏”郎君官改为敞史,将诸部族宰相、节度使帐改为司空,其主旨就是将诸部族管理机构的长官有意识地改换为具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职官意味的名称,此均可视为太宗刻意袪除契丹部族化而使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重要举措。正如任爱君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将原有的契丹语官吏称号,部分地改变为汉语官号,标志着中原封建体制下不仅在契丹政权内部被容纳,而且还在以一种崭新面目时时刻刻地濡染和影响着契丹体制建设的继续发展。”[28](P.109)不过,伴随太宗驾崩,改造契丹部族体制的重任就只能由后继者完成了。
太宗大同元年(947)四月,让国皇帝耶律倍长子永康王兀欲“僭越”即皇帝位于柩前,导致皇太后述律平“大怒,发兵拒之”[25](卷287P.9367),虽然在耶律屋质的斡旋下达成“横渡之约”,但并未平息契丹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短暂的世宗朝,先有“李胡与太后谋废立”[1](卷72PP.1337~1338)事件,后有耶律天德、萧翰谋反之乱局,最终导致“祥古山之变”,世宗为泰宁王察割所弑,寿安王耶律璟即皇帝位,是为辽穆宗。一系列变乱后,皇权又从让国皇帝耶律倍一系转还回太宗耶律德光一系。穆宗被弑后,世宗皇帝次子耶律贤即皇帝位,是为辽景宗。景宗驾崩后,年仅12岁的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皇帝位于柩前。至此,辽朝皇权在耶律倍系与耶律德光系的摇摆终画上句号。经过景圣两朝的不懈努力,辽朝社会的政治生态秩序再次平稳步入太祖、太宗时既定的王朝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演进轨道。
圣宗与母后在耶律斜轸、韩德让等一批蕃汉臣僚的辅佐下,成功地稳定与巩固了辽王朝社会秩序,这亦给圣宗加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以及在太祖、太宗改造契丹部族体制基础上再次改造契丹部族体制提供了契机。《辽史·营卫志中》曰:“圣宗之世,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旧为五十四部。”[1](卷32P.427)也就是说,圣宗朝的部族体制改造在承袭太祖二十部的同时,又分置、增置三十六部,总为五十四部。按《辽史》修订本校勘记的说法:“大黄室韦部小黄室韦部 本书卷三三《营卫志下》云:‘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皮韦户。太祖为挞马狘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中略)涅剌拏古部。与突吕不室韦部同。’则大、小黄室韦或即上文突吕不室韦、涅剌拏古二部之重出。”“已上四十九节度 按自品部至五国部共五十部。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与大、小二黄室韦部或系重出,又奚六部列为七部,则计为四十七部。”[1](卷46P.857)所谓奚六部乃为太祖时析分重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初为五部:曰遥里,曰伯德,曰奥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尽降之,号五部奚。天赞二年,有东扒里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笴山以拒命……太祖灭之,以奚府给役户,并括诸部隐丁,收合流散,置堕瑰部……遂号六部奚。命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1](卷33P.439)。实际上,太祖奚王府五帐分析分重组为六部,即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与堕瑰,但太祖将奚六部合为一部视之,“以勃鲁恩权总其事”[1](卷2P.20)。《辽史·圣宗本纪四》载,统和十二年(994)十二月,“诏并奚王府奥理、堕隗、梅只三部为一,其二克各分为部,以足六部之数”[1](卷13PP.157~158);《辽史·营卫志下》载:“奥里部。统和十二年以与梅只、堕瑰三部民籍数寡,合为一部。并上三部,本属奚王府,圣宗分置”[1](卷33P.442)。据此可知,《辽史·百官志二》列置奚七部显然是有问题的,明显衍出已被合并的“堕瑰部”应以《辽史》修订本校勘记的说法为准。另,《辽史·百官志二》所列置的四大王府,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六部,被称为“大部族”,而余下诸部族则被称为“小部族”。若剔除大、小室韦系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重出以及堕瑰部,圣宗统和十二年后的小部族数量当为四十七部,而大部族中的“奚六部”又在小部族中分别计数,“奚六部”之大部族数当予以减除。实际上《辽史·百官志二》所列的圣宗统和十二年后的大部族与小部族的总数仅为四十九部,即使将已升帐分的拔里、乙室已二后族计算在内亦仅有五十一部。对照《辽史·营卫志中》的记载,显然脱漏圣宗时所置的室韦部,而拔里、乙室已二后族于太祖时已升帐分,独立于部族之外,实际上圣宗时析分重组的部族数量当为五十二部。
圣宗虽然在承袭太祖二十部(止为十八部)的基础上,又“分置”“增置”三十四部,数量显然远超出太祖时的部族数量。不过,这些部族的管理体制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太祖时,契丹诸部族设置夷离堇总领之,重点在于统领兵马之事,具有明显的游牧族群部族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特征。尽管太祖“更诸部夷离菫为令稳”,初步实现了部族首领官僚化,但对部族体制的改造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太祖心目中的王朝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状态,故循序渐进地推动契丹族群对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仅是太祖的理想夙愿。太宗绍位后,随着契丹统治区的不断扩大,继续沿着太祖抉择的道路推动官制改革更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强化部族首领官僚化,使契丹部族体制政治生态模式逐渐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政治生态模式转化。然太宗对部族体制的改造亦未达到圣宗对部族体制政治生态模式改造的那样彻底,这或许是太宗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圣宗稳定与巩固辽朝社会秩序后,便沿着太祖、太宗既定的部族首领官僚化的改革道路,继续对契丹部族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圣宗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等“大部族”仍沿用太宗时所改称的“大王”官名,而对“小部族”一律设置部族节度使。如“品部。其先曰拏女,阻午可汗以其营为部。太祖更诸部夷离菫为令稳。统和中,又改节度使”[1](卷33P.437)。“撒里葛部。奚有三营:曰撒里葛,曰窈爪,曰耨盌爪。太祖伐奚,乞降,愿为著帐子弟,籍于宫分,皆设夷离菫。圣宗各置为部,改设节度使,皆隶南府,以备畋猎之役。”[1](卷33P.441)“特里特勉部。初于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侦候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圣宗以户口蕃息,置为部,设节度使。”[1](卷33P.441)“奥衍女直部。圣宗以女直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戍镇州境。自此至河西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讫于五国,皆有节度使。”[1](卷33P.443)故元末史官有“已上四十九节度,为小部族”[1](卷46P.820)的说法。唯五国部于兴宗重熙六年(1037)八月,“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1](卷18P.247)。总体说来,圣宗朝的部族体制徒存其形式而已,实际上已完全被纳入到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之中,可以说,圣宗已全面完成了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转换的改造。
关于契丹部族节度使,《辽史》亦记录有于圣宗朝之前设置者。如会同三年(940)二月,“奚王劳骨宁率六节度使朝贡”[1](卷4P.51);景宗乾亨元年(979)三月,“耶律沙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筈皆死之,士卒死伤甚众”[1](卷9P.109);乾亨二年(980)十一月,“宋兵夜袭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1](卷9P.112)。奚王六节度使,很显然对应的是太祖析分部族时的“奚王六部五帐分”,在朝曰奚王府,由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而六部太祖分设夷离堇,故元末史官很可能将奚王府之六节度使前置于太宗朝,实应称六夷离堇。景宗朝突吕不部节度使亦是这种情形。至于属国属部之北大浓兀于“天赞元年,以户口滋繁,糺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以统之”[1](卷34P.450)的记载,更是将夷离堇前置的典型。概言之,此种现象的出现很可能是元末史官在对应前史、后史之官制名称异同时,无意识地将圣宗朝始设的节度使代入至前史之中而造成的。
圣宗强化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举措,一直沿袭至辽末而未曾改变。圣宗太平八年(1028)九月壬子,“北敌烈部节度使耶律延寿请视诸部,赐旗鼓,诏从之”[1](卷17P.228)。萧和尚,“(开泰)八年秋,为唐古部节度使”[1](卷86P.1460)。耶律仁先,“重熙三年,补护卫……改鹤剌唐古部节度使”[1](卷96P.1535)。耶律马哥,“清宁中,迁唐古部节度使”[1](卷83P.1433)。耶律庶箴,“咸雍元年,同知东京留守事,俄徙乌衍突厥部节度使”[1](卷89P.1486)。耶律适禄,“乾统中……时上京枭贼赵钟哥跋扈自肆,适禄擒之,加泰州观察使,为达鲁虢部节度使”[1](卷95P.1529)。从举隅者不难判断,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于圣宗官制改革以来就从未停歇,一直持续至辽末。圣宗于小部族设置朝廷任命的部族节度使,其意义在于,诸部族虽然仍保留部族组织的政治生态模式,但从本质上说这些部族已完全纳入到了辽朝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下地方州县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之中,使得太祖时所施行的部族体制下的政治生态演进模式得以完全确立起来。圣宗时选择这种绍承太祖时所既定的政治生态演进模式,进一步推进了古代中国北疆游牧族群与内地农耕族群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均质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论:契丹族群政治生态道路抉择的历史意义
罗新先生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所谓‘民族’,都首先是政治组织,是政治体,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政治体是实质,血缘联系通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述。内亚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固然有变动,但作为各政治体基础的民众,当然存在着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变化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社会成员或其后裔,与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并无两样。”[29](PP.68~69)活动于王朝国家北疆社会的契丹族群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政治体,自北朝有记载始,便以政治体的政治生态模式,与王朝国家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导致契丹族群政治生态演进模式并未如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描述的易洛魁人部落组织那样“联盟借助于巧妙的立法而自然形成”[4](P.122)的原生态自然演进的政治生态模式,亦未如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所描述的克钦社会结构那样“关心的是实际上克钦人的行为与理想中克钦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30](P.367)的政治生态模式,而是一种受农耕族群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次生态的自然演进的政治生态模式。但契丹族群进入国家前的政治生态路径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学家所总结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态模式之演进路径,契丹族群仍沿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酋邦→早期国家的诸阶段发展演进,但是当辽太祖“变家为国”后,其野心逐渐膨胀,“颇有窥中国之志”[20](卷72P.1005),故而做出了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道路抉择。换言之,当契丹族群没有强力的领导者且遭受其他族群掣肘,甚至无法主宰自己的社会走向时,其政治生态模式只能是沿着人类学家所总结的那样,按照人类社会“原生态”政治生态模式演进的路径前行;当契丹族群有了强力的领导者且能摆脱其他族群掣肘时,契丹族群便有权力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生态演进模式,尤其是雄才大略的太祖阿保机并不满足于强力主宰契丹族群社会秩序,还要像王朝国家皇帝那样,成为“天下”共主。太祖阿保机清醒地意识到,仅按照中国北疆游牧族群的政治生态模式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的,必须改弦易辙,破除抱残守缺,实施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打破契丹族群固有的部族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才能实现“天下”共主的夙愿。故此,太祖没有继续以匈奴、突厥等中国北疆游牧族群的政治生态模式演进路径向前发展,而是选择以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向前发展,这充分彰显了太祖阿保机聪慧而深邃的洞察力与敢为人先的坚韧与魄力。
辽太祖对辽朝政治生态模式演进路径的抉择,对于中国北疆族群社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加速了中国北疆游牧族群对王朝国家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而且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绍位的太宗、圣宗等皇帝,踏太祖之圣迹,慕华夷之同风,持续践行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策略,不断强化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运行模式,使以中国北疆契丹族群为核心所建立的辽朝成为中国古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这不得不说契丹族群政治生态道路的抉择具有不同于匈奴、突厥等中国北疆游牧族群与中原内地农耕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意义。契丹族群政治生态道路的抉择,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北疆社会的历史发展在辽王朝发生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