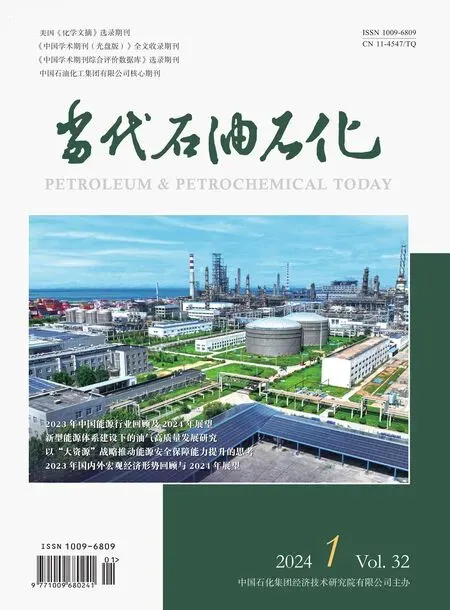以“大资源”战略推动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思考
钟富良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728)
能源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今全球地缘格局和经济结构加速重构,不仅深刻影响能源市场,也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传统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是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借助国际合作与能源贸易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联通,是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但在以全球化视角开展贸易合作方面还需加强。
1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能源署(IEA)首次提出“能源安全”以来,其概念和内涵经过了不断丰富和完善,衍生出了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使用安全、能源科技安全、能源经济安全、能源治理安全等多个维度,但“以合理价格不间断获得所需能源”一直被作为核心和本质内容。从这一角度看,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战在于石油的经济安全稳定保障。
1.1 石油是能源安全的最大短板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能源需求保持长期稳定增长,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2022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69.5亿桶油当量,是美国的1.7倍,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7.3%。但由于资源禀赋限制,作为我国能源消费主体的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速在较长时间内一直低于需求增速。2000年以来,我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长1%~2%,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10%左右,但同期石油和天然气需求的年均增幅分别为4%和12%。受此影响,我国的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对进口油气的依赖程度不断走高。2000—2022年,我国一次能源整体对外依存度由17%上升到25%,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完全能够自给,煤炭基本保持自给自足,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则几近翻番,已分别超过70%和40%[1](见图1)。

图1 2000—2022年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及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
考虑到石油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接近20%,远高于天然气的8%,而且其对外依存度也是所有化石能源中最高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石油的刚性需求程度远超天然气,以及我国在核能、水电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较强自主可控能力的现实情况,石油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短板和弱项。
1.2 石油的系统韧性是能源安全的主要瓶颈
2021年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能源危机,其中欧洲最具代表性。分析欧洲最近两次能源危机可以看出,无论是2021年下半年极端天气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断崖式下降引发的电力危机,还是俄乌冲突引发的天然气危机[2],其本质都是系统韧性的缺乏,即当能源系统暴露在突发有害风险中时,缺少应对冲击的快速有效缓冲和恢复能力。我国的主要一次能源都或多或少存在系统韧性方面的不足,但与煤炭、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因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系统韧性不同,影响我国石油供需系统韧性的核心因素主要来自外部。
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已达48个,进口原油5.08亿吨,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石油资源区,中东在我国原油进口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是处于第二位的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3倍,沙特和俄罗斯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比例都达到了17%,是其他国家的2倍以上(见图2、图3),原油进口来源国集中度达到45%。另外,近年来,随着世界宏观环境从“大缓和”逐渐进入“高波动”,国家间博弈不断深化,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欧佩克+”推行限产保价政策,俄乌冲突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地缘和经贸调整加速国际秩序的分化和再平衡[3],国际石油市场的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加之欧美主导全球油气贸易体系、掌握油气海运关键服务环节,并将其作为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以中印为代表的石油消费国只能被动应对供应链变化,进口石油的安全高效执行已成为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方面。

图2 2022年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区构成

图3 2022年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构成
1.3 定价权欠缺是能源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
受“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限制,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结构与全球油、煤、气“三分天下”的格局不同,表现出“煤为主、油为辅、气为补充”的特征。虽然石油在我国整体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远低于煤炭,但由于基数较大、对外依存度较高,导致每年的进口成本巨大。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除2015年和2016年外,我国每年用于进口原油的成本都在1.0万亿元以上,2022年达到2.4万亿元,原油在进口商品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了10%,占当年GDP 2%(见图4),国际油价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4],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图4 中国原油进口金额、占GDP比重与布伦特油价变化
由于我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才加速进入国际石油市场,而此时的市场体系已经成熟且主要由欧美主导,使得我国虽然凭借规模优势快速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在石油价格形成过程中一直被“边缘化”,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如,2021年和2022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分别比2020年下降了6%和1%,但进口成本分别大幅增加了36%和99%,主要原因是油价大幅上涨。此外,以我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主要油气消费国还长期被迫接受“亚洲溢价”。以沙特原油为例,根据普氏的统计数据,2019年以来,沙特向亚洲地区出口重质原油的价格分别平均比欧洲和美国高3美元/桶和2美元/桶,最高时甚至接近10美元/桶(见图5),其他地区出口到亚洲的原油也存在类似情况,导致我国进口原油的成本长期高于欧美国家。

图5 亚洲与欧洲、美国进口沙特重质原油的价差
2 “大资源”战略的内涵及对能源安全的意义
自1861年第一船美国煤油成功抵达英国伦敦,拉开跨地区石油贸易序幕以来,世界石油市场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中东、非洲、亚太、欧洲、地中海、远东各区域相互联通,生产、运输、保险、金融各环节紧密协同,长约、现货、期货、纸货各种形式互为补充的全球一体化石油贸易体系。“大资源”战略就是基于这一体系,在以贸易维系国家能源安全的思路指导下,把不同时、区的石油资源,以及与实现进口石油与国内需求平稳有序衔接的相关途径、方式和手段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考虑。
2.1 跨时、跨区匹配资源,提升石油进口渠道多元性
虽然全球石油资源呈现较明显的集中性特征,70%的常规石油资源位于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北美三大地区,56%的原油出口来自沙特、俄罗斯、加拿大、伊拉克和美国,但从主要原油的品质分布来看,在不同资源国和地区间有一定的近似性和相互替代性,与我国地理位置的差异造成主要原油出口地区在交易周期上有所区别,为跨时、跨区进行资源匹配创造了条件,也是“大资源”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
以占我国进口原油总量近20%的沙特原油为例,其主要品种(沙轻、沙中、沙重)均为中质高(含)硫原油,除同样产自中东地区的阿曼原油、阿联酋迪拜原油、科威特原油等与其品质相似外,产自美国的Mars原油、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等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对沙特原油形成替代(见图6);在交易周期上,美国原油通常比中东早1个月交易,俄罗斯原油一般与中东有2周左右的交易时间差。因此,在获取进口石油资源时,可以充分综合考虑国内需求、市场走势等因素,对这些原油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在石油资源区域性不平衡导致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空间受限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尽可能多地与主要资源区产油国建立相对稳定且长期的能源合作关系,有效减少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图6 全球主要原油品种的品质对比
2.2 船和货紧密结合,提升石油进口执行过程安全性
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东北(中—俄)、西北(中—哈)、西南(中—缅)和海上互为补充的石油进口通道体系,较好保障了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和多元化。但从绝对量来看,海上依然是我国进口石油的主要途径。根据路孚特(Refinitiv)数据,2022年,我国海运进口石油总量4.4亿吨,占全年进口总量的86%,其中81%由超大型油轮(VLCC)承运、11%由阿芙拉型油轮(Aframax)承运、7%由苏伊士型油轮(Suezmax)承运[5]。
与管道的计量点交接方式相比,通过海运方式进口石油涉及的主体范围广、操作链条长、执行环节多,而把各主体和环节连接起来的关键是船。因此,将进口石油(货)和船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是“大资源”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一方面,明确资源来源的同时,必须对资源所在地的装港情况、所需船型、航线、船舶供需等进行全方位考虑和谋划;当出现某一区域或航线的运力供应紧张时,甚至需要因此切断所涉地区的资源获取,以确保进口石油“运得出来”。另一方面,油轮在海上航行时会面临各种不可预知风险,货主需要时刻保持对船的关注,以确保货物安全;而且国际船运市场是动态的,国内对进口资源的到港时间、成本等要求也时常出现较大变化,需要及时对航线、航速等作出调整,甚至更改物流方案、更换船舶,以确保进口石油“运得回来”。只有将船和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确保石油从生产国到我国的整个贸易过程经济高效、平稳有序,从而更好保障能源安全。
2.3 实货与期纸货一体协同,提升石油进口经济性
世界银行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倡议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利用期货和期权的套期保值作用来更好地从事商品进出口贸易,从而获取更大的收入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6]。就石油而言,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长期被迫接受“亚洲溢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对国际石油市场实货和期纸货交易的参与度不同,介入期纸货市场的时间晚、参与度低、话语权弱、利用期纸货工具套期保值的意识较差。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进口来源多、规模大、可预测性强,要避免在国际市场被“针对”和“挤兑”,不仅要在实货资源获取中更加小心谨慎,还要主动了解期纸货市场规则并积极参与,配合实货需求,选择合适的期纸货工具开展套期保值,平抑价格风险的同时争取市场话语权。“大资源”战略需要特别重视石油实货和期纸货的互补、紧密联系特性,期纸货既是实货的延伸,又是发现实货价值和平抑价格波动的主要工具。一方面,可以将具备实物交割功能的期纸货工具作为资源获取渠道之一;另一方面,要以实货进口需求为背景,选择合适期纸货工具,把资源成本锁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从经济性角度最大限度提升我国的能源安全水平。
3 推进“大资源”战略的思考
3.1 高质量国际化是推进“大资源”战略的基础条件
“大资源”战略最核心的是从全局、全链条审视“资源”,构建以国内需求为核心、国内外全要素联通的动态网络,利用全球化解决能源安全保障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做到高质量国际化,持续提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国家层面,借助能源外交相关渠道,构建多边对话与沟通机制,全方位加大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力度,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对外合作环境。企业层面,强化人力资源、业务发展、管理变革的“三位一体”,根据国际市场变化调整国际化经营布局、优化一体化团队配置、改进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深化内部前中后台相互赋能和内外部一体化协同合作,打造引领行业发展的一流竞争力。
3.2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进“大资源”战略的有利抓手
油气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头戏。2013—2022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从不足3亿吨增长到5亿吨以上,天然气进口量从500亿立方米增长到1 500亿立方米,其中大部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我国原油进口量最大的10个国家中有6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LNG进口量最大的5个国家中有3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管道气则全部来自“一带一路”沿线[7]。虽然面临地缘、商业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拥有全球约2/3的油气资源,我国也已经与大多数沿线国家建立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扩大油气进出口等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应作为“大资源”战略的主要发力方向。
在合作方式上可以从软、硬两方面入手。硬合作方面,以现有油气贸易为中心,在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向贸易链条的上下游延伸,探索油气资源开发、船舶海运协作、炼油化工生产销售等领域的新型合作模式,充实跨国、跨区域合作内涵,打造相对牢固的能源供应“大后方”。软合作方面,以能源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积极与沿线国家探讨将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国内期货市场作为平台的油气价格、结算相关合作,推动构建具有局域权威性的油气交易市场和定价机制,进而扩大在相关产业标准和规制方面的合作,打造良好合作环境。
3.3 提升市场话语权和促进国内期货市场发展是推进“大资源”战略的必然结果
从“大资源”战略必需的全球资源一体化、船货配合、实货与期纸货协同3个主要方面来看,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全球资源网络,具备一体化统筹的基础;借助原油“大买家”优势,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在国际市场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内船东和造船企业,为石油进口提供保障;但在实货与期纸货协同上还有所欠缺,主要体现在多数国内石油进口和贸易企业主动参与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等国际石油市场的程度较低、市场话语权较弱,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国内石油期货市场还需进一步探索丰富衍生品类型、深化与国际规则对接的新方式。
当前,国际石油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给我国石油进口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以“大资源”战略为踏板,进一步提升市场话语权和完善国内期货市场提供了契机。一方面,虽然北海布伦特、美国WTI、中东普氏窗口都是欧美主导下的成熟基准油市场,但随着WTI原油纳入布伦特价格体系,以及阿布扎比洲际交易所(IFAD)推出穆尔班原油期货,全球基准油市场正迎来一场革新[8-9],我国与欧美在新机制和市场上处于相近“起跑线”,且我国拥有实货需求规模优势,可通过实货与期纸货协同,深度参与价格形成,更多地把消费国“声音”传递给国际基准油市场,提升整体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大资源”战略下,我国石油进口企业将围绕低成本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从套期保值角度提出更多对国内期货市场的需求,在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规则“走进来”以及我国相关制度“走出去”,加速国内期货市场与国际接轨,更好发挥期货市场在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