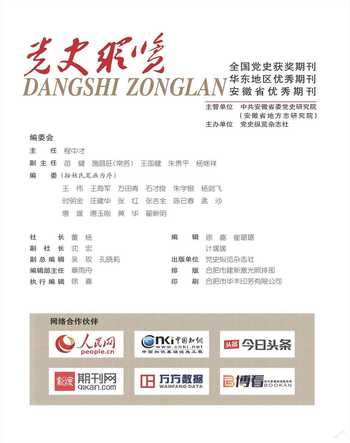毛泽东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艺术
张家康
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对此,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和美术评论家傅雷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语言艺术高手。”
博洽多闻
196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与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握手并说:“我读过你的文章。”这使得坂田昌一十分惊讶和喜悦。当时接见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场。第二天,周培源、于光远二人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们。于是,他们猜想毛泽东可能要和他们谈谈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
果不其然,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谈起了这篇文章。毛泽东“或躺,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使我们毫无拘束,就像在老朋友家里做客一样。这次一直谈了三个钟头”。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
毛泽东密切关注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给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后来,杨振宁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轻松和漫谈性的谈话,毛主席非常有办法使我不感到拘束。”当时,毛泽东与杨振宁进行了广泛的谈话,谈的最多的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论,还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惠施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但是看不见‘马。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看不见‘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宇称不守恒原理:“宇称守恒,宇称又不守恒。我是赞成宇称不守恒。”杨振宁坦言,毛泽东所引用的公孙龙、惠施的话,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感觉毛泽东“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的伟人之一,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对于思维过程、对于各个领域的概念都感兴趣。”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对毛泽东也有同样的印象。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让李政道惊讶的是,一见面,毛泽东就想了解物理学中的对称问题。他们谈到了理论与实践、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当李政道讲到科学研究总是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时,毛泽东说:“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毛泽东对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极有兴趣,希望李政道予以演示。
李政道回忆说:“我们的座椅之间是一个茶几,上面放着铅笔、笔记本和两杯绿茶。我把铅笔放在笔记本上,把笔尖指向毛泽东,然后再把笔尖转向我。铅笔转过来又转回去。我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样的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
在与外国友人的交谈中,毛泽东一方面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另一方面又风趣横溢、诙谐幽默。一次,毛泽东在会见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时,这些阿拉伯的朋友们谈到了各国间的纷争。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突然,他问起了客人:“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看着满脸诧异的客人们,毛泽东笑了起来,又连连发问:“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客人们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对客人们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位众神之主,叫‘玉皇大帝。”说着又话锋一转:“如此看来,天上也不会平安,因为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客人们听罢哑然无声,过了一会儿,又都一起拍起手来,钦佩毛泽东是一位想象力丰富又含蓄蕴藉的智者。一件事、一句话,由他的口中而出,就能被赋予新的含义,打开人们的思路。
通晓古今
1936年7月,红军大学迁到保安。这里条件十分简陋,唯有石洞多,石洞里供奉的多是道教元始天尊。红军大学的师生们用3天时间,自己动手清理石洞,整理出了一所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开学这天,毛泽东前来祝贺,他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元始天尊是传说中的主持天界之祖,是道教上清派信奉的最高神。毛泽东在这里以“元始天尊”的弟子比喻学员,鼓励他们好好“修炼”,学好知识,随时准备下山,以迎接革命斗争的风暴。
1939年3月,由红军大学改编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编成第五纵队,即将开赴敌后根据地。行前,纵队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前来做动员报告。一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通俗化的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下山的故事,他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给这位老头三样法宝:一是杏黄旗,二是四不像,三是打神鞭。现在同志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不久,这三样法宝的提法,正式出现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1957年6月,毛泽东派车去迎接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图书校勘专家冒广生(鹤亭)到中南海晤谈。冒广生的儿子、剧作家舒湮也陪同前往。毛泽东熱情地接待了他们。冒广生觉得毛泽东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当时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冒广生指着舒湮对毛泽东说:“我儿子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两人由此聊到了历史上真实的秦桧和宋高宗赵构,毛泽东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他指出:“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毛泽东还当场吟诵了文徵明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一作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以此表明自己对这件历史公案的态度,冒氏父子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
1958年8月,毛泽东到江苏视察,时任省委书记江渭清汇报了特大台风的危害。毛泽东接过话茬说:“台风也可以一分为二呢。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从汉中出兵,一路打到徐州,正在兴高采烈与文武百官置酒庆祝,项羽率领三万轻骑突然来袭,把刘邦打得措手不及,大败而逃,项羽衔尾而追。刘邦正在危急的时候,突然天上刮起一阵台风,顿时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项羽只好收兵。刘邦才得保存性命,率残部逃回洛阳。”他以此说明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只要善于总结规律,相机而动,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毛泽东好学多思,每接触新事物都要认真研究一番,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1964年8月24日,在与人谈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辛弃疾的这首词是《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毛泽东认为他们都有朴素的科学精神,这些诗句包含地球是圆形之意。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话。在同刘大杰谈论文学史时,毛泽东说:“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随后,毛泽东又谈到梁武帝,谈到了范缜,谈到了唐宪宗,又由清代的乾嘉学派谈到了桐城学派,谈到了龚自珍。毛泽东说:“乾嘉学派‘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桐城学派‘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龚自珍‘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学派;后来又有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
寓庄于谐
毛泽东常用生活中的事例来入情入理地阐述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一些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战士都还记得,毛委员在闲暇时,会坐在黄洋界的一棵大树下和他们侃大山,摆龙门阵。欧阳毅将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还形象地比喻‘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把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在给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做报告时,毛泽东尤为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一次,他在给红军战士演讲时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必须懂得革命的道理,而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掌握不了那么多。我今天只讲‘二三四这三个字的道理,请大家用心记住。”他接着说,“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战争不断,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要用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四,是指革命军队除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建立工农武装,主力才会有后备军;第三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对立起来,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建立我们的政府;第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
毛泽东只用三百多个字和几分钟的时间,寓庄于谐、化繁为简,用最通俗的语言,让工农战士们好懂易记,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后,凡听过这场演说的人,仍对这场演说记忆犹新。
军委二局是技术侦察机关,地位十分重要。可由于特殊的机密性,该局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功绩都不能公开。毛泽东非常关心军委二局,常勉励他们做革命的无名英雄。1939年秋的一天,毛澤东来到军委二局,在讲话中夹带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需多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了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鞋的小石头,经过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比喻恰如其分、深入浅出,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听了后心明眼亮,备受鼓舞。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艺术教育家王朝闻曾说,自己对毛泽东的“信仰虽有崇拜性质,但在认识上却不是盲目的”,“是他那历史的功绩、富于个性的言行,直接间接地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初,王朝闻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有两件事给王朝闻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一件是他穿着有补丁的衣裤,在广场上给鲁艺全体师生作报告。当讲到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引用‘黔驴技穷的寓言时,还模仿了驴子的一个动作,用一只脚向后一蹬,引得大家都笑了。我自觉在这样的笑里,主要不是觉得这个动作滑稽,而是它体现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切关系。……另一件,是院领导陪他到西山看望工作人员。当走到我的窑洞门口,听说我是搞雕塑的,他立即说:‘你是做泥菩萨的。……感到他应用群众语言的习惯,和这种语言也有幽默特征。”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出访苏联。当飞机腾空至几千米高空时,毛泽东和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讨论起哲学问题,他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尤金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回应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哎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尤金无奈地耸了耸肩,毛泽东笑了:“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毛泽东比划着说,“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在场的人听了都心悦诚服,尤金连声夸赞:“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如坐春风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对象,无论是名流学者和党政军领导人,还是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他都能善于针对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做到以理动人、以情感人,使人时雨之化、如坐春风。
1938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抗大作报告,在讲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时,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说起了《西游记》。他说,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猪八戒缺点不少,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孙悟空很灵活、机灵,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动不动就回花果山,三心二意;还有小白龙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终于取得真经。这种寓教于乐的政治宣传教育方式,很受学员们的喜爱,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
毛泽东历史知识丰富,常以通俗的方式,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普及历史知识。例如有名工作人员来自河南荥阳,毛泽东便问他:“荥阳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头一关,你知道吗?”又说,“你知道河南的简称为什么叫豫吗?因为古代河南是出大象的地方。”
1958年8月,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视察大江南北。一天,张治中向毛泽东介绍随行的秘书余湛邦。“是干钩于吗?”毛泽东问。“是人禾余。”余湛邦回答。“yu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禾余,有人刖俞,有口人刖喻,有虞姬的虞。”毛泽东温和而又诙谐,说到这里,又用手指着奔流的江水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他又补了一句,“其鱼甚多咧!”谈话风趣,态度平易,一下子就消除了余湛邦的紧张和拘谨。
1962年12月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崔英在一次周末晚会上遇見了毛泽东。当毛泽东知道她的姓名后,笑吟吟地说:“那么你的爱人可能姓张了。”看到崔英的一脸茫然,毛泽东又笑了,“你读过《西厢记》吗?”崔英恍然大悟:《西厢记》写的是书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毛泽东这是用自己的名字开玩笑呢。崔英笑了,回答说读过。毛泽东又问读的是哪个版本,崔英回答是王实甫。毛泽东告诉她:“你应该再读董解元写的《西厢记》诸宫调,那本写得好,文词写得美。”
毛泽东语言机智幽默,善于以语言技巧,化解见面时的生疏,打开会谈的话匣子。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在他的书中回忆过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场景:“基辛格问他身体如何。毛用手指着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毛用一种哲学家的语气说道:‘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接到上帝的请柬。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说出这种话,真使人大吃一惊。基辛格微笑着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毛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好吃力地在一本便笺簿上写下:‘我服从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毛的幽默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特色。”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也给了类似的评价,他说:“毛泽东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话语当中。”(题图为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责任编辑:孔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