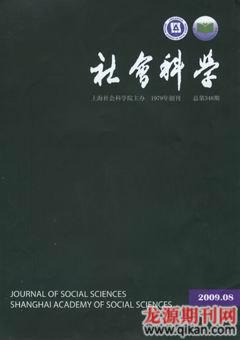婚姻礼仪:一个多学科的分析框架
摘 要:从已有研究来看,婚姻礼仪的研究处于多学科的分析框架内:历史学视角重视脉络辨析;民俗学视角重视文化解读;人类学视角侧重意义追寻和理论探讨;社会学视角侧重社会变迁和宏观背景。目前的婚礼仪变迁研究在连贯性、系统性、研究重心分布、研究视域以及中西理论视角差异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树立问题意识、加强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双重分析是婚姻礼仪多学科研究的关键。
关键词:婚姻礼仪;多学科;分析框架
婚姻礼仪研究,是从文化维度对社会变迁的探讨,它在理解中国社会变化上具有独特性,由于婚姻礼仪能丰富指示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人际网络和仪式规范等,因此,婚姻礼仪的研究,将是对中国社会变化文化维度的审视和深度解析,通过研究社会变迁背景下婚姻礼仪的兴衰状况及其背后社会力量的变化,可以解析它和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这对婚姻礼仪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婚姻礼仪研究成为一个多学科分析框架的根本原因。
一、 概念梳理
1.概念及其研究范围
婚姻礼仪研究涵盖范围较大,大致而言,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传统婚姻礼仪中的仪式变迁研究。婚姻礼仪研究既关注那些传统礼仪形式的变迁,也关注那些派生和新生的礼仪形式。婚姻礼仪研究在不舍弃以往的研究重点的前提下,还把重点扩及到它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变化过程。研究的礼仪形式不仅有较大的正式的礼仪如传统六礼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等,还有细微和非正式的礼仪形式如定情、做媒、相亲、吃茶、嫁妆、哭嫁、花轿迎娶、传代、撒帐、闹新房和回门等的变化。(2)婚姻仪礼中的礼物研究,如聘礼、陪嫁、信物、定情物和其他礼品。礼物是仪式的符号代表,富有象征意义,因此也是解读婚姻礼仪的关键,如体现大家族思想的“茶礼”①,也有体现政治倾向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②,还有体现消费实力的金银钻饰等,所以婚姻礼仪研究将关注各种仪式场合如订婚、婚宴和满月礼中亲友所提供的物品或礼品的种类、数量及其时代特征等。(3)对婚姻礼仪场合及其过程演示的研究,如订婚、拜堂、婚宴、满月宴和婚庆纪念活动等。这其实是通过仪式活动、参与人的角色分配及其场景展示来考察仪式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力量状况,以期探讨在社会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仪式参与者之间潜在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4)婚姻礼仪背后的社交关系网络。通过婚礼或节庆活动中亲族内部各成员间的拜访或馈赠等交往状况,来探讨这种仪礼交往背后网络维持和社会支持的延续或变动状况。(5)婚姻礼仪中传统文化内涵及其演变的解读。关注那些特定仪式中的乱语禁忌、生子祈福和文字祝语等,这里探讨婚姻礼仪主旨的变化,如体现宗族思想的生育文化在婚姻仪式中地位的降低,以及体现商业消费侵入的享乐文化地位的提升等。(6)各种新生或派生婚姻礼仪的研究。关注那些突现或普遍化的新生仪式,如婚纱照,同时关注一些具有持续性、重复性或周期性的派生仪式,如结婚纪念活动和情人节等,由于这些新生或派生的礼仪形式日益渗透到日常家庭生活中,所以对其研究可以透析现代性力量在婚姻礼仪中的侵入或增长状况。
中国婚姻礼仪有一个特殊类型划分——传统/现代,大致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新婚姻法的颁布为时间界限。这种观点认为传统婚姻礼仪相近于古代婚礼仪式(以六礼说为主,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式繁琐,否定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而现代的婚礼礼仪则指剔除了具有封建因素的婚姻礼仪,具有仪式简化、倡导性别平等和肯定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的特点。然而,这种关于婚姻礼仪二元对立的提法也存在问题,即忽略了婚姻礼仪更为复杂的变迁过程和多样的影响因素,因为无论婚姻礼仪变得多么现代,它也是从传统的婚姻礼仪中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嫁接和更替过程在二元独立的简化解释中容易被忽略,同时现代婚姻礼仪还受到了市场化理论和消费文化的影响,这些都容易成为传统/现代二元简化解释中的盲点。因此,关于婚姻礼仪的传统和现代之分是对中国婚礼仪礼剧烈变迁,特别是某些婚礼形式突变及其混乱呈现的一种语言表达自觉,有关这种二分法的合理性尚缺乏反思和深究。
2.婚姻礼仪研究的意义
婚姻礼仪研究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前者指它能推进婚姻家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后者指它能增进大众对社会变迁的理解。
就学术意义而言,婚姻礼仪,作为一个多学科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开展有助于拓延传统的婚姻家庭学研究。婚姻礼仪是婚姻的一个基本面,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它是理解和解释现代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仪式在婚姻家庭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得到了重视。一项对中产阶级婚姻家庭中礼仪(ritual)和奥秘(myth)的研究发现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凝聚和团结出现问题的原因: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实践独立和分离的礼仪和奥秘叙事,事实上与家庭强调团结凝聚的价值观念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注:Steven M. Tipton & John Witte Jr.(eds.), Family Transformed Religion,Values and Society in American Life,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 D. C.,pp. 196-207.)。社会家庭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逐渐趋于冷门,其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结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和代际关系等亟需拓展,婚姻仪式结合了其他人文学科如人类学和民俗学,后者可以为婚姻家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解释视角,因此婚姻礼仪研究是婚姻家庭研究融合多学科研究的一种表现,有利于婚姻家庭研究新领域的不断拓展。
就现实意义而言,婚姻仪式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连续性。对于婚姻礼仪变迁的看法有不少误区,要么认为中国婚姻礼仪还在沿袭传统做法;要么认为中国婚姻礼仪已完全脱离传统。其实,中国的婚姻礼仪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性进程,其中既有传统形式的延续,也有现代形式的新生,还有传统和现实形式之间的某种变相结合。婚姻礼仪的多学科分析,既能理解变迁的脉络性进展,也能理解变迁涉及的层面和程度。如在对婚姻礼仪中新旧礼仪形式的消长研究中,我们不但关注旧礼仪(如订婚的一度缺失和媒人婚介的衰落等),还关注新兴仪式(如拍婚纱照仪式和结婚周年纪念仪式等)和一些仪式礼节的延续(如满月酒等),通过这些可以考察中国婚姻家庭的价值观、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过程,而这些又都与传统因素的断裂或延续、现代性因素的生成及发展以及两者间交互作用等深层次问题紧密相关。
同时,婚姻礼仪及其变迁研究,是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回应。婚姻礼仪是中国传统礼仪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昏礼者,礼之本也”,这是说婚礼是礼之根本,从发生学讲婚礼是礼之得以产生的根据或伦常最原始的基础(注: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4页。,在对中国古礼的“五礼(吉、佳、军、宾、凶)”、“八礼(丧、祭、射、御、冠、婚、朝、聘)”和“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的概括说法中,婚姻礼仪是其中根本的一项(注:朱宁虹主编:《中华民俗风情博览》卷一《礼仪生活》,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婚姻礼仪,作为中国传统仪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体现后者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礼仪从其本质来看是一种和谐文化,它强调秩序和规范,因此,婚姻礼仪研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它可以为和谐家庭建设和公共政策的文明建设提供最新的社会服务经验,为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文化提出新的建议,使其及时注入新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内涵。
二、婚姻礼仪的多学科分析
婚姻礼仪的研究应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应用和分析。就对目前婚姻礼仪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有关婚姻礼仪的研究成果已呈现出了一种多学科的分析框架,然而,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因而研究侧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如下:
1.侧重脉络辨析的历史学研究视角
历史学对婚姻礼仪的研究,多关注婚礼仪式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关于婚礼的起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婚礼原为“昏礼”,从“昏”的天时时段推断婚礼源于抢婚,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其是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个体婚的原型(注:黄浩:《昏礼起源考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还有学者详细解释了婚礼中更为具体的礼节的由来及嬗变,如铺床、迎娶、下轿利市、拜堂、喜宴、坐帐、撒帐、闹房、拜舅姑和回门等(注: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王萍概述了我国古代婚姻礼仪及其演变和发展,以上古传说以及周、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等朝代更替为线索,介绍了婚姻礼仪的大致状况,其中在周代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婚姻礼仪,即所谓的婚娶“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后世的婚姻礼仪便是以此为基础得以发展:宋代以“亲迎”作为最隆重的婚姻礼仪,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内容保留至明清时代,即使现在也还行之于某些地区和村落(注:王萍:《中国古代婚姻礼仪述略》,《南都学刊》(哲社版)1995年第4期。)。
2.重视文化解读的民俗学研究视角
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多注重对婚姻礼仪的文化意义进行探讨和解说。对婚娶“六礼”及相关仪式如哭嫁(注:彭谊:《隐藏在民间哭嫁与哭嫁歌中的女性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的解说数不胜数,如有研究者认为在“纳采”中男方向女方求婚用雁作礼品,主要是借助鸿雁顺乎阴阳飞行有序的自然属性,体现人们对家族秩序的期望,“纳吉”则是男方在家庙问取求婚女子姓名的吉凶状况,主要是为了取得自己祖先神灵的认可和保佑
等等(注:吴成国:《中国人的礼仪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作为中国人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闹洞房”,对新人及其家庭关系的适应和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尚会鹏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系统地解释“闹洞房”的社会功能、巫术功能及其与性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闹洞房是一种具有明显积极作用的群体参与行为”(注:尚会鹏:《闹洞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3页。)。
3.侧重意义追寻和理论探讨的人类学研究视角
人类学研究离不开田野实践,就婚姻礼仪而言,人类学多研究原始群落的亲属关系及其相关的各种仪式,尤其注重对仪式象征意义和喻指的解读,如非洲恩登布人(Ndemb)婚礼前的女孩子的入会仪式(initiation ceremony),其隔离做法是为在婚礼作准备(注:[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页。,非洲中南部本巴人(Bemba)结婚前针对女子的成年仪式“奇孙古”(Chisung)中充满了对女孩子的肆意嘲弄,而这种嘲弄是为了锻炼她们的意志以适应婚后生活的磨难(注:汉德尔曼:《仪式/壮观场面》,《国外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某些地区的婚姻礼仪中也有类似做法,如广东某地区,待嫁女性要隔离生活一个月,在一个特意预备的房子中由同龄姐妹陪伴生活,这种隔离生活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婚姻生活的苦难和责任做准备(注:Freedman,Maurice,“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玊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273-295,p.292.)。
人类学领域内的理论研究,为婚姻仪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仪式,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也是基础性的研究领域,因此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的仪式研究成果,特别是理论研究。在有关仪式的理论探讨上,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仪式功能理论,涂尔干关于仪式是神圣/世俗的区隔的认识,纳普对仪式的过程性研究及阶段(分离、过渡和组合)和阈限(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划分,后仪式研究大师特纳对仪式过程的特征的深入探究(仪式阈限的模糊性、仪式角色的可逆转性、仪式阶段的封闭状态、仪式展示过程的权力场域)(注:[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 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3-110页;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都为婚姻仪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
4.侧重社会变迁和宏观背景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社会学的婚姻礼仪研究,多与社会转型及结构变动的宏观背景相关。李银河通过个人生活史的深谈,较细致地描述了北京一户林姓后代从1934—2000年的婚礼变迁状况,在讨论婚礼变迁的过程中,李银河发现影响婚礼变迁的因素不仅有时代特色,还有社会阶层因素(注:李银河:《婚礼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通过分层多阶段系统抽样方法对上海的1092户居民的调查中,徐安琪等人研究发现婚礼形式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大致而言,20世纪60年代,上海婚礼的主要形式是双方家庭聚餐;70-80年代婚宴逐步成为首选婚礼形式;90年代旅游结婚颇受青年青睐,而俭朴的茶话会形式和集体婚礼较少被上海青年所接受(注:徐安琪、王莉娟:《90年代上海家庭变迁——上海市家庭调查报告》,载沈崇麟等主编《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吉国秀通过对东北清原镇20多年的婚姻仪礼变迁研究,尤其传统婚姻仪礼如订婚的复兴,发现婚姻仪礼变迁其实是地方民众应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变迁的一种策略反应,正是在婚姻仪礼的变迁中,民众重组了传统婚姻仪礼、重构了社会网络,同时在婚礼经费的支付中姻亲比重不断加大,预示着亲属关系中双系平等化发展的趋势(注: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993年徐安琪通过对798对上海夫妇与各自配偶父母的联系情况进行统计表明,在两性平等意识日渐内化为人们自觉行为的上海,家庭网络已实现向双系并重过渡,无论平时还是节日,夫妻与亲属间的交往频率均未呈现向夫系亲属倾斜的趋向,反而有倚重女系亲属的端倪(注:徐安琪:《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在对太仓农村的300户居民的调查中,王伟发现节日中亲属关系的来往情况具有新特点:来往比例最高的亲属是“妻子的父母”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印证了家庭制度的双系化和家庭网络支持的女系依重(注:王伟:《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并存——太仓农村家庭调查报告》,载沈崇麟等主编《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三、婚姻礼仪多学科分析中的重点
在多学科的分析框架下,婚姻礼仪的研究出现了趋同和集中的特点,这种研究态势与婚姻礼仪研究依赖的学科背景关系并不大,而是与婚姻礼仪研究中向来的研究重点和趋向有关,大致而言,有关婚姻礼仪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三个方面:
1.婚姻礼仪与亲属制度的关系探讨
婚姻礼仪的探讨离不开对亲属制度的关注。婚礼,从词源意义来看,它是两个不同的家(宗)族联姻交好、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开始(注: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的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4页。;但这种亲属制度的研究多富有批判性,这是因为传统婚礼的形成、流变,其核心的价值观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是一种妻为夫纲和传宗接代的庆典(注: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婚礼仪式上新娘的哭嫁行为,就是表达了女性对这种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婚姻的微弱反抗(注:万建中:《“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彭谊:《隐藏在民间哭嫁与哭嫁歌中的女性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但在婚姻仪礼与亲属制度关系的理论探讨上,却一直存在“家系论(decent 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 theory)”之争,其争议根源是对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认识不同,前者强调争论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而后者认为婚礼的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乱伦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联姻网络是组建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些理论讨论多集中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注:吉国秀:《婚姻习俗研究的路径:评述与启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婚姻礼仪与家庭成员人生礼仪关系的探讨
在婚姻礼仪研究中,有的还注重仪式对参与者主体性影响的研究。该研究探讨婚姻仪式对仪式参与主体身份转移和人生经历塑造的重大影响,因此多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仪式参与者在仪式中以及前后角色、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变化上,John W. Engel Source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统婚礼是一种转移仪式(transfer ceremonies),因为经历婚礼的女性遵从了传统的从夫居,婚后女性不仅仅是到丈夫居处和其生活在一起,而且是通过放弃自己在娘家的居处、身份和作为女儿的权利来成为夫家的一个新家庭成员,即成为夫家媳妇的身份(注:John W. Engel Source,“Marria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of a New Law”,獼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玍ol. 46,No. 4 (Nov.,1984),pp. 955-961,p.959.);尚会鹏着重研究了婚礼中的一个礼仪环节——“闹房”,认为闹房是具有明显积极作用的群体参与行为,同辈群体的戏谑有利于密切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关系,加速新娘角色的转换、适应夫家新环境(注:尚会鹏:《闹洞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93页。)。
3.婚姻礼仪的形式变迁及变迁动因的探讨
在对婚姻礼仪的变迁看法上,有研究者认为,整体上来看婚姻礼仪中的婚礼呈现了一种简化的趋势(注:薛亚利:《婚姻关系》,载陆晓文编著《上海社会发展与变迁:实践与经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在对婚礼变迁的具体探讨涉及形式的历史变迁,如注重“六礼”的传统婚礼,拜天地、旅行结婚、茶话会、家庭聚餐和现代婚宴的过渡或更替等,在对婚姻形式的变迁探讨上,还涉及到更为具体的方面,如婚礼礼品从简到繁的变化(注:李银河:《婚礼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婚礼消费从少到多攀升,婚礼支付的亲系的转移性变化(注: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婚姻仪式变迁探讨还涉及到城乡差异,John W. Engel Source认为城市里的婚姻变化要比农村地区显著,婚姻法的颁布和执行在城市里要比农村成功(注:John W. Engel Source,“Marria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of a New Law”,獼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玍ol. 46,No. 4 (Nov.,1984),pp. 955-961,p.960.),中国人的旧式婚姻以“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择偶标准和结合途径,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大城市已基本绝迹,而“介绍”方式成为城市婚姻的主要结合途径(注:谭深:《家庭社会学研究概述》,《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婚礼形式的变化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变迁动因的探讨。针对婚礼礼仪的简化,吉国秀认为订婚的取消或结婚仪式的俭省,主要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国情造成的,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之际的经济窘困是最终根源,她对东北清源镇的婚礼研究发现,1958-1961年的挨饿期间,居民的物质财富除了用于生活以外所剩无几,很少有能力举办订婚和婚礼(注: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然而,有学者认为婚礼仪式变迁的动力来自国家权力及其颁布的法律政策。John W. Engel Source认为新中国成立之际颁布的新婚姻法导致中国家庭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如新婚姻法颁布导致婚姻的合法性从仪式举办转移为登记程序,因此取代家庭与家庭联合作用,国家现在控制一个人和“谁”、“何时”和“如何”结婚(注:John W. Engel Source,“Marria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of a New Law”,獼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 46,No. 4 (Nov.,1984),pp. 955-961,p.960.,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重新塑造了婚姻中两性的亲密关系(注:Freedman,Maurice,“Rites and Duties,or Chinese Marriage”,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255-277.)。然而迪亚蒙特却认为国家无力改造婚姻家庭,因为国家期望通过改造婚姻来实现政治目标的家庭革命只是一场乌托邦,毕竟婚姻家庭是最难以撼动的社会层面(注:Neil J. Diamant, 玆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獴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薛亚利:《家庭革命的乌托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6月号。)。
四、婚姻礼仪多学科分析中的问题
从现有关于婚姻礼仪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能体现婚姻礼仪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分析框架,但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而言,现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是因为婚姻礼仪的研究成果在连贯性、系统性、研究重心分布、研究视域以及理论视角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具体而言:
首先,婚姻礼仪变迁研究的连贯性问题。以往对婚姻礼仪变迁的研究,大致有一种共识,即认为新中国成立是传统婚姻礼仪和现代婚姻礼仪的划分界限,但这种判断无法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何中国婚姻礼仪变迁会出现一个突然性的转变,即为何传统的婚姻礼仪会出现突然性中断?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和更为复杂的国家权力运作以及社会转型等问题的探讨相结合,以往研究中相对缺乏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对婚姻礼仪变迁的探讨也缺乏对婚姻礼仪中各种形式礼仪的变迁状况的分类的专题性研究,如婚纱照、婚宴和满月酒礼仪的历史变迁探讨。
其次,婚姻礼仪研究的系统性问题。婚姻礼仪的学科研究分割,造成对婚姻礼仪研究从整体上来看缺乏系统性,历史学侧重对婚姻礼仪发展脉络的梳理,民俗学侧重习俗及文化含义的介绍,人类学着重发展仪式理论等。就婚姻礼仪主题而言,这些分布在各个学科内的研究成果之间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很多研究只是相关性或涉及性的片段研究,而非专题性研究。
再次,婚姻礼仪研究的重心不均衡问题。就目前的婚姻礼仪研究状况来看,明显存在研究重心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研究古代婚姻礼仪的多,而研究现代婚姻礼仪的少;介绍婚姻礼仪某个方面的多,探讨婚姻礼仪系统构成的少;描述婚姻礼仪大致状况的多,探讨婚姻礼仪整体变迁的少;分析婚姻礼仪和亲属网络关系的多,探讨婚姻礼仪和主体身份以及人生经历关系的少;研究婚姻礼仪形式变化的多,探讨婚姻礼仪变迁动因的少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婚姻礼仪研究领域空间还非常大。
又次,没有注意到婚姻礼仪研究中的冲突问题。婚姻礼仪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盲区,就是忽略了婚姻礼仪中潜在的冲突问题。无论是传统婚姻礼仪还是现代婚姻礼仪,并不是统一的共识性的仪式演示,其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具体如在对订婚或结婚的礼品数量、日期选择、礼仪形式、礼金额度等的看法,姻亲本亲和新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这些冲突的背后涉及到礼仪参与者们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婚姻仪式从来都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抽象物,这对于现代的婚姻礼仪来说尤其如是,日益开放的社会分层及日趋增强的社会流动让异地通婚增多,让仪式融入更多的地域差别,同时经济地位的纵向分化也让婚姻礼仪牵扯利益纠纷,这些都让礼仪具有更加多样性的呈现以及引发相互碰撞冲突,因此对婚姻礼仪中的冲突研究将是不可或缺的一块,然而,婚姻仪式内含的冲突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予以注意。
最后,婚礼礼仪及其变迁解释上的中西理论视角差异问题。在婚姻礼仪的认识和解释中,有些研究运用的是西方的理论,如人类学的仪式阈限理论,而有些研究运用的是中国的礼仪规范理论,特别是儒家思想,还有些研究是两者的结合,理论视角的不同决定对婚姻礼仪解释的不同,如婚姻礼仪的功能,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解释来看,体现了中国传统“礼”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道德修养的塑造上,也即更强调仪式的控制功能和文化传承(注: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的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但西方仪式理论,特别是从涂尔干、纳普和特纳等人的仪式理论发展脉络来看,他们更强调仪式本身的能动性和反社会结构力量(注:[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202页。)。应该肯定的一点,就中国婚礼仪式的变迁解读中,中西理论都提供了一定的阐释空间,但中西理论及其对婚姻礼仪的解释存在差异和诸多不同,因此,中国的婚礼仪式及其变迁研究,须考虑到中西理论解释的差异问题。
五、婚姻礼仪变迁多学科分析框架的基础和路径
婚姻礼仪,作为一个多学科分析的特殊领域,现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与以往对婚姻礼仪的认识狭隘有关。大致而言,有三类认识偏颇:首先,在婚姻礼仪研究上缺乏问题意识,难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其次,没有认识到婚姻礼仪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性概念,该概念在婚姻礼仪研究中具有显要的地位及作用;再次,没有认识到婚姻礼仪的研究必须把握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重分析,没有认识到其分析要把宏观因素如社会转型和微观因素如主体性转变结合起来,具体如下:
1.问题意识——研究发现
的确,婚姻礼仪研究中某种选题是带有历史色彩、文化性或日常化特点,这也让这些选题一时难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以跻身重大研究领域之列,但这种看法并不尽然,因为在婚姻礼仪研究中,并不缺乏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如在婚姻礼仪变迁上的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婚姻礼仪为何会有一个突然转变?新中国建立后由婚姻法导致的家庭革命对婚姻礼仪到底有何影响?为何有些仪式如订婚会在一段时间废又在另一段时间兴呢?还有一些看起来和传统礼仪理念不相融甚至相反的新仪式如婚纱照,为何会发展为现如今一个普遍化的婚姻礼仪?等等。因此,在婚姻礼仪研究上需要一种问题意识,那种认为婚姻礼仪研究缺乏重大问题的研究,其实是对婚姻礼仪认识的不足。
在婚姻礼仪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其实是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如问题敏感性和方法的多学科应用能力的更高要求,因为在这种问题意识背后,不只是体现了研究者对婚姻礼仪所涉复杂社会事实的尊重态度,同时还体现了研究者对这些复杂社会事实探索的精神。
2.双重分析——研究路径
对婚姻礼仪的多学科分析,必须把握宏观和微观双重分析,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又与个体成员人生和经历紧密相关的特殊文化表象,婚姻礼仪同时又受到中国社会转型、国家控制以及市场开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其分析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加以反观。从宏观层面来看,要着重分析婚姻礼仪背后社会转型期间国家权力控制的变动,婚姻礼仪的历史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婚姻礼仪和国家权力、现代化发展及经济改革变动,还有文化传承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1)从政治角度来看,婚姻礼仪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家庭领域渗入程度的某种变动,中国的婚姻礼仪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积淀的仪式演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婚姻礼仪从相对较复杂过程仪式转变为相对较简略的程序仪式,这是一个突然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和国家强力推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世纪,城市的婚礼举办需要一套独特的合法性获得程序如单位介绍信等,这些都是国家对婚姻具有强有力控制的表现;然而,如今,婚姻礼仪尤其是婚礼的形式选择更多地成为个人的自主选择,婚姻家庭成为和职业领域有着明确区分的私人领域,国家除了一个计划生育控制外几乎不能对婚姻家庭有何干涉。
(2)从经济角度来看,婚姻礼仪反映了经济改革的推动、各种市场化力量的持续生成和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增长。从传统的家族亲友到小型的各种形式的聚会再到中介公司举办的多样化婚礼,市场化力量开始进入到婚礼的举办主体中去;从婚礼的参加者来看,从地缘的家族成员到业缘的职业群体,这反映了婚礼背后社会网络关系的变化;从婚礼形式的某些内在冲突和多变来看,又可以看到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性的不断趋强。
(3)从文化角度来看,婚姻礼仪反映了传统文化影响的式微。传统的婚礼仪式充满了宗法思想,以前的各种仪式如铺床、撒帐等都体现了生育的首位强调,然而在现代的婚礼仪式中生育已不再成为婚姻的首位因素,对两性情感的强调和幸福享乐的追求开始成为婚姻仪式演示的重点,这证明了婚姻仪式中家族意识的弱化。
从微观层面来看,婚姻礼仪是一种具有时间性和礼仪性的社会交往行为,通过这种社会交往行为,既可以探析宏观的滞性传统力量和扩展性现代力量如国家以及市场相互之间的张力变化,又可以审视婚姻礼仪及其变迁对社会成员主体性的影响,从总体而言,中国婚姻仪式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成员普遍主体意识的趋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1)从婚礼仪式的多元化及隐含的矛盾冲突来看,婚姻仪式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婚姻家庭更为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婚姻礼仪经历了从繁到简的变迁过程,但就目前的婚姻礼仪而言,选择繁还是简的仪式形式,往往是当事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所以时下既有奢华场面的礼仪形式,也有简略近无的礼仪形式,这些都体现了社会成员的理性选择;(2)从婚礼仪式中新旧仪式的更替,尤其是各种新兴礼仪,反映了家(宗)族本位向成员本位的转变。传统婚姻礼仪中“媒人桥介”的衰落和“父母之命”的式微,都体现了婚姻的选择从大家族的族群选择中剥离出来,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的选择;(3)从婚礼仪式的性别模式来看,婚姻仪式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两性地位平等发展的历史性的进步。在新兴的婚姻仪式中,“婚纱照”是一种可以观照两性关系变化的新式婚姻仪式,尤其可以反观女性在婚姻地位上的相对提高。
总之,婚礼礼仪,作为一个多学科分析框架,它的研究开展将会非常丰富,也会展现许多研究亮点。说到底婚姻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社会领域,因此也是相对难以撼动和改变的领域,但建国以来中国的婚姻礼仪却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道义合法转向程序合法、从亲族选配到个体自主、从生育价值首位肯定到感情价值首位肯定、从女性弱化地位到两性平等地位等等,这些变迁无疑是强大社会动因推动的结果,对这些动因的解析势必要涉及到分析启动婚姻礼仪变迁的国家力量,具体探究这种力量是如何强力介入和多方位渗透的;同时要分析婚姻礼仪变革中后续的推动力,即市场经济变革是如何具体接替的;还要分析来自文化滞后观念和传统文化力量的牵制,毕竟婚姻礼仪是传统文化积淀的生活领域,对婚姻礼仪及其变迁深层动因的追溯探讨必须是多学科分析的介入。
(责任编辑:薛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