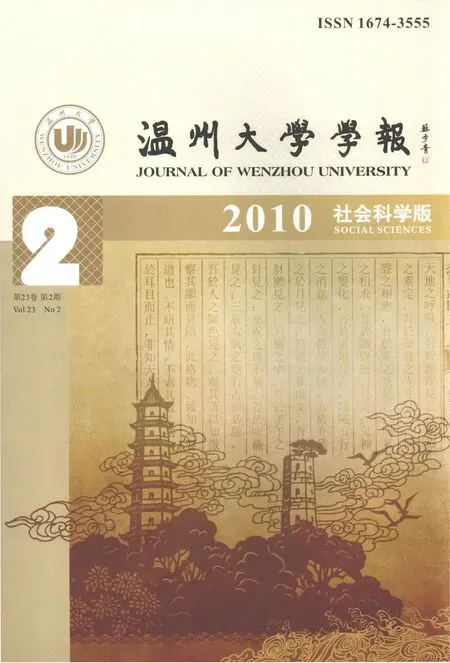从法国“新小说”看后现代主义的悖论
陈婷婷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从法国“新小说”看后现代主义的悖论
陈婷婷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后现代主义迷失在否认定义的文字盘旋之中,已经掉入了定义的陷阱;“新小说”坚信世界和人生毫无意义,这种认知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尤其当它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新小说”反对阐释,拒斥合理的故事情节,而读者受传统阅读心理的制约,阅读时会自动赋予“新小说”以意义和情节的完整性。
“新小说”;后现代主义;悖论;定义;意义;阐释
一、无法拒绝的“定义”
法国“新小说”派是后现代文学中最具争议的流派。被评论家划入该流派的作家的创作风格如此迥异,这让意图概括“新小说”特征的学者一直无从入手。虽然“新小说”派作家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定义以及所谓“新小说”派的创作特征,拒绝被划归到这个惹人注目的阵营之中;但是这种拒斥本身,就足以让“新小说”派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流派。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定义的拒斥意味着现代人开始正视自己思想上的混乱状态。相对主义和多元化是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像超市的商品琳琅满目,顾客可以凭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认为存在是被以及通过个人的行动来定义的——人就是他的作为。对萨特来说,人是自由的,他们应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如果他们做错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宽恕自己。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令人惊愕的自由的责任’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苦恼的源泉。”[1]3自由选择成了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状态。因此,人们需要转换传统的有序观念,认清多元或混乱是这个时代的风貌,也是这个时代文学和艺术的主要特征。
西方文学史上,对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现代派等思潮也曾经有过种种争议和不同界定。罗列权威们所下的定义,选择貌似中庸的观点给予肯定,是国内一些学者介绍这些理论行之有效的做法;但这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却很难行得通。“要想讲述一个清楚连贯的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故事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预设之一就是:当你努力想使本来不连贯的事情变得似乎连贯起来时,歪曲常常也就发生了。”[1]38“新小说”对定义和宏大叙事的拒斥,束缚了想要给它下定义的评论家,因为他们不愿意掉进自己挖好的陷阱之中。
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通过与现代主义的对比,去捕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质。相当多的评论者认为,后现代精神卷曲在现代主义的巨大躯体之中。现代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学术殿堂以及博物馆的经典。以“新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显然不屑甚至反对作为经典的现代主义;但事实上,二者的界限并没有某些文学史所划分的那么清晰。现代主义的很多努力,如达达主义致力于填平日常经验和高雅艺术之沟壑,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引以为豪的举措。很多现代派艺术家的创作已然体现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当杜尚买来的抽水马桶在博物馆成了目光所凝视的对象时,它的静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颠覆,一种大胆的消解,一种坚定的宣言:艺术可以是任何东西,没有什么值得顶礼膜拜的,抽水马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博物馆的殿堂,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新小说”派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走得更远,他们普遍倾向于认为:一切都是娱乐。这种观念直接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权被消解。对大多数电视观众而言,百家讲坛和各种选秀娱乐节目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可供观众选择的娱乐产品或精神放松的调剂品。从网络上各种肆无忌惮的评论也可以看出,传统上作为文化代言的大学教授,不复是令人仰视的精神贵族。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面临地位与认同危机的知识分子体验的一种直接而详尽的叙说,是人们对其产品需求减少的结果。”[2]89
“在所有建筑、文学、音乐、艺术、摄影、表演艺术、哲学和批评领域,还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他们使用这个词,都是希望去探索、指明、确立某种断裂,并使之合法化。同时,他们促使人们运用一种新的分析模式,以区别于他们自己领域中已有的分析方法、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后现代主义。”[2]29这种安全稳妥的说法,确实让各类评论者都无刺可挑。最不易被人诟病的说法也许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都是合法合理的,不需要权威来确立标尺。
社会学家康纳甚至指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从外部来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空间了;讨论后现代主义——哪怕是以超脱的考察形式,或者以反面批评的形式——就是成为其组成部分。”[3]14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充分肯定不同解释层面的互补性,努力从如何定义的无谓争论中挣脱出来;却不知不觉地迷失在否认定义的无休止的文字盘旋中。宏大叙事对我们思维模式的控制力量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樊笼。当我们写下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上述特征的时候,我们已经掉进了定义的陷阱之中。
二、消解不了的“意义”
过去,基督教价值观在孩提时代就配备给欧洲人。人生永远有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指向来世,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星球短暂的栖居生涯中好好经营自己的人品。精神上的长期依附所形成的依赖心理,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的松动出现了无法填补的可悲的空白。后现代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自然会带上一抹绝望的疯狂的调子。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反抗性和颠覆性的力量,后现代主义仍然没有放弃对人道主义的梦想。
当今社会,交通和通讯设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发达,人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焦虑。曾经,教堂里的会众都是大家庭里的弟兄姐妹,彼此给对方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现在,戏院影院里的人们只是偶然的集合体,散场后彼此仍然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是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写照。对此,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感受尤为深刻。孤独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任何时代都没有例外;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会用梦想或信仰来赋予人生以意义,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种无意义的生存状态。
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不去建构一个虚假的世界,挖掘一些虚假的人生意义。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被宣告破产,“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在“新小说”派的嘲笑中被质疑、被消解。社会学家戈尔德曼认为罗伯•格里耶和其他人创作的“新小说”是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的极度商品化所作反应的一种表现;在那一条件下,意义和重要性已决定性地从活着的人转向了物品”[3]168。
“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洛德·西蒙曾经说过,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罗伯•格里耶也曾指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他甚至一再宣称,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的唯一的敌人,就是所谓的意义。在格里耶后期的创作以及其他“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中,游戏的精神越来越明显。难道“新小说”果真是无意义的胡乱涂鸦或游戏恶搞么?
康纳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被广为谈论的,经常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骚乱和无序,也许并非是完全的失控、真正的失序;而仅仅表明的是更为深层的整合原则。因此,也许存在一种‘失序的规则’,它允许一种较为容易的控制机制,在有序与无序、地位意识与戏谑性幻想、渴望,情感控制与控制消解,理性算计与享乐主义之间摇摆。”[2]89新小说派认识到世界毫无意义,这种认知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当这种认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文学整合原则的深层基石正在于这种认知。
印刷文字具有“一种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4]换句话说,“新小说”派不得不诉诸于文字来表达他们的观念;而一旦使用了文字这个工具,意义就出现了。而且,“新小说”派作家传达了这个时代的迷惘和失望,他们认识到“人生是无意义的”。当他们确信出路并不存在的时候,这种迷惘和失望就更加震撼人心。表面上看他们仅仅想要陈述客观事实,但最终还是逃不脱价值判断。只要存在价值判断,世界或人生就不再是无意义的。
波德里亚曾指出,“消费社会患了溃疡,必须给它补充一个灵魂。应该说这种关于病态社会的巨大深化,这一拒绝对真实矛盾作出任何分析的神话,身为当代治疗者的知识分子对此负有很大的同谋责任。然而这些人还想把毛病确定到基础层面上去,这便造成了他们先知般的悲观主义。”[5]鲍曼提出质问,“这些知识分子的功能是什么?谁是他们的听众?谁是他们到处寻求和企图对其施加影响的人?他们将向这些人说些什么?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6]“人生没有意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惹人注目的论点和卖点,共鸣之声却寥寥无几。因为对普通读者而言,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三、无从摆脱的“阐释”
19世纪文坛偶像巴尔扎克,试图充当历史的记录员或文坛的拿破仑,在虚构的小说的世界,自信满满地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萨特挥舞着人道主义的大旗,肯定过这种主体性——人是他的行为的总和,人是自己命运的总设计师。在上帝这尊偶像倒塌的废墟上,大写的“人”站起来了。这个人必须要对自己、对世界乃至对人类负责,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我思故我在”映射出的是一个狂妄的“小我”,在他们那里,“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新小说”派的文学使命就是要解构这种主体意识浓厚的传统小说。所以,“新小说”积极地邀请读者参与创作,鼓励读者把阅读小说的体验等同于参与某种游戏。
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从语言层面入手解构了传统侦探小说所构建的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窥视者》讲的是一桩奸杀案。推销员马弟雅思在岛上推销手表的时候,一个牧羊少女被人奸杀了。奸杀案之前,是关于推销员行程的大量细节描述;奸杀案之后,是推销员非常值得怀疑的种种言行举止。而小说最关键的部分,奸杀案的案发经过,却只字未曾提及。那几个小时仿佛从空中蒸发。故事在此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或空白,连作者也指出他能确定的只是奸杀案的发生。断裂和空白成了故事的核心。我们找不到杀人动机,我们一路猜测着凶手却永远得不到答案。读者进入小说的世界,犹如进了没有出口的迷宫。
罗伯•格里耶时时担心读者会把他的文本当做传统的小说甚至真实的记录来理解,担心读者从他精心布置的空白和混乱中整理出清晰的情节线索,给他的文本内容贴上种种意义的标签。他在《走向新小说》中强调,“小说应该坦白承认其虚构功能。”[7]“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这可能形成纯粹组合的写作方式,如他的《在迷宫中》始于一名士兵在一个小镇上的游荡,是许许多多虚假开始、离题内容、若干叙述主题的变化和重复形式的混合;而这些变化构成了小说自身。”[3]180格里耶在文本的叙述中常常插入一个超然于小说人物之外的声音,大谈小说的创作和功用,坦白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
学者们一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我们带着系统阐释的目的去解读它们,但我们早已习惯于在这个表面上嘈杂无序的世界中尽力去发现某种逻辑和某种内在秩序。阅读一个文本,无论是对文本的人物还是主题,我们习惯于给出一个清楚的分析。这种阅读心理和阐释惯习早已形成定势。在阅读和分析中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赋予文本以深度和意义,完全不理会作家的不满和抗议。
阅读“新小说”,读者确实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创作中去。这种参与,与作家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不是参与游戏的乐趣,而是苦思冥想的艰辛。读者孜孜不倦地赋予断裂以完整,赋予文本以意义,寻找清晰答案的冲动贯穿于文本阅读的始终。换句话说,在作者尽力消解意义的同时,读者和批评家正努力在被解构的意义废墟上重建新的意义大厦、新的秩序和新的理解途径,包括赋予其否定和怀疑的品质。从这个层面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是难以实现的。
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与传统的解读方式的矛盾,体现在几乎所有后现代艺术作品的解读之中,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后现代范式的轮廓在文学领域中比在其他领域(比如建筑和绘画领域)要模糊得多,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力极其有限。严格说来,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还没有真正走进普通读者的视界,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理念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的。不经过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洗礼,读者就不会有阅读心理的转变。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创作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那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四、结 语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定义本身就是一种应该被拒斥的“宏大叙事”,因为它会歪曲人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新小说”派的作家们积极响应这种观点。评论家在提及这一文学流派的时候,虽然也会反复强调“新小说”派对定义的拒斥,承认各种争论和异议的合法性,尝试新的分析模式,这种努力本身其实就是在为“新小说”设立新的定义。可见传统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评论者难以跳出定义的陷阱。后现代主义坚决拒斥意义。“新小说”最为标新立异之处,可能就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传统认知的彻底否定。他们认为,既然人生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要在文学中徒劳地虚构意义?但当“新小说”派作家写下“人生无意义”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传达现代人的迷惘和失望,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新小说”派作家一再强调其作品的虚构性质和混乱特点,反对读者去理解和阐释他们的作品。而读者在传统阅读心理的指导下,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在搜寻一个完整的合理的故事,赋予混乱以逻辑,赋予作品以意义。后现代主义创作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合作,但是现实中的“合作”反而背离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期望,让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
[1] 乔治•瑞泽尔. 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3] 史蒂文•康纳. 后现代主义文化: 当代理论导引[M]. 严忠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 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5.
[5] Baudrillard J. The Consumer Society [M]. London: Verso Books, 1998: 188.
[6] 丹尼斯•史密斯.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齐格蒙特•鲍曼传[M]. 萧韶,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15.
[7] 罗歇•米歇尔•阿勒芒. 阿兰•罗伯•格里耶[M]. 苏文平, 刘苓,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4.
Analysis of Paradox in Post-modernism through French “New Novel”
CHEN Tingting
(Oujiang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While post-modernists lost themselves in entangling with words of denying definition, they have already fallen into a trap of trying to give a definition. Writers of “New Novel” convinced that the world and life were meaningless. In fact, this conception itself is meaningful, especially when it is expressed in writing. Writers of “New Novel” were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rejected arranging reasonable plots in their novels. But readers, who a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reading psychology, do automatically give “New Novel”meanings and complete plots in reading process.
“New Novel”; Post-modernism; Paradox; Definition; Significance; Interpretation
I565.4
A
1674-3555(2010)02-0084-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周斌)
2009-11-08
陈婷婷(1970- ),女,安徽芜湖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