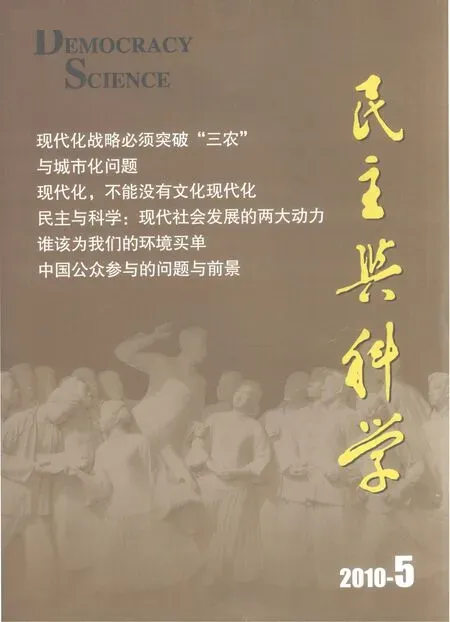现代化战略必须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
■任玉岭
现代化战略必须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
■任玉岭
一、当今现代化的推进必须要切重时弊抓住重点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经历了建国后60年的艰苦奋斗和曲折历程。特别是近32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现代化建设步伐,迎来了跨跃发展。令世人瞩目且惊叹的“中国奇迹”,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推到了世界第二,超越了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00美元一大截。有学者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条件能持续不变或进一步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在2035年前后赶超美国。如此大好形势和美好前景,不仅已经和正在实现着我们革命先烈近百年来抛头颅洒鲜血为之奋斗的梦想,而且也极大地激励着中国每一个人在无比振奋和自豪的同时,更加雄心勃勃,“敢下五洋捉鳘,敢上九天揽月”。
但是,在当前已出现的莺歌燕舞的形势面前,我们还必须要居安思危。特别是在经过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尤其需要“脚踏实地”地看一看和“仰望星空”地想一想。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科学发展观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中不仅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而且讲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感。今天在专门讨论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时候,十分需要冷静的思考一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究竟出现了什么障碍?应重点解决和突破的有哪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步伐,我们必须要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切重时弊、抓住要点,才能为我国现代化的推进提供出更有价值的重要建言。
近十年来,在大量的所见所闻面前,从亲身的实践感受中,我深深地认识到我国当前现代化的最大时弊是“三农”和城市化过于滞后,“三农”和城市化作为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要突破的关键之关键,重点之重点。作为中国现代化战略之举,必须要在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上下功夫。
二、必须把“三农”问题的解决上升为现代化战略的关键
现代化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有它的“全域性”,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现代化不能替代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承认,发展可以有先有后,也允许现代化水平有高有低,但是,无论如何过大的收入悬殊和过大的城乡差距,是不能判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户藉的人口和在城市过着农民生活的人至今还占据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仅从人本主义出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
为了现代化建设,中国农民从建国初期开始,就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的发展做出过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远在1952年到1978年,国家就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资金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1994年间,国家又以“剪刀差”的形式再次使农村无尝的贡献出15000亿元。农村每年平均向城市贡献938亿元。由于长期的取多予少或只取不予,造成中国农村失血过多,广大农村失去了投资能力,农民只有生存的保证,而缺少生财之力,从而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稀缺,交通不便,管理混乱,人均收入过低长期存在。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中国革命、中国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坚持打土豪分田地,刺激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坚决性。解放初的十年中,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接着在农村推行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形式的合作组织。虽然是因为操之过急,造成了对“三农”发展的破坏性危害,但不可谓用心不良苦。包括毛泽东本人,他也是希望农村发展越快越好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支持农村改革,实行了田地的包产到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后来邓小平在提出要在上世纪未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一是界定了800美元的小康标准,二是同时强调了要使占人口总量80%的农民达到小康的重要性。为了认真解决“三农”问题,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指示,就是“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先后共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为推动农村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而出台的。应该说我们的“三农”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多数农村面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由于农民的话语权过弱和农村不易创造“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所以,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较少愿意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到农村去。正因为这样,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并非十分得力,由此产生的以下两个突出问题,正在抑制住我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一)全国农业产值在GDP总量中已经降为10%的情况下,还有近70%的人仍是农民或过着农民生活。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没有哪一个农业人口还在20%以上,实际上,远在1998年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均已降到10%以下,美国是2.44%,德国是2.89%,英国是1.9%,法国是3.89%,加拿大是2.83%,荷兰是3.7%,澳大利亚是4.83%,以色列是3.08%,日本是4.78%,意大利是6.16%,新西兰是5%左右,韩国是10.59%,近年来韩国农业人口已经降到5%左右。
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况,绝不是崇洋媚外,照抄照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从中国农村人口过多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现代化的道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允许有过多人口依靠农业为生的。现代化是依靠高的劳动生产率,促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提高的。而在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足1.8亩,而且又要主保粮食生产、大多数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很难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我们是绝无可能把数以亿计的人口留在农业生产战线的。因此,大量减少农业人口,这不仅是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规律问题,而且也是解决分配相对均衡和保全域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伴随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全国农业总产值已经在GDP总量中降为10%,并将继续走低。但是至今我国还有近70%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对现代化的推进已经形成了瓶颈。
我国报出的城市化率是45%以上,但由于有近2亿的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再加上各城市郊区被城市化的几千万农民也还没有真正市民化,所以农民的数量被认为接近70%。去年教育改革中爆出的中小学生中农民子女占80%,这就显示出农民在中国所占比重的过大和对其进行分流与减少的必要性。
(二)全国人均GDP已超过3700美元情况下,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仍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我国的改革发展,是从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起步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可用于发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按照不均衡发展理论,将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率先投入东部地区和城市,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加快发展,而且可以打破当时的“大锅饭”体制,促进竞争,增强发展活力。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招是十分有效的,取得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不均衡发展,也确实造成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至本世纪初我们31个省市的地区差距已经达到1:13,这同当时美国50个州的差距为1:2,英国12个郡的差距为1:1.68相比,要大的多。我们的城乡差距,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1:1.8,90年代的1:2.5上升到2009年的1:3.32。按实际购买力比较,已经扩大到1:5以上。
不管是城乡差距的拉大,还是地区差距的加剧,其利益受损的主要承受者还是农民。如今,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三,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700美元,并已高出中等发达国家平均2000美元一大截的情况下,中国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到1000美元。我们国家农民平均收入尽管达到5600元人民币,已同小康水平相接近,但由于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已出现了平均数字下掩盖的更多问题和矛盾。例如广东省,是公认的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在粤西北和粤北地区的部分农村还仍然贫困。有人比喻以平均值看待问题的弊端说,就如同一个大厅里本来有99人分文没有,而由于外面进来一个百万富翁后,平均起来则全部都成了万元户。贫富悬殊和农民收入过低,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停留在43%。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7,明显高出了世界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今年初连续发生的六次小学和幼儿园血案及富士康连续13次的跳楼事件,既反映了基尼系数扩大后给社会带来的危机和灾难,也暴露出年轻的农民工收入过低和生活压力过大的窘迫局面。
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推进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和水平的情况下,“三农”问题已经演变为最突出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为人而发展,靠人去发展,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今现代化的推进中,一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战略重点,把突破三农问题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三、必须看到城市化推进的缓慢明显制约了现代化的发展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市的大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大发展。实践证明,哪里城市规模大,哪里的经济就大发展。要解决好中国现代化的关健——“三农”问题,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快速进展。
世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在55%以上,日本、韩国当时达到75%。而我们呢?说是城市化率达到了45%,而实际上近2亿的农民工,再加上各城市新入编的郊区农民,他们大多还没能过上市民的生活,将这些人除去,城市人口充其量也只有30%多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同工业化水平相比落后了近20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配置极其不均衡。例如西部12个省区,即使按现行的统计方法,其城市化率仍有9个省区低于30%,云南、贵州、西藏和广西的城市化率还不足20%。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绝大部分集中于沿海省区,而中西部却十分紧缺。如河南省已是超亿人口的大省,而副省级城市却一个也没有。
城市化推进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大城市进入设障过多,城市的明显扩张未能与增加人口职责相对等。本来城市的发展是由资本的大量投入带动的,因此,资本投入越大的地方,就应该承担更多的城市化任务,应该接纳更多的农民变市民。然而在我们的城市化中,投资最多的地方,往往都是拒绝农民在城市落户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都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这些城市最需要农民工,农民工的人数在这些城市往往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当然也有一些另类的超大城市如广东东莞,在那里农民工早已超过1000万人,甚至1个虎门镇就有农民工和外来就业的大学生近百万人。农民工虽然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但他们在大城市定居,却因政策的限制,没有可能。我们的一些大城市,这些年来拼命地进行扩张,大面积地占用土地,修宽马路、建大广场,挖湖泊,造园林,门槛越来越高,就是忘记了让农民变市民。
我国城市化的第四个问题,是对发展三产和服务业重视不够,抑制了就业岗位的开拓。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仅城市就业压力每年就多达千万人之众,况且农村还有剩余劳力近2亿人。如何开拓就业岗位,减轻就业压力,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就是要推进城市化,做好人口的有效聚集。一般而言,人口越大的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越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越大。美国因为有50%以上的人住在大城市,它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0%。世界很多超大城市的第三产业都达到50%以上,有一些可达60%,纽约则达到80%还要多。三产实际是为人服务的,越大的城市分工越细,服务性需求越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城市的很多服务项目,在小城镇是无法成立和不可能创造效益的。所以,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必须要重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至少要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到一定比例。另外,我国的大城市发展中,只重视美化、绿化和亮化,大量拆除下岗工人一条街,商品一条街、摊贩一条街以及街头的农贸市场等。由此造成个体工商户十几年来不仅不升,反而有了明显锐减。所有这些做法,既抑制了就业,也抑制了城市发展,并且也抬高了城市门槛,阻止了城市化的推进,阻碍了农民变市民。
在解决“三农”问题之初,我们就提出了要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分流农民的思路。但是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和既得利益群体要维护自已的既得利益,所以使农民的减少和分流,以及城市化的推进遇到了特大难题。中国到底要不要让更多农民进城和大力推进城市化?以及怎样推进城市化?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理论界的争论也影响了决策层的决心。
此中最影响城市化推进的理由有如下五种:
第一种理由是: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影响下,过份强调了大量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经常用于说教的,一是担心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二是担心出现拉美那样的“城市化陷阱”。为此,人们在中国设计了“两栖类”,让亿万农民工成了城市中永远的“飘族”。理论家认为,这样“进可入城打工,退可回家种田”。如此貌似完美的设计,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并在实践中得到漫延和滋生。但着实讲,这种理论,它不仅使城市化的思维陷入了迟疑和犹豫的泥潭,而且也导致城市化实践走向了凝滞和停顿不前。
第二种理由是: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为理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发展。由于国外的大城市发展中,确实出现过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所谓的“大城市病”,所以我们早期研究城市化的人,一开始就提出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指导性观点。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法律中就已经得到体现。由于这样,虽然很多大城市大量需要农民工,而且很多农民工也工作于大城市,但大城市却拒绝农民工留在城市中。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在大城市已经干了二三十年的农民工,仍不能在城市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他们的子女也长期无学可上。很多农民工已从青年走到了老年,子女都出生、长大成人并成了第二代农民工,但他们依然没有城市户藉可言。他们大多住在城乡的结合部,他们的生活与农民没有二般。
第三种理由是:受“逆城市化”的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成了战略重点。国外的城市化经历过由分散到集中并出现了再次分散的三个阶段。大城市形成后,城市里的生活环境遭到污染,当汽车遍及每个家庭后,很多人把居住地点选到城外的农村。我调查过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洛杉机,其周围都有70多个小城镇。而我国情况与其不同的是,第一个阶段的集中还十分欠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很低,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农民工本土本乡的小城镇,显然是有悖于城市化的推进的。很多农民工把赚的钱弄到老家镇上去建房,而全家还留在大城市工作和发展,这既造成土地资源和农民工财产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市场发育和调动内需。
第四种理由是:“伪城市化”的做法,放缓了对城市化的推进。
我国的城市化由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建设部出台了“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将工作于城市6个月的人都算做了城市人口,于是,城市化率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但是这只是统计口径的改变而已,除此外,对入城的农民工和新市民的待遇毫无改变。经济学家把这种“城市化”称之为“伪城市化”。“伪城市化”像一层迷雾遮住了人们的眼睛,抑制了社会上对城市化的呼吁,改变了社会上对城市化的视听,减弱了决策层对城市化的重视,放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第五种理由是:“户籍制度必须维护”,挡住了城市化的去路。
我国二元经济的形成是由上世纪50年代末实行城乡户籍分治导致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本来在今天电子化、信息化时代是很容易推进的,但一方面由于城市户籍负载有更多的权益和福利,在很多城市人已经忘掉农民当年为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时,很不愿意让那些为今天城市发展再次流下更多汗水的农民工从中分出一杯羹。另一方面客观上存在一种误区,总认为小偷、犯罪都是农民工造成的,对农民工亲近爱护不足,防范惊惕有余,总怕改革和放开户籍之后,给城市造成混乱,增加警察更大负担。为此,有关方面总是把户籍制度视为社会安定的“救命稻草”,不希望改革,不愿意改变。由此直接限制了城市化的推进,也限制了现代化的进展。
四、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必须做好八项工作
(一)农村方面
(1)在农村大力组织和推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
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经济效益,多是农产品自身效益的3~10倍。我国农民人多地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既难以与市场对接,也难以致富和发展。近些年来,虽有一些龙头企业进入农村,并得到国家扶植,但因为农民与企业没有利益联结机制,加工、运输、销售的利益难以进入农民之手。相反,如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河南省刘庄等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农村原来合作组织在改革开放后没有解散并转向与市场对接的结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让农民在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中获得更大收益,一定要在国家的大力扶植下,建立和推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尽快改变农村的小农经营方式,促进农民与市场对接。
(2)成立更多的专门支持农民、投资农村的国家和地方银行。
“有钱才能赚钱”,没有钱必难发展。农村发展难,就难在没有钱。国家财政对农村支持曾长期停留在5%~10%,银行对农村、给农民的贷款长期来极为少见。为了支持农村发展,我们应该像当年农村拿出50%以上总收入支持城市那样,拿出国家更多财政收入和金融贷款回报农村。要制定宽松政策,除建立国家级专业投资银行外,还要大力兴建地方性农业银行,专门支持农民,大力投资农村。可以把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建设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作为资金扶植的对接点。
(3)把教育均衡落到实处,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直管。
农村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展,关键还在能否把农村教育抓好,能否使更多的人才在农村涌现。根据本人的深入调研,在县与县财政收入相差几倍、几十倍的情况下,必然造成义务教育的天差地别。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校开不起英语课、计算机课、还有美术、音乐课,已使很多孩子在起跑线上同富裕地区的孩子拉开了难以追赶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学校“标准化”和“教育均衡化”在很多地方仍停留在口头上的尴尬局面,建议学习国际上较通用的做法,把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直管,特别是欠发达地方的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应由国家财政包起来。以此回报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支持和贡献。
(4)改变资金投放的“钓鱼政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到农村”,这是国家做出的重要决策。但在执行中,多把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在了大江大河和公路的建设之中,而真正涉及农村或农民最渴求的农村基础设施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些粮食产区,自来水建设、水利建设,特别是农村道路建设,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有不少地方生产粮食还没有灌溉设施,依旧靠天吃饭。因此,国家应全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特别是粮产区的农村,把农村道路修起来,把农村的水利建设搞起来。
(二)城市方面
(1)要突破农民工在城市落户问题。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大批农民工。既然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又将永远与城市共存,如此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农民工当市民?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工享受同市民一样的待遇?为避免既得利益者设障和阻拦,对农民工的安置问题不能只靠各个城市随心所欲,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尽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住房问题,不解决住房问题就表明对农民工转市民绝无诚意。考虑到农民工收入过低,廉租房的安排一定要对农民工开放。
(2)要突破中部城市的发展和布局。
考虑到2035年左右,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70%,届时城市人口将达10亿人以上。如何使其中的约5亿以上人口真正在城市中安排好,这需要作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进行筹划和安排。为此,我们一定要在遵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发扬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最能办大事的优势,对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突破及合理布局。
(3)要突破大城市对人口的接纳。
改革开放后,我国真正的城市人口实际只增加一倍,但城市面积却已经扩张7倍。而这些扩张又大多都在大城市,大城市既然占去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财富,就应该承接更多的农民变市民。现在我们的农民工和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大多都飘在大城市,如果大城市不承担这一使命,接受他们,我们城市化的任务将极难完成。从城市容积率看,我国的大城市还存在着接纳新市民的巨大潜力。城市容积率在日本、韩国均为2,我国台湾、香港分别为1.2和1.6,而我国平均才0.5,上海是最拥挤的,容积率也才0.8,比日、韩城市容积率还低1倍以上。因此要突破中国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接纳问题,尤其要高度重视降低大城市的门槛。只有这样城市化才能更好推进。
(4)要突破大城市发展数量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农民变市民的使命繁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有众多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很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周围,发展小城镇不可避免。但作为城市化战略而言,要解决中国数亿人口的入城问题,我们还必须重视大城市发展,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数量和规模都还远不能与中国城市化的任务相适应。
发展大城市是中国国情的特别需要,无论从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岗位考虑,还是从节约土地和保18亿亩耕地红线着想,发展大城市都是需要的。客观实践证明,城市越大,三产的比例越大,服务业就业岗位占总就业岗位的比例也越大。都发展小城镇,三产难发展,服务业岗位难产生,不利于就业安排。另据统计,一般建制镇人均占地155平方米,中等城市人均占地108平方米,大城市人均占地88平方米,特别大城市人均占地仅53.4平方米。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均占地可减少3倍。为此,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减少城市化对土地的占有,也应该把发展大城市作为战略,作为重点。
总之,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今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的关键期。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向新的高度攀升,我们必须切重“三农”滞后的时弊,抓住城市化的重点。只有认真突破作为现代化短板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有一个大的新跨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来得更快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参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