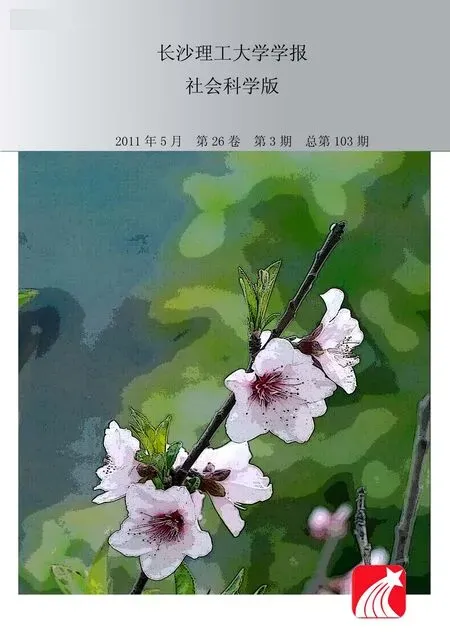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
——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一、从新儒学的产生和语境看其早期思想
新儒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现代哲学于中国从西方移置现代性的军事体系、工业体系、教育体系、学术体系等一整套实体现实的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现代化高度物质文明中的问题,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提出要用中国传统的“心物调和”去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困局,给世界思想画出了一个整体图景: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现在谁都知道,这一论点非常肤浅。然而,在当时却给了被五四运动全盘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反弹的契机,于是清末以来中体西用和国学复兴的思潮,很快以一种新样态重新出现,这就是致力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新儒家哲学。刘述先对新儒家历史,有“三代四群”的归纳:[1]第一代分两群,第一群为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二群为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为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新儒学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一直演进至今的哲学潮流,虽然1949年在大陆悄然消失,但在台湾继续存在,继而扩展到海外,改革开放后才又从台湾和海外回返大陆。对于中国现代哲学来说,主要的问题有:在20世纪20~40年代,新儒家怎样兴起和发展?呈现了什么样的思想?这样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的整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这思想为何在中国现代哲学定型的共和国前期消失?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虽不在此详讲,但却有提必要),这就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定型语汇与新儒学在台湾的语汇之同异,特别是同的一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在深层上的一致性。新儒学的出现和在民国的实绩,主要体现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熊十力《新唯识论》(1923)、方东美《哲学三慧》(1937)、冯友兰“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1939~1946)等功力深厚的著作里。虽然这些新儒家们都怀有用中国哲学提高中国的民族自信心和提高民族的思想境界之用心,而且也要哲学这一无用之大用的特质,努力去大用于中华民族的主体心性转型。然而其主要人物是学术专家,其论述方式主要是学术的,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显出极强的政治化工具化时,新儒学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不得不求诸于学术本身和思想本身的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之归于学术型的大类之中。新儒学从全球的文化互补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这两大方面去宣扬自己的学说,在对全球整体和全球互补的体认中,中国哲学的强项是内圣型的心性和境界,因此二者得到了最大的强调,不但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作用,而且新儒家们还认为具有救世的功能,即由古代型的内圣外王变为现代型的心性和境界而开出民主和自由。这一自家宝藏的体认,都是在与西方哲学框架的比较中突出来的。按照前面所讲的新儒学的三代,第一代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在这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的哲学中特别明显。正因为中国特质是在中西比较中突显的,而这一比较又在一个中国极需经世致用的时代中,从而他们的中国哲学在显出特质的同时,也显出了“落后”的一面。第二代则力图在突出中国哲学特色的同时,大力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同的一面。从唐君毅的《哲学概论》(1963)到牟宗三《中西哲学之汇通十四讲》(1990),都是这一路向。第三代,开始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中突显中国哲学的特质。从中国现代哲学的整体演进来看,新儒学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定型以后的事,对其叙述应该有一个新的语境。而新儒学第一代则正是中国现代哲学定型过程中发生并与之形成一种互动,因此,这里主要讲新儒学第一代的哲学。
二、梁漱溟论哲学特质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一种中西印哲学(尤其是中西哲学)的比较展开,并在比较之中抓住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在梁漱溟自己看来,中国哲学的特质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问题不同,即在设定哲学所处置对象时,西方和印度哲学把对象看成是静体对象,而中国哲学则把对象看成是变化的;第二,方法不同,静体的对象需要的是理智(即西方式的严密逻辑),变化的对象则需要直觉(即中国式的本质直感);因为是把握静体的对象,西方人用了明确固定的概念,为了掌握变化着的对象,中国人的概念是活动的浑融的。由这两大方面的不同,梁漱溟进一步得出了中国哲学的几大特点。为了让这些特点得到突出,不妨继续用序数词予以提示,第三,认定态度与不认定态度的不同。静体的对象和固定的概念,让西方人对二者的关系抱一种明确的认定态度;变化的对象和活动的概念,让中国人对二者的关系抱一种灵活的不认定态度。梁漱溟在该书“孔子的不定认态度”一节中说:
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事实象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推,则成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推去,必至流于墨子兼爱基督博爱的派头;再推下就到了佛教的慈悲不杀;再推不但不杀动物也要不杀害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也不要毁坏他才对;那么这个路你怎么走呢?你如果不能做到最后尽头一步,那么你的推理何以无端中途不往下推?你要晓得不但后来不能推,从头原不应判定一理而推也!所以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我的直觉上对对于亲族的情厚些,就厚些,对于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对于生物又差些,就又差些;对于木石更差了,就更差些。你若判定情厚、多爱为定理而以理智往下推寻,把他作成客观道理而秉持之,反倒成了形式,没有真情,谬戾可笑,何如完全听凭直觉!然而一般人总要推寻定理,若照他那意思看,孔家谓“钓而不纲,弋而不射”,“君子远庖厨”未免不通:既要钓何如纲,既不纲就不要钓;既要弋就射宿,既不射宿也就莫弋;既不忍食肉就不要杀生,既杀生又何必远庖厨。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收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能则通之至。[2]
这里的一般人的思维/理智正是西方的认定型思维/理智。这种西方的认定型思维/理智是执一的,而中国的为认定的思维/直觉则如舜那样“执两端而用中”,从而“执一”与“用中”是中国与西方的第四点不同。这里“执两端”既包含“直觉的自然求中”,还包含“理智的拣择求中”,“双、调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的办法始终着眼在这上头,他不走单的路,而走双的路,单就怕偏了,双则得一调和平衡”。[2](P149)可以说中国人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也是隐而不显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2](P123)而这里又内蕴了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不同态度,就是孔子对“生”的赞美。这可以算是中国哲学在比较中的第五个特质。梁漱溟引了一大堆孔学名言,如“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然后总结道:“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从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气春意。”[2](P127)用对生的赞美把中国与印度(死的涅槃)区别开来之后,在生的态度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什么呢?梁漱溟认为是在“生”中的“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他说:“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2](P136)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在比较中显出的第六个特质。这种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与墨子~西洋的计较利害态度区别开来。①梁漱溟在把这两种态度进行比较中讲清了何为不计较利害态度并对之进行了价值上的肯定:
当我们作生活的中间,常常分了一个目的手段:譬如避寒、避暑、男女之别,这是目的;造房子,这是手段。如是类推,大半皆这样。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理智——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为分别的;若当作真的分别,那就错误而且危险了。什么错误危险?就是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如我们原来生活是一个整的,时时处处都有意味;若一分,则当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那一段生活的附属,而自身无复意味。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盖多有这种错分别——尤以聪明多欲人为甚——以致生活趣味枯干,追究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等等,其而情志动摇,溃裂横决。孔子非复常人,所见全不如此,而且教人莫如此;墨子犹是常人,所见遂不出此,而且变本加厉。墨子事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事事都求其用处。其理智计较算帐用到极处;就把葬也节了,因为他没有用处;丧也短了,因为他要害处;把乐也不要了,因为他不知其何所为。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个“为什么”,都有一个“用处”吗?这都是随感而应的直觉而已。[2](P138-139)
以上六点确实呈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然而,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斗争现实中,“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与时代要求哲学成救亡武器是完全对立的;在西方工业体系和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现实中的重要因素的时候,“不认定态度”和“非确定概念”完全与工业体系的原则和教育体系的方法相对立。因这两个方面的对立,梁漱溟讲出的中国哲学的特质时,失去对时代的影响,但另方面却突显了时代哲学所忽略的东西:一种丰富而又灵活的“心性”。正是这种对中国心性哲学的独特体认,成为了新儒学的一种文化自信。
三、熊十力论哲学特质
熊十力《新唯识论》更是把梁漱溟呈出的中国哲学的心性论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且不但将之作为中国哲学的特质,而是作为一般哲学的特质。如果说梁漱溟用中西印的比较来突出中国哲学的性质,熊十力则用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来突出中国哲学的性质,西方哲学是科学,因此在哲学上陷入错误(戏论/虚妄),中国哲学是哲学的,从而充满了哲学本体论的真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可以概括为两大点,第一,以中国哲学“心物不二”大智大慧来反对西方哲学唯心/唯物的二元对立;第二,以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大慧大智来反对西方哲学现象/本体的截然两分。
心物不二,被熊十力表达为“心非超物独存,物不离心独在”。[3]虽然熊十力的“心物不二”是从本体论角度讲的,而不是从现象论上讲,但他必须面对西方科学史的挑战,于是他用中国哲学术语和思想去统合西方科学之论,这又与“体用不二”紧密相联。对“体用不二”,熊十力反复多次地以大海为例:““譬如大海水喻本体现作从沤,众沤喻一切人或一切物。即每一沤都是大海水炽然腾跃著现”一方面“大海水全现为一个一个的沤,不是超脱于无量的沤之上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每一沤都是揽大海水为体”。[3](P22)因此,不是每一沤(本体之用)后面还有一个独立于众沤之外的本体。再从“体用不二”回到“心物不二”。熊十力用《周易》的术语来予与解说,中国哲学的体用不二的宇宙是运动变化着的:“本体流行,翕辟成变,即依辟而成为心,依翕而成为物。”[3](P71)把这一思想运用于科学史上的宇宙演化,“地球当未有生物时,动物知觉与人类高等精神作用虽未曾发现,而宇宙之大心,所谓辟者,要自周流六虚,无定在而无所不在。上下四方曰六虚,犹云太虚。鸿蒙未判,此心固与气俱充,无量器界凝成,此心即随气器遍运”,[3](P70)“夫辟无定在而无不在,其势无所集中,未免浮散,翕则分化而凝成众物,物成,即有组织而非散漫。故辟乃得翕为工具,因以显发其势用也”。[3](P71)总之,宇宙的物界演化在一辟一翕之中,首先形成质碍层,然后形成生机体层,此层复分为四,植物机体层、低等动物机体层、高等动物机体层、人类机体层。在质碍层中,如《易》之“坎卦”,阴陷阴中而不得出,宇宙大心陷其中未得显,作为宇宙大心体现的辟虽陷于其中,但“其潜驱默运乎质碍层,固致健无息也”。[3](P71)而在生机体层四层中,宇宙大心越来越显,至人类机体,宇宙之心得到了最高的体现。照熊十力看来,宇宙演化一辟一翕,辟翕之用本就是本体之显,本体就在辟翕之中,因此宇宙演化的一辟一翕就是体用不二。宇宙演化的一辟一翕,辟体现为宇宙大化流行的动力,即宇宙大心,翕为宇宙流行中的物成,即为宇宙的物界,因此,宇宙演化的一辟一翕就是心物不二。宇宙大心本就存在,只是在质碍层、植物层、低等动物层、高等动物层中为物质所阻碍,②未能辉煌显现而已。然而从本体论上讲,仍然是心物不二。到了人类,其物质条件即生命构成可以对心物不二有自觉意识,这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为心物不二的思想。可以表述为:“本心即是性,便随义异名耳,以其主乎身曰心,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曰性,以其为万有之大元曰天,故尽心则知命知天,以三名所表实是一事。”[3](P26)
在人的层级,一方面人对心物不二可以有思想的自觉,但是在现象中,人又因生命构成的方式和面对物质世界认识,看不见心物不二的真谛。熊十力是从中国哲学特别是从印度哲学的话语来讲心物不二的。在熊十力看来,心在作为本体时是本心,心在认识外在具体事物时是通过具体的五官(眼耳鼻舌身)来认识,五官各自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方面,比如一个瓶,眼看见瓶的色,耳听见瓶的声,鼻闻到瓶的气味,舌尝到瓶的质味,身触到瓶质性(软硬粘爽),每一官只能认识瓶的一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个体系(识),心把通过“意”把各个官能本来分看的识,综合起来,形成关于事物的认识:这是瓶(法)。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由世界本身的极微(地水火风)并按色声味嗅触综合形成。一方面,五官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构成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这一心与物在认识上的合一,一方面让心成了与具体物直接紧密关联的具体之心,熊十力称之为习心(即由认为事物而来的习得之心),另方面让物构成了与人直接紧密关联的具体之性(具体物的定义,如这是一个瓶)。这种以习能的六根对外物的认识,熊十力借用了一个印度哲学的术语来表达:量智。习心为了更好的认识事物,发挥着人的量智,精细着人本来分离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另方面在精细着人的六根的同时深化着对物的六识(色声嗅味触法),因此,六根是被外物牵着走的,人越被外物牵着走,越要认清外物,于是不断地发明着各种六根的延长物——工具。对外物的认识越深越广越多,习心越厚而越是失去了本心。人要想得到本体,通过习心而量智,量智而习心的循环进步是不行的。熊十力说:
哲学家谈本体者,大抵把本体当做是离吾心而外在的物事,只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哲学家都不外此作法,遂致各以思考去构画一种本体,纷纷不一其说,如彼一元二元多元种种之论,犹如群盲摸象,各自以为得象之真而实都无是处.更有否认本体专讲认识论者,此种主张可谓脱离哲学之立场.哲学所以脚根稳定者,因有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哲学家为本分事未识得,才研究知识论,本分事系禅家语,即谓本体。今乃立意不承认有本体而只在认识论上钻来钻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立场。[3](P25)
既然“哲学家将本体当做外界独存的物事来推度者是极大的错误”,那么,“本体非外在,当于何求?”“求诸己而已矣。”[3](P25)即超越习心,返回本心,不用量智,而用性智,“性智为本来固有,犹[王]阳明所谓良知”,[3](P24)正是超越量智的性智让人回到本心,“故于此心识得吾人真性,亦于此心识得万物本体”。[3](P26)熊十力说,这也正是孟子讲的“尽心知命知天”之旨。因此,心物不二同时也就是体用不二。熊十力说“夫心不失本体之德,故即心而识体,譬之于众沤而识大海水也。此即用即体之义,首须明白。既于心而知其是本体显现,则万化真源,不外一心,故说心为万物之主”。[3](P167)因此,体用不二/心物不二的重点在本心在性智,而不是在习心在量智,习心/量智让人重五官,进而发明工具延伸五官而一方面失去心的整体,另方面走向工具体系,反过来,重工具重逻辑其实是重分离的五官,工具既让人失去了世界,又让人失去了本心。可以说,重量智重六根重工具,形成的是科学,而超越习心的局限,运用性智,回到本心,认识本心,才是哲学。因此,重工具而产生科学,重本心而保有哲学。西方认识论看起来也自称是哲学,其实是科学,中国哲学对本心的体认而形成的心性论才是真正的哲学,是正确的哲学本体论。熊十力《新唯识论》强调了超越现实物界、超越现实工具、超越现实习心以达到本心的一种心性论哲学,对本心作了极大的高扬,突出了新儒学的根本特色。但当其为了强调本心,而把本心与习心,本心与现实、本心与工具对立起来,从而忽略了习心的具体复杂性、现实的具体认复杂性、工具的具体复杂性,比如,现实的现象里,有没有具有本质性的现象(典型现象)、不具有本质性的现象(非本质现象,与本质相反的现象(假象)的区别呢?在工具性的建构中,有没有对认识本性有用的工具、对认识本性无害的工具、让人丧失本性的工具的区别呢?在习心中,有没有体现了本心的习心,不体现也不妨碍本心的习心,对本心有妨碍的习心的区别呢?而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呈现的具体习心形态、现实形态、工具形态,是中国的现代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对之忽视,决定了熊十力型的新儒学难以进入中国现代进程的主流。
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
如果说熊十力《新唯识论》几乎全是用中国型和印度型的东方哲学来突出中国儒学的特质,那么冯友兰《新理学》一方面对宋明理学加以继承,另方面引入西方新实在论逻辑,其叙述方式是西方的,其叙述内容是东方的。与熊十力一样,冯友兰在哲学不同于科学这一基础上来讲哲学,他设计出三分两学的理论框架,三分即现实(冯称为“实际底事物”)、科学(冯称为“实际”)、哲学(冯称为“真际”),两学即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将现实世界进行科学或哲学的理论提升。现实是一个,即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事物,理论总结有两种,对把具体的事物进行科学的抽象或哲学的抽象,由具体到一般,形成人类的理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和心物不二,不断地用大海与众沤的中国型比喻,冯友兰讲三分两学的时候,不断地用一个逻辑学的西方型比喻:“方”。
人面对世界,总是面对具体地事物,这就是三分中的未曾被理论化的现实世界,叫“实际底事物”。冯友兰说:“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地存在的事事物物。”[4]举例来说,现实中有很多“方”的事物,方形桌子、方形屋子、方形广场、方形田地……。把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方的事物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总结,叫“实际”,冯友兰说:“实际是指所有底有事实底存在者。”[4](P10)实际“是忽略具体方的事物的具体性,如桌子、屋子、广场、田地等,而只得出“方”的共性,即关于“方”的科学定义:“凡方底物皆有四隅”(即方是四条边相等组成的空间)。[4](P20)这一科学判断虽然不管方形物有多少种类,每一种有多少数量,但它涉及了包括了所有事实上存在方形物,这就是“实际”一词的首要含义。把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方的事物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总结,叫“真际”。冯友兰说“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4](P10)这里“有者”之“有”即Being,这个西方词汇是,说了是(to be),但又不说是什么(to be something),用冯友兰的话说是“我们更进一步而离开一切方底物,即属于方底物之类之实际底物,而只思及方之为方者。”[4](P20)从而得到哲学的命题:“方有四隅”。这与科学的命题“凡方皆有四隅”,区别何在呢?科学命题涉及到实际中的一切方者(所谓的“凡方”)。而哲学命题则可以“不管事实上果有实际底,方底物存在否”。[4](P21)由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的真际以“方”为例进行了细说:
我们可以为,事实上可以无实际底方底物之存在,但如其有之,则必有四隅。如此,这个判断,这个命题,即不是及于实际而是及于真际者,即不是对于实际特别有肯定,而是对于真际有所肯定。哲学中的命题,大都如此。
方底物之所以为方者即“方”。照上所说,“方”可以是真而不实。如果实事上无实际底方底物之存在,方即不实,但如果事实上有实际底方底之存在,则它必有四隅。实际底方底物,必依照方之所以为方者不能逃。于是可见“方”是真,如果“方”是真而不实,则“方”是纯真际底。[4](P21)
同时,对实际的事物、实际、真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义:
实际底事物蕴含实际,实际蕴含真际。此所谓蕴含,即“如果——则”之关系。有实际底事物必有实际;有实际必有真际。但有实际不必有某一实际底事物;有真际不必有实际。我们平常日用所有之知识,断判,及命题,大部分皆有关于实际底事物。哲学由此开始,由知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宋儒所谓“及微知著”,正可说此。及知真际,我们即可离开实际而对于真际作形式底肯定,所谓形式底肯定者,即其所肯定,仅是对于真际,而不是对于实际,换言之,即其所肯定,是逻辑底,而不是经验底。如上所说“方有四隅”即其例。[4](P21)
这里三分是以一个不断向上抽象的层级:由实际底事物到实际到真际,但由于高升到了哲学的真际与科学的实际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哲学和科学二者的差异,特别上有与现实的关系上,显示出来,一个是关系实际的,一个是脱离实际的,因此,人类思维进路由实际底事物(现实世界)到实际(科学)到真际(哲学)的同时,又显出了实际(科学)与真际(哲学)的根本区别。从而,对冯友兰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世界、科学、哲学的三级进路,而是科学与哲学这两学的区别。
对实际事物的科学进路,从个别的具体事物到一般的科学总结,科学既来自现实但不离现实,而且要有助于现实的理论认识,因此,科学得到“一般”,专注在内容上,即这事物作为事物来说,究竟是何种事物(类),由什么构成,依什么原理运转。对实际事物的哲学进路,从个别的具体事物到一般的哲学总结,哲学既来自现实但可以离开现实,因此,不是专在一般的内容,而是专在一般本身的性质,即这事物为什么是此事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冯友兰说,科学是自然的,哲学是本然的,“本然者,本来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4](P10)科学是为得到了一般的内容,因此需要对事物进行具体的物质分析,需要科学实验,正是在这一物质分析中,科学/技术/工具发展起来,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工具进一步推进的内容的认识,“事物之类之数量,是无尽底。一类事物之理之内容亦是很富底。科学家向此方向研究,可以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他不断地‘格’,即不断地有新知识得到,所以科学可以日新月异地进步。”[4](P10)哲学是为了对一般(类物)作性质的、真理的分析,即作为类的此性质何以究成为这一性质,既必有此类事物之理。因此,哲学对一般(类物)的分析,不是内容的分析,而是形式的分析。哲学把现实中的经验提升到逻辑的命题,虽然这一命题必然在现实中具有普遍性,但却不依现实中是否有具体的实物而存在,也不对这一普遍性的具体内容感兴性,而只对其逻辑的形式感兴趣。“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底,逻辑底,而不是事实底,经验底……暂先举普通逻辑中所常举之推论之例,以明此点。普通逻辑常说:凡人皆有死,甲是人,甲有死。有人以为形式底演绎底逻辑何以能知‘凡人皆死’?何以能知‘甲是人’?如欲知‘凡人皆有死’则必须靠归纳法,如欲‘甲是人’则须靠历史知识。因此可见形式底,演绎底逻辑,是无用底,至少亦是无大用底。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由于不了解形式逻辑。于此所举推论中,形式逻辑对于凡人是否皆有死,及甲是否是人,皆无肯定。于此推论中,形式逻辑所肯定的只是:若果有凡人皆有死,若某甲是人,则甲必定有死底。于此推论中,逻辑所肯定者,可以离开实际而仍是真底,假令实际中没有人,实际中没有是人是甲,这个推论所肯定者,还是真底。不过若使实际中没有人时,没有人说它而已”。[4](P9)由于哲学是不与现实相联的形式分析,它不以实验工具,因此,冯友兰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念”。[4](P6)在纯思中“心观大全,他并不要取真际之理一一知之,更不必将一理之内容,详加研究,所以哲学不能有科学之日新月异底进步。”[4](P16)科学由于从实验、工具、技术中得到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知识,因此。科学是可以用来作用于现实并改造现实的,科学促进了现实的进步,现实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哲学由于可以不涉现实,从而“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对之(现实)无所肯定,或甚少肯定,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对之(现实)有所肯定者,又不可统治,不可变革。所以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就一方面说,真正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不合实用”。[4](P13)
冯友兰通过将科学与哲学作的一系列对比,科学是实验的,哲学是纯思的,科学是实际的,哲学是真际的,科学是自然的,哲学是本然的,科学是内容的,哲学是形式的,科学是经验的,哲学是逻辑的,科学的有用的,哲学是无用的……并在这一对比中,把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呈现了出来,成为了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最哲学底哲学。但正是因此这最哲学底哲学是无用的,对实际无主张、无肯定的,从而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救国存亡,没有了直接的关联,与中国现代化急需要的工业体系、教育体系、学术体系没有了直接的关系,从而这一对宋理学接着讲的新儒学在逻辑上再严密,形式上再完美,也进不了急需一种作为现实斗争武器的时代主流。
新儒学在中国西方印度的比较中突出中国哲学,在与科学和实用的对照中突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哲学境界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突出科学)和印度(突出宗教),不同于科学和实用的生命境界,这鲜明地在冯友兰的思想中体现出来,冯友兰的五重境界,最高的天地境界,是在超越了前三种之后获得的,主要的是在人中获得的,中国哲学的天地,不同与西方哲学宇宙规律,是理论层面,而不是历史层面,天地境界不是在历史的进化中获得的,而是在历史中任何时刻都可以获得的,是一种与道同化的自然境界,而不是一种在推动历史前进在历史线型的最前端最高点才能获得的进化境界。当中国现代性需要的是一种历史进化,从传统到现代或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化中,新儒学的生命境界和天地境界当然要被走在历史进化线最前面的马克思主义所战胜了。
[注释]
①梁说.“这个态度问题,不单是孔墨的不同,并且是中国西洋的不同所在。”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8.
②熊十力《新唯识论》第71页说:“质即是碍,曰质碍。自鸿蒙肇启,无量诸天体,乃至一切尘。尘字,本佛籍。佛言尘者,犹今云物质。都是质碍相。质碍相者,生活机能未发现故。”
[参考文献]
[1]刘述先.现代新儒学研究之省察[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0(3).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8-129.
[3]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2.
[4]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