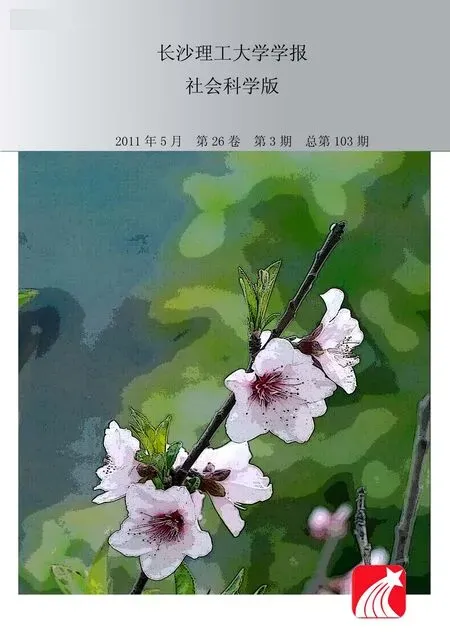论权力运行的道德法则
唐土红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732)
权力的“道德规则”,中外许多思想家早就有所论述。如秦简《为吏之道》就已有官吏道德标准:“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三国志·魏书·李通传》也有为官道德准则“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明代梁寅谈到为官之道时也说“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①但在阶级社会思想家往往倾注于理论原则的阐释,对“是什么”的问题关注较多,而对于“为什么”却置于边缘化境地,以致提出的诸多权力道德准则成了空中楼阁。封建时代的这些为官准则由于制度本身的阙限最终难以实现。权力运行的道德准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这些准则,这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伦理问题。
一、勤政:权力道德的逻辑起点
一般而言,勤政是与为民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就是政府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时,要以人民为核心,体现人民的意愿和意志,尽心尽责、勤奋工作,推进人民事业的进步、发展和繁荣。
政府权力不同于一般性社会组织,其根本宗旨即在于为社会和人民提供优质服务。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也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起码道德要求。因为:首先,权力的价值指向决定它要勤政,人民是权力服务的对象。服务人民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就是要求领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为民造福,满足人民的需要,做为民解难的贴心人。其次,权力的来源决定它要勤政。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权力是建立在人民的公意基础之上的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为人民勤奋工作,以达惠民、兴民和利民。再次,权力对象的性质决定它要勤政。权力管理的事务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其实质就是人民的事务,要把这些事务处理好,使人民满意,就要“勤政”,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权力的勤政原则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直为政治思想家关注。古希腊城邦追求“善”的生活其实内涵了权力的“勤政”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在欧洲中世纪被所谓的神学“光环”所掩埋,但通过此后文艺复兴的涤荡后,直至今天仍闪烁着时代价值的光辉。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中,普遍都把勤政为民原则作为必不可少的行政道德原则加以要求和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中的民本思想一直闪烁着“勤政”准则的光芒,萦绕在百姓心目中的“仁君”、“青天”等清官情结其实也折射出人民大众对政府官吏勤政为民道德操守的期盼。一方面,思想家们告诫统治阶级要关注民生,如孟子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 尽心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勤政行为给予讴歌和积极肯定。荀子也反复强调“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荀子·君子》),要求为臣的敬业守职。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为官准则,在很早就为人率先垂范。如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据说孔子做“委吏”时,钱粮算得准确清楚;做中都宰官仅一年,就因政绩斐然而四方官吏以他为榜样;做大司寇仅三个月就做到物价平稳,男女别途,路不拾遗。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由普选产生的公职人员必须对人民尽心尽责,勤政为民。社会主义权力观一方面反映了权力的人民属性——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它又指出从政人员的职责——向人民负责。它“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
勤政则是现代政府权力运作必不可少的准则,它要求:一方面,应尽量满足公众的需要,这就要广开言路,通过多种途径,及时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当忠诚于人民,“忠诚原则是一个要遵守真正的允诺的原则”。[2]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忠诚原则同样适用,它要求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大力提倡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二、廉明:权力运行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廉”的最基本意思是节俭、不贪,明即指为人清明,二者合用主要指掌权者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时能够抵制诱惑、摒弃私心,保持自身清白。
廉明作为政治道德要求,最初源于《周礼》“既断以大事,又以廉为本”。具体言之,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自古以来,“廉”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为官准则,是关系江山社稷的根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被古人称之为礼、义、廉、耻“四维”之一的“廉”在管子看来则是“国之大维”。汉代马融在谈到为官清明之于社会和个人的意义时认为,“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能正俗”(《忠经·守宰章》)。因此,廉作为一种美好品格,一直深受开明君主和圣贤之士的赞赏和效仿。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廉作为为官准则尤为统治者重视,武则天在亲撰的《 臣轨》中,单列“廉洁”一章,对为官之清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把考课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和教育制度,其中考廉是关键性的内容,在考课的清、政、才、廉四格中排在首位。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它只是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工具,在专制面前它之于广大人民而言不过是徒托虚名的幻想。但是,我们万不可就此否定它的普世价值。任何社会,清正廉明都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和评价从政行为善恶的普遍性社会标准。在权力腐败几乎成为世界各国通病的情况下,廉明行政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中,正处于急剧变化而又仍需不断深化改革的风口,面对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倡导并坚守廉明行政的道德原则仍然是今天我国行政伦理学课程的应有之义。因为,廉明的关键就在于为民掌好舵、执好政,这就意味着不将人民授予的权力视为谋取个人私利的筹码。廉明的道德原则事实上是与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相连的,尚若没有廉明作为价值引导,要想提高现代社会应具备的两大权变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从表面上看,执政能力尽管只是个人才能水平的反映,与廉明的道德原则较疏远,但要知道,一个飞扬跋扈、不知廉耻的人,哪怕他能力超群,也必定会遭到民众的唾弃和“群起攻之”。
廉明不仅仅是指掌权者自身的廉洁,它还应包含权力运行成本的廉价和运行过程的透明。就廉价而言,廉价政府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体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状况而提出的最打动人心的革命口号。尽管资产阶级在骗得人民信任掌握政权后并没有实现它当初的道德诺言,但这一口号本身还是有历史进步意义。历史证明,建立廉价政府,降低权力运作成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民众的负担,这本身就是道德的行为。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府目标模式:廉价政府。他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3]
廉明原则还有一方面内容,那就是透明。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监控的必要前提,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说来,政府决策不透明,不受监督,不允许争论,不向社会公开的地方,腐败的危险、公共资源被滥用、公共投资不当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从反腐败的角度看,透明是一把利剑,它能对公务员进行有效监督,使他们不敢、也没有机会发生腐败行为。封闭性和神秘性是专制政府权力运行的特点,这种模式把真正的广大权力拥有者——人民置于权力主体之外,本身违背了权力的道德律令。事实上,道德的政府并不畏惧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权力制度只有公布于众,让公众了解,人们才能对其做出科学的价值评判,才能符合和体现人们对它的道德要求,真正实现对权力政治制度的价值追寻。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与旧政权的区别时指出:“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受它。……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4]现代社会,权力的透明性日益显得重要,它已成为凸显政治制度本身价值性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容。实践证明,权力组织系统的透明度越高,它所汲取的社会认同性因素和合法性支持也就愈多,权力组织系统的适应性也就越强,“任何要求政治过程进一步开放的运动本身都可能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然而一旦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达到了某种程度,政治体系反而愈加趋向于稳定”。[5]
三、诚信:权力赢得社会信任的最基本条件
诚信简言之就是诚实守信。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诚信最初是一元二分的,诚往往与天道相联,强调真诚勿欺、表里如一的诚实品格。《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中而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朱熹解释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信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内心的虔诚,如《说文》认为“信,诚也,从人,从言”。二是指具体的行为表现,如《辞海》对信的解释是诚实、不欺和信用。最先将“诚”与“信”连用的人是管仲,他在《枢言》中论道:“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从而把社会“诚信”与政治“诚信”结合了起来。
在古人看来,诚信不仅是对人格属性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是政治价值的显现。在中国历史上,不管儒家还是法家都无一例外地把它视为为政之本,对其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儒家历来认为,政治诚信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教化资源,统治者既是政治管理者又是道德教化者,其目的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君主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臣下,臣下就会以相应的态度对待君主,只有君主恪守信用,臣民才会讲信用,“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人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傅子·义信》),诚信关系国家的治乱兴衰和社稷的安危,“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守”(《吕氏春秋·贵信》),政治人才的选拔尤其要注重诚信标准,“人先信而后求能”才能取信于民,进而保持邦国的长治久安。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政府诚信理论只是演绎了从事实到事实或从价值到价值的路径而缺乏一种内在逻辑的话,那么,社会契约论的政府诚信理论则演绎着从事实到价值的必然性逻辑。按照契约论思维,政府权力源于公众权利,公众构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必须按公众的要求为公众提供良好服务。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种委托代理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之上,因而,诚信的道德原则也就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题中之义。作为权力之载体——政府,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就应忠实于委托代理契约,承担履约的道德责任,以期获得委托人的持续信任。
诚信之于政府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6]一个连起码的诚信道德规范都难以做到的政府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不是崇“善”的政府,更难以想象它会是一个给社会带来繁荣和幸福的公平、正义的政府,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从来就得到人民的无限推崇。就像司马光所言,“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7]
现代社会,政府已不再是特殊利益的代言人,而是社会普遍利益和普遍意志的体现者。政府哪怕极微小的失信行为,都可能引起人民对权力的怀疑甚至否定,给社会诚信建设带来撼慑甚至可怕的打击。目前,各国政府诚信匮乏综合症不但成为行政管理中的一大瓶颈,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因素。就此,克林顿政府曾诚信缺失问题论道:“我们不仅面临着预算赤字和投资赤字,由于联邦政府的绩效赤字,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信任赤字。除非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否则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8]推进政府诚信建设,对于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巩固政府合法性与权威性,醇化社会风气,并将其作为社会诚信体系的突破口极具现实意义。
在当代,政府诚信程度直接反映并影响着社会诚信的现状,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是否坚实,从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一个言而有信、恪守诺言的政府,不仅可以带动诚信行为在整个社会的处处遵守,而且还可以极大限度地推进社会诚信风尚的建设。斯宾诺莎认为:“统治者不凭信义来处理政务就办不好,这样的国家就不会是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持得久远,其政治上的组织必须是这样,就是使统治者没有法子失信或妄为。”[9]较之社会,政府诚信有更高要求,因为“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10]所以,政府诚信建设首先要求政府雇员对人民怀有真诚善良的动机,不能为诚信而诚信或因诚信而走形式主义道路。
四、公正:权力运行的根本价值指归
公正既是权力道德的重要范畴,又是权力行为和政治活动的价值指归。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多个领域,但任何领域的公正都含有普遍的道德意蕴。经济上,它体现着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政治上,它强调不偏袒任何人和任何团体;伦理上,它是对个人、团体、政府的规范和评价。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内含了三种理念,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理念。平等侧重于人的种属尊严;自由强调人应有的天赋、能力及自身发展与选择的个性;社会合作则主要体现社会整体精神,弥补平等和自由的不足。对于权力执掌者而言,公正就是要正当、正直、秉公执政、公道正派,对人和对事都应一视同仁。
公正作为权力运行的价值归宿实际上是对公民天然权利的体认,它源于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人作为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具有天生的平等性,其应有权利不能因种族、性别、收入等外在因素受到影响,更不应受到侵害。“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作为个人是平等的,在人性上也是平等的”。[11]人的平等性就要求政府均衡各种利益关系,平等、公正地对待当事人,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和特权。按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维路径,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政府也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充当着各种利益关系的裁判者角色,它要使“所有人的声音在权力的走廊里都能被听到”。[12]也就是说政府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它不应偏袒任何一方。
公正行政是权力的本质要求,也是行政管理者在运用权力时必须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它维系着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对于现代公共行政来说,公正无非是标明政府的社会正义供给的尺度,是作为一个标准而存在的,是衡量公共行政健全状况的标准”。[13]公正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正观念一开始就塑造着人的灵魂,人们在追求公正中所表现的正直心态也是社会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德文在谈到公正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时认为,“在一切正义的原则当中,对于人类道德上的公正是最实质性的”。[14]如果人类忽视对公正的追求,“不仅因为它产生的直接罪恶而应被深恶痛绝,而且由于其后果也许更加有害,因为它歪曲我们的理解力,破坏我们对未来的估量,因而从根本上打击我们的道德辨识力和人格的真正力量及其形成”。[14](P534)公正行政直接关涉到人们自身的安全感和人之为人的起码尊严,所以,“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应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正这一根本价值取向……通过体制改进及政策的优化整合实现交换公正、分配公正、规则公正及权利与义务的对等”。[15]
在公民权利意识高度觉醒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哪怕一件小事的不当处理也可能引起人们的巨大愤懑。民主时代,权力如缺乏公正之德及依公正建立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和结构,那么,再美好的设计最终也将流于镜中花、水中月,成为一种徒有虚名的幻想。政府如何贯彻公正原则就成为权力运行道德的重中之重。首先,政府必须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在一切生产要素市场化的今天,应该把社会补偿与个体贡献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政府的调剂职能,防止因两极分化出现的“马太效应”。其次、政府应该给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将公正而不是无私作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16]也就是说在处理公务时,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能有歧视、偏见或特权,对所有的人和事都要一视同仁。再次,权力行使要坚持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最起码前提,程序公正要求发扬民主,疏通和拓宽民主渠道,善用协商对话,广开言路。“两个人分一个苹果,无论怎么切,都不容易达到完全公正,因而难免抱怨,但如果让切苹果者后取苹果,就不再会有抱怨,这就是看得见的公正”。[17]最后、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前后不一、反复无常的决策都会伤害实体公正;朝令夕改或闪电式地出台某些完全出人意料的决策也会导致当事人合理利益的丧失。
勤、诚、廉、公的道德准则体现了权力运作的客观要求。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因为他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联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管理、和协调,直接关系着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人们对政府职员也有较之其他从业人员有更为严格的规范要求及道德期望,所以,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就必须遵循以上基本的道德准则。
[注释]
①《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4.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4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4]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87.
[5]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7.
[6]陈生玺.政书集成(第二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699.
[7]司马光.资治通鉴(一)[M].合肥:黄山书社,1997.13-14.
[8]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16.
[9]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51.
[10][美]菲利克斯·A.尼格罗、劳埃德·G.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郭晓来等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0.
[11][美] 穆蒂莫·艾德勒.六大观念(郗庆华,薛笙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70-171.
[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9:经济转轨与政府的作用[R].北京:中央财政科学出版社,2000.82.
[13]张秋立.论新时期我国行政价值观的重建[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4):87.
[1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原著选辑(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34.
[15]唐志君.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J].行政论坛,2001(3):23.
[16][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02.
[17]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