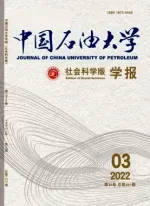论村民自治的有效与有序实现
郑健
(中国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55)
论村民自治的有效与有序实现
郑健
(中国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55)
实行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内在逻辑的体现和要求,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农村改革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这使得村民自治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现实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各自与自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等方面的问题,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有序地实现。因此,处理好党的领导权、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和规范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具体运行是促进村民自治有效有序实现的主要路径。
村民自治;民主;权力;有效有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兴起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兴起和发展,对于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调动其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发展基层民主以及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当前村民自治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的无效和无序。究其原因,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分别同自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村庄内部自治权的运行等方面的问题是导致村民自治无效和无序的根源。因此,本文拟以有效和有序为两个维度,以上述三个问题为切入口,试述村民自治的完善。
一、村民自治的源起
(一)村民自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治理的现实选择
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实行“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农民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被计划”。农民不但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没有农产品的交换权,甚至也没有最起码的劳动自主权。在田地里种什么、怎么种都不是农民自己决定,而是由公社或生产队决定。[1]改革开放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用益权。这种经济民主释放了极大的自主空间,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市场意识提高,在价值规律调节下自主安排生产活动。如此一来,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单向的“命令—服从”方式进行乡村管理已不合时宜。而村民自治既能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积极性,又能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适应了此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得以推广。村民自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管理民主主要是通过村民自治的完善来实现,而且作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发展也需村民自治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村民自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农村改革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
(二)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的内在逻辑
公共权力是人们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凝聚成的相对于其他力量和权力客体的制约力量。公共权力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的,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其终会消亡的归宿。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利益关系简单,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以分散的状态由社会成员共同行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成员利益分化的物质基础逐渐形成。经济上处于优势的成员成为强势群体,专享公共权力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劣势的成员则成为弱势群体并受权力支配。由此,公共权力开始“上行”集中并异化为少数统治阶层的权力。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兴起,并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世界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商品经济具有自发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前者表现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主活动,后者表现为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和人们经济联系的加强。这些催生出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追求并强力消解传统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格局,牵引权力“下行”分散。权力“上行”集中的实质上是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日益全面和严密,而权力“下行”分散则是权力对社会控制的减弱和向公民权利的还原。当今时代正处于权力“下行”分散的历史阶段,经济、知识等社会要素和力量对社会资源调配、利益实现的影响甚至支配日益凸显,公共权力已然或正在退出某些社会领域。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在乡村领域的适当退出,还原为乡村公众的权利和自由。[2]因此,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内在逻辑的体现,反映了权力演变逻辑的要求。
二、村民自治的理想状态是有效和有序
(一)有效和有序源于社会的“公私”二元受力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处于“公私”二元受力中。所谓“公”,即外在利益取向;所谓“私”,即内在利益取向。“公”与“私”源于利益的内在矛盾:“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3]。利益是具有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会产生各种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内在动力,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时便转变为利益,满足需要的天然要求也就转变为利益实现的主体性,即利益主体的内在利益取向。同时,利益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因此,利益主体实现利益必然要和其他利益主体发生联系,并且利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利益主体利益的实现。这就使得利益主体要具有外在利益取向,对自己负责的同时也需对其他利益主体负责。“私”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活力和张力;“公”是维系社会的力量,表现为约束力、规范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处于“公私”二元的平衡作用力中,如果约束力太大,自主空间就会萎缩,社会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如果张力太大,就会造成更多利益冲突和对抗,社会将陷入无序和混乱。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社会控制紧密,过度强调集体的统一性而忽视个体的主体性,抑制个人追求利益实现的内在动力,使整个社会有秩序而无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地理顺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逐渐重视个人的主体地位和权益的实现,赋予社会更多的自主空间,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没能提供及时必要的规范,致使人们的内在利益取向无序扩张,造成了一些利益冲突、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公私”受力平衡,在释放自主空间、激发人们内在利益取向的同时,必须跟配相应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秩序。这样,人们在通过社会关系实现利益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增强彼此的关联性,提高人们的共同体意识,进而促进社会走向自我管理。
(二)有效和有序是村民自治的基本维度
“公”“私”受力平衡是社会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而有效和有序是考量受力平衡的两个维度。所谓有效,是指人们的内在利益取向得到激发,并且人们有实现主体利益的能力与机会。这需要社会具有适度的自主空间和开放的发展机会。所谓有序,是指人们的内在利益取向得到引导和规范,同时外在利益取向的自觉性随之增强,不致因内在利益取向的无序扩张造成社会混乱。这既需要道德、价值等非正式规则自律式的规约,也需要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外律式的规约。诚然,在某些领域,自律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社会的高度发展最终将使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升,外在利益取向内化为思想与行动的自觉,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下,有序的整体实现与维护更加需要公共权威和正式规则的外律。
社会的“公私”二元受力要求村民自治的实施和完善必须坚持有效和有序两个维度。有效的村民自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村民自治的实施能够刺激村民的内在利益取向,调动村民积极性,增强乡村社会的活力;二是村民各种合理与正当的诉求能够得以表达和实现;三是形成真正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促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有序的村民自治主要表现为村民的内在利益取向能够得到必要的引导和规范,不至于引致利益冲突,从而造成治理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有效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有序是村民自治的保障。只有坚持有效和有序两个维度才能使村民自治更好地趋于完善。
三、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经过30年的实践,村民自治显露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的无效和无序。有些地方村民自治受基层党委和政府的越位干预,加之自治权运行缺乏制约,使得农民主体地位得不到尊重,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发挥,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从而严重影响村民自治的有效性。有些地方由于基层党委和政府的缺位,没有对村民自治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规范,致使农村治理失控,村民自治无序。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处理不当
基层党委作为农村党支部的上级组织,对其进行领导理所应该,但是这种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如果基层党委凭借对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来直接干预应属村民自治的具体事务,损害农民自治权益,那么就会制约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党作为领导核心,又具有整合、动员社会资源和协调利益矛盾的功能,党的领导权的介入又是推动村民自治趋向完善的重要动力。因此,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处理不当,或者领导权覆盖自治权,或者领导权过于乏力,都是造成村民自治无效和无序的重要原因。
(二)基层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处理不当
农村社会管理中实际存在着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乡镇的行政管理权,其功能是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基层;另一种是村民自治权,其功能是通过村民的共约等方式对村庄进行自我管理。[4]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而在实际操作中,基层政府惯于将村委会作为自己的“下级”,依然采取自上而下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使得村委会行政化,疲于应付基层政府下派的行政管理任务而逐步丧失自治功能。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和帮助是其应当承担的重要职能,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完善和规范。因此,行政权与自治权关系处理不当,或者越位,或者缺位,也是村民自治无效和无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村庄内部自治权的运行存在问题
自治权运行即村民自治的实际操作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村民自治偏重于选举。村民自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但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往往囿于选举,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主要是参加投票。这样一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不到重视和落实,村支两委行使自治权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村民自治只能异化为被选举出来的少数人的自治。另一方面,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承载着对广大农村社区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职责,它由村民中的党员选举组成,其领导人在党组织系统内通过党员选举或上级党组织任命产生;而村民委员会则是村民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作用在于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它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其领导人由全体村民选举而来。[5]村党组织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由上级党组织授予的,而村委会的权力是自下而上由村民授予的。这就使得村党组织倾向于对上负责,村委会则倾向于对下负责,当“上”“下”不一致时,村支两委关系就难以协调,从而对村民自治产生消极影响。另外,乡土势力也影响自治权的运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宗族势力从本宗族利益出发干预村民自治,破坏选举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使村民自治异化为大族主导的自治,甚至有时还阻碍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威胁、利诱、贿赂等非法手段渗入和操纵村民自治,严重干扰农村的经济社会秩序,败坏农村风气,侵犯广大农民群众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四、村民自治的完善
完善村民自治就是要使村民自治有效且有序地实现,更好地发挥村民自治的功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时代价值。如上所述,村民自治无效和无序主要是因为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行政权分别与自治权的关系,村庄内部自治权的运行等方面的问题。因而,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是完善村民自治的主要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保障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责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乡镇党委要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的章程充分行使职权。这一方面表明,村民自治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实行村民自治的政治基础。尽管村民自治制度发端于“草根”,缘起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是,村民自治制度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实践中日益成长和规范则得益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推动。[6]72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另一方面表明,坚持党的领导不能与村民自治相冲突,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村民自治的充分实现。所以,协调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就是要将坚持党的领导与保障村民自治相结合,实现党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偏废其一都是不可取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这些对于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矛盾是必要的,但党领导权的介入力度应适当,方式需合理。当然,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的协调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步调适。
(二)构建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在社会的“公”“私”二元受力中,行政权是“公”的表现,而自治权是“私”的表现。如果行政权太过强大,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太过严密,自治权得以行使的社会自主空间就会萎缩,社会发展将失去活力。反之,如果自治权无序行使和扩张,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就会增多,乡村治理将陷入失控和混乱。因此,在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构建双向互动的“分工—合作”关系是实现乡村社会“公”“私”二元受力平衡,既可维持社会秩序,又能激发社会活力的有效途径。
1.“权力—权利”视角下行政权与自治权双向互动关系的构建
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适当退出,是公共权力向乡村公众权利和自由的还原,而行政权是公共权力的重要部分,因此,行政权和自治权的关系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这就为行政权与自治权双向互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权力—权利”视角。
首先,行政权必须保障自治权利的有效实现并约束其无序扩张。权力来源于权利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共识。人民将权力授予政府是为了让其保障自己权利的有效实现,如果政府不对人民负责,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人民就可以收回授出的权力。因此,保障权利的有效实现是权力最基本的职责,也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权利作为公众表达和实现利益的手段,体现着公众的内在利益取向,在利益实现要求主体性的驱动下,公众可能会因“私”废“公”,违反社会规则,从而对社会和谐造成冲击。因此,行政权作为一种规范力,应当承担约束权利无序扩张、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责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其次,公民权利能够有效制约行政权。既然权力来源于权利,是公民权利的让渡,那么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人的道德和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权力的行使存在失范或失当的风险,从而会危及公民的基本权利。[7]基层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它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损公共利益。加之,基层政府的负责人往往自上而下地产生,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对上负责而忽视乡村公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必须用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防止行政权的不当和不法使用。为此,应采取如下措施:(1)逐步探索和实施乡镇长公推直选制度,建立基层政府领导人任用方面的民意表达机制,以增强选人用人的合法性。(2)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开辟和畅通对政府的监督渠道。(3)完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增加村民自治方面的内容,重视和提高社会评价在绩效考评中的比重,引导政府重视乡村公众的利益诉求。
2.“治理”视角下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工—合作”关系的构建
“治理”一词首先出现在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报告中,此后人们对“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所谓“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和。当今社会正由管理逐步走向治理,这是权力“下行”分散的表现。治理打破了传统的公共权力垄断社会管理的格局,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制和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共权力将“分散”到社会组织身上,权力主体不再单一。治理的目标在于善治。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8]因此,治理理念必然引致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工—合作”关系的构建。
首先,合理界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作用范围。自治权是公共权力向乡村公众权利的还原,这本身就是权力分工的过程。合理界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作用范围是构建两者“分工—合作”关系的基础。两者作用范围的界定实际上是政务与村务的划分。政务是政府管理的事务,它具有国家意志性,是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事务。村务是在一村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它涉及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共同利益,是由一村之内的村民共同管理的事务,具有群众自治性,体现的是一村范围内村民的公共意志。[9]乡镇政府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涉及的事务应属于行政权作用范围,而凡是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属一村范围内村民可以自己处理好的事务,可纳入自治权的作用范围。
其次,发展村民组织,促进乡村社会发育。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所需要的现代社会发育严重不足。[10]分散的农民在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力量较弱,难以成为独立的主体与政府展开分工与合作。因此,必须支持农民在共同需要和利益基础上形成村民组织,使村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发育,夯实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基础。
(三)规范村庄内部自治权的行使
村庄内部自治权的行使即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实际操作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有效有序实现,甚至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因此,规范自治权的行使,解决村民自治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当务之急。
1.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
村民自治素有“草根民主”之称,它先是由农民草创,后经国家力量自上而下推动,逐步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更加了解乡村社会的实际,也更能够创造出适应生产生活需要的自治形式。在村民自治30年的实践中,很多创新之举都来自农民。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国家力量进行引导和推动是必要的,但这适宜在宏观层面进行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这本身就是村民自治的体现。农民作为自治的实践主体,有能力创造也有权利选择更合适的自治形式。尊重农民的创造,发挥农民积极性是村民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可以因地制宜地完善村民自治,增强村民自治的可操作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如果不顾地区差异搞“一刀切”,必然影响村民自治的可操作性,而发挥农民创造性,可以使村民自治在框架性的规定内根据当地实际得以完善,从而增强其可操作性。再次,有利于取得农民认同,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其创造性就是要让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完善。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有利于取得农民认同。
2.完善村民自治必须引入“过程”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村民自治是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的一系列“过程”。而在实践中,“过程”概念的缺失往往使村民自治仅囿于民主选举单一环节,其他三个“民主”得不到落实,最终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异化为少数村干部的自治。在这四个“民主”中,民主选举是基础,其他三个“民主”是保障。围绕民主选举这一基础环节,可把村民自治分为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三个阶段。选举前要加强宣传和动员,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自治的内容和程序等,做好组织动员工作,营造浓厚的参与氛围;选举时,严格选举程序,落实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差额选举、秘密投票等选举原则,严厉打击不正当选举行为,保障村民真实意愿的表达;选举后,建立和畅通村民参与机制,加强对自治权行使的监督,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充分实现。这三个阶段合而为一,共同构成村民自治的过程,不可偏废。
3.理顺两委的关系
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的两个基本组织,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后者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因此,两委的关系实际上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理顺两者关系就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组织的领导,实现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和协调统一[6]73。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相关法律法规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有利于乡村社会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村民自治的有序实现。其次,合理划分村两委的职责,建立协调统一的工作机制。目前很多地方的“四议制”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村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享有提议权,然后由村两委商议,再由村党员会议审议,最后交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这就使村两委既分工明确,又协调统一。
4.积极应对乡土势力的影响
首先,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宗族势力。对于宗族势力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虽然它会对村民自治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在聚合表达农民利益、协调农村的社会关系、监督制约村“两委”等方面亦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宗族势力的存在与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宗族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其存在具有长期性和合理性。因此,对农村宗族势力应加以引导规范,趋利避害。一要健全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宗族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活动进行规范,对其违法活动应承担的后果及处理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领导与指导作用。适当考虑宗族在当地人口较多的因素,将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具有正义感、能热心为群众服务、在宗族中具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人吸收进领导班子[12],将宗族势力引导到促进村民自治有效与有序实现上来。三要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民主、平等、法治等公民精神,增强其抵制落后观念的自觉性。
其次,坚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一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为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提供坚强的组织和政治保证。基层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增强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决心,为村民自治保驾护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其人本意识、宗旨意识、廉政意识,坚决查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净化干部队伍。二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击黑恶势力,保障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是政府应该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而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城乡之间差别明显。因此,政府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在农村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要协调多方,建立农村治安联防体系。纵向上建立和完善县、乡镇、村三级联防体系和机制,横向上警力下沉,实现警民联动,多方齐抓共管,形成打黑除恶的合力。
五、小结
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内在逻辑的体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农村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这使村民自治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现实性。因此,实施和完善村民自治是推动乡村治理良好发展的必然举措。但是,由于当前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分别与自治权的关系以及自治权的运行等方面的问题,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有序地实现。因而,在立足于中国实际、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解决好上述三个问题,是当前促进村民自治有效有序实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结构的主要路径。
[1]俞可平.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3):50.
[2]郑健.政治权力视角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探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3):47-48.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9.
[4]卢福营.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9(6):65.
[5]张长立.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冲突与协调[J].江苏社会科学,2009(6):102.
[6]黄辉祥,徐增阳.村民自治的提升:实践创新与制度建设——略论“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J].东南学术,2009(1).
[7]王振亚,张志昌.超越二元对立: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新型关系探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15.
[8]尹冬华.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现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
[9]周贤日,潘嘉伟.论村民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8.
[10]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6.
[11]刘玉凤,王栋.农村宗族势力的生存逻辑与治理对策[J].求实,2010(7):90.
[责任编辑:陈可阔]
On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and Orderly Villager Autonomy
ZHENG 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Qingdao,Shandong 266555,China)
Implementing villager autonomy i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public power evolution but also the realistic choice of adapting rural reform and prompting new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which makes villager autonomy both have regularity and reality.However,in practice,as proble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autonom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primary government and autonomy,and the running of autonomy in the village,villager autonomy is difficult to come truly effective and orderly.As a result,solving the above problems is the main way to promote the villager autonomy to be effective and orderly.
villager autonomy;democracy;power;effective and orderly;governance
D638
A
1673-5595(2011)06-0058-06
2011-03-21
郑健(1986-),男,山东昌乐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