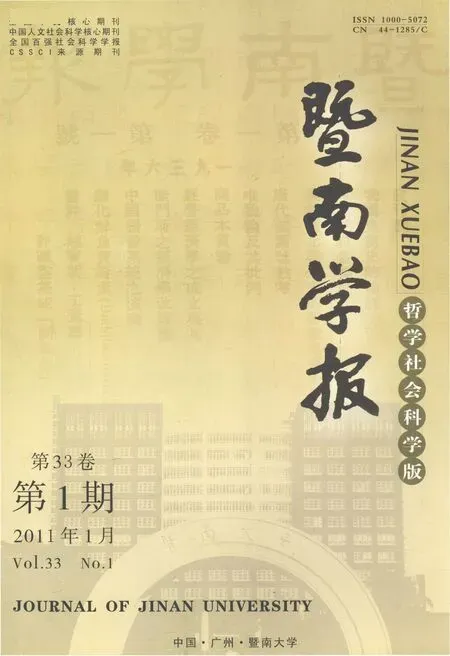粤东闽语n尾韵文白异读及其与ŋ尾韵和鼻化韵的关系
吴 芳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粤东闽语n尾韵文白异读及其与ŋ尾韵和鼻化韵的关系
吴 芳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对粤东闽语n韵尾分析发现,n韵尾在山、臻二摄中一部分属于文读层,一部分属于白读层;在曾、梗二摄中全部属于白读层。从语音演变规律来看,粤东闽语n韵尾向ŋ韵尾演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鼻化韵是n、ŋ韵尾尚未完全合并前由两者弱化并脱落而来。
粤东闽语;阳声韵;层次;演变
一、粤东闽语n尾韵文白异读层次
(一)粤东闽语中n尾韵的分布
粤东闽语大部分方言阳声韵尾中都缺少-n韵尾,本文通过粤东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及梅州丰顺等地共166个闽方言点的调查,共发现36个方言点的音系中带有-n韵尾。根据方言中拥有-n尾韵母数量的多寡,我们将这些方言点归纳为以下6个方言小片①具体论述参见本文作者《粤东闽语鼻音韵尾的类型、分布及演变趋势》(2010)。:
1.潮州凤凰片(6个韵母):un尊云,in真藤,uan专原,iεn电建,an兰艰,ɯn银斤。
2.海丰北部片(5个韵母):un尊云,in真藤,uan专关,ian电建,an兰艰。
3.饶平三饶片(3个韵母):un尊云,in真藤,uan专原。
4.揭东及普宁片(2个韵母):un尊云,uan专原。
5.海丰中部及云澳片(2个韵母):un尊云,in真藤。
6.汕尾及海陆丰南部片(1个韵母):un尊云。
在音系调查中,-n韵尾及由-n韵尾演变而来的-ŋ韵尾②为行文简洁,文章用“(-ŋ)”表示由-n韵尾演变而来的-ŋ韵尾,如:an(aŋ)表示“an韵母及由an韵母演变而来的aŋ韵母”,其它相类的韵母同此表示。,主要分布在山、臻、曾、梗四摄中。在具体分布上,山、臻二摄呈现出的情况较相近,可归为一类;曾、梗二摄的情况可归入另一类。对此,下文将山、臻二摄作为一组,将曾、梗二摄作为另一组。
(二)n尾韵的文白异读层次
1.山、臻二摄-n韵尾的文白异读层次
-n(-ŋ)韵尾字大多集中分布在粤东闽语山、臻二摄中,按照韵母文白异读对应规律,我们将这些-n(-ŋ)尾韵母的文读层、白读层初步归纳如下表①具体调查中,因同一方言点内不同发音人或同一发音人在不同情况下-n韵尾发音不稳定,有时又呈现出-ŋ韵尾特征,对此,我们用“/”记录。如:“瓶”pan55/paŋ55,表示该方言点“瓶”字-n韵尾的发音不稳定。:

表1 尾韵粤东闽语山、臻摄n的读音层次
由表1可知,山、臻二摄中的-n(-ŋ)韵尾大多都来自文读层,与中古中原官话山、臻二摄的语音格局相互对应。但还有少部分-n(-ŋ)韵尾出现在白读层中,韵母形式为an(aŋ)、un(uŋ)。这些字在粤东闽语口语中极其常见,如凤凰话:潘(pun24)水[洗米水]、行船(tsun55)、拳(kun24)头、鱼鳞(lan55)、姓陈(tan55)等词。从来源上看,这些口语词都是粤东闽语固有的方言词,因此可知,这些字的读音应属更早期的层次。综上,粤东闽语-n韵尾一部分属于文读层,一部分属于白读层。
2.曾、梗摄-n韵尾的文白异读层次
中古曾、梗二摄的阳声韵原本为-ŋ韵尾,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曾、梗二摄开口韵同样也存在一部分-n韵尾,主要表现为 an、in两个韵母。一般只要臻、山二摄中有an韵母类型的方言,曾、梗二摄也有an韵母;臻摄中有in韵母类型的方言,曾、梗二摄中也有in韵母:

表2 粤东闽语曾、梗摄-n尾韵
其中,韵母an(aŋ)主要分布在曾、梗二摄白 读层中,与韵母eŋ或iŋ形成文白异读:

表3 粤东闽语曾、梗摄an(aŋ)韵文白异读层次
但韵母in(iŋ)则很少与其它语音形式形成文白异读:

表4 粤东闽语曾、梗摄in(iŋ)韵母
表4显示,曾、梗二摄韵母为in(iŋ)的字一般无其它异读情况,但根据粤东闽语文白异读对应规律,仍可知韵母in(iŋ)属于白读层。当然,要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还须借助福建闽南方言相关材料进行分析。我们以厦门话、漳州话及泉州话的情况为参照:

表5 福建闽南方言曾、梗摄in韵文白异读层次①表5中厦门话的材料选自《汉语方音字汇》(2003);漳州话选自马重奇的《漳州方言研究》(1996);泉州话选自林连通的《泉州市方言志》(1993)。
表5可知,厦门话、漳州话和泉州话中曾、梗二摄的in韵母发音较稳定,in、iŋ韵母具有音位对立,并形成文白异读。其中,in韵母为白读层,iŋ韵母为文读层,参照此对应规律,我们可进一步确认粤东闽语曾、梗二摄中的in(iŋ)韵母应属于白读层。
对于粤东闽语曾、梗二摄中的in(iŋ)韵母无相应文读层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粤东闽语文白异读系统自身特征的规定。我们知道,音系的文白异读从一开始产生时,文读音和白读音就进行着激烈的竞争[4],一个字最终选择文读或是白读,又或仍保持异读,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结果。粤东闽语是一支文弱白强的闽南方言,这就表明在文白异读竞争中,粤东闽语的白读层的势力强于文读层。这样,在曾、梗二摄中,与in(iŋ)韵母对应的文读层次在竞争中被白读音同化就不足为奇了。可见,粤东闽语曾、梗二摄的-n(-iŋ)韵尾只出现在白读层中。
(三)-n尾韵文白异读层次小结
通过具体方言的分析,我们得出粤东闽语-n韵尾的文白异读层次如下:
1.山、臻二摄的-n韵尾主要有两方面的来源:一些-n韵尾主要来自受中原官话影响而形成的文读层;另一些则来自更早期的白读层。
2.曾、梗二摄的-n韵尾从历史到现代都只出现在白读层中。
二、n韵尾、ŋ韵尾和鼻化韵的演变关系
从-n韵尾文白异读层次的探讨中可以看到,粤东闽语阳声韵文读层只有-n、-ŋ韵尾两种形式,而白读层除了-n、-ŋ韵尾外还有鼻化韵的形式。对于粤东闽语文读层的来源,学术界比较一致,而方言现状上,文读层-n韵尾向-ŋ韵尾演变也是显而易见,对此,本文就不再对粤东闽语阳声韵文读层展开论述。下文重点讨论阳声韵白读层中的三类语音形式之间的演变关系。由于-n韵尾在粤东闽语中只存在于山、臻、曾、梗四摄中,因此探讨是在山、臻、曾、梗四摄的白读层中进行。
我们认为,更早期的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的阳声韵形式应同样存在阳声韵尾,其中,山、臻二摄应为-n韵尾,曾、梗二摄应为-ŋ韵尾。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的阳声韵形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四个韵摄阳声韵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表6 粤东闽语阳声韵历史白读层各形式在山、臻、曾、梗四摄中的分布
下文同样将山、臻二摄作为一组,将曾、梗二摄作为另一组,对各摄阳声韵的具体演变情况进行论述。
(一)山、臻摄白读层-n韵尾、-ŋ韵尾和鼻化韵的演变关系
对于闽南方言阳声韵中同时存在-n、-ŋ韵尾和鼻化韵的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早期闽南方言阳声韵尾-n、-ŋ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首先合并为-ŋ韵尾,此后一部分-ŋ韵尾因为鼻韵尾弱化变为鼻化韵形式,另一部分-ŋ韵尾仍旧保留,从而演变为今天山、臻二摄白读层中同时具有-ŋ韵尾和鼻化韵两类韵母的现状:
早期的闽语可能也是-m、-n、-ŋ三个韵尾并立,但是在相当早的时候(或许在唐代),很多闽语这三个韵尾已经都合并为-ŋ韵尾。这一层次是闽语共有的白读层。稍后,闽南话受到一种有-m、-n、-ŋ三个韵尾并立的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者是来自北方移民,或者是北方的权威方言),结果又引进了-m、-n、-ŋ三个韵尾并立。而在此之前,闽语共有的-ŋ韵尾白读层,闽南话己经都变为鼻化韵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音韵层次。[5]114
对这一解释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我们认为,山、臻二摄一部分-n韵尾的确曾演变为-ŋ韵尾,但另一部分则同时弱化为鼻化韵形式,即鼻化韵并不是从-ŋ韵尾演变而来,而是直接从韵尾弱化而来的。具体理由如下:
1.外来方言进入本地方言的改造规律证明早期山、臻二摄-n韵尾在中古时期并未全部演变为-ŋ韵尾。
我们知道,在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中,文读层往往是来自外方言的,这个外来的语音层次在进入本地方言音系时,必须经过本地方言音系的调整改造:“弱势方言向强式方言移借文读语汇时,若文读语汇的读音是本地系统所无,本地系统一般会在读音上作若干调整,使文读的声韵调值都能符合本地人的发音习惯。”[6]85
因此,在历史上,中古中原官话在进入粤东闽语时必然也经过了粤东闽语音系特征的改造。就山、臻二摄阳声韵尾而言,中古中原官话为-n韵尾,假如粤东闽语在中古之前山、臻二摄-n韵尾就已完全消失,一律演变为-ŋ韵尾,那么外来的中原官话山、臻二摄-n韵尾只凭借“空降”形式是不可能在粤东闽语音系中落脚。按一般的推理,这个外来的-n韵尾至多不过在粤东闽语固有音系格局的限制下,被改造为-ŋ韵尾或其它形式(如鼻化韵)方能进入本音系的框架。但粤东闽语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如潮安凤凰话中“船”tsun55、“鳞”lan55、“陈”tan55等词自古以来就为当地口语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词,这些词在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根本没文化的老人口中至二摄-n韵尾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是宋元期间借自官话的历史层次:“东南方言该历史层次(曾、梗二摄-n韵尾的层次)应该来自中原官话,当时的中原官话曾摄、梗摄已经合并,而且曾摄、梗摄的韵尾不同于宕摄、江摄、通摄”,“属于闽南话新白读层(或称旧文读层)的-ŋ/-ŋ音类,应该是比切韵更为晚近的年代,而不是比切韵更早一些的南朝。”[5]

对这一解释我们也表示怀疑。事实上,在-n、-ŋ两类阳声韵尾分立的现代汉语方言中,曾、梗二摄阳声韵尾归入-n的情况也不属罕见,这种情况在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及闽方言中都存在,具体例证如下①表9-12中,成都话、武汉话、双峰话、梅县话的材料引自《汉语方音字汇》(2003)。:

表9 部分江淮官话[7]及西南官话[1]曾、梗二摄-n韵尾的语音情况

表10 部分吴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语音情况[8]

表11 部分湘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语音情况

表12 部分客赣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语音情况[10]

表13 部分粤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语音情况①材料来自甘于恩教授主持的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04BYY032)。
以上这些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读音情况大致表现为三个类型五种情况:
1.曾、梗二摄阳声韵尾皆为-n韵尾。如:合肥话。
2.曾、梗二摄阳声韵尾为-n、-ŋ并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1)-n、-ŋ形成文白异读,-n韵尾为文读。如:梅县话。
(2)-n、-ŋ无文白异读。如:吴川话况。
3.曾、梗二摄阳声韵尾为-n韵尾和鼻化韵并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1)-n韵尾和鼻化韵形成文白异读,-n韵尾为文读。如:无锡话。
(2)-n韵尾和鼻化韵无文白异读。如:六安话。
我们认为一些汉语方言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情况确由外方言借入,但另一些方言应该是由自身音系演变而成,粤东闽语正是如此。
前文已说到,-n韵尾在粤东闽语曾、梗二摄的文白异读中就属于历史白读层。从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字来看,这些字基本都为粤东闽语口语常用字。以潮安凤凰话为例,我们在调查中获得的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字主要包括:“等、藤、层、曾[姓]、拯、称、秤、绳、塍[田地]、剩、蝇、零、轻”等,这些字在粤东闽语口语中十分常见,当中不少字甚至只用于当地独有的方言词中,如:胡蝇[苍蝇]、作塍[干农活]、零只[有几个]等词。
我们知道,文白异读的形成首先是通过方言词汇的接触开始渗透的,来自外方言的词汇往往不同于本地方言的词汇。既然粤东闽语曾、梗二摄这些读-n韵尾的字都是本地地道方言词中的常用字,那么这些字就绝不可能由外方言借入。换言之,粤东闽语曾、梗二摄-n韵尾应是音系自身固有的读音,在音系中应属于比较古老的历史层次。
粤东闽语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情况在福建闽南方言中同样可得到印证。福建闽南方言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字大多也以常用口语字为主:“(厦门话)曾摄读为-n韵尾:丞、嶝、藤、升、绳、拯、凭、秤、孕、塍、赠、层、曾、等,梗摄读为 -n韵尾:屏、明、皿、凊、轻、瓶、亭、钉、挺、跉、零、蛏、省”[5]111。
在以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为代表的福建闽南方言中,曾、梗二摄阳声韵一共存在三类阳声韵形式:-n韵尾、-ŋ韵尾和鼻化韵。如果认为福建闽南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层次是外方言渗入本音系而形成的旧文读层,那么-n韵尾这个历史层次也应该与音系中的鼻化韵形成文白异读,但在福建闽南方言的范畴内却无法找到这种痕迹。相反,却可看见-n韵尾和鼻化韵分别与-ŋ韵尾形成文白异读,-ŋ韵尾为文读层,-n韵尾和鼻化韵都为白读层的方言事实。由此可见,福建闽南方言曾、梗二摄-n韵尾的历史层次与鼻化韵的历史层次一样,都为方言自身音系固有。
事实上,一些-n、-ŋ韵尾分立的汉语方言中,还存在曾、梗二摄开口阳声韵只读-n韵尾的情况,如:
在杭州话、合肥话等方言中,曾、梗二摄中并不存在文白异读的情况,这表明这些方言曾、梗二摄中只存在一个语音历史层次。如果认为曾、梗二摄整个历史层次都是来自其它方言,恐怕颇让人难以置信。如此,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历史层次应该是方言自身音系演变而成,也就是说这些方言曾、梗二摄读-n韵尾的情况是自身音系固有的特征。在闽语的范畴内,甚至在汉语方言的范畴内,都存在着曾、梗二摄自我演变为-n韵尾的方言事实,那么,粤东闽语曾、梗二摄中的-n韵尾由自身方言音系演变而来就不足为奇了。

表14 杭州话[5]、合肥话[1]曾、梗二摄开口韵读音
(三)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阳声韵白读层的演变关系
通过对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各阳声韵形式之间的关系分析,我们可得到早期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阳声韵白读层的历史演变关系如下:

可见,早期粤东闽语山、臻、曾、梗四摄阳声韵中也存在-n、-两个阳声韵尾,后来随着自身音系的发展,一部分-n、-韵尾开始发生合并,最终都变为-ŋ韵尾,如山、臻摄二摄韵母的形成;另一部分 -n、- ŋ 韵尾因为韵尾弱化并脱落,最终变成了鼻化韵的形式,如山、曾、梗三摄中鼻化韵的形成;还有一部分-n韵尾因为演变滞后仍旧维持原本的语音形式,如山、臻、曾、梗四摄中的 an、in、un 韵母。这种语音格局在中古中原官话进入粤东闽语音系前就已形成。
[1]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2]马重奇.漳州方言研究(修订版)[M].香港:纵横出版社,1996.
[3]林连通主编.泉州市方言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戴黎刚.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C].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杨秀芳.论文白异读[J].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1-105.
[7]孙宜志.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06.
[8]陈立中.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鲍厚星.湘方言概要[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因不同著作记音的形式不同,尤其在声调上,本文皆原文直接引用,未作改动,以保持原貌,便于查考。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吴奕锜]
H17
A
1000-5072(2011)01-0097-08
2010-10-26
吴 芳(1980—),女,广东揭阳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教学与研究。
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粤东闽方言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类型学研究》(10JDXM74002);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揭阳闽方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