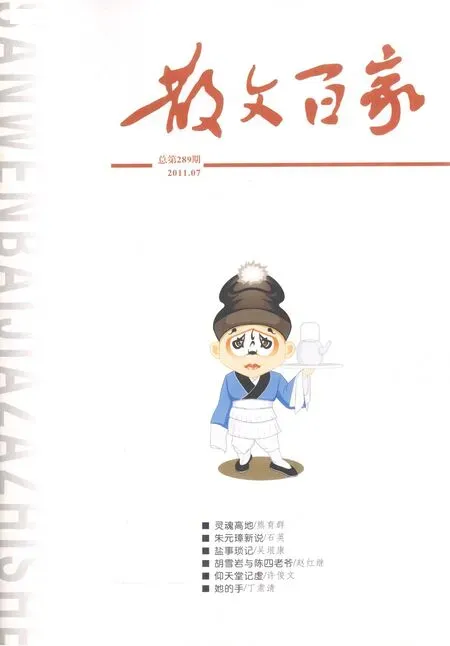朱元璋新说
●石 英
说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我不完全看到的,研究其心理状态及发展轨迹的文章即有多篇;是否有专著(书籍),我尚未看到。但也足以说明:人们对这位出身于底层的洪武皇帝,是抱有非同一般兴趣的。
我所读到的该朱的心理剖析,主要是说由于其出身卑微,曾当过在当时说来并不体面的这个那个,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自卑感;而在登上“龙位”之后,这种潜在的反差反而无比地加大,乃至疑神疑鬼,变本加厉地猜忌,近似鲁迅笔下的阿Q,因秃则延及“光”、“亮”也心犯忌惮。这样,该朱便因疑虑而生抑郁,尤其是在太子朱标夭折后,更是日夜担心他亲手创建的朱明王朝受到旁人觊觎而谋篡,乃至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案冤案,竟至株连无已,杀得十分开心。举其大者:如原丞相胡惟庸案。该胡固然有专权树党之行径,但究其实,并无真正证据谋反大罪,却在洪武十年(1380年)被杀,而且在胡死后又不断累加罪状,洪武十九年言其通倭,洪武十三年又制造胡曾通北元里应外合,等等。任意大兴党狱,无限株连,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世称“胡狱”。更有甚者,由胡案而延及李(李善长)案。该李本是朱元璋得力的“后勤部长”,后任左丞相,并封为韩国公。就是这样一个为朱元璋立下汗马功劳,并为其儿女亲家的元老级人物,亦为朱所不容,在胡惟庸处死十年后,仍以莫须有的胡之同谋罪处死无商量。稍后(1393年)又制造蓝 玉谋反案,将这位被封为凉国公的勇敢善战的 大将军杀害,并株连残杀达一万五千余人。此 外,还有几位不明不白、疑点重重的功臣之死 也多半与该朱皇帝有关。如在他夺取天下的战 争中被誉为军师诸葛亮的刘基(刘伯温),本 在天下初定时即仿汉初张良之举,辞官归里。 但就是这样,仍然受到该朱的猜忌,不久死 去。表面上说是忧愤而逝,实则是朱皇帝借丞 相胡惟庸对刘基进谗,派人将刘毒死而除掉心 头之患。另如与该朱同生死共患难、亲如手足 之情的开国重臣、名将徐达,表面的死因是病 卒(53岁),但据信是该朱“御赐”与徐所患 之疾相克的烧鹅,造成不治之结局。综观该朱 之绝对思路,此说无疑是可信的。有意思的 是,还有几位功臣之所以得以幸免,大半是因 为过早的去世,这里有常遇春,是早在1369年 北伐蒙元班师途中暴病而死的。当时朱皇帝还 未腾出手来思考“久安”的万全大计,常遇春 英年早逝反而捡了个便宜。这一点决非是虚妄 的推论,二十年后被彻底清除的蓝玉就是常的 得力部下,以株连无已的法则看,常遇春则是 很难逃脱干系的。还有一员大将胡大海,早在 该朱登基前的1362年就已牺牲,当然也就不在 清除之列了。至于该朱的凤阳同乡、后被封为 “东瓯王”的汤和,因为太熟悉哥们的性格 了,他在适当时机自请解除兵权,因而深得皇 上欢喜,致使该汤得以古稀之年善终,这真是一个少有的特例。
数百年来,关于朱洪武大杀功臣的行径很多人都是熟悉的。笔者小时候,在我的故乡可谓妇孺皆知,其行为动机人们也懂得是为防这些功臣位高权重而造反,影响了朱姓皇朝之运祚。如上所述,近年来海内外有不少人也都饶有兴趣地探索与剖析这位朱皇帝何以如此杀得疯狂,杀得眼红!大抵不出“猜疑成性说”、“心理变态说”,“重度抑郁症病态反应说”。而我经过较长期思考,对史料的揣摩,尤其是结合其他一些封建统治者的共有心理状态加以该朱皇帝的出身、阅历和独特个性综合研究,尤其是结合民间对人际关系亲疏的发展变化规律的辩证认识,始有此意旨,即“近极易烦,密久多忌”。具体说来是——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与这种发展变化关系很大。这就是朱元璋所赖以起家并奠定基业的将相班底,其主要成员除刘基(浙江青田人)等少数人为外省籍,而大都与他均为濠州(凤阳)同乡或与凤阳毗邻稍稍扩大一点范围的同乡。其中徐达、汤和也是凤阳人,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等是定远人,而常遇春是怀远人……这样组合起来的举事骨干以至后来的将相班底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地域亲情优势,以其出发点到阅历性情,应该说是都彼此了解,便于交流,特别是起事的早期相互较易于信任。虽然未必是“上阵父子兵”,却也是“乡亲哥们兵”,自然就彼此了解,心心相通,配合默契。如果说在起始阶段,这种乡亲集团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到后来,作为集团首脑的朱元璋,无疑是看到了这种自然亲密关系的好处和优势,再加以淋漓尽致的利用与发挥,而且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长,有意识地进行分工与职务安排,并给予了许多显赫的封号。
按一般平面思维推论,这种乡亲班底的确在事业奠定与发展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效益,近世也有“老同乡、老同事、老同学”相互借重而共同受益的现象。上个世纪前半期著名的蒋总裁、蒋校长就极端重视乡土效应。其最亲 信的将领不仅要黄埔出身,更看重浙江人。如 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乃至特务头子戴笠、毛 人凤等,都是浙江人。而且这些人最后都随同 他去了台湾(当然也有例外,曾担任过国民党 政权台湾省省长的陈仪也是浙江人,只是因为 蒋在败退中陈心生异念,即被蒋干脆利落地残 杀。可见乡亲关系在蒋那里也并非绝对靠得住 的)。
而作为早于蒋某人六百多年前的朱皇帝, 乡亲集团在天下既定后立马就走向了反面。其 实原因很简单:从本质而言,封建统治集团内 部的乡亲关系本身就是双刃剑,维系存在的力 量是非常脆弱的。作为“家天下”朱明皇朝的 开国者,就连同姓的亲子间亦能发生尔虞我 诈、相互残杀的举动,何况是异姓哥们之间? 起事之初,因为利害基本一致,需要相互协 同,相互借助,甚至是一损皆损,所以比较紧 密的乡亲关系当然是相互有利的,但当大事已 定,君臣关系已定,各自的身份便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尽管君王对昔日的哥们伙伴封以这个 “公”、那个“王”,也还是改变不了实质上 的巨大差异。当日彼此知根知底(包括睡觉打 呼噜,吃杏不吐核这类生活习性也瞒不了对 方);尤其是在相互借助时的忍让和妥协的积 淀,这时都重新浮出水面。“知根知底”不仅 不再构成优势,甚至反成为最大的犯忌之事; 往日的忍让与妥协如今可能转化为另一种心 态:君王一方不妨重新加以盘点而“秋后算 账”。假如这时昔日的伙伴、现时的功臣头脑 再稍欠清醒,仍然贪恋昨天的亲近无虑,那就 极可能招来腻烦,由烦而觉得讨嫌。到了这个 火候,纵对君王喊上八百个万岁、万万岁,恐 也不会听起来“耳顺”。有人可能从历史上的 “好皇帝”中提出不这样的例证。譬如年号章 武的蜀汉皇帝刘备,不是对丞相诸葛亮基本上 仍如以往吗?可惜比他晚上千余年的、建立起 统一的大明帝国的“第一任”朱皇帝没有他那样的好性情、耐心烦;更根本的一点是形势不同,处境不同。蜀汉说到归齐不仅未得统一,在三国中也从未真正地横起来,刘先生不仅需要诸葛亮,就连赵云、魏延乃至廖化这样的将领也需要。而大一统后的朱皇帝这时就觉得他们不似原来那么需要了。愈是原来太亲近、太无距离,这时反而愈觉应该拉大距离,甚至有怕烧怕燎之虞。此乃“近极易烦”之谓也。
另一个方面,作为昔日的伙伴,今日的功臣,即使想转弯,也难保一下子消除不了已经形成的习惯心理,一下子适应不了那种壁垒森严的君臣之距。何况他们也都被封为重量级的高官,一下子也拿捏不好很难合适的尺寸。譬如胡惟庸,身为丞相,在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在过去随便惯了,突然收拢得很紧,也真难为了他,如果再私欲膨胀,不善于也不想夹着尾巴做人,那就离倒霉不远了。从他的实际情况看,不也真的是“专权树党”吗?而且已经“讨嫌”还不知趣,仍以妒忌之心撺掇主上,进一步清除本已隐归故里的刘伯温。单从这件事上说他与朱皇帝的心气也许是吻合的,但他却没有想到:干完了这一单生意之后便更为皇上看透了他存在的危险性,实际上离他的死期更近了。可见,逆着自然是不行的,有时顺着同样也不行。而那个李善长,儿女亲家的特殊身份从一般意义上说好像多了一道护身符,但在特定情况下(特定的人、特定的心境)反而多了一种致命的因素。原因很简单,就是过于亲近了,还可以说是亲上加亲——老乡、战友加至亲。见面忒频,促膝谈心的机会很多(如在现在,动辄打电话,没准儿情况更糟),其中有些话皇上肯定有爱听的,但难保也有些是不顺耳的。以朱元璋后来的心态和性情,注定不顺耳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该李还没有眼力架,沿袭过去的老路献这个策那个策,更不必说是捡这个漏那个漏的,那必然会加重主上耳噪。如果是普通人之间,只是疏远淡化也就是了,可别忘了,这是封建体制下的君臣关系,特别是碰上该朱这样 一位特定的“君”,那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生 就是死,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折衷的处理办法, 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永远见不着他,彻底解决也 便彻底舒服。只要他惦记上哪个,纵然逃到天 边,恐也难免被定点清除之厄运。我想,这是 那位儿女亲家到死也许明白也或许一直未彻底 明白的“辩证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 们这些人的结局,部分的也应怪自己。太看重 甚至醉心于那个“亲近”了,他们未必能看彻 “双刃剑”的厉害。在这方面,真正出身农家 的徐达在大事已定后处理得是相当难能了。他 平时万分谦恭谨慎,除了在被召见时偶在莫愁 湖“棋胜楼”与昔日的老搭档杀上一盘(恐也 要让主上几个子儿)外,基本上是深居简出, 保持自以为恰当的距离,当然更无结党营私之 类的勾当。如此这般,即使“御赐烧鹅”助了 死神一把是真的话,皇上也不会公布他的什么 罪状,而且还隆重地封了一个“中山王”。对 于另个“送别”了的昔日的军师刘基,生前曾 封为诚意伯,死后又谥号“文成”。谁说杀昏 了头的朱皇帝不会区别料理呢?这已经给徐 达、刘基一类留足了面子。不仅如此,估计也 会仿照一千多年前的魏王曹操那样还要加以 “厚葬”哩。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是,从一般人的 本性和心理学角度上说,不论是何种类别的关 系,君臣、朋友、情人等等,欲要保持永久的 至亲至密难度是极大的。密久则疲,密久则 忌,忌甚则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也许正因如 此,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君 子之交淡如水。如此虽无巨利亦少大患。而夫 妻关系的潜隐致命因素是:习以为常。因此, 致使许多明公为之开出“保鲜”药方——夫妻 应经常积极想出新招,使“审美疲劳”注入新 鲜活力,双方都能感受到如初恋和新婚燕尔般 的浪漫与刺激。这种想法很好,招也频出,但 欲奏奇效,谈何容易!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一千几百年前唐玄宗与杨玉环的久蜜不衰的爱情佳话。且不论事过久矣,谁也无法得见其全部真相究竟如何,多半是从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和后世洪昇等人的剧作中获得的强烈印象。即使是百分之百地可信,在成千上万的男女之间也不会占到多数的概率。至于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些爱得要死要活热恋男女的典型,常使多情者感动得涕泪横流。但人们也注意到:这些典型故事多集中于“始”,而回避了“久”,更并不在意“终局”如何。其实,我们本文的焦点在于“密久”,而使人感到忧虑、难度最大的问题也正在这个“久”字上。与此相对的强劲吸力则是新奇。我听到一个“小故事”,说一位年轻的女士在终于得见她崇慕已久的特大腕儿时,只是一次紧紧握手就使她回去三天舍不得洗手。而她的丈夫也是位有名的演艺界人士,据信他们之间握手绝对不会妨碍她及时洗手,恐怕连一天也坚持不住。因为她所处的角度与追慕者不同,她不可将她枕席之间的大腕当成“天王”,仰视为神。我从来没有将此视为一个无聊的笑话,也绝不认为这与上述对朱皇帝的心理剖析无关。它恰恰印证了以上所言相当多的人之本性,无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课题。
不可否认,“密久”而未崩的友朋、情人等尚属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世间也是存在的,但那无不是经过大小曲折、或隐或显、反复折冲双方相互修补、诸多建设工夫才能达到的,不是“顺其自然”所能之;而且局 外人也只能见其表面。所谓鞋子挤不挤脚, 只有自己的脚才真正知道。更何况,个人关 系又绝不可与封建时代的政治关系可比,而 君臣之间又是政治关系的最典型的体现。而 且,作为朱元璋这样一个极为独特的君王, 他所主导的人际关系又是人的某种本性的最 深层的体现。因为朱皇帝也是一个人,一个 特定的人,他的心理效应自然要集中地乃至 残酷地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 上。在他的身上,“近则易烦,密久生忌” 这种法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种由 “烦”而忌,由忌而恶的结果之一就是:他 从此不再设丞相,只设“内阁首辅”,而且 一直延续到近三百年的大明皇朝终了。可 见,“忌”、“恶”得何等决绝!
当然,以上对于朱元璋深层心理剖析尤其 是在人际关系中的残酷体现,只是该朱生命史 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不等于这位明代开国皇帝一生作为的全部。如 果论及业绩的话,这位洪武皇帝还是很有些可 圈可点的东西的。我历来认为,作为封建帝 王,他的个人品质与其业绩之间是不宜简单对 号的,有时还可以表现出很复杂的情状。因 此,他们是不好与普通人一样在“鉴定表”上 填以“优点”“缺点”的。所以,本文也不可 能对该朱的“优点”和“缺点”作出全面的综 述与分解,这是毋须赘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