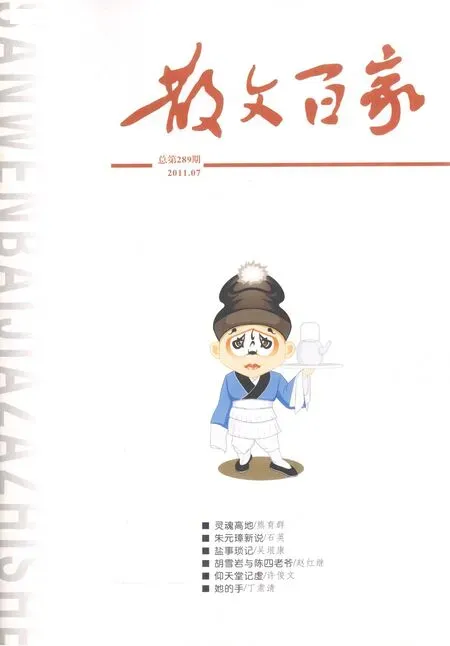仰天堂记虚
●许俊文
去仰天堂,缘于意念微妙的那一动。
当时,我正躺在杏花村的草地上闭目养神。是的,为诗人杜牧曾经畅饮的那酒忙碌了一年,我想享受一下江南寒冬里短暂的暖阳。朋友却在电话里说,新年第一天,该把事情放一放了,不该放的也得放一放了,去仰天堂看看,总该可以吧。
经他这么一撺掇,我原本安静的心就活泛了。这人心一活,就像被风蛊惑的浮云,你拴是拴不住的。况且,又有这么个值得玩味的好地名,不去,恐怕心是不会安分的。
我这人,对地名比较敏感,譬如瓜州、米兰、阳关、漈下村、秋浦河、杏花村、盱眙等,我都是冲着名字去的。去了,不管怎的,图个心安。
其实,仰天堂有什么好看的呢,不就是一座山,山上有座庙么?这话,不能说是错,但也不能说是对。这就等同于说“人不能单靠吃米活着”,乍一听,是这么个理,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全是那个理。仰天堂的山是寻常的,庙也是寻常的,去过那里的朋友跟我提起,都说没啥看头。在去往仰天堂的路上,我跟一位“放冬口”(位于山间的田畈里,生长着许多嫩绿的冬青草,可放牧)的村妇打听山上的情况,她手都懒得指,只努了努嘴:抬头不就看到了么,爬上去一身汗,不值得哦。我下意识地目测一下,此山高约五六百米的样子,却陡峭。轮廓模糊的山尖上挑着一朵云,我仰望了半天它也没挪动一下,像一面风中静止的灵旗。听说这朵云的定力非同一般,你无论什么时候眺望,它总是那个禅定的样子。我想,一座山再普通,能有一朵云不离不弃的眷顾着,厮守着,想必这山也是有几分灵性的。
上山的路极难走。陪同的朋友二十年前上过此山,说是有一条小路可以勉强通行。然而,眼下那条小路已被疯长的野草与杂木挤兑得踪影全无,于是,我们只得在没顶的斑茅与藤树的纠缠中,手脚并用地且钻且行,摔跤是难免的,受点皮肉之苦也并不奇怪。想想通往“天堂”的路也许正该如此吧,它不会让你顺畅地抵达,更不会让你平步青云。这一想,心中也就释然了。
一路上我都在猜想,为什么叫“仰天堂”呢?想来想去,也许是此山的高度使然吧。你看,山下的田畈是低的,路是低的,村庄是低的,李白曾五次游历的秋浦河也是低的,而那些世代生活在低处的人们,总渴望一种高度,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虽然他们无法企及,但终生俯身大地,偶尔仰望天堂总该可以吧?因而我敢说,仰天堂与其说是一个地名符号,倒不如说是一味虚拟的心灵之药。
在山顶上,我见到了那座空洞的寺庙。对,空洞。虽然庙舍倒有十余间,但门前的香炉是冷的,那口黄铜铸就的大钟,上面积着一层厚厚的浮尘,也不知冷寂了多久。相反,野草却来得热烈,它们得寸进尺地往禅院蔓延,尽管严冬暂时阻止了它们放肆的脚步,但开春后它们肯定会更加肆无忌惮,且兴高采烈。
这一切,似乎都缘于那个风烛残年的宋师太。我见到此人时,她半坐半躺在藤椅上,脚下放着奄奄一息的火盆,不知道是谁为谁取暖,仿佛火盆与主人都在延续着生命最后的余温。见此情景,我上前恭恭敬敬地向老人道了一声安,她吃力地抬起眼皮,想把身子坐得尽量直一些,可是努力了几次都未能如愿,就只能那么半躺着,双手合十还我以佛礼,嘴角颤了颤,却没有声音。此时,寒风从手指宽的门缝争先恐后地挤进来,游魂似地到处乱窜,原本空洞、冷落的殿堂就愈发地寒彻骨了。
这宋师太,独守禅院已经七十六年了。这个赢弱的女人,假如她生活在山下的村庄里,这把年纪也该儿孙绕膝了,可她却偏偏把自己的少年、青春、中年及晚年,都交给了寂寞的仰天堂,现在死亡就匍匐在身边,她连喝口热水都艰难。尽管如此,她还是一脸的淡定,神态安详,仿佛一息虽存,但万缘已寂,而一条沿途缀满乱花浅草的往生之路正在她眼前徐徐展开。不怕你误解,我也喜欢“往生”一词。对,喜欢。这个说法比我们常用的死亡、去世、作古更能让人心里觉得温暖、熨帖。往生,往生,它给人以行进的动感与欢快,甚或还有那么几分难以言说的冲动与窃喜。虽然宋师太没有表达她对死亡的态度,但她坦然的神情分明在告诉我,当生命渐渐卸下沉重的躯壳,心灵却获得了解脱与自由,谁能说这不是一种重生呢?
我在禅院里转了一圈,该看的都看了,一切都因为缺少主人的照拂而显得冷寂、荒凉。当我踅回到老人的跟前,想问一问她的身世,可话一出口,不成想老人又施了一个礼,含混不清地吐出“恕罪”二字,顿时让我尴尬难以自容,一时间,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得那么难堪的捱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逃逸的出口,我把话题转到墙上朴初老撰写的那副对联上,我说,一个人要是能够看遍千江月该多好。听我这么一说,老人一直微阖的双眼慢慢地睁开来,目光只一闪,复又合上了。许久,她才轻声低语道:人生也有涯,那是不可能的。人,只要守住自己的一方明月,那千江 月又有什么相干呢?老人的话再次使我脸红。 事后一想,不是什么呢,千江有水千江月,假 如你的心灵因蒙尘而晦暗,即使明月当空,那 又能怎样呢?
这老人的心中有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明月 呢?我不得而知,但禅院后那条通往山顶的小 路,却多少能给我的想象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 注释。站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山下那条“四季 澄碧如秋”的河流,清且涟漪的河水,观月当 然不成问题。想象中的宋师太,无数次于幽冥 的夜色中伫立山顶,静观水中皎洁的月华,直 到把自己看老,老成仰天堂的一个故事。
试想,一个人一生以看月来抵挡红尘的诱 惑,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专注与持守!反正我无 法做到。我常常在纸上打扫红尘,却又不得不 在红尘中扑腾,向生活乞讨,甚至羡慕那些在 红尘里淘得真金白银的人。不错,尘埃里的生 活是多么养人,你可以昧,可以欺,可以贪, 可以各种理由放纵自己的欲望……可宋师太 呢,她选择了远离尘俗的仰天堂,用自己那一 双干净的手侍弄菜蔬、果树、茶叶、砌房子、 修路,掌着油灯读经,寂寞难耐时就站在山顶 上看月。她说,自己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一直 都是心甘情愿的。她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给我 看,我轻轻地拢握着,冰凉冰凉的,一直凉到 我的心里去。其实那哪里叫手呢,委实就是一 截裸露的老树根。眼下,面对着越来越近的生 命大限,老人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
……断续的交谈中,我告诉宋师太,禅院 中的那株腊梅开了。老人“哦”了一声,轻声 念道,该落雪了。我说外面正下着雪呢。老人 又“哦”了一声,就再没有下文了。
在我准备给这篇短文画上句号时,那天一 道去仰天堂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宋师太 人已经走了,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这 么说,她是一个人上路的。
宋师太,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