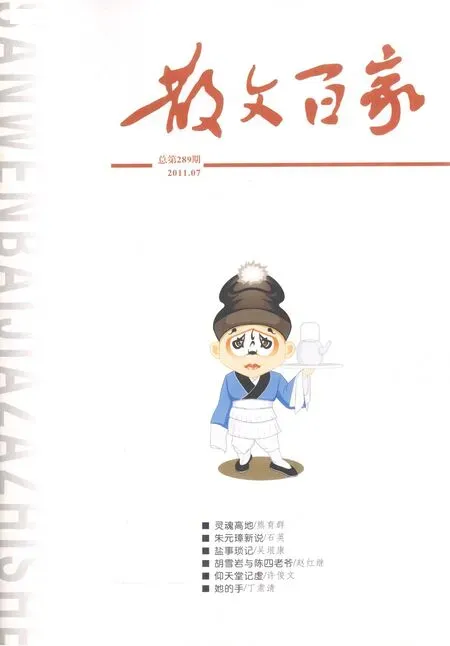父亲的戏班
●郭文锁
我家祖上曾办有一个平调戏班,唱响三省七县,家境也很不错。可是有一年唱戏到磁县时遭遇匪徒劫持,戏班被掠夺一空,家道从此衰落。父亲小时候,经常爬上楼梯,独自站在我家的古楼上,观望那些蒙尘的戏帽,敲打虫蛀过的皮鼓,把玩敲破了的铜锣。这些都是祖上遗留下来的旧物,静物无言,它们的存在好像在为古楼下的子孙讲述着祖上曾经的辉煌和落没的悲凉,仿佛可以听到那苍凉的锣声从遥远的深邃的历史深处传过来,咿咿呀呀的唱腔里,那飘飘的水袖,轻快的莲步就在眼前晃动……它们是一幅画面,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情调,也许这就是血脉文化的精髓传承过程。
父亲虽然身在农村,一生劳作于田间禾下,但他是个事业型的人,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些样子来。建国初,农村文化生活落后,可以说是空白,村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连个响器班(鼓乐班)都没有。父亲那时正年轻,就与他的同伴凑钱买来鼓乐器具,请来师父教他们吹拉弹唱。那师父是何许人我不知道,只说是冬天的夜晚,他们去学习的时候,都从自家带上柴禾,到那学习的地方凑在一起,生一泊火,围着火堆,一边取暖一边学习。父亲学的是操大锣,师父让他把锣提在手里,师父把手掌放在他的后背上,师父拍一下他的脊背,父亲就敲一下,师父拍两下,父亲就敲两下,这样一下一下才慢慢学会。父亲不但学会操大锣,还学会“捉”二锣,那二锣叫也,略比锣小,没有绳系,打的时候需用左手食指轻轻挑起,右手用长薄木板击打,发出“来来来”的声音。大锣敲起来是慢腾腾半天来一下,那小 旋子却是急匆匆一下赶一下,前去学习的有五 六个人,有人学会了吹唢呐,有人学会掌鼓 板,父亲学会操大锣,叮叮当当,没多长时 间,村里办红白事就有了他们。他们那时也就 是图个高兴,寻个乐呵,吸上几盒烟,喝上一 点酒,自娱自乐,很是高兴。随着时间的推 延,他们的“响器班”都出了名,据说有一次 到山西省黎城办丧事,在街头与另一伙鼓乐班 遭遇,双方一下子较开劲,非要争个山高水 低,结果吹唢呐的当场就吹吐了血。进入上世 纪六十年代,村里要办剧团,这样,父亲和他 们的响器班转向剧团组建,招集演员,外出山 西请来教戏的师父,这样父亲就走进了剧团, 无意间又重蹈了祖上复辙。
父亲就走上了剧团领导岗位,比如请师父 来教戏,与县里文化馆交道,到外面写台口联 系演出,出戏的时候挨门挨户做演员的工作等 等。就把手里操锣的活儿传与了别人,也像当 年师父教他时那样,拍着别的后背,随着节 拍,一下,一下,又一下……
涉县这地方,地处河南、河北、山西三个 省交界处,从戏曲上讲,东去有武安的平调, 南下有河南的豫剧,西去有山西上党梆子。因 为来村里教戏时的老师是山西人,自然就学成 了山西梆子。山西梆子唱起来粗放高昂,激情 四荡,多是武戏,适合我们北方人,特别是农 村人的口味。那些戏目到现在我都能记着,有 《二进宫》《铡美案》《下阴曹》《穆柯寨》 等,这些戏目在北方多见,也演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游龟山》等。村里每年都要唱戏,春天唱,秋后也唱,到过年时更要唱。当时涉县村村有剧团,村村建剧院,天天唱着这些戏,大人小孩子都会背了,再唱时就或没人看了。于是就与外村交流,让别村的戏来我村唱,我村的戏到外村去演。
从小我记得,我家古楼前的小院里到了晚上就是排戏,那请来的老师好像是我家请的一样,吃住就在我家里。一到晚上,父亲就点上汽灯,把我家院子照得明晃晃的,发着沙沙的声音。在灯影里,老师手把手教学员移莲步,出云手。我还小吧,最多三四岁,夜深了,我还想看,母亲别着我睡觉,我站在炕上从窗户里向院子里偷看。我村的戏越唱越好,每年全县都要进行汇演,而每年父亲都会代表剧团领回一面锦旗。这是荣誉,是全村的光荣。每次出戏到外乡演出,父亲把这些锦旗都带上,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班戏是有实力的。我村的唱遍了涉县的大小山村,还唱到山西左权,唱到邯郸峰峰,唱到河南林县。
因为通常唱的那些老戏目,已不能吸引观众,影响剧团演出创收,父亲就跑到山西左权县,请一位韩姓老师,在我村教戏三年,排出连本戏《呼延庆打擂》。这戏一经推出,又着实让村里的剧团火了起来。
为了唱戏,父亲不知道结交了多少人,有过多少朋友,经常有人为剧团的事寻到我家里来,到了吃饭时间自然就在我家里吃饭,为此没有少让母亲抱怨。有一年我在一个村里遇一老者,他听说我是昭义村的人,就提起父亲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一下笑起来,说问对人了,我是他的老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办剧团没有走向职业化,培养起的演员一个个谋心挣钱,出戏就有一搭没一搭了。随着父亲那一代人年岁的增加,剧团出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停下来。戏衣戏箱是我父亲早先请人做的,有的是他南下郑州买回来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浸注着他的精力与 情感,但有一个事实不能改变,——它是村里 的,是集体的,不是我家的。那些戏箱只好封 存起来,蒙尘仓库深处。
在父亲七十岁那年,村委会决定,要拍卖 戏箱戏衣。那时我家受灾不久,生活很困难, 根本就没有钱。父亲不想错失这些东西,就找 到了当时一起创业的四个老人,用二千块钱把 这些东西买到手里。七十岁的老人啊,手里拿 着自己早年经营的戏衣戏箱,激动得不得了, 几个人高兴地说:“好了,好了,这些东西成 我们的了,成我们的了。”
七十岁的老人又四处找钱,到郑州购置新 衣新帽,又重新招集演员,敲敲打打又出戏 了。
记得我在更乐打工的那年冬天,听说父亲 带了剧团来邻村演出,我一听就去了。在朋友 的带领下,我来到后台,真见到了父亲。他身 上披着厚厚的棉衣,在一个劲地咳嗽。有人告 诉我,父亲生病好几天了,让我劝他回去。可 是父亲却说没事,拉着我的手,指着台下黑压 压观众说,你看,台下多静,我们的戏在这里 唱响了,唱响了……
父亲的股份剧团又在外演了五六年,他们 的资产从刚买下来时的两千元发展到两万元。 那些年我刚成家,帮不了父亲,反而有时得花 他唱戏挣回的钱。只到他七十八岁那年,真的 走不动了,五个老头坐下来围成一圈,把戏箱 平分了。
一分五份,各自拿回家做个念想。
父亲往回运了五大箱。有戏衣,有戏帽, 有刀枪,有锣鼓,我的儿子这时五六岁了,回 到老家见到这些东西,高兴得不得了,拿拿这 个,动动那个。看到孩子玩着这些东西,父亲 说:“我小时,就记得在咱家的楼上就放着戏 衣,戏帽,有虫蛀过的鼓,有敲破了的锣。”
我心里一惊,传承这东西,逃也逃不掉 啊。最难忘。那时我刚毕业,第一次当班主任,又逢上那个年代……”师母怕乔老师过分怀旧,插话说:“不管你们走到哪里,干啥工作,都牵着他的心。特别是你这个郑一民,他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电视上看到你讲话,到处给人显摆:这是我的学生!”
乔老师怕师母说出他更多的秘密,笑着站起来招呼大家说:“走,我带你们参观参观我的冬瓜园吧。”
冬瓜园在乔老师的住院西侧,是在一块废弃的旧宅基地上开垦种植的。灿烂的秋阳下,郁郁葱葱的瓜叶丛中躺满青皮白霜枕头一样的大冬瓜。乔老师自豪地指着那些他亲手种植浇灌管理的冬瓜说:“我这是废地利用。一共种了200棵,全用农家肥,每棵结两个瓜,估计今年能收一万多斤。”
“乔老师,这么多冬瓜,您老俩咋吃得完啊?”一个同学吃惊地问。
乔老师老伴神秘地眨眨眼睛说:“他哪是为自个吃啊。退休了没事干,看不见学生心里烦,侍弄它们既是锻炼身体,也是为社会做点奉献。朋友来了,送一个;邻居待客了,摘一个。他不让卖,只为图个自己乐呵!”
秋风好像配合师母的介绍,吹动摇弋的瓜叶,让那些藏头缩尾的硕大冬瓜尽显原型,犹如一群在碧波中聚会荡漾的海豚,壮观而令人震撼。惊叹中我突然明白了乔老师对冬瓜的那种奇特而深邃的情感:
是啊,那哪能卖呢,那是乔老师用心血和 汗水浇灌的又一个硕果园呀!在外人看来是冬 瓜,在他看来就是一群不会说话的“学生”。 他像在学校对待学生一样亲切认真,每天精心 施肥浇水、除草打杈,默默用余热做着力所能 及的事奉献社会,用收获证明人生价值和人民 教师的伟大品格。
乔老师发现我们用敬慕的目光盯着他,羞 涩地哈哈笑着说:“别听她瞎说。今天你们来 了,每人带个冬瓜走,就算帮我克服困难 了!”
我们不敢劳累老师,就自己下手摘冬瓜。 乔老师指着一个个头最大的冬瓜说:“这个送 给一民,回到城里叫你的同事们也尝尝我种的 冬瓜。”
那个冬瓜足有50多斤重,两个人抬着才 装上车。要告别了,我紧紧握住乔老师的 手,望着他满头银丝和满脸皱纹中呈现出的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幸福和自豪,从心底由衷 升起一股股热爱和崇敬的浪涛。人们谈老 师,常喜欢炫耀高中老师和大学导师对自己 人生的帮助,其实初中、小学的恩师们同样 是伟大的人,他们不图报答,无怨无悔,犹 如春蚕吐丝,用一生的辛勤劳作为祖国和民 族支撑起最基础的人才大厦,更值得我们尊 敬和永远不能忘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