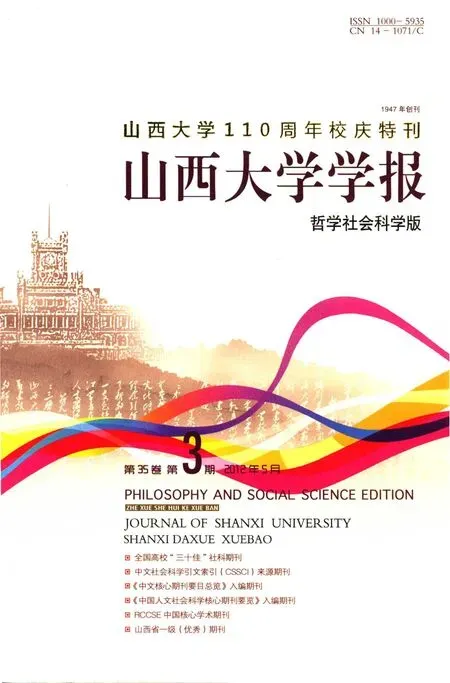语言与理解——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殷 杰,何 华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由语言引导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语言在此是讨论的主题。不仅诠释学的对象、过程和人类世界经验被认为是语言性的,而且通过揭示语言与语词的特质,诠释学的普遍性得到证明;之前讨论的经验结构、问答结构、视域融合等内容在对语言的分析中被具体化。《真理与方法》发表以后,伽达默尔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并开始关注分析哲学宣称的“语言学转向”。①写作《真理与方法》的时候伽达默尔并不知道这一转向。他曾说“‘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我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尚未认识”,这是该著再版时的补注。[1]541他十分重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与之有相近之处。[2]127-128在与杜特(C.Dutt)的一次谈话中,当被问到,“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融合是语言的伟大成就’适用于‘生活共同体的一切形式’,是什么样的语言能有这样的作用?”伽达默尔回答,“我只能这样回答,我是完全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没有私人语言’。”[3]因此,我们把伽达默尔对使理解成为可能的一般语言的关注称为“语言转向”。他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完成了诠释学的普遍化。这种分析可能被认为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本文试图分析得出这种倾向并不存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这种语言转向对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罗蒂(R.Rorty)对伽达默尔的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直接参与到麦克道尔(J.McDowell)哲学思想的发展中。
一 语言与诠释学的普遍性
《真理与方法》的一个目标是要揭示诠释学的普遍性。“通过把语言性认作这种中介的普遍媒介,我们的探究就从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诠释学这种具体的出发点扩展到一种普遍的探究。因为人的世界关系绝对是语言性的并因而是可理解性的。正如我们所见,诠释学因此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遍方面,而并非只是所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1]616诠释学的普遍性是指,诠释学所谈的理解、解释,是人类的普遍经验,是人与世界遭遇的普遍方式,而不仅仅发生于精神科学。《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有意识地重申他这方面的认识,在文章《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1966)中他谈到,“解释学问题,如同我已经加以阐明的那样,并不局限于我开始自己研究的领域。我真正关心的是拯救一种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代文化的基本事实,亦即科学及其工业的、技术的利用。”[2]10由于诠释学的基础地位,它可以纠正人们对自身经验的认识。在《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自述》(1975)中他更清晰地指出,“在所有的世界认识和世界定向中都可以找出理解的因素——并且这样诠释学的普遍性就可以得到证明。”[1]805
可以看出,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学的普遍化与语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是联系自我和世界的中介,是意识借以同存在物联系的媒介。语言不是世界的一种存在物,是人的本质结构,而且语言相对于它所表述的世界并没有它独立的此在,语言的原始人类性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在世存在的原始语言性。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所表述的世界,还存在一个自在的世界。世界自身所是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与它在各种世界观中所显示的东西有别。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这就是语言的世界经验,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这种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都是先行的。因此,伽达默尔说,“‘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1]584
语言与人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我们在语词中思想,思想就是自己思想某物,而对自己思想某物就是对自己言说某物。思想的本质就是灵魂与自己的内在对话。伽达默尔把思维和语词的关系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相类比以说明思维与语词本质上一致。说出事物本身如何的语词并没有自为的成分。语词是在它的显示中有其存在。因此,并不是语词表达思想,语词表达的是事物。思想过程就是语词形成的过程。语言是思想工作的产物。语词是认识得以完成的场所,亦即使事物得以完全思考的场所。他用镜子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语词是一面镜子,在镜子中可以看到事物。此比喻的深刻之处在于,镜子表达的是事物,而不是思想,虽然语词的存在源于思维活动。
语言表达事物,并非事物是语言的对象,二者也是统一的。伽达默尔对之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光的比喻做了更形象的说明。语词是光,没有光就没有可见之物,同时它唯有通过使他物成为可见的途径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的。事物在语词中显现,称之为“来到语言表达”。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自在的物和表现出来的物,某物表现自身为的东西都属于其自身的存在。因此存在和表现的区别是物自身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却又不是区别。这里包含了一层意思,语词表达的内容与语词本身是统一的。语词只是通过它所表达的东西才成其为语词,语言表达的东西是在语词中才获得规定性。甚至可以说,语词消失在被说的东西中,语词才有其自身或意义的存在。这事实上就是他在《人和语言》(1966)中所说的“语言所具有的本质上的自我遗忘性”的表现。“语言越生动,我们就越不能意识到语言。这样,从语言的自我遗忘性中引出的结论是,语言的实际存在就在它所说的东西里面。”[2]66
以上语言与世界、思维和事物的关系是对语言普遍性地位的描述。诠释学是普遍的是因为,诠释学所描述的理解和解释与文本的关系和人与世界通过语言发生的关系一样。理解属于被理解的东西而存在,理解已参与了意义的形成。语言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语言的一个特质是,语言是事件。语言的事件性质就是概念的构成过程。概念不是演绎而成,因为演绎解释不了新概念如何产生;概念也不是通过归纳产生,因为人事实上不需要用抽象就可以得到新的语词和概念来表达共同经验的相似性。因此概念是自然地构成的。人的经验自己扩展,这种经验发觉相似性,而不是普遍性;语言知道如何表达相似性,从而新的概念形成。伽达默尔数次用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一支部队是怎样停住的”来说明经验中一般或相似性如何形成的。这支部队是怎样开始停步,这种停步的行动怎样扩展,最后直到整个部队完全停止,这一切都不能或有计划地掌握或精确地了解。然而这个过程无可怀疑地发生着。关于一般知识的情况也是如此。[2]65一般知识进入语言是由于我们表达事物时与自己的一种无定局的对话形成的。人不可能一次把握思想的整体,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需要语词不断创新。语词的不受限制的产生,正反应了思想意义展开的无限性。也就是说,物在词中显现总是有限的,而物在向我们不断的言说却是无限的,伽达默尔称之为“隶属”。语言是这种隶属的场所,是调解有限与无限的中介,由此“语言是中心(Mitte),不是目的(telos)。是中介(Mitte),不是基础(arche)。”[4]综上所述,就语词是不断自然生成的过程来说,语言是事件,就它作为事物不断言说的场所来说,语言是中心、中介。语言所起的事件和中心的作用是理解和解释的具体化,而语言的普遍性直接促成了诠释学的普遍性。
二 语言与理解的客观性
由于伽达默尔承认理解者的偏见,传统,历史境遇以及时间距离是理解的条件,并且认为不可能纯粹地认识理解对象,在《真理与方法》出版后以贝蒂(E.Betti)和赫斯(E.Hirsch)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指责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性观点中存在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以维护理解的客观性。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的确有理解意义多元化的内容。对文本或历史的理解中,并不是理解和解释对象本身,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你”而与之进行对话。理解者“我”与“你”彼此开放不断形成视域融合,而理解的意义获得就是“你”“我”在视域融合中形成的共识。这一内容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地位特殊。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说,“本书中关于经验的那一章占据了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关键地位。在那里从‘你’的经验出发,效果历史的概念经验也得到了阐明。”[1]11正是在此伽达默尔有信心应对关于指责他的诠释学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说法。
伽达默尔探究的是,“理解怎样得以可能?”或我们在理解时什么同时发生,或人的理解的结构,以说明“……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1]6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以及做出的所有解释都是文本自己的表现,并非解释者的主观臆想。所有的解释都是对文本的解释,统一于文本。
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媒介,解释就是理解进行的方式,因此理解和解释是统一的。理解文本与文本对话首先是重新唤起文本的意义,在这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已经参与了进去。这一步伽达默尔与贝蒂和赫斯有根本的区别。贝蒂认为解释的对象是“富有意义的形式”,解释是重新认识“富有意义的形式”中包含的意义,理解则是对意义的重新创造。[5]这里虽有主观创造,但依然是以恢复本来意义为目的。赫斯则认为文本的“含意是可复制的”。[6]他们都认为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来获得文本作者的“原意”。伽达默尔看来,文本作为文字流传物是记忆的持续,它超越它那个过去世界赋予的有限的和暂时的规定性。使文本能这样超越的是语词的观念性(Idealität)。我们可以借用利科(P.Ricoeur)的观点来理解伽达默尔的这一术语。利科说,“书写使文本对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7]也就是所谓作者的死亡,文本的诞生。这样文本就打破了作者的语境而获得自己的语境。文本作为语词在我们的世界中以我们的语言与解释者形成对话,文本的语词自身的这种言说性,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语词的观念性。这样才能“……通过记忆的持续流传物才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并使所传介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1]504这是我们一开始不直接理解和解释对象本身的原因。
伽达默尔说,“理解通过解释而获得的语言表达性并没有在被理解和被解释的对象之外再造出第二种意义。”[1]514这是因为理解是对话、交流,意义在此之中得以显现,这表现为一个语言性过程,语言与其所表达的思想是统一的。我们还是引用“道成肉身”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文本与解释者对话,使双方的思想在语言中体现出来,语词表达意义,但并不是语词作为形式反映意义,而是意义的形成就是语词形成的过程。更进一步说,意义“来到语言表达”并不意味着获得第二种存在。意义在语词中的显现属于文本自身。这样语词意义和文本是统一的。因此,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伽达默尔多次用游戏来类比语言,“当游戏者本人全神贯注地参加到游戏中,这个游戏就在进行了,也就是说,如果游戏者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仅仅在做游戏的人,而是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游戏就在进行了。因为那些为游戏而游戏的人并不把游戏当真。”[2]67这里面的关键内容是:(1)游戏不是单纯的客体,人参加而使之有其此在;(2)游戏的行为不能被理解为主观的行为,因为游戏就是进行游戏的东西,游戏的真正主体是游戏本身;(3)参与者的完全投入,语言是游戏。在这里就去除了自我意识的幻觉和认为对话是纯主观内容的观点。
三 语言与“第二自然”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关于语言的讨论得到麦克道尔的关注。麦克道尔说,他自己概括伽达默尔关于语言的思想希望能去除使分析哲学家们看不到《真理与方法》中丰富洞见的障碍。[8]151
麦克道尔对伽达默尔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伽达默尔和戴维森论理解与相对主义》(2002)一文中。下面首先简要概述他对伽达默尔的理解。
麦克道尔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人的在世(being-in-the-world)具有原始语言性[1]575。任何人的在世都由一种或另一种语言形成,也可以说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由语言形成的。人们使用共同的语言,进入语言游戏,它包括了非语言学的实践以及人的习俗等,在其中语言行为被整合入一种生活形式。人们在传统中成长,就是要学会说一种语言,学会用词来回应眼前的过往事物,学会言说关于世界的普遍特征,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符合“我们”(we)的言说。
关于使用一种共同语言方面的认识,可能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是对这种语言进行控制,依据精确的语法和语义规则来控制语言行为;成功的语词交流依赖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共有这种控制能力。这就是说,好像有一种机械的装置可以做出任意一个语句的意义。从上文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中可以看出,这种按规则预先设定的对谈根本算不上真正地使用语言。更需要注意的是,从这种观点可能得出,用同样的词去意谓同样的事。无论是伽达默尔的语言观还是弗雷格(G.Frege)式的意义理论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如果人们使用共同的语言,还可能有所谓的“正确用词”的要求,即在语言实践中共同遵守一些规则,以保证共享语言的人相互理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产生的来源。如果是来源于某个权威,比如语法学家,他可能具有某种特权,被塑造成某种超级个体。因此戴维森(D.Davidson)据此认为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互理解并不需要共同语言。布兰顿(R.Brandom)则认为,共同语言是需要的,但是为避免产生超级个体,应该保证语言游戏参与者相互间责任义务地位的界线,这就是语言社会性中的“我—你”(I-thou)图景。[9]但是界线的保持使“我—你”双方的行为相互延伸到对方受到限制,共同语言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这样布兰顿的观点与戴维森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伽达默尔共同语言图景可称之为“我—我们”(I-we)式的。一种共同的自然语言是“我们”(we)的所有物,是共有的传统内容,在此语言的形式与传统内容是不可分的。它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种规范形式,这种形式并不能被还原为主体的活动,因为它是语言游戏参与者世界观不断融合的结果,它不是固定的,于是不能归于超级个体。
麦克道尔这样来概括伽达默尔的语言观,首先可以看成是对他在《心灵与世界》(1994)中的一些观点的补充说明。他说,“我写到由概念中介的(心灵)向世界的敞开,部分地是由对传统的继承构成的,我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而援引传统。”[8]134引入传统的原因是要说明概念能力可被引入主体控制之外的感性运行中。受主体控制的概念能力是自觉的,而在感性活动中的概念参与是自发的。要使这种自发的理性概念活动看成是合理的,就有必要把它界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麦克道尔称之为“第二自然”,即理性概念能力是第二性的,是人在共同体中通过语言学习从传统中习得的。这样当人的眼睛向世界敞开时,世界作为维特根斯坦式的情况的总和,在经验中出现在固定信念的理性背景中,也就是说感性的作用对我们信念的形成产生理性影响。这一观点不仅被评为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是常被指出会陷入相对主义。这是麦克道尔概括伽达默尔语言观要考虑的第二方面。
如果感性的活动中参与了概念或已有信念的内容,看起来很难说世界观客观地描述了世界。每个人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概念理性能力,因此人们对同一世界有了不同的世界观。相对主义特征在此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像戴维森认为的那样,感性活动只从概念范围之外对信念的形成起初级的因果影响,就能免去相对主义的嫌疑。麦克道尔认为,一方面自己不排除世界对心灵的因果作用(戴维森意义上的);另一方面这种因果作用不在理性之外。人们没有必要赋予物理科学透彻到事物的真实关联性的独特能力,其他因果性思维活动没有必要以可用物理词汇描述的因果联系为基础。[8]139概念没有边界的意思是,只要人在最初的感性活动中接触世界,就有概念活动的参与,但是主体与对象之间是有区分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批评麦克道尔的哲学陷入唯心主义是把认识论问题混淆为本体论的。于是,如伽达默尔所说,没有人怀疑,世界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存在并且也许将会存在。这是如下意义的一部分,即所有人在语言中形成世界观而存在。[1]580没有人怀疑世界大部分存在于一条界线之外,这条界线环绕意向性的领域。但是,我们可以把世界对信念的形成的影响理解成为已经在概念范围之内,并不是来自外界的冲击。如果外界的影响直接对信念起确证作用,这就是“所予神话”。这样世界就是世界观的主题(topic),不同的语言能表达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用伽达默尔的术语说是不同的世界对应不同的视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世界”的谈论进入一个语境,在其中伽达默尔坚持认为这些世界观的多样性并不包括任何关于世界的多样性。这是麦克道尔为自己的哲学不存在相对主义的阴影这一观点给出的论证。
四 诠释学与唯名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之所以被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关注,是因为其诠释学与实用主义哲学有相近之处。虽然伽达默尔著作的名称是《真理与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在其中说真理在诠释学中的含义。我们可以推断,他的真理观一定不是符合论,因为伽达默尔并不主张通过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来理解世界,他认为对世界的理解是一个无尽的不可预期的过程。普特南(H.Putnam)这样批评真理符合论:一种信念对于现实的任何一种这样的符合,都只能是对于在某种特定描述之下的现实的符合,而这样的描述没有一种是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具有特权地位的。[10]换成伽达默尔的话,就是人在某一处境中形成视域,又在不同的处境中进行着视域融合。这暗示了不同的视域之间地位平等,没有那一个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正好与罗蒂哲学中的对话理论、反表象主义观点相近。特别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进行语言转向之后,诠释学成为哲学的一个方面,“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1]615作为其标志性的论断在罗蒂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罗蒂认为伽达默尔的这一观点对唯名论做了最好的概括,这里的唯名论主张一切本质都是名义上的。[11]22-23理解一个对象的本质,只能是重述那一对象的概念史;更好地理解某种东西就是对它有更多的可说的东西,就是以新的方式把以前说过的东西整合在一起。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起认为对事物理解越深离实在越近;唯名论认为可利用的描述越多,描述间结合越紧密,我们对这些描述所表征的对象的理解就越好,或者说我们理解的就是描述。这些描述中没有一种有特权可以达到自在的对象,或者说“自在”本身也只是一种描述词汇。因此描述任何事物没有终点,其过程是伽达默尔式的视域融合,罗蒂称之为“再语境化”。[11]27我们可以看出,罗蒂对伽达默尔的解读经过了实用主义滤过,过滤掉了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关于理解和语言的本体论内容,只省下方法论层面上的内容。麦克道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在理解与真理的联系、语言意义和客观实在的把握、意义和思想的社会本质方面对伽达默尔重新解读,形成自己独特的关于知识、心灵与世界关系方面问题的分析理路,对笛卡儿开启的现代哲学传统在这些方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Hans-Georg Gadamer with Carsten Dutt,Glem W.Most,Alfons Grieder and Dörte Von Westernhagen.Gadamer in Conversation:reflections and commentary[M].ed.and trans.byR.E.Palm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56.
[4]Wachterhauser B R.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204.
[5]伽达默尔.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6-128.
[6]赫斯.解释的有效性[M].王才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56.
[7]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42.
[8]J.McDowell.The Engaged Intellect[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9]R.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38-39.
[10]罗蒂.实用主义哲学[M].林 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11]Edited by B.Krajewski.Gadamer’s Repercussions:Re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