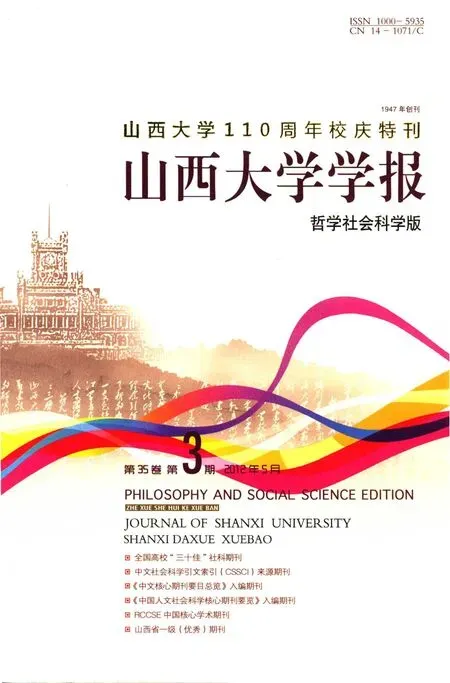试论唐前文化转型对小说的影响
王 平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学术界对唐前小说的分类缺乏统一的认识,或以题材内容为依据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或以文体叙事为依据分为志怪、杂传、杂事、志人四类。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偏颇之处却相一致,那就是割裂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实际上,文学作品的分类应当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入手,正因为两者关系的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类型的不同。以小说作品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形象的相互关系为分类依据,唐前小说可以分为神话、志怪、志人三种类型。神话小说处于小说的萌芽阶段,意义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形式,只能以现有的形象表达某一意义。志怪小说稍稍前进了一步,虽然意义与形象之间仍有不和谐之处,但小说作者借助某一形象达到宣扬宗教教义的目的是明确的。当志人小说将描写的对象转向现实人生时,其形象自然要取自现实中的人,其所要表达的意义也逐渐明确,但仍然受到了当时文化思潮的制约。
一 卜筮宗教文化与上古神话
变竟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在以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特此再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当然应从上古神话说起。尽管神话幻想中隐含着宗教信仰的因素,与作为艺术的小说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发生上毕竟有某些渊源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有关神话的文字记载远远滞后于产生神话的时代。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经历了文化的变迁。因此,今天从各种古籍中所见到的上古神话,便显得繁杂、零乱,甚至于相互矛盾,即所谓“同神异格”、“异神同格”、“同事异神”等芜杂现象。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正是从这些混乱的现象中,我们有可能发现宗教文化对上古神话演变的影响,并进而理清上古神话演进的轨迹。
上古神话首先是原始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这一时期的神话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如著名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虽然这一神话在《三五历纪》①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开辟原始》引《三五历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和《五运历年纪》②清·马 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中的记载不尽相同,但其反映幻想中的自然形成却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像这类保持上古神话最初面目者不过是凤毛麟角,因此也就特别宝贵。
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卜筮宗教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它是对原始宗教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烧灼过用作占卜的兽骨便是明证。[2]到了商代,这种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殷墟甲骨卜辞中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其降堇”[3]等卜辞,这就是说,自然界的风雨变化、年成好坏以至于战争胜负等人事活动,都是由“帝”的意志和命令所决定,“帝”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宰。从这些甲骨卜辞中还可以看出,日月风雨山川和死后的商王及其大臣,都是帝所统率的天神,它们分别担任帝的“臣正”、“工臣”,辅佐上帝统治世界。在这种卜筮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神话,自然神逐渐演变为英雄神,如关于羿的神话便是如此。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4]405从这则记载中可知,羿是一位天神,所以才要到“下国”、“下地”去解除危难。他所听命的是“帝俊”;而“帝俊”乃中国古代东方部族所传之上帝,其妻有日神羲和、月神常羲。《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5]《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6]这些神话都带有卜筮宗教文化的特征,因为这里出现了主宰自然的“帝俊”,但同时也保存着原始宗教文化的某些痕迹,帝俊之妻乃是太阳,且生出“十日”。这一神话继续演变,在《淮南子·本经训》中便有如下记载:“逮之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7]“羿射九日”这则神话所表现的当然是先民幻想战胜干旱的愿望。但羿已非天神而是尧臣,已经变为英雄神;他从听命于帝俊到服从于天子尧,已经含有“神话历史化”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在卜筮宗教文化影响下,原来天地生成的自然神变成了造物主、创世主的神话,如关于女娲、神农的神话便是如此。《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8]这位女娲不仅造出了人,而且还补过天,[9]因此她成了人类的始祖和救世主。神农即为炎帝,《礼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10]《淮南子·时则训》又称:“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11]赤帝也就是炎帝,在这些记载中他带有鲜明的自然神特征。《世本·帝系篇》云:“炎帝神农氏。”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12]3自此,炎帝、神农合二为一,神农也成为“尝百草”[13]、“教农耕”①清·马骕《绎史》卷四《炎帝纪》引《春秋元命苞》,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的始祖神。
由于卜筮宗教文化的影响,神话中大量出现了“帝”以及英雄神,但其宗教信仰的性质却并未根本改变,只不过从对自然神的崇拜演变为对天帝及其部属神的崇拜而已。殷周之际出现的《周易》既是卜筮宗教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含有某些新的文化因素,如观物取象、阴阳变化等观念。到西周末、春秋初,终于对卜筮宗教文化提出了怀疑和否定,人们开始用阴阳、五行等观念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是史官。因此可以说文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巫史分离,宗教文化开始被史官文化所代替。
二 史官文化与“神话历史化”
在现存史籍中,最早用阴阳之气解释自然现象和国家兴亡的,见于《国语·周语上》。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史伯认为,天地间存在着阴阳两种气,这两种物质力量“不失其气”,自然界和社会就安定。地震不是天命,而是由“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所引起。由于阴阳二气的失调才发生了地震,引起了“川源”阻塞。“周之亡”的原因不在于“天命将终”,而是缺乏水源,无法保证万物生长。“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而且这还有历史的先例:“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所以三川震是西周灭亡的征兆。[14]
春秋时期,卜筮宗教文化被进一步否定,史官文化进入了高潮。众多的史官和士大夫都用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并强调了人事的作用。《左传》中便保存了这方面的许多材料。公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宋国发现陨石和“六鹢退飞”,人们认为这种不常见的现象,是人事吉凶的预兆。但是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15]鲁国的闵子马认为“祸福无门,惟人所召”。[16]晋国的太史蔡墨用“五行”来说明祖先神:“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17]邓曼也认为“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18]郑国子产说得更透彻:“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19]这些言论虽然还未能完全否定“帝”和鬼神的存在,但已对卜筮巫祝的作用给予了贬斥,提高了人的作用和地位。春秋后期老子以天道无为观点否定了天道有为宗教观念,从而取消了造物主上帝的地位。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将宗教天命论改造为天之历数。“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0]所谓天之历数,也就是自然变化之理,天地运行之理。[21]他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22],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3]这一切都表明了卜筮宗教文化的普遍动摇。
史官文化与儒学文化取代宗教文化,必然对已有的上古神话给予深刻影响,从而产生了“神话历史化”的现象。先民幻想中的神话变成了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神话中的众神变成了历史中的人物。这样一来,关于天地开辟及自然现象起源的神话遗留材料便极少,关于本族始祖起源及文化超人的材料相对来说却要丰富得多,并且特别注重他们的家系及道德的善恶。
在上古神话中,黄帝最初之神职是雷神,“黄帝以雷精起”①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河图帝纪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炎帝是火神已如上述。但是后来炎帝成了黄帝的同母异父兄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②清·马骕:《绎史》卷五《黄帝纪》引《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页。炎帝兵败,蚩尤崛起,为炎帝复仇。“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24]他“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25]黄帝成为“行道”的帝王,炎帝和蚩尤则是叛上作乱的臣子。在此基础上,司马迁继承先秦史官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观点,就将其全然历史化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26]共工与颛顼之争也是黄帝、炎帝战争的继续。共工是炎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的后裔,[4]407因为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遂成为叛臣的代表。《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27]在这些形象身上,还残存着上古神话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先民战胜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愿望。但其已被描述为历史,反映了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景况。
再如帝喾。在《山海经》中作帝俊,乃生日月之神,但历史化之后,就成了黄帝的曾孙,“年十五岁,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他的四位妃子分别生了后稷、契、帝尧和挚,皆有天下。[12]6后稷本是从天上取百谷之种育植于人间的神,[28]在这里又成为帝喾之子。帝尧则径成为人间帝王,勤劳、节俭、尚贤、爱民种种事迹屡见于《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之中。
以上论述表明,史官文化和儒学文化取代宗教文化,使人类历史与神话幻想合为一体,从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了历史著作的发达和以虚构幻想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滞留疲弱。所谓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也与这一文化转型有关系,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古代小说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少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著述被归入了历史著作的范围之中,或者不少历史著作中又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这些又为后来小说的创作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素材和艺术想象的依据。
三 魏晋玄学与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又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型。迅速崛起的玄学和广泛传播的佛、道二教,强烈震撼了汉武帝以来儒学独尊的地位。被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在汉代被理解为道术的佛教,开始与玄学相结合;原来仅在下层社会活动的道教,逐步迈入了社会上层。这一文化转型使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代小说经历了漫长的胚胎期,终于呱呱落地,开始了它日益成熟的历史。
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两汉时期以神仙信仰为对象的小说不同,它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作主要的表现对象。正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29]33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它所表现的人,不再停留于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更注重于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精神格调。这一切都与魏晋时期的玄学直接相关。
首先,魏晋玄学对外在的权威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从而表明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魏晋之际,阮籍、嵇康以老庄为师,使酒任性,玩世不恭,认为名教与自然相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0]大胆地“非汤武而薄周孔”,[31]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32]认为名教礼法是“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33]主张“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讽刺礼法之士不过是裤中之虱。[34]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适意,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当时不少文人指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检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35]“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36]这些现象从某一方面表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人格的觉醒。志人小说也借此应运而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魏晋玄学相映衬。
其次,魏晋玄学更注重本体论的探讨,从而强调了人内在的精神本体。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王弼认为虚无的“道”或“无”是产生万物的宗主,“有”从“无”中产生,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三《王戌传》附《王衍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14页。王弼说:“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37]“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38]这就是说,外在的功业名利都是“无”这一本体产生的,所以都是有限的和易于穷尽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无限的和不可穷尽的。王弼认为只有“圣人”才具有这种精神本体:“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②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91页。因此,内在的精神格调成为品评人物的最高标准和原则。表面外在的功名、道德、学问、气节,逐步让位于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等内在的精神因素。《世说新语》虽然也赞美了“王祥事母”、“王戎死孝”、“阮裕毁车”、“管宁割席”、“荀巨伯访友”等德行气节之事,但这不过仅占全书的几十分之一。作者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摆脱拘束,托怀玄胜,远咏老庄,以清谈为经济,以隐逸为高洁,不以物务缨心,甚而讲求服药饮酒的名士风度。如著名的“刘伶纵酒”、“阮籍见嫂”、“王徽之访友”、“谢安屡辞朝命”、“孙安国与殷中军谈论”等,展示的都是脱俗的言行;“庾子嵩读庄子”、“殷中军论佛经”等表现的都是内在的智慧;“王右军如游云惊龙”、“嵇叔夜若孤松五山”等,赞美的都是高超的风貌。这种对内在精神格调的重视,对古代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魏晋玄学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哲学命题,从而触及了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问题。王弼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39]言词形象都是可穷尽的传达工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有限的工具去表达出那不可穷尽的无限本体。言词形象是外在的“形”,无限本体是内在的“神”。所以,“言不尽意”就是要求“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外在形象并不是最终目的,表达出人物的内在神情才是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世说新语》在表现技巧上也完全遵循了这一宗旨,作者往往以极其简洁的语言描写,就使各类人物“气韵生动”,跃然纸上。如“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步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40]739-740再如“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40]740寥寥数语,而人物的内在精神无不毕现于眼前。
四 佛道二教与志怪小说
如果说志人小说是魏晋玄学的直接产物,因而带有玄学的种种特征,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则是佛道二教的产物,是佛道二教观念教义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尽管前者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表现对象,后者以虚幻的神鬼为描写对象,但是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都是文化转型的结果。
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的情况来看,汉代小说以方术神仙为主要内容,是方士自神其术的宣传品。但是,由于儒家经学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它受到轻视,不仅数量极少且大都已经亡佚。诚如班固所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41]它不过是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它的作者是“闾里小知者”、“刍荛狂夫”一类下层人物,它的功用最多不过“一言可采”。这种小说观是正统文学观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小说的发展。
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并未被这一小说观捆住手脚。他们热衷于模仿《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内传》、《汉武帝故事》、《汉武洞冥记》等典籍,倾心于搜神志怪、叙谈因果、议论冥祥,如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颜之推《还冤志》、王琰《冥祥记》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从文化这一角度考察,就在于佛道二教对主流文化——儒家学说的冲击与背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极其猛烈的程度。从上层统治者到文人士大夫,再到下层民众,笃信佛道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出现大量志怪之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志怪小说的创作主旨与佛道二教密切相关。《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关于其创作主旨,作者干宝自称为“明神道之不诬”。[42]《晋书·干宝传》叙述更为详尽:“干宝字令升,……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43]可见干宝是一位笃信神仙术数等道教观念的文士,他撰写《搜神记》,实质上就是为了宣扬道教。再如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还冤志》等,则全是“释氏辅教之书”。其创作主旨乃在于有意识地宣传佛教,而这些小说的作者也无一例外的都是佛教信徒。史称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44]王琰自谓“稚年在交阯。彼土有贤法师者,道德僧也。见授五戒,以观世音金像一躯,见与供养;……琰奉以还都。……寄京师南涧寺中。……琰昼寝,梦见立于座隅,意甚异之。时日已暮,即驰迎还”。[45]《四库全书总目·还冤志》称:“自梁武以后,佛教弥昌,士大夫率皈礼能仁,盛谈因果。之推《家训》有《归心篇》,于罪福尤为笃信,故此书所述,皆释家报应之说。”[46]当然,也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刘敬叔的《异苑》,兼容佛道二教。其创作主旨虽不如上述小说佛道分明,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宣扬佛道,在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区别。
其次,从内容上考察,志怪小说乃是佛道二教教义观念的具体化、形象化与通俗化。它们所宣扬的佛道观念教义,往往并不那么系统严谨,而带有粗俗化、片面化的倾向。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土,至魏晋时期达到高潮。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因为在思想上与魏晋玄学有相似之处,所以迎合了上层社会的需要,偏重于对佛教义理的探讨,但佛教并未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之后,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著名僧人慧远大力倡导因果报应之说,作《明报应论》、《三报论》,认为众生在未达到“神界”之前,总是循着“十二缘起”说所指的因果链条,处在生死流转、累劫轮回的痛苦之中。生死祸福、富贵贫贱都是报应。报应又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今生之报是前世作业的结果。①东晋·慧远:《明报应论》、《三报论》,见《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100页。这种伦理化的教义最易为人所接受,因此,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教义几乎全部集中于报应灵验之上。至于其他高深的义理,志怪小说中就很少涉及了。这是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
与佛教不同,道教本身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渊源“杂而多端”。从古代的宗教观念、巫祝文化到神仙信仰、方术方士,从汉初的黄老思想到谶纬神学,道教无不吸收继承。东汉时期,道教仅在民间传播。至晋代而迅速发展。晋武帝时葛洪著《抱朴子》、《神仙传》、《隐逸传》等书,其《抱朴子·内篇》反复论述服药求仙必成,仙人必有。书中援引历代神仙故事以及仙经所记载的说法作为立论的依据,夸大药物和道术的作用,认为服药能令人长生不死、道术能令人飞升。南朝齐梁间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把神仙分成许多等级,“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47]除神仙信仰外,道教还宣扬鬼怪变化、禳邪却祸的法术。因此,道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就显得芜杂零乱。如《搜神记》卷一至卷三记述了神农、赤松子、彭祖、葛玄等道教崇奉的神仙或教主;卷六至卷十记述了妖祥卜梦等与谶纬神学相关的事物;卷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十九记述了物怪变化等与鬼神崇拜相关的事物;卷十五、十六记述了鬼事及还魂事等与佛教有联系的现象。其间还有一些采自民间传说。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搜神记》“只是搜罗一些神怪故事,至于这些故事反映了哪种人的思想,作者往往不加区别”。[48]作者干宝反映的是道教观念,这是非常明确的。只是因为道教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集合体,所以才使《搜神记》也异常庞杂起来。
至于《搜神记》还表现了佛教的轮回说,其实也很好解释。北魏时著名道士寇谦之就采纳了佛教轮回报应说,他借太上老君的口气说道:“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又说:“死入地狱,若轮转精魂虫畜猪羊而生,偿罪难毕。”[49]道士陶弘景也采取了佛教这一观念。同样,佛教教义中也吸取了道教长生神仙思想,如南岳僧人慧思在《立誓愿文》中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借外丹力修内丹。”[50]佛道二教观念的相互采用沟通,对志怪小说当然也有影响。上举刘敬叔《异苑》便是一例。
再次,从艺术表现来看,志怪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当然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事。但是其作者却要力证这些故事的真实可靠。干宝发誓说他的《搜神记》“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滂”。[42]王琰在《冥祥记》中则编造出“某些方面符合于一定的史实或生活的本来面貌”[48]的故事,以取信于人。这样一来,作者便力求使故事具体、生动,从而在艺术技巧上下了不少工夫。如《搜神记》卷十六所记卢充与崔少府之女冥婚事,墓中结合却在阳世重逢,并且“同坐皆见”。崔玉赠卢充金碗,被崔氏姨母得知,遂将卢充与小女儿接至家中。“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后来,“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51]卢植即为现实中人,《后汉书》有《卢植传》可证。这类故事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已具有较为显明的小说艺术特征。
鲁迅先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52]然而他又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0]39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还不是小说的自觉时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以为主要还是在于小说尚未与玄学和佛道二教彻底分离。玄学、佛教、道教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来,但这时期的小说毕竟具备了小说艺术的雏形,为后世小说创作的发展成熟,铺就了一层不可或缺的台阶。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2]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24.
[3]郭沫若.卜辞通纂·天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364-366.
[4]山海经·海内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5]山海经·大荒南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353.
[6]山海经·海外东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285.
[7][汉]刘 安.淮南子·本经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26.
[8][宋]李 昉,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48.
[9][汉]刘 安.淮南子·览冥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99.
[10]礼记·月令[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736.
[11][汉]刘 安.淮南子·时则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84.
[12][汉]宋 衷,著[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帝系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8:3.
[13][汉]刘 安.淮南子·修务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92.
[14]国语·周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6-27.
[15]左传·僖公十六年[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093.
[16]左传·襄公二十三年[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360.
[17]左传·昭公三十二年[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62.
[18]左传·庄公四年[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020.
[19]左传·昭公十八年[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03.
[20]论语·阳货[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2088.
[21]田昌五.孔子的天道观[M]//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2:521.
[22]论语·雍也[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2019.
[23]论语·先进[M].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2046.
[24][宋]罗 泌.路史·蚩尤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1-22.
[25]山海经·大荒北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385.
[26][汉]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
[27][汉]东方朔.神异经[M]//说库.扬州:广陵书社,2008:17.
[28]山海经·大荒西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358.
[29]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33.
[3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906.
[31][魏]嵇 康.与山巨源绝交书[M]//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1322.
[32][魏]嵇 康.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M]//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1337.
[33][魏]阮 籍.阮籍集·大人先生传[M]//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1316.
[3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901.
[35][晋]应 詹.陈便宜疏[M]//全晋文:卷三十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4.
[36][晋]干 宝.晋纪总论[M]//全晋文:卷一二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68.
[37][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94.
[38][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略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5.
[39][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0:609.
[40][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1][汉]班 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77-1378.
[42][晋]干宝.搜神记序[M]//全晋文:卷三十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70.
[4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33.
[44][梁]沈 约.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974.
[45][晋]王 琰.冥祥记自序[M]//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276.
[46][清]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小说家类[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1208-1209.
[47][南朝梁]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M]//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2.
[48]曹道衡.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J].文学遗产,1992(1):26.
[49][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M]//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16.
[50][南朝陈]慧 思.立誓愿文[M]//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六.台北:佛佗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791.
[51][晋]干 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3-205.
[52]鲁 迅.而已集·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