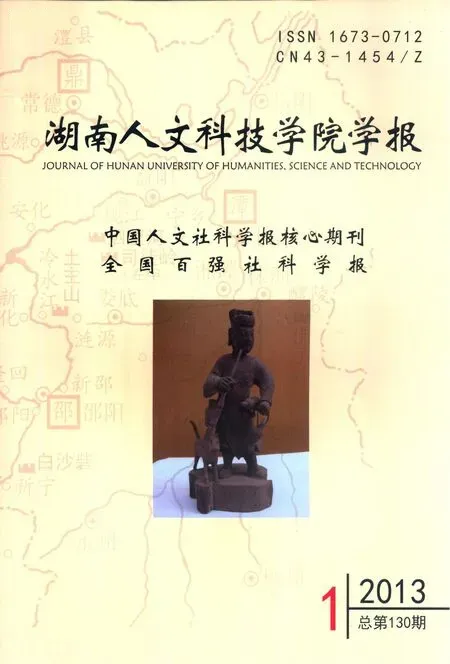冲突与选择——再评娜拉
涂兰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系,湖北咸宁437100)
1879年,易卜生在罗马和意大利名镇阿马尔菲写成三幕剧《玩偶之家》,随着娜拉形象的诞生,妇女的觉醒以及“妇女往何处去”的问题震憾人心。《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介绍始于五四前夕,由于契合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娜拉”成为一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代名词。然而,娜拉的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贴上了某种意义标签的符号,对于易卜生和他笔下这一不朽的文学典型,我们永远都无法给以单一角度的简单评价。
有人将娜拉的出走看作一次性格发展的突变,认为之前的娜拉千依百顺,最后却果断坚决,这是她固有性格的不合逻辑的发展,别扭而生硬。挪威评论空艾尔瑟·赫斯特就曾说:“它们只不过是一座已经完工的纪念碑的碍事的支架,……并将永远时时刻刻妨碍我们单纯地体会娜拉的情感。”[1]也有人认为,娜拉是将屈辱消融在爱与梦中的典型。无论是突变论还是渐变论,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变”。在这里,笔者则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娜拉的性格发展,将“变化的娜拉”视为“选择的娜拉”再评这一经典人物形象。
一 选择的娜拉:主动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选择的娜拉”是相对于娜拉的整个生活而言的。“选择”的意义在于它的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将娜拉由一个被动接受生活的弱小女子转而成放置在一个主动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位置上。这并非笔者企图另辟佳径的随意图解,传统阐释学原理告诉我们,要对作品进行准确的阐释,关键在于对文本作准确而深入的解读。说明娜拉性格内涵的最好依据还是她自己的言行。
剧情发生在克里斯替阿尼遏的托伐·海尔茂家里。娜拉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女主人,拥有一个事业有成爱她的丈夫,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还有些诸如爱吃甜杏仁饼干之类的小嗜好,被丈夫亲昵地称为“小松鼠儿”、“小鸟儿”。圣诞前夜,这位年轻漂亮的少妇正忙着作节日前的准备工作。她的生活似乎是无忧无虑温馨快乐的,连她的亲密女友林丹太太也忍不住这样评价:“娜拉,你心肠真好,这么热心帮忙!像你这么个没经历过什么艰苦的人真是尤其难得。”“你只懂得做点轻巧活计一类的事情,你还是个小孩子。”却引起了女主人公的激烈争辩。
娜拉 我?我没经历过——?
……
娜拉 (把头一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喔,你别摆出老前辈的架子来!
林丹太太 是吗?
娜拉 你跟他们都一样。你们都觉得我这人不会做正经事——
林丹太太 嗯,嗯——
娜拉 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2]20
的确,娜拉有烦恼,甚至在生活的艰难中她独立支撑了一切:她和海尔茂结婚八年,并非过着奢华的生活。在丈夫病重,父亲垂危,家庭经济又很拮据的情况下,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又不惊扰父亲,她瞒着家偷偷伪造父亲的签名借了一大笔疗养费。丈夫病好了,娜拉却长期独立承担着沉重的负担,俭省家用,熬夜工作,东拼西凑来还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剧情开始的时候。可见,娜拉绝非不经世事。对于幸福,她有着不同一般的感受和抉择。就像她认为林丹太太供养母亲、帮助弟弟多年是值得骄傲的那样,她对自己暗中救过海尔茂一命的事实也是万分得意的。她说:“有时候,我实在觉得累得不得了。可是能这么做事挣钱,心里很痛快,我几乎觉得自己像一个男人。”[2]26
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呢?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娜拉在家庭中玩偶的地位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这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从娜拉和海尔茂关系的定位上,的确,海尔茂将娜拉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无论严辞训斥,还是软语欺哄,目的都是为了从经济上、生活上,乃至思想上严格控制娜拉。就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2]122然而海尔茂自以为控制着一切,却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更是一点也不了解娜拉。
反观娜拉的行为,她的孩子气里却带着理性的目的。娜拉对自己的地位的认识比海尔茂要清醒得多。早在第一幕,娜拉就向林丹太太解释:“像托伐那么个好胜、要面子的男子汉,要是知道受了我的恩惠,那得多惭愧,多难受呀!我们俩的感情就会冷淡,我们的美满快乐家庭就会改样子。”[2]25为了隐瞒冒名借债的真相,她故意装出一副傻兮兮的样子讨好海尔茂。并且,在处理与海尔茂的关系上,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并利用了自己的谦虚和显得无知无助使海尔茂非常受用。可见,娜拉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理智的人,相比之下,海尔茂却显得无知得多。
二 俄底浦斯情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娜拉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甚至是她的主动迎合海尔茂最终造成了眼下的局面。问题在于,当她受到科洛克斯泰的威胁时,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说出真相,让海尔茂实践他保护娜拉的诺言?如果说这一点是基于娜拉对海尔茂的理性认识的话,那么她又为什么一直既拖延着又渴望着矛盾爆发那一刻,而最后才毅然选择了放弃?
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阿斯特里德·萨瑟曾借用查斯盖特·斯莫格尔关于女性内疚情结理论分析过《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这种精神分析的方法也为本文讨论的问题提供了视角。查斯盖特·斯莫格尔声称,俄底浦斯情结并不为男性所专有。“男性性征崇拜”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欲望的象征性表达——女性不是想成为男性,而是想通过成一名独立自主的女人以摆脱母亲。俄底浦斯式冲突如果要解决,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果这一矛盾消除了以致女儿重新主动认同母亲,那么她将发现自己已安全度过了这一关;如果女性继续将父亲理想化,而没有认可母亲,那么“父亲”就已经被内化了(这就是“超我”或负疚情结)。
《玩偶之家》中,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正是纠结在这样的俄底浦斯情结中。对娜拉而言,海尔茂是她理想中的“父亲”,在她的生活中,娜拉始终不能放弃对这个形象的幻想。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娜拉同时对海尔茂有着理性的深刻了解,于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娜拉性格中挥之不去的矛盾,理想促使她留恋、拖延,而理性则告诉应当面对现实,做出选择。
由此当我们重新审视作品的前面一部分便会发现,娜拉的无邪天真以及缺乏自我意识的确增强了海尔茂的兴趣,并强化了他的权威地位。但是站在娜拉的立场,这是她内心的挣扎妥协的结果。她对于海尔茂的幻想压倒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选择了在自我欺骗中逃避,而她那不时冒出来的理智又使得她的这种逃避以夸张的,似乎完全丧失自我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意识的主动压制。可以说,娜拉始终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撕扯着自己。
娜拉的这种情绪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她对于“奇迹”即将发生的预感、渴望和恐惧。为此她表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言谈举止:
娜拉 喔,你怎么会明白?那是桩还没发生的奇迹。
林丹太太 奇迹?
娜拉 不错,是个奇迹,克立斯替纳,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别让它发生。
……
林丹太太他明天晚上就回来。我给他留了个字条儿。
娜拉 其实你不该管这件事。应该让它自然发展。再说,等着奇迹发生也很有意思。[2]93-94
所谓“奇迹”实际上是娜拉一个美丽而悲壮的梦想:柯洛克斯泰终于把揭发信放进信箱了,它将对丈夫刚刚显出光明的前途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以娜拉对海尔茂的了解,她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但却宁愿相信海尔茂的表白:“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为了她,海尔茂是肯舍弃一切的。而她只要亲眼看到这种“奇迹”发生,就会在极大的幸福中无怨无悔地以死来为自己和丈夫赎清一切罪孽。剧中,她几近疯狂地跳起了特兰特拉土风舞。传说中,这种舞蹈与毒蜘蛛的叮咬有关,它或是用来治毒,或是毒发后的结果。这正是娜拉此时理想与内心的恐惧汇聚达到的高潮。
然而,“奇迹”终于还是没有发生。在破灭的理想中,娜拉终于坦然面对了现实,正视了自己,也因此冲破了俄底浦斯情结的影响。放弃现有的一切离家出走则是剧情合理发展的结果。
可见,冲突与选择构成了娜拉的性格发展过程,并最终决定了她的生活道路。尽管有女权主义者认为,娜拉关于出走的宣布,简直就是一篇“妇女独立宣言”,然而1888年,易卜生在挪威妇女权利同盟的一次宴会发言中却指出:“我不是妇女权利同盟的成员。我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毫无有意搞宣传的想法。”“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人的运动。”娜拉这一人物形象的创作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最后娜拉选择了离家出走的道路或多或少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这也是符合易卜生一贯的创作思想的。娜拉的选择同样体现了易卜生主义“全有或全无”的生活原则:要么拥有完美的家庭,要么弃绝它。娜拉毕竟是易卜生创作的人物链条上和谐的一环。
[1]艾尔瑟·赫斯特.娜拉[M]//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21-322.
[2]易卜生.玩偶之家[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