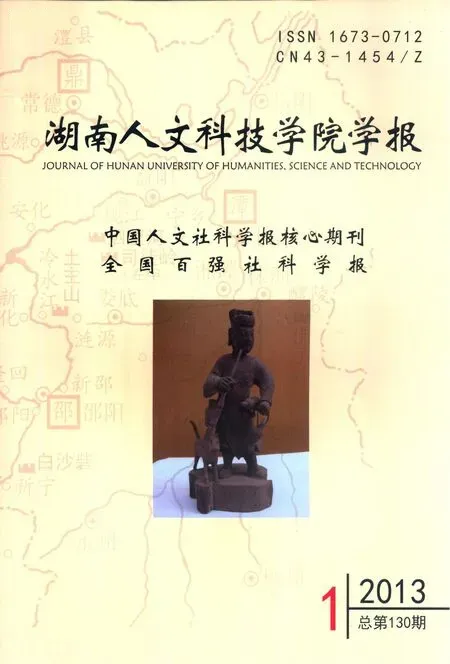唐代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
段祖青,罗佳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越南古称“交趾”,是一个与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关系的民族和国度,其先祖雒越人是公元前4世纪中国境内楚国灭亡越国后南迁到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据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载,雒越人的祖先乃“神农氏之后”。又据伏胜《尚书大全》载,神农与帝尧治天下时,其管辖“南至交趾”。秦朝统一六国,置象郡,将交趾纳入中国版图,历两汉、三国、两晋直至隋唐,均隶属中国封建王朝统辖之下。尤其到了唐代,中央政府除了在政治上更为加强了其管辖权如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安南”一词始见于文献)外,唐朝与安南各民族的关系,可以说已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作为唐代文化辉煌之表征的唐代诗人诗作,更是成为了把两地联结起来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载体,这种载体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唐代寓越诗人对于安南之社会、自然与人的艺术反映,我们姑且称之为“安南书写”。“安南书写”的主体是被唐王朝诏贬至此的朝廷命官或地方政府官吏,其使命之一是执掌安南作为唐王朝之隶属地的政治权力,体现出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客体(对象)则是安南地方的社会状况、自然面貌、人类生活内容,目的在于昭示两个地方在这几个方面的同异或影响路径。综合此主客体方面观之,“安南书写”是一种政治与非政治的反映。这里我们以唐代寓越诗人杜审言、沈佺期、裴夷直、高骈、许浑、项斯、于濆、裴泰、马聪为典型个案来揭示“安南书写”的内涵与价值。
一
构成安南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安南节候物貌的真实反映,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诗歌书写对于异地异物之艺术再现的深刻影响。
中国的律诗是在初唐定型和成熟起来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是杜审言和沈佺期(以及宋之问)。很巧的是,这两位成就卓越的诗人都曾贬寓安南。据《新唐书》卷201《杜审言传》载:“中宗神龙初(705年),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峰州即今越南永富省。检《全唐诗》所编杜审言诗一卷来看,写于贬途之中、到达贬所以及遇赦回归中所作诗共4首。其中《旅寓安南》是典型的安南书写之作,细致地描写了安南地方的物候气象,该诗云: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踰万里,客思倍从来。
交趾(安南)地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气温高暖炎热。因此花草茂盛,时蔬瓜果常生,少见华夏中原大地之仲冬寒冷。《旅寓安南》把诗人亲身所历、亲眼所见的南国物候和出产叙述得清晰明白,从五言律诗的结构形式来看,首联总叙安南风候殊于华夏,颔联、颈联详写物候与物产,尾联以殊方异俗勾起思乡之情收束全诗。这种对于安南的自然物候书写,在沈佺期笔下亦有浓重的表现。
沈佺期与宋之问齐名,执初唐诗坛之牛耳。武则天执政期间,沈佺期累官迁给事中、考功,长安四年春,坐考功任上受贿事被弹劾,入狱。中宗神龙元年(705),由于交通二张,“会张易之败,逐流驩州”,景龙元年(707)遇赦北归。沈佺期流放安南(驩州)的两三年中,作诗20余首,对于越南的风土民情、地形物候进行了真实而浪漫的艺术书写,如果把他贬越途中、寓越期间和北归路上所有关于越南事物的诗歌题材统计起来,则安南书写的诗歌共有22首,是唐代诗人中留下安南书写作品最多的一个,而其中直面书写安南物候物产等题材的诗则有《度安海入龙编》、《初达驩州两首》、《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答魑魅代书寄家人》、《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从崇山向越常》、《题椰子树》、《夜泊越州逢北使》等10余首。《度安海入龙编》云:
我来交趾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氓在,鱼盐旧产传。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别离频破月,容鬓骤催年。昆弟推由命,妻孥割付缘。梦来魂尚扰,愁委疾空缠。虚道崩城泪,明心不应天。
该诗作于神龙元年(705年)诗人贬交趾初到龙编县(今越南河内东北)时。诗歌所写安南气候炎热少寒冷,日月星辰偏处南方,是故温热多暑。由于交趾靠海,海滩狭长,多产鱼盐,又多野雉猛禽,故《后汉书·南蛮传》云:“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1]2835又《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云)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落水中。”[1]838综合全诗来看,诗人对于越南气候、物产的诗性书写,勾勒了越南人民古老而依天靠地的生存环境,实有重要的史料意义,让后人看到古老的越南人民在怎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顽强不屈地繁衍生息的图景。
由于交趾地处偏南之地,除了如上所述气候炎热酷暑难当的节候被书写于诗中,另一个险恶的气候现象便是瘴气熏人,毒癘时刻危及人类生命。这种气候和地理环境,诗人在《初达驩州两首》之二中称为鬼门:“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这种恶劣环境早晚旦夕、一年四季都不曾间歇:“炎蒸连晓夕,瘴癘满冬秋。”实为不宜久留之地:“西水何时贷,南方讵可留?”气候的极端现象也使动植物的生死存亡显得特别怪异,故《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云:“炎方谁谓广,地尽觉天低。百卉杂殊怪,昆虫理顿睽。闲藏元不蛰,摇落反生荑。虐瘴因兹苦,穷愁益复迷。火云蒸毒雾,汤雨濯阴霓。……山空闻斗象,江静见游犀。”该诗是诗人对于越南之气候、物产、生命现象的全面综合书写,是所有唐代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中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从物产方面来书写,安南地区除了上述陆生动植物外,在植物世界中,最富热带亚热带气候特征的便是椰树了。对此,沈佺期有专作的《题椰子树》,该诗云:
日南椰子树,杳袅出风尘。丛生雕木首,圆实槟椰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途林果,移根随汉臣。
椰树属典型的热带作物,外形婀娜多姿,果状圆实润泽,四时枝繁叶茂,是安南难得一见的美丽风景。这种极富诗情画意的安南书写,也给远谪他乡的游子骚客平添几分快慰,暂以慰藉那思乡的忧苦抑郁之情,所以尽管诗末两句稍有对椰果比不上石榴的微词,但那也只是一种美中不足的喟叹。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现对椰树果实的赞赏之情,诗人有意在作品中引用关于椰果的神奇传说,使这种客观书写又蒙上几许浪漫美丽的色调,让读者如痴如醉。据《南方草木状》卷下载:“(椰树)其实如寒瓜。外有粗皮,次有壳,圆而且坚。……俗谓之越王头,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同卷又云:“槟椰树高余丈,皮似青桐,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对比诗人的诗性书写和草木之信实的记载,自然是前者更引人入胜,充满艺术的智慧和光辉。
对于安南地区的气候物产等的书写,除了上述杜、沈的神来之笔外,唐代寓越诗人中诸如高骈、裴夷直、许浑、项斯、于濆、马戴等亦有出色的描写。如高骈,他曾被懿宗派往安南供职,期间有多首关于安南书写的诗歌,如《叹征人》、《赴安南都寄台司》、《过天威径》、《安南送曹别赦归朝》、《南征叙怀》等。如《过天威径》云:
豺豹坑尽却朝天,战马休嘶瘴岭烟。归路崄巇今坦荡,一条千里直如弦。
安南气候多瘴癘,山路多崎岖,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裴夷直也是寓越诗人,武宗即位出刺杭州,后斥驩州司户参军,在安南任上,作有《发交州日留题解炼师房》、《南诏朱藤杖》、《崇山郡》、《江上见月怀古》等诗歌。如《崇山郡》写越南的险恶环境云:
地尽炎荒瘴海头,圣朝今又放驩兜。交州已在南天外,更过交州四五州。
交州荒凉炎热,而所去之崇山郡更离交州遥远,“已在南天外”,则其酷热瘴癘可以想见。
许浑作为寓越诗人,“会昌中,以监察御史为岭南从事”,虽然没有信史记载他流放、贬谪,或任职安南,但从他为数不多的诗作中可推知他到过安南,如《南海府罢京口经大庚岭赠张明府》、《送黄隐居归南海》、《登尉佗楼》、《南海使院对菊怀丁卯别墅》等10余诗作都涉及越南之地之人。其安南书写之作在数量上仅次于沈佺期,在内容上也多写安南节候物象等,如《送黄隐居归南海》:
瘴雾南边久寄家,海中来往信流槎。林藏弗多残笋,树过猩猩少落花。深洞有云龙蜕骨,半岩无草象生牙。知君爱宿层峰顶,坐到三更见日华。
又如《登尉佗楼》的尾联云:“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合此两诗观之,一者书写他所熟悉的安南风物,二者明确写到“越人”,以此推知他曾寄寓安南应无问题。
此外,项斯的《蛮家》、《寄流八》,于濆的《南越谣》,马戴所作与项斯同题的《蛮家》以及《赠越客》、《送从叔赴南海幕》等均有关于安南节候物貌的书写,从中亦可推知他们为寓越诗人。
此外,从各种书籍和文学作品的记载来看,还有两种情况可以证明唐代诗人与越南人民的交往,一种情况是史籍所载贬谪安南却没有作安南书写之诗传世者,如裴泰、马聪等,但却有其他名望高贵的诗人为他们作赠别之诗,如权德舆作《送安南裴(泰)都护》,韩愈作《赠刑部马侍郎(聪)时副晋公东征》。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无法知晓其姓名的诗人远寓安南,但有著名诗人文豪为他们作赠别之诗,如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李郢《送友人之岭南》等等。这两者也是一种间接的或侧面的“安南书写”,限于篇幅,不作多究。
二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因,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性、生活习惯和心理信仰;同时,相邻国家或民族之间由于交往的频繁、彼此接触的深入,因而彼此融入对方的生活风格、民俗风情。对这些人文景象的诗性描写,也成为唐代寓越诗人安南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以沈佺期和许浑为突出代表。
交趾之南有一个古老的国度,据说名贯胸,《山海经·海外南经》云:“贯胸国在其东,其为人胸有窍。”又《淮南子·坠形》云:“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穿胸民。”高诱注:“穿胸,胸前穿孔达背后。”可见这个国家的生民有一种穿胸洞背的习俗,受其影响,交趾(越南)居民也贯胸。沈佺期贬寓安南,亲眼所睹,故书之于诗,《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云:“遇坎即乘流,西南到火洲。鬼门因苦夜,瘴浦不宜秋。岁贷胸穿老,朝飞鼻饮头。……适越心当是,居夷迹可求。”写驩州的民俗,居民穿胸鼻饮的独特风格。据《后汉书·杜笃传》注引《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又《新唐书·南蛮传下》:“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此见风俗之异殊。
战国时期的楚国南方边远地区的居民有雕题(额上刻绘花纹)的习俗。屈原《招魂》云:“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屈原在这里只笼统地说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当沈佺期远寓安南,亲眼看到了越南居民雕题的习俗时,便立刻写之于诗。其《初达驩州两首》其二云:“流子一十八,命予偏不偶。远配天遂穷,到迟日最后。水行儋耳国,陆行雕题薮。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雕题之俗,这里显然指安南各民族的习俗,《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交趾与雕题,其意可解。又沈佺期于神龙二年写有《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再次书写安南民族雕题的习俗,该诗云:“家住东京里,身投南海西……火云蒸毒雾,汤雨濯阴霓。周乘安交趾,王恭辑画题。”诗借东晋王恭安抚岭南雕题百姓的故实表达诗人渴望治理安南民众的情感。又神龙二年沈佺期在驩州再作《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其中有云:“涨海缘真腊,崇山压古棠。雕题飞栋宇,儋耳间衣裳。”沈佺期类似的书写之诗还有不少。这些对当地人们安居乐业的风俗习俗的真实反映,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安南人民的历史风貌、生活情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中原传统节日,随着唐代寓越诗人的到来,也被两个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幸福而愉快地享受着。诸如相传缘自春秋时代介之推故事的寒食节,于东晋以降极为风靡盛旺的上巳节,都在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中屡见不鲜。仍以沈佺期诗为例,可知这些节日在安南的情景。其《岭表寒食》云:
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飭。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争朝发,轩车满路迎。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
寒食节尽管含有几分纪念意味,心情略显严肃,但百花争艳,柳色翻新,轩车满路,人头攒动,踏青赏春,自然欢洽愉快,使诗人掩饰不住感物而发的惬意与爽朗。
上巳节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一般为旧历三月三日。这一天,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士子文人,成群结队,郊游于曲水回流,祓禊宴饮,怡然自乐,如兰亭集宴,古今佳话,久传不绝。沈佺期《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云:
两京多节物,三日最遨游。丽日风徐卷,香尘雨暂收。红桃初下地,绿柳半垂沟。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鞲。禊堂通汉苑,解席绕秦楼。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无亭不驻马,何浦不横舟。
身处流放之地,虽然有一种莫名凄苦的孤独之感,但当传统的上巳佳节来临,忆起往昔春风徐来、丽日温熙、红桃绿柳,众人捧觞祓禊,流水浮盏漂逥,其乐融融,顿时一切失意全无。中原传统佳节被诗人带到安南,一者以文化审美之内涵熏染异城他乡,是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方式;二者通过回忆过去的美好以慰藉此时因贬谪而受伤失意的心灵。因此,诗人笔下的这种间接的安南书写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意蕴。
唐代是佛教在中土传播和被信仰得极为昌盛的时代。大批诗人放逐安南,他们也带去了深邃的佛教文化。同时,佛教也被许多安南本土的士子文人所接受,他们除了接受来自于唐代寓越诗人的传播,还通过其他途径主动接受佛教的影响,如通过那些来到大唐帝国出访、留学、为官、经商以及从事其他生活的人们耳濡目染佛教的教化。所有这些内容,亦构成寓越诗人安南书写的另一个方面——越南人民的宗教信仰。在这里,本文拟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当时,安南地区佛教庙寺极多,从寓越诗人的作品中记载的著名佛寺主要有静居寺、绍隆寺、法云寺、建初寺等等,书写佛教文化、佛教信仰最多的寓越诗人主要有沈佺期和项斯。
沈佺期本人就是一个虔诚信佛的文人,曾参与武则天策划组织的由张昌宗领衔修撰的包罗儒、释、道三教的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辑工作,对佛理、教义极其精通。因此,他寓贬安南,就广寻佛寺,拜谒佛僧,与他们广为交往、深究佛理,其《九真山静居寺谒无碍丈人》云: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烦恼,山上即伽蓝。小涧香为刹,危峰石作龛。候禅青鸽乳,窥讲白猿参。藤爱云门壁,花怜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挂浴衣堪。弟子哀无识,医王惜未谈。机疑闻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缘理,聊宽放弃惭。超然虎溪夕,双树下虚岚。
该诗宣讲佛法,一切皆由佛法前定,鸽、猿都无法逃脱此佛法,又因缘皆为万象之因果条件,而不二法门则是一种认佛理为至理、无须费口费舌的“不言之教”,以上这些佛教理论,是九真山静居寺(故址在今越南清化北)无碍丈人主修的重要内容。诗人拜谒他,在交谈会通之中,获得此一理解,反映了当时安南境内佛教传播的情况和佛教的思想内涵。
沈佺期还有一首《绍隆寺并序》:
绍隆寺,江岭最奇,去驩州城二十五里,将北客毕日游憩,随例施香回,于舟中作。
吾从释伽久,无上师涅槃。探道三十载,得道天南端。非胜适殊方,起谊世归难。放弃乃良缘,世虑不曾干。香界萦北渚,花龛隐南峦。危昂阶下石,演漾窗中澜。云盖看木秀,天空见藤盘。处俗勤宴坐,居贫业行坛。试将有漏躯,聊作无生观。了然究诸品,弥觉静者安。
该诗描写诗人去绍隆寺所感,宣讲了佛教中的涅槃、禅静,强调无我空灭的境界,是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一脉在安南传播的例子。中国禅宗传入越南,是在6世纪末。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596)于南朝陈宣帝太建六年(574年)到达今越南河东省法云寺,创建“灭喜”禅派,宣讲禅理。而随着唐帝国建立以后中国禅宗的昌盛,寓越文人或官吏更把禅理传播到安南,使本已在安南初具禅派的佛教信仰更为深厚。沈佺期写此诗约为唐中宗神龙三年春(707年),禅宗经过了100多年在安南的流传,其禅理禅法已经很成熟,故诗中所云“试将有漏身,聊作无生观”,是要求人生试观无生之理以破世俗之烦,因为万物实体是无生无灭的,要达到“无我”与“空”的境界,这便是禅宗的“参悟”、“参禅”。这首诗所书写的安南佛教情景,无疑表现了唐代的中国佛教禅宗对于越南宗教流播和宣传情况之影响,是安南书写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
项斯在流寓越南期间也广与僧院佛徒交往,一方面主动去寺庙和僧人参禅论佛,一方面写作大量赠别僧人的诗歌作品抒发彼此之间的深厚交谊。他在《哭南流人》中说:
遥见南来使,江头哭问君。临终时有雪,旅葬处无云。官库收空剑,蛮僧共起坟。知名人尚少,谁为录遗文。
从诗中可知,项斯在寓居安南期间,偶尔际遇被安南国派往唐廷去的僧人,一见如故,作品倾吐的正是那种喜出望外的惊讶以及见时短别时长、相见难别亦难的难分难舍之情。
项斯的另一首《送越僧元端》云:
静中无伴僧,今亦独随缘。昨夜离空室,焚香净去船。
这里的越僧元端,无疑属于中国禅宗一派的高僧,与前述沈佺期所写绍隆寺之僧无异。
沈佺期、项斯诗歌对于安南佛教禅宗的书写,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关系、文化关系的旨趣所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诗性与人的心理情性、宗教情性之间天然无隙的逻辑关系,这是唐代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