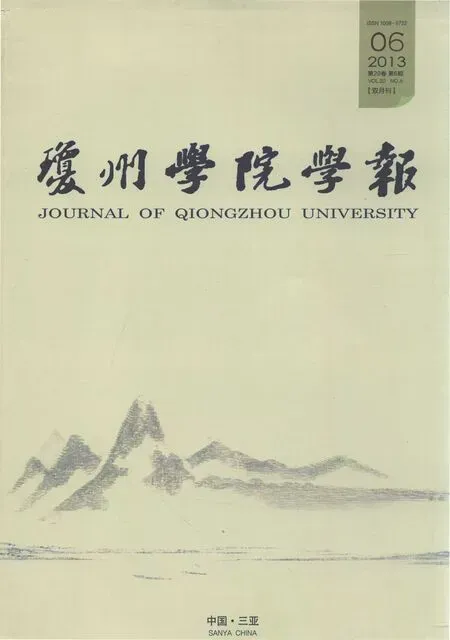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一、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及其纲要
东盟作为协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967年,其最初的成员国有五个,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与菲律宾,经过四十多年的演变发展,东盟的成员国发展到10个。东盟不仅被看作是开创了独特的东盟方式来解决区域内国家间争端、保障该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繁荣的地区主义的榜样,同时,东盟也开创了更具活力的实践,逐渐带动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区域外的大国加入以东盟为主体的地区性论坛来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
东盟自成立以来,建立了一系列的规范原则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并巩固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东盟规范与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范与原则;区域自治和集体自主的规范与原则;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抵制东盟军事协定及偏好双边防务合作的规范与原则。[1]东盟处理成员国关系的规范与原则,不仅被《东盟宪章》奉为法律,而且也被外界称赞为处理国家争端与区域问题的“东盟方式”。显然,这些规范与原则已经被经常用来处理东盟成员国关系与地区问题,以保障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政治与安全组织的顺利运行。然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并不单是局限于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合作,而且还包含经济合作与社会文化的合作。2003年10月9日,第9次东盟峰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发表了《巴厘第二协约宣言》,该宣言文件包括“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正式将东盟的社会文化合作统合到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当中。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13届峰会上,东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制定“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纲要,以确保采取具体措施推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宗旨是通过打造共同的社会文化认同,促进区域内人民生活与福利发展,建立一个充满关爱、分享、包容与和谐的社会。它强调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发展观念来促进东盟国家及其人民的团结,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促进人的发展;保障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正义与人权;保障环境持续发展;建构东盟认同;缩小发展差距。[2]应该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规划与远景是东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纲要中,强调建立以人的发展和人权保护的规范原则成为一个根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了东盟的关注。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东盟从1994年开始着手建立“政府间人权委员会”(ICHR),而且2009年7月召开的第42届东盟外长会议已经接受了该委员会提出的参考条款。在2009年10月泰国举办的第15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差安—华欣宣言”,宣告东盟成立四十年来首个人权组织——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正式成立。虽然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宣称其职责主要在于推动人权保护,将其角色定位为东盟秘书处与各成员国的咨询组织,而不是具备执行权的独立机构,但该组织的成立仍然标志着东盟在建立地区人权机制的进程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高度赞扬了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成立的意义,称赞它是推动与贯彻新《东盟宪章》文件与精神的重要步骤,为东盟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与人权保护铺设了道路。[3]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建立,不仅反映了东盟向更高层次、更全面整合的区域组织发展的趋势,而且也反映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发展及其对东盟的影响。亚太地区正在扩大的多边论坛正在逐步将东盟与东盟区域外的其它大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东盟区域外的国家也逐渐利用多边机制来敦促一些东盟成员国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改革国内治理方式。[4]这表明东盟在扩大的地区主义与实施多边外交的背景下,正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不断增长的压力,尤其要求东盟在政治民主化与人权保护方面建立统一的规范原则。由此可见,寻求规范一致性不仅是正在成长中的东盟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也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更应该看到,中国作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对话国与战略伙伴国,除了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深化经济合作来推动双边关系外,必须更多地思考如何与东盟在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合作上寻求共识,以有利于全面、稳固、深层次地推动中国-东盟关系。
二、东盟社会文化认同与规范建设:一个多视角的考察
东盟作为一个包含十个成员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国土面积、民族构成、社会文化遗产与认同、殖民地历史、后殖民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种文化与社会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无疑使社会文化认同与规范一致性的建构成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立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如何在一个充满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内基本达成观念与规范的一致,不仅是维护东盟各国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东盟共同体发展的重要保障。东盟作为十个成员国的地区组织,虽然尚没有建立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认同的全面的社会文化规范与原则,但一些东盟重要成员国的社会与文化原则在引导建立东盟社会文化认同标准与原则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印度尼西亚的潘査西拉原则所包含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菲律宾麦格赛赛奖倡导的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利他主义与公益精神以及当代马来西亚“文明伊斯兰”运动所蕴含的文化现代化观念,虽然带有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烙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东盟国家在社会文化认同与原则上达成的共识与发展趋势。
首先,作为包含极端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东盟地区,应将提倡不同文化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与尊重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原则。印尼作为东盟的发起者与重要成员国,一直将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潘查西拉作为现代印尼的政治原则与社会文化准则。作为立国基础的潘查西拉原则,其包含的神道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等思想,不仅体现了印尼多元宗教文化的精神,而且也蕴含了西方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正如当代印尼著名的作家与启蒙思想家S.Takdir Alisjahbana所言:“潘查西拉原则有效地整合了当代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运动”。[5]132虽然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印尼作为一个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国家,伊斯兰教从来没有被确立为印尼的建国基础。相反,自印尼独立以来,“潘查西拉”至少在宪法层面被确立为国家认同,虽然在现实政治中,各个政党或者团体对潘査西拉原则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往往被用来包装各自的意识形态或者作为攻击竞争对手的工具。[5]133-134即便如此,应该肯定作为国家认同的“潘查西拉”在法律制度层面保障了印尼在政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规范原则建立,为包容、民主、人道、团结、正义等观念成为印尼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共识奠定了基础。虽然自印尼建国以来,一方面,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坚持伊斯兰教国的政治理想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文化观念,反对潘查西拉原则,反对主张多元文化的社会建构,但另一方面,潘查西拉原则越来越得到不同宗教团体的广泛认可。2010年印尼政府决定授予印尼多元文化之父、已逝世的前印尼总统阿布杜拉赫曼·瓦希德民族英雄的称号,这不仅反映了印尼人民对瓦希德的爱戴与尊重,更集中体现了印尼社会对潘查西拉原则,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与捍卫,这表明,印尼社会正逐渐在社会文化观念建设上达成共识,即多元主义作为一种促进国家团结、稳定与繁荣的重要理念与原则必须得到保证。应该进一步看到,印尼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坚持与捍卫不仅对印尼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东盟而言,也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与价值,东盟作为建立在多元社会与文化基础之上的地区组织,急需加强社会与文化的规范原则一致性认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与尊重等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应该成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差异中的统一”的美好社会蓝图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东盟各国(除新加坡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国家,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观念、发展模式与发展途径也是一系列值得重点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及正义、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等问题,是包括东盟在类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东盟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观念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不可否认,在东南亚国家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制度中,国家/政府作为唯一合法的权力机构,成为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历史上,由统治阶级/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变革模式长期主导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在后殖民时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东南亚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度的提高,来自公民社会的力量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组织逐渐成为推动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越来越重要的主体,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的治理方面,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已逐渐被东盟多数国家接受。
公民社会作为与国家、市场并立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东南亚国家普遍作为后发民主的国家,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上鼓励与推动公众参与式民(participatory democracy),并将其作为政党民主选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已经成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与褒扬的社会观念。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公民社会及其NGO的发展以及其参与政治变革、农村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已引起东盟其它国家的关注,尤其是菲律宾政府也建立了支持NGO参与基层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机制。如在马科斯专制统治被推翻后,非政府组织在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被阿基诺政府肯定,其地位得到国家宪法的承认,鼓励建立和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组织的建立被写入1987年菲律宾宪法。1991年,菲律宾政府进一步奖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发展的决策权纳入“地方政府法规”(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机构中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席位,非政府组织对地方发展战略的决策权,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地方立法机构中的席位。[6]这些法律不仅从制度上保障了公民社会参与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权力,而且也从政府权威的层面肯定了民众参与式民主的社会文化规范。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公民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利他主义与公益服务精神已逐渐在东盟地区被奉为现代社会文化的风范。享有亚洲诺贝尔奖声誉的拉蒙·麦格赛赛奖的日渐广泛的影响即反映了亚洲社会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嬗变,体现了一种得到亚洲公民社会认可的亚洲价值观。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价值观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哲学领域中备受争论的话题。“亚洲价值观”并非泛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价值观,而只是指东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和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强调以“重经济、轻民主”的“亚洲秩序”来对抗具有普世倾向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以李光耀与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遭到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批评。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以自由为宗旨的发展观念”,不仅批评了李光耀与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对自由的漠视以及为威权主义合法性统治辩护的本质,并且指出其忽视探索亚洲历史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因此才导致完全将自由视为”西方”价值观念的偏狭。该奖是纪念菲律宾共和国已故总统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而设立。设立初期,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与菲律宾国内政治背景,特别是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与削弱战略,这个奖的某些获得者并没有得到一些国家与政府的认可。②拉蒙·麦格赛赛基金会是由菲律宾政府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设立的,其宗旨是弘扬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的“崇高精神、正直以及对自由的贡献”。在冷战思维影响下,1959年该基金会曾颁给分裂主义者达赖喇嘛“社区领袖奖”。笔者注。但是撇开初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半个多世纪以来,麦格赛赛奖越来越突出的社会服务精神、思想文化创新精神、社会正义与和平谅解精神无疑应该视为推动亚洲社会文化进步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无疑是多元文化的亚洲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③麦格赛赛奖在成立之初设立了5个奖项,分别为:政府服务奖、公共服务奖、社区领袖奖、和平与国际谅解奖、新闻文学和创造性交流艺术奖。2001年增设新兴领袖奖。自1958年以来,已经有200多位亚洲各界人士获得麦格赛赛奖。自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费孝通、英若诚、梁从诫、袁隆平、高耀洁、吴青、潘岳、傅企平与霍岱珊曾获得该奖。笔者注。
第三,东盟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宗教文化影响的地区,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中,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发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逐渐呈现出具有现代性转变的特征,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内部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以及外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冲击的多重挑战,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成为涉及东盟各国政治发展与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社会的现代性成为东南亚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与族群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问题成为影响东盟社会文化规范认同的重要因素。但自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伊斯兰教被塑造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教以及马来西亚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核心,成为捍卫马来人特权与马来人精英巫统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工具,马来西亚这个自诩为“真正的亚洲”的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却是一个将种族歧视合法化与制度化的伊斯兰教国家,这样的国家能否代表真正的亚洲与亚洲社会的现代化方向?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政治强人马哈蒂尔统治马来西亚的20多年时间里,国家主导的伊斯兰化的价值观念全面渗透到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促进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7]而马来西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强化了了巫统种族主义与伊斯兰化的政治逻辑,这种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更将其包装成为成功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典范,而马来西亚社会内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人权等问题却被掩盖在国家辉煌经济成就的华衮之下,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模式实际是亚洲许多国家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步入21世纪后,随着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马哈蒂尔的卸任与“交权”、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以马来人特权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不断增长的批判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复兴,迫使马来西亚统治集团的核心——巫统,不得不在其意识形态上做出改变。2002年发起的“文明伊斯兰”运动即是这次改革的政治口号与主要内容。2004年9月,作为马哈蒂尔继承者的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阐述了“文明伊斯兰”的10大原则,包括:信仰真主;公正及负责任的政府;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民;掌握知识;均衡而全面的经济发展;有品质的生活;维护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益;文化与道德的完整;保护自然环境;国防建设。[8]“文明伊斯兰”的出台,引起了国内外对马来西亚伊斯兰的热烈讨论。马来西亚政府将“文明伊斯兰”定义为“一种基于伊斯兰文明的观念,全面发展人类、社会与国家的道路”。西方国家也对马来西亚的“文明伊斯兰”却表现出欢迎的姿态,美国主管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Karen Hughes女士称赞“文明伊斯兰”为其它国家的穆斯林树立了强大的榜样。[9]而在学术界,马来西亚伊斯兰学者普遍将其视为“进步伊斯兰”,而一些非伊斯兰学者则视其为“延续巫统政治合法性的宣传工具”,[10]或者是由官方主导的强化族群认同的宗教文化运动。[11]尽管对马来西亚的“文明伊斯兰”思想与运动褒贬不一,尤其是指责伊斯兰教的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工具化,但应该看到,在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语境下,这是伊斯兰无法逃避的命运,甚至是不可回避的责任。与马来西亚历史上不断延续的其它伊斯兰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伊斯兰”蕴含值得肯定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尤其是它倡导的“温和与节制、宗教与道德、团结与合作、发展与均衡”等社会文化发展观念代表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现代性转变的方向。这与马哈蒂尔威权时代的全面伊斯兰化价值观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并且对亚洲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三、社会文化规范建设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
自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与印尼与新加坡的复(建)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今天,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对话伙伴到睦邻互信,再到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来看,政治交往与经贸往来成为主导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两大主轴。21世纪,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2002年11月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2003年温家宝总理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等均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入了经济、政治、安全合作的新阶段。总的而言,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多交集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尤其是依靠政府外交与经济外交来促进双边关系,这是中国-东盟国家关系2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重要模式。但这种外交战略与模式强调政府/经济在外交关系中的角色与影响,而忽视了民间/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在对外关系中的角色与影响,这很难保障中国-东盟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威胁论”大有市场、中国与数个东盟国家存在岛礁纠纷、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区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扩大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影响的复杂情况下,如果忽视了与东盟国家加强民间/社会交往以及文化交流,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便极有可能坍塌。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东盟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升级表明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可忽视的脆弱性。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进入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对话与合作应该超越单纯的政治经济合作,更广泛地延伸到社会文化规范建设领域,只有在政治互信、经贸互惠、社会文化规范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与全面深化中国-东盟关系。
在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认同与规范上,中国-东盟是否能达成某些方面的一致呢?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创造了举世注目的奇迹,同时也创造了罕见的社会经济发展失衡与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失序与道德失范也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中国亟需在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建设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规范与认同。上述东南亚国家倡导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规范,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他在致辞中提出并着重阐述了“包容性增长”理论,即包含了以人为本、民众参与并共享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等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加强政治互信与深化经贸合作的同时,必须探索建立一致的社会文化规范,促进社会文化共同发展,才能长期、健康地发展深化双边关系。
[1]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47 -48.
[2]ASEAN Secretariat.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EB/OL].(2009 -07 -20)[2010 -12 -10].http://www.aseansec.org/5187 -19.pdf.
[3]ASEAN Secretariat.Another Step Forward for Regional Human Rights Cooperation[EB/OL].(2009 -07 -20)[2010 -12 -10].http://www.aseansec.org/PR -Another-Step-Forward-for-Regional-HR -Cooperation.pdf.
[4]William Cole ,Erik G.Jensen.Norms and Regional Architecture:Multilateral Institute Building in Asia and its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M].West Sussex: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244.
[5]S.Takdir Alisjahbana.Indonesia Social and Cultural Revolution[M],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6]Segundo E.Rpmero,Jr,Rostum J.Bautista.Philippine NGO in the Asia Pacific Context[M].Tadashi Yamamoto,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Singapore/Tokyo,ISEAS/JCIE,1996:188-189.
[7]Seyyed Vali Reza Nasr.Islamic Leviathan:Islam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we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05.
[8]Mohammed Sherif Bashir,Islam Hadhari.Concept and Prospect[EB/OL].[2010 -12 -15][2010 -12 -29].http://mdarik.islamonline.net/servlet/Satellite?c=Article_C&cid=1153698300078&pagename=Zone- English - Discover_Islam%2FDIELayout,
[9]Ioannis Gatsionunis.Islam Hadhari in Malaysia[J].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2006(3):78 -88.
[10]Terence Chong.The Emerging Politics of Islam Hadhari[C]//Saw Swee Hock and K.Kesavapany.Malaysia:Rec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6:38 -42.
[11]陈中和.族群认同与宗教运动在国家政策的运用:初探马来西亚巫统文明伊斯兰运动[J].东南亚学刊台湾,2005(2):9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