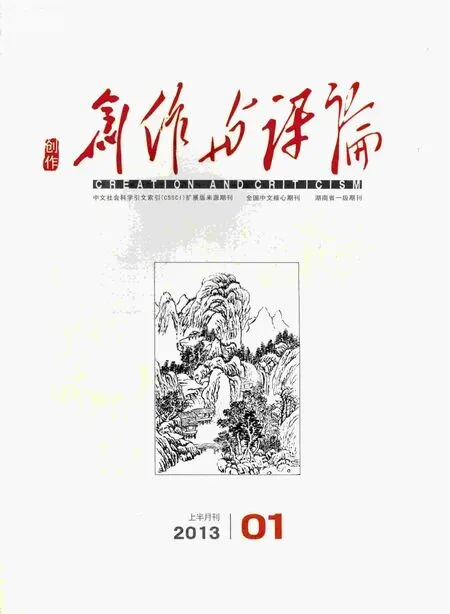在仰观深察的叙事里展开诸多纵深探究——韩少功长篇新作《日夜书》阅读札记
○ 舒文治
读《日夜书》,需要跟随叙事的节奏而仰望、探查、停顿、迂回、泻落、标识和对照,因此,我也只能用一种戏仿“散碎笔记体”的形式,录下一些感受与分析。
一、开放的文本需要放开的阅读和批评
“扁平时代的写作”正面临着方向迷失、深度翻空、高度削平和文化淹没、自我分裂及价值瓦解等问题,对此,韩少功进行了严辞诘问和精准解剖。他的写作该是自觉对这些边界的示警,对这些陷阱的飞越、蛊惑的叫板,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个人写作义无反顾的坚守与自信,还有对隐匿于体内的种种妖魔进行“驱魅”与“解魅”,还会对精神可能抵达的地平线及其过程不停的远眺与探访——我们一直对这样的写作充满着期待。这也是“扁平时代的阅读”所必须的自我救赎,我们的阅读不能不谨慎而挑剔,不能不升级杀毒软件,也不能不与我们信任的作家“签约”。私下的,我们还觉得“片断体”仍不过瘾,“山南水北”之外还要有婆娑世界,“思想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不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
就在这种信任、期待和导入了苛求的混合心态下,我抢先读到了韩少功的长篇新作《日夜书》,同时也遇到了表述自己阅读感受的真正困难:这该是一部怎样的书?如果按照作者自己对以前的两个长篇的归纳——《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暗示》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那么,《日夜书》是否也能用一两个提炼后的字符来大体示义,即使韩少功的心里有谱我们也难以打谱,我总感觉到,这是一部你说不准、说不好、说不清的书,是一部接通记忆、切入现实、打开遮蔽的书,是一部不断自我放逐、自我为难、自我较真的书。它是知青小说?是,然后又不是(它也写同龄的非知青、写下一代、写外号“酒鬼”的猴子、写当代官场等等);它是诗意化的哲理小说?是,然后又不是(它也津津乐道于技术、实写农村的粗野下作、颠覆一般意义上的诗意等等);它是异于《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情节线索大致可循的结构完整的小说?是,然后又不是(它经常开岔,不断越界,另接话题,弧线频抛,说收就收);它是不断设谜又解谜的自我追问之书?是,然后又不是(它不布迷魂阵,不作高深莫测状,紧紧依靠坚实的生活和密集的细节,“来说明自我与外部世界是怎样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①)
我也必须止住自己在书中的打滑,否则,阅读只会变成一种言不及义、云山雾罩的谈玄与轮空。我在作者的一个大胆揣测里找到了放纵的理由:“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那种呼拉拉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②这是韩少功对新批评的鼓励与实践,鼓励我们对文本作出不拘一格的解读,对作者的纵深探究进行再探究,在“对话与潜对话”的语境里实现以读者对谈作者,以品评抓对叙事,以经纬校对流变,以描述遥对冥想,以局限面对无限,如此,我们应邀参加一场没有确定目标、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终极价值的审美探究之旅、命运追寻之旅、人间关怀之旅,以此契合作者“想不清楚的写小说”的本义,以批评的放开对应文本的开放,以可能的意义标示隐含的意义。我甚至还认为,这种随心所读、纵横边界、不受学院规训的批评,也是作者能够宽容一笑的批评。
二、串联并联通电、接天接地通灵的叙事模型
《日夜书》在结构上看似很散漫随意,没有刻意为之的分章分节、主线副线、设局设障、呼应暗合,但它几近无痕地融合了回忆的遥接与现实的切入,把感受、判断、分析、探询杂糅于一体而不显拼装的折缝与出格,即使是对个人意识暗区的潜入,对头顶星空与体内“上帝”的冥想,对时空里人生定局的求解等,都进去自由,往来无碍,从容不迫,这也很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叙事方式,以区别于《马桥词典》结构主义的形式追求,也区别于《暗示》在“高难度的自我较量”中因急切探寻而造成与阐释和阅读的紧张关系。
期望韩少功要有形式突破和言说扫障的读者可能会对《日夜书》的叙述方式心生疑惑,继而难免失望。因为《日夜书》不是那种带给他们直观惊喜和窥探过瘾的书,也不是要在题材上抢热点、表现上抢眼球的书。在其他同龄作家都不屑于再从知青生活中深度开掘时,他仍然把自己的第三个长篇的取镜框和长焦距对准了知青岁月留下的“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陈晓明对此曾作过一个可以不断得到印证的分析:“在他个人记忆深处,始终包裹着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知青情结’。”③写什么的问题往往由作家的个人经验和创作态度决定,而对同一个题材怎么写、能写出什么的问题往往十分复杂,必须作出具体的文本解读。如果你希望灵魂恢复苏醒和敏锐的状态,渴望获得一种揭开真实、逼近真实的体验,那么《日夜书》不但不会让你失望,而且它会不断将你引向深切的体验,既为你烛照“记忆的黑暗中沉睡的内容”,也为你涌现“一片徐徐洞开的光明”,因为它的叙事涵括能够提供这样的心智滋生空间和某种精神人格的约定。
《日夜书》的叙事不是自然叙述的简单回归,也不显示韩少功年近花甲创新精神的衰退,它是韩少功创造的又一种个人化叙事模型:仰观与深察、庄重与戏谑、叙述与分析、批判与宽容、看够与看穿、放飞与回归等等这些貌似相对的两极,它们结构成一种奇妙的混合,一团绕而不乱的线圈,包括小说因素和非小说因素的交融,成为了回忆、思考、状物、抒怀、追问不断引向深入的串联与并联,就像“技术魔怪”贺亦民手中的万用电表一样,两极相连后立即产生了通电点燃心智的奇妙效果,不经意间又接天地阴阳,直到通灵的化境。
小说要串联并联的是,“我”熟知的知青朋友们的经历暗纹及其日后的流变,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结,他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及其下一代,他们与同代人、国外人,与插队落户的当地农民——在同时空或异时空里构成的或显或隐、多层对接的复杂关联。而且这种串联并联又超过了文本的叙事边界,接入到作家的其他作品中,形成了新的互文意义。比如,白马湖茶场知青们的穿着行头、生活习性、精神爱好、言说及思维习惯、日后返城的聚会和命运流向等,在《暗示》穿插描述的“太平墟”知青群体中,在韩少功有关知青的多篇各种体例的文章中,都有回应和链接。我不是从文本考据意义上来进行举例,而是要说明《日夜书》的叙事非但不是以一种自我封闭、记忆断流的方式行进,更是如孔见所言:“通过这些经验记忆的系统解读向读者举证,在我们尚未开口说话的时候,彼此的交流就已经开始,潺潺涓涓或是滔滔滚滚地进行着……”④
它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是,生命到了知命之时,感悟到了通达之时,文化到了厚积之时的一种随心取象,俯拾皆是,处处禅机;且大道平常,义在言中,悟在言外,往往能使阅读产生令人怦然心动、欲辩忘言的会心一笑。深入文本,既有对历史、身体、自我多重品格及存现方式的处处点击,也有对人间真情、人性光芒、生命尊重毫不避俗的时时颔首。既对应着“我们全在阴沟里,仍有人仰望星空”的自我较真,也有自我更远的放逐:“流星在头上飞掠,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星空在缓缓旋转,我现在该往下写吗?目光下的山那边似乎就是世界边缘,是滑出这个星球的最后一道坡线,我犹豫的笔尖该往哪里写?”这种灵魂出窍的通灵意境在文本中不时灵光乍现,也延续着作者(叙述者)多年来一直保存的敬畏,对康德式的头顶星空和内心道德的敬畏:“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⑤对此,寒光闪闪的解构主义的手术刀是不是也要下手切割呢?至少,我觉得,面对接通生命真实感知和美好情怀的文学,批评该有一个从哪里下手、并有破有立的基本立场,总不能刽子手一般的一排排都砍下去,如果批评变成了李逵的板斧,倒也成为了一件省心憩脑的快事。
批评也应该进入文本,参与创造,生成新义。只有深入到《日夜书》的叙述流程里,我们才能把握人物各不相同的命运,看到同异交织的自我,倾听到人与万物的声音交响,它们互相作用与反作用,彼此阐述与补充,暗中对话又对抗,形成了一种意义可以不断生发和等待探究的网状结构,每一个网结都串并起来,既摹拟了大脑的认知与记忆结构,又向着同状的生活打开,向着引发无限沉思的天穹奔腾。
三、多种身份和被多层塑造的叙述者
《日夜书》也采取了韩少功惯用的“我”的叙述视角。但对《日夜书》中“我”的分析,会发现此“我”非“彼”“我”,此“我”也非老韩,此“我”更有他的特殊意义。
《马桥词典》中的“我”,更多是词语及其言说环境的考证者、见证者,也是适度的参与者,他以知青身份出现;《暗示》中的“我”更多是对言外之言、象外之象及其遮蔽系统的质疑者、揭露者,他是一个思想突围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作家本人,文本中韩少功也无数次跳出来指路、举证、论辩,确切“呈现着一个探索者和怀疑论者的坚定面言”。(谢有顺语)
《日夜书》中的“我”要更为复杂,他多棱,多层,也多义,可以一层层给他剥去身份的社会符号,被塑造的文化符号,不断接近他的内心真实,也就接通了理解人性、个性及其因果链条上某些环节的秘道。
“我”肯定已不单纯是那个总要依靠个人记忆与经验的自我,作者在《日夜书》末尾的附记中确定无疑地道出:“本书写作得助于小安子(安燕)的部分日记,还有聂泳培、陶东民、镇波、小维等朋友的有关回忆,使书中的某些故事和人物得以虚构合成。”它虚实相生地、诗意反诗意地呈现包括“我”在内的一个群体,他们真实而深切感受到的生命暗区、历史体验、现实之痛,记忆的储存及修改,梦境的链接与断裂。
阅读之后,可以较为清晰地列出“我”的身份清单、关系清单、经历清单,这些足以说明“我”这个叙述者在韩少功的新作中,已经异于以前的“我”,现实脉络比较明朗可辨,开始有迹可循了;更要说明的是,这几份清单并不能洞穿“我”的内心隐痛及其化解,不足以标识“我”的存在意义、特殊意义。
“我”的意义是在文化纵深里,也在被多层塑造的流程之中,这才是韩少功对“我”的重塑意义。正是这个互为因果、互为材质、互为模具的回环过程,成就了《日夜书》对塑造人物的无数模具的翻检,对时间和命运的独特审视和意义之旅。
“我”的模具是由自我与他人、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本能、人性与物性、精神与物质共同锻铸而成的。
“我”从小耽于幻想,困于疑惑,虽其成因不详,但足以使“我”对远方的山川原野充满乱想,对青春的动荡全力以赴,对自我的不断打开心怀不倦的求索。如果没有这种特有的精神秉性,“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内观的冥想者,就不会总有一种概括、探究的思想冲动,也就不会以如此的方式叙述。
白马湖的知青集体生活,塑造了“我”的义道重情,架通了“我”理解他人、相处他人的多个路游器,也为我洞开了男女之情的秘密,订下了相守依偎的内心盟约。同时,白马湖的农民及其生存环境,使“我”对个人性格的复杂性、生存处境的尖锐性、人间真情的不灭性、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了然于心,纠结之后,也融通于心。
数十年观人观物观场的练达洞明,让“我”对人性的黑洞、现实的箭矢都有了内心的预知与预防,保持着“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而来自学院的知识背景,源自内心巨大的困惑,加之本能、文化与经验的互证,使“我”对“泄点”与“醉点”、“常态”与“异常”、“身体”与“上帝”以及“基因”与“基果”等这些重大而玄深的课题饶有兴趣,并形成了一套个案分析的认知体系,借以看清自我与他人,看到文化的纵深,看到“上帝”的存在方式,表现出“困而知之”。也为这种打破小说框架的引申叙述及深度分析找到了依托的可能,并使这种“冒险的、生疏的、前景不明的写作状态”避免了生硬的插入。
“我”的模具还可以不断进行材料分析,而且这种塑造在小说中由人扩展到了动物,猴子“酒鬼”它在知青们的集体塑造下,真正沐冠而猴了,能够作拱打揖了,由此可见,人和动物都是文化环境塑造的产物。这就为解释“我”如何被塑成一个独特反常的叙述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否则,我的批评也就无法得出以下结论:正是这一个被多层塑造的“我”,处在“时间/空间的文化坐标中”的“我”,他的经历、气质、思想与环境和他人相生相成,有了人的体温、血肉和骨架,既避免成为被操练的精神道具,又可能完成诸多探究的叙述使命。他与韩少功塑造的一系列的“我”构成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具思想深度能指的既清晰又模糊的特异形象。
如果视野打开作一比较,“我”有着《惶然录》中佩索阿一样的精神特质,韩少功在《惶然录》中文版序言中,对这一精神特质作了概述和提示:这是以自我分裂、自我怀疑、自我对抗来进行的一个人的精神挑战,把自己分化成一个精神化的人、一个物质化的人、一个个人化的人、一个社会化的人、一个科技化的人、一个信仰化的人,以亲证人类心灵自我粉碎和自我重建的一个个可能性。在“我”的内心战场和外化图谱上,都可以按对位法则找到布点和虚实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精神气质的大致归类,其经历和形象无法类比,“我”的存在意义更是纯粹韩少功式的赋予。
四、多义场里的意义升腾
《日夜书》以一种新的梦壳般的形式容纳着韩少功的活性思想。既有他一直思考并充分表达出来的与各种问题的博弈,也有他的心想疆域向星空、向体内、向历史现场、向技术想象、向文化纵深、向基因谱系的拓展,随着叙述的推进,这种拓展渐行渐远,越锲越深,力图以一个人的感受来抵达人类认知在某一个时间之局里的遥远边界。这也注定是一次艰辛而又冒险的意义探询之旅,因为“我”思想的行囊装得太满,很可能会使小说变成理论索引,使审美变成精神体操,这两者都容易导致思想遮蔽形象,意义因膨胀而使小说的美学图型发生变形。
韩少功对此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叙事,表现出进入通融之境的小说家对“多义场”的从容控制。他塑造、激活的那一个“叙述者”没有添乱和越位,他自动地从个人经历、学识、秉赋及各种隐秘关联中产生问题,真诚求证,寻找解释的路径。
这些问题和探询及表现方式纷至沓来:既有那个时代生活还原后的真相揭露,也有革命串味又如何变味;既有知青们的身份暧昧、精神隐痛和生活别处感,也有农民们的丰驳本色和生活哲学;既有文革中各路知识大侠的复活,也有对马涛这一“哲学王者”和贺亦民这个“技术魔怪”的反讽与戏谑;既有身体的囚禁与作祟,也有精神的病变与逃逸;既有历史巨大的创口,也有体制性的痼疾;既有爱情背后的人性切口,也有政治强奸为何能屡屡得手;既有跨国界的彼此自闭,也有两代人的相互撕裂;既有自然的激荡雷鸣和生命的多种呈现,也有死亡的如影随形、早已开始;既有技术创造的现代神话,也有现代人的全面萎顿;既有“点”位后面的社会历史,也有隐形上帝的操控和道德对行为的生理发动等等,它们在我的阅读笔记本上列出了一长串清单,还可以不断开列下去,此义生彼义,重重叠叠,构成了我理解到的《日夜书》的“多义场”。对它们的一一解读显然是批评的不堪承受之重。
我更关注的是,“我”的心想及表述的重心在哪?它们从“多义场”上能再升腾出什么意义?“我”的目光频频投向自身及同时代人不可回避的各种形而下问题,即使是形而上的叩问,也避开了康德式纯粹理性批判的艰涩之路,又避开了尼采式与上帝的彻底决裂,它们虽然内在急切,但表现出面相温和,散发着中国式通融求达的智慧光芒,并不刺眼。其意义升腾之势虽难以驾驭,但仍然被韩少功得心应手地安顿在51个章节之中,错杂而有序。
这是一个把全部问题都纳入心想之后的求道者的思想布局,他既与自己对局,又与“上帝”手谈,他敢于把生命纳入星空的棋盘,他乐天知命地接受对局的结果——这一出也许已经接近尾声的独幕剧,这一来自星空和尘埃间的身体的自然熄灭。此时,我却分明看到了燃烧,升腾于天际的燃烧,多义性的思想燃烧,带给了我洞开的光明和怦然心动,正如韩少功自己所言:“真正燃烧着情感和瞬间价值终决的想法,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到大脑之外的更多体位,关涉到整个生命。”
“我”是以“整个生命”作为自问和求解的献祭。“我”的全部生命感知与心动帮我实现了“隐秘升腾”:“我”在万物涌现中体验到了此在的一切快乐与痛苦,一切拥有与放弃,一切过去和未来,此时,“我”如经历重重炼狱和精神浸游后的浮士德一样心神俱醉,一样的由衷赞叹:上帝,这一切多么美好!
《日夜书》意义之旅的结束语与《浮士德》的诗意终结奇妙的对应着。
韩少功已从对理想主义的紧张思考和操切表述转换成一种乐天知命、通融广大的慈悲情怀。我感觉到《日夜书》里人性的光芒胜过了意义的追寻,人间的关怀胜过了思辩的剑锋,它们照亮着我,也沐浴着我,使我的阅读时时越过阐释的通道和意义的长廊,直接聆听到阳光和星斗的密语。我要说:读《日夜书》,于我有福了。
五、终点回到起点的虚构:时间的作品
批评不是猜谜,但批评总要沿着作者有意无意留下的路标一路提问,一路探访。在这部由一个个被质感回忆、人物气味、心理刻痕布满的日夜构成的书里,作者综合进行着历史虚构,会将我们的思绪最终引向哪里?
叙述者虽然会将自己的动机隐匿,但他总会出场在场,他总要将自己最隐秘的感受与我们一起分享。
“我”按成长时序的出场在第3节,不满十六岁的“我”有点青春期叛逆,有点无所事事,也有被忙于革命和下乡的哥姐们抛弃的感觉,但与郭又军雨中命定的相遇,把“我打向了远方”,从此开始了这一场“延时开播的电影”。经过15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跳格与跨界,“我”走到了第51节(结尾),文本中写法很奇特微妙、于简朴的表述中蕴含丰富信息一节:在星空座标中,经历了漫漫日夜旅行的“我”回到了混沌初开状态,感受人间如同天堂。在此,《日夜书》暗合了汤之《盘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生命常新的一种自觉与自信。
按照第5节提供的“回看我的一生”的视角,这几十个章节就是时间电影“一格一格”让我严格就范的注定。对于注定,我们无法修改,但我们可以提问:谁在设计“我”出演怎样的角色?是什么在排演“我”、塑造“我”?这前格与后格之间的无数空格里隐藏着什么?是什么使“我”非如此不可?又是什么使“我”退回到“粉粉肉团”的原点?
面对这些连环而来的困惑大阵,“我”总是试图解谜,但新的谜团会随着解谜而不断产生,一个连着一个,一个连着数个,永远不会终结。“我”的困局也就是我们的困局,“我”的注定也就是我们的注定,只是需要我们也一同走进这间放映室或胶片库。在此,《日夜书》借助“我”再一次将个人在时间和命运里时时生发、不可摆脱的困惑集中而强烈地呈现了出来,即使那刚刚诞生、刚刚抵达的“我”,对于万物涌现的第一反应,就是一连串稚嫩而老道的惊讶和设问,粗略计数,一口气就提出了二十几个自问,当然,都是没有答案也不会提供答案的自问。因此,《日夜书》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借隐喻表现人类普遍性精神困惑的书,是一部汇入了对时间经验的错杂感受的书,也是企图超越时间控制的书。并且,《日夜书》又是一部探询时间的书,是一部有限向无限发问的书,是一部解释的有效性有时会失效的书,也将是一部处在时间制造的流沙与纸浆里经受时间校验的书,正如它的书名经过反复用心比较、筛选而最终确定:日-夜-书。
注释:
①韩少功:《好“自我”而知其恶》,《想明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②韩少功:《想明白·台湾版自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③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④孔见:《韩少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⑤韩少功:《我与〈天涯〉》,《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