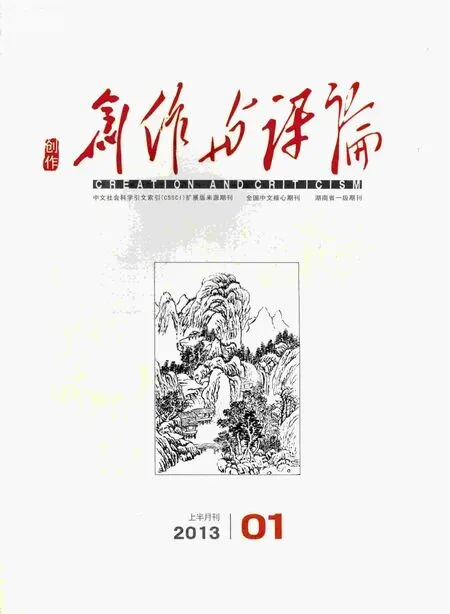时代情绪的诗性书写——以韩少功《日夜书》为中心
○ 廖述务
一
韩少功的小说常常散发出浓重的泥土气息,这一次也不例外。长篇小说《日夜书》依旧以“陈旧”、不时髦的知青生活为基本的书写场域。“陈旧”二字,意在表明这一题材已经被中国作家无数次征用和光顾。因历史原因,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知青写作差不多就是乡土文学的另一个代名词。与当年的“文化热”一并兴起的“寻根”,也是知青写作披上“文化”外衣所上演的文学曲目。不过总体来说,“寻根”文学群体成于“知青”,亦败于“知青”。郑义、李杭育、张炜、阿城、韩少功等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倒转过来说,是知青的乡土生活成就了此一群体的创作。他们乐于回望乡土,其实意在重温独特、体己的生命经验。将这一生命体验铭写在林海中、大漠里,至少可以为创作赋予独特的个性。
值得玩味的是,有一些作家在“寻根”之后就销声匿迹,基本结束了创作生命,因为他们已经打捞完生命旅程中有限的“乡土”经验。因时代原因,该群体的主体部分既没能参透西方,也没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于是只能把文化处理成逆时的有待寻找的“神话”。“寻根”难以避免出现早产。更重要的是,这件沉重的文化外衣,于无形中钝化了作家感知时代情绪的敏感触须。其实,并不止于知青作家为书写对象所挟持,莫言也是如此,从成名迄今,就一直无法走出那块粗鄙放诞的红高粱地。他过于信任自己乖张暴戾的文风,而漠视当下,疏于观念的介入。
在同辈作家中,韩少功算是不多的能持续把摸到时代脉搏的人。早期的《爸爸爸》还迷恋于边缘山寨楚文化的别样风情,《女女女》就来了个变身,开始大胆尝试以楚文化诡诞的意绪去琢磨、参悟城市日常。之后,当他意识到寻根的危机,就开始寻求突破。1980年代后期起,创作开始融汇不少先锋色彩。近年的韩少功回到农村安居,似乎放了一个再“寻根”的烟雾弹。其实,这一阶段的创作已经与“寻根”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去除了为“文化”而“文化”的矫饰,留下的是平淡与自然,并有了更深沉的现实情怀。《赶马的老三》、《第四十三页》、《怒目金刚》等作品,执着于对公共正义的诗意构想,有着相当强烈的介入意识。他与同代作家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明显,即在一个时代情绪之弦紧张到近乎绷断的语境中,他没有闭目塞听,完全听任于依依呀呀的文学感觉,而是尽力让个人的情绪通达宽广的时代。新作《日夜书》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诞生的,那么,它有没有接续韩少功自身的写作传统呢?回答是肯定的。
《日夜书》中处处可见时代情绪的涨涌。在这部小说中,韩少功涉及不少新观念,同时又延续了许多他一直关注的话题,并将部分话题变得更加醒目。而且,小说在形式上的探讨也引人注目。形式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形式的革新既为观念所催逼,也为从时代情绪的重压中突围准备了美学基础。这部小说涉及到的社会人生繁复多样,在此只能择其精要而述之。
二
人物马涛在整个故事中特别“抢镜”,他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有关民间思想家的敏感问题上。在当代文学中,还很少有小说直接去描绘这个独特的群体,除却主体的盲视,语境所施予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韩少功亦庄亦谐的语调定然会使某些读者不快,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导致现实世界的马涛们强烈的批评与反弹。其实,对马涛的理念,“我”并不是一个断然的反对者,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是他的死党和追随者。他引我走入知识之途,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青春。在后来的“告密”事件中,“我”还扮演了马涛的忠实捍卫者角色。但马涛极为自负,常以历史的改写者自居。于是,常人与日常都成了他思想的敌人。他与郭又军的几次比斗,在监狱中对妹妹马楠的苛刻要求,以及在美国的多方申诉,都在为“自大狂妄”一词作注,在在令人叹息。扭曲的人性必然带来思想的变质,他终于戏剧性地将忧世伤生与持守真理蜕变成了名利的跑马场。
无疑,马涛是个悲剧性的角色。但人们若以嘲笑姿态将其轻易打发,那就顶多流露了自身对历史的不敬。对这个人物,韩少功有着特别的考虑,这是他个人知识分子反思史的一次深化。在很早以前他就说过:“一个民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质量。我们这个民族一直挨打,一直落后,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质量有毛病,中国知识分子质量上有毛病。”①那么,他心仪、首肯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怎样的呢?张承志、史铁生将小说作为精神的旗帜,为拯救灵魂而战,就被韩少功引为知己。在他看来,这样的作家是“圣战者”,是“心诚则灵,立地成佛”的精神突围者。凭借“心”的力量,“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②。对于历史人物,韩少功欣赏的也是人格健全者。比如苏轼,就是一个乐天派,是个“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的人物。历史上命运坎坷、遭遇不幸的文人确实不少,但是有几人能像苏轼那样坦然面对呢?韩少功不由得发出感慨:“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③只要有完美的人格,即便处在对立的阵营,依旧是值得钦佩的。对左派格瓦拉的尊崇并不妨碍韩少功对右派吉拉斯的由衷赞美。历史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所站的立场,“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④。
在韩少功这里,“美分”或“毛粉”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个人的人格品质。在以“主义”定尊卑者那里,这显然有点主次不分,甚至颠倒黑白。而究其实,不难发现其寓意良深。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少功有关“理想者”的构想持续至今。这是对启蒙理性意味深长的回味与坚守。现如今,启蒙四面楚歌,人们弃之如敝履。王晓明就曾指出,80年代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都在谈“人”;90年代随着社会分化,核心词变成了“阶层”;而近些年则转移到了“国家”⑤。国家主义借“复兴”的东风裹挟一切,批判性的理性思考日趋稀缺。韩少功这个老“新左”,依旧执着于人的品质,确乎冒着被pass的危险。尤其在左派日益被国家主义收编的情形下,他明显成了一个步调不太一致的异类。尽管如此,他并不缺理性的同道,哈贝马斯就坚称,启蒙在西方依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在现代性层面,中国作为西方的学生,放言启蒙已死,是否为时尚早?
三
小说中的贺疤子则与马涛构成了有趣的对照。马涛有着“辉煌”的抗争史,而他因家庭的不幸,很早就浪迹街头,成为独霸一方的扒王;相比前者的出口成章,高视阔步,他蛇行鼠窜,秽语连篇。他的电工技术也来路不正,全凭一腔热情,玩命拆装,无师自通。当马涛为了自己民间思想家的身份四处呼号时,贺疤子似乎一直对各种头衔的深意领会不清,更不擅长扮演诸多高贵角色。作为人文学者,马涛恨不得为“新人文主义”申请自然学科才有的发明专利,而贺疤子则做了另一个技术共产主义的林纳斯。贺疤子也许不够完美,但至少有了韩氏“理想者”的一些风姿神貌。
堪与学界乱象比肩的莫过于官场生态的恶化。人物陆学文身居副厅高位,但别无所长,碌碌无为。他签批文件,永远只有两个字“同意”,或一个字“阅”,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建议。哪怕只是两分钟的发言,也离不开手下人的发言稿。“我”于是只能安排他当“陪会”的角色。当然,他还是有一些为官的“特长”,比如对很多大人物及各位亲属的姓名、履历、爱好、人际关系、家人状况等,他都能如数家珍,如同情报局的活档案。深谙为官之道,使得他仕途一路看好。“我”力图阻止这个家伙扶正,反倒身陷囹圄,提前退休。尽管小说只有对“我”所作所为的正面叙说,但背后那只无形的手无处不在。这无疑暗示,那个只会“陪会”的废物在官场有着巨大的活动能量。这样一个人物能翻江倒海,其隐含的讽喻义就尽在不言中了。
民间思想家、学界、官场都似乎过于沉重,也过于“小众”。《日夜书》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则形而下一点,当然也更接地气。在消费语境中,除却疯狂的购物欲,人还容易犯两种“毒瘾”:情欲的与快乐的。有关情欲的书写在韩少功以往创作中都极为少见,只在《暗示》、《报告政府》等文本中偶露一点“肉色”,并很快遮掩起来。《日夜书》有关这个话题的书写密度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部作品。这倒不是韩少功需要这些东西来赚取眼球,恰恰是情欲在当下的意义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它甚至成为某些人根本的存在方式,即以情欲为“家”。小说中有关“泄点”与“醉点”的讨论最是有趣。作为描述高潮的两个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中的“吃饱”,与生物性更为相关;而“醉点”,则相当于饮食中的“吃好”,与文化性更为相关。福柯就认为,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连接了身体与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⑥。这可以成为“醉点”理论的有效注脚。不过,现实的“酒肉”饕餮之徒,往往只知泄点,而忽视醉点。这个时代的症候就是,当人们忙于为身体营造舒适处所的时候,常常忘了那更需安置的孤苦的灵魂。身体写作以及有关身体的研究,也常常陷入误区,成为性与肉身的炫目表演,失去了最根本的历史文化依托。至于将“快乐”也描述为一种毒瘾,更可算韩少功别具一格的语义发明。这在新生代女性身上最是常见。军哥的女儿丹丹就犯上了“快乐”瘾。这种快乐是由商家开发出来的,并且随着时尚的风向标不断升级。当使用价值退居次位,符码价值一路攀升之后,快乐就不再简单,而是与金钱构成了直接的兑换关系。
若将韩少功的语义进一步发挥,可以说,消费社会正是一个情绪失控,“毒瘾”全面发作的时代。
四
前面所述仅涉《日夜书》较为醒目的几个话题。在一部作品中容纳这么多观念相当不易,它几乎成为时代情绪映射于虚拟空间的一个核爆点。形式上的革新与变通有时就来自观念形态的催逼。箱子容积一定,但具体的容装能力往往与装箱方式直接相关。写作一部长篇,若不为版税所动,紧凑得当的就尤为必要。《日夜书》无疑将不算长的文本的功效扩张到了极致。马涛、吴场长、“我”、贺靶子、郭又军、小安子、笑月、梁队长,有关他们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足够蔓延、拖沓成一个浩漫的长篇。其实,许多作家就是这么做的,如同油田分解、打包贺靶子的发明一样。
线性叙事显然已经无法承受时代情绪的全面合围与重压。它历来热衷于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以简单明了、曲折动人为旨归。作为一种排他性书写,它更像景点明确的随团旅行,任何旁逸斜出,各行其是都是有害整体的。因此,通俗小说与线性叙事易于结成良缘。而且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甚至大部分经典现实主义作品,都以线性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因为它足以应付前现代相对简单的观念形态。《日夜书》的前十节,给人一个假象,韩少功似乎已经与线性叙事握手言和。但在第11节中就跳出了有关“泄点”、“醉点”的讨论,而且这一方式在后面持续出现,比如“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话题就都是在前文的某个节点上生发出来的巨型情节。这类巨型情节若欠缺煞有介事的理论介入,将显得异常突兀,乃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它们就像拦路打劫者,突然的闯入无端破坏了行人预定的宁静旅行。不过,高明的叙述者正可借此在线性叙事之外,加入一些无法揉捏进去的内容。比如“器官与身体”部分,就为叙述者以理论性阐释的方式介入社会问题提供了契机:“基因”也是“基果”,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因此,文学“回到身体”一类口号,显然不宜止于春宫诗和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理论在这里显然有双重作用:既便于形成新的叙述节点,为语义扩张提供方便,又可以扮演叙事之外的阐释者。阐释无疑是观念介入更为简洁有力的方式。
这种既扮演叙事者,又充当阐释者的写作方式早在《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中就有表现。这时,作家越位行批评之职,其控制欲甚至超过全知全能视角。这是叙事中的高危项目,没有超常的见识,往往就会成为蹩脚的自导自演。韩少功以其见识的深刻,为这种写作形式提供了智力保障。
在叙述层面,《日夜书》还体现了韩少功创作的怪诞式诙谐风格。怪诞式诙谐在早期的《爸爸爸》中就有体现。丙崽这个智障,是整个山寨后生们调侃、取笑的对象。再加上仲裁缝的迂腐,仁宝的假新派作风,整个文本都诙谐化了,成为一个狂欢化的文本。无论是新派的仁宝、旧派的仲裁缝,还是顽劣的丙崽,都在这怪诞的戏谑面前无从遁形。尤其是丙崽,文本借助诙谐表达的是一种开放性与未完成性,并试图见证一种内部生机与残敝共存的复合物。《日夜书》中,紧张到近乎绷断的时代情绪之弦通过怪诞式诙谐得到纾解,并促成了新道德的生成。吴天保文化有限,对官话一窍不通,在任何文件上只会批上“同意报销”几个字。因对现代文明的陌生,他和知青交流起来,也常常闹出笑话。但一说起粗话来,就酣畅淋漓,总说到点子上,且形象别致生动。他对共产党管到裤裆里来一事(指计划生育)极为不满,生了三个儿子,因此被摘掉官帽,接受审查和批判。他酒后调戏胖婶,惨遭“蹂躏”,还被妇女们虐待命根子。吴天保的诙谐、粗鄙,与那个时代不着边际的理想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讽。他那与泥土、肉欲相关的生命力给“我”不少启示,促使“我”对人生之意义再三追问。在巴赫金那里,老朽的孕者身上死亡与新生诙谐地共存,其目的在于否定死亡,召唤新生。在梁队长尤其是吴天保身上则是粗鄙与美德诙谐性共存,其目的在于促成新道德。梁队长坏了下体,戴绿帽子后,亦忍气吞声,很不光彩。但在其他事上却变了个人。他豁出去也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并风风光光将她们嫁出去。欠堂叔的钱,利滚利,他也坚持还完。堂叔死后,依旧力主“做七”,圆圆满满地完成了七天奠礼。吴天保对待梅艳、万哥的方式,就见出这“浑”人心中其实有一杆公平“秤”。在这种怪诞式诙谐语境中,韩少功出色地塑造出一种新的道德人形象。他们与《怒目金刚》中的吴玉和、《赶马的老三》中的何老三一起,构成了一个新道德人的形象谱系。经由诙谐风格的营造,《日夜书》得以突出时代情绪的合围,找寻到一块建构新道德的语言飞地。
注释:
①韩少功、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②韩少功:《灵魂的声音》,《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韩少功:《处贫贱易,处富贵难》,《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韩少功:《完美的假定》,《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⑤王晓明:《中国之认同的现实与期望》,《天涯》2008年第6期。
⑥〔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刘小枫、倪为国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8页。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