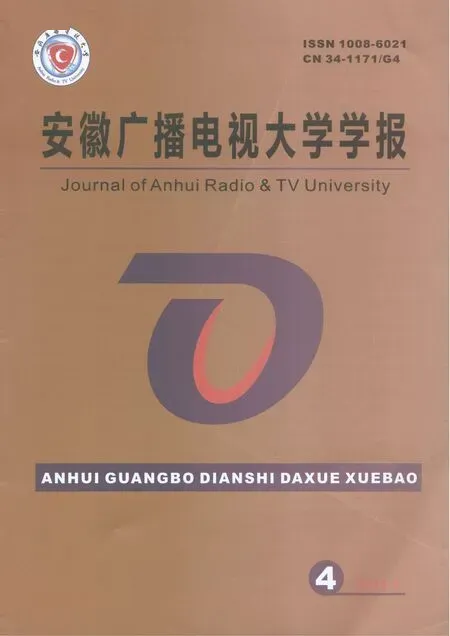适应与选择下的“杂合”
——“林译小说”翻译策略解读
张 锦
(河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适应与选择下的“杂合”
——“林译小说”翻译策略解读
张 锦
(河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引进“杂合”的概念,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对“林译小说”翻译策略进行解读与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林纾在其小说翻译中采用的是“杂合”策略,这种“杂合”是表现在语言、文化、诗学各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的 “杂合”;是其多维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社会维、译者维、诗学维、读者维、 赞助者维和目的维的基础上,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林译小说;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策略;杂合
“林译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长久以来,林纾的翻译就是译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之一。作为译者,林纾本人不通西文,只能与他人合作,25年间翻译了大约162部外国文学作品。这样产生的译文,其忠实性、准确性不免让人心存疑虑;而林纾本人又用文言文来翻译外国小说,对原作内容进行增删,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原作的某些文化因素进行归化。他这些大胆的翻译行为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学者们所津津乐道。对于林纾翻译的研究和评价,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景象,各种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而正如朱纯深所言,“在有些课题的研究中,换一个观察角度,便可能带来新发现新见解”。[1]为此,本文拟摆脱传统译论对于“忠实”“对等”的追求,放弃“归化”“异化”“直译”“意译”的绝对划分,引进“杂合”的概念,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对“林译小说”翻译策略进行重新解读与分析。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翻译中的 “杂合”
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胡教授在2004年所著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对该理论有详细论述。该理论的要点是“译者为中心”,认为翻译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具体来说,译文生成的过程就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也可以说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即译者选择译文)的总和。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可见,译文生成过程中的“翻译生态环境”由两部分组成:译者选择原文文本时原文、原语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运用特定翻译策略生成译文时译文世界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该理论还认为,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的评价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程度”最高的翻译。显然,该理论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同时对翻译实践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杂合”或称“糅合”,来自现代生物学,指不同种、属的动植物间的杂交行为及其结果。由于当今世界各学科之间的不断杂合,该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也被移植到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中,主要指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交融这一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这种文化间的杂合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多语杂合文本或单语杂合文本的形成。翻译正是译者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权衡,使“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也有一些来自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成分,二者有机地杂合在译文中,使得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原文,也与译入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因而表现出杂合的特点”。[2]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杂合”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是译者能动、多维地适应译文世界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二、“林译小说”的“翻译生态环境”
上文已经提到,“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文生成过程中的“翻译生态环境”由两部分组成:译者选择原文文本时原文、原语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运用特定翻译策略生成译文时译文世界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由于本文集中讨论“林译小说”的翻译策略,不涉及原语文本的选择,所以本节所探讨的“翻译生态环境”特指译文世界所构筑的“翻译生态环境”。
林纾的翻译生涯始于1897年,终于1921年,历时25年。从社会政治维来看,时值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整个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译者维来看,唯有译书才是“开民智”,报效国家的最迅速、有效的办法。林纾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爱国文人,起初想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方式报效国家,在历经七次失败之后便放弃了这条道路,后来,受梁启超等人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林纾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他说:“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3]。从读者维来看,林纾心目中的读者是士大夫阶层。这些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变得极为保守,害怕接受新事物,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而不得不将眼光投向西方。从交际维、文化维、诗学维和语言维来看,这些预定的读者对外界知之甚少,带有明显的排外倾向。在他们看来,尽管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和日本,但在文化上始终是影响世界的中心,单就文学而言,西方没有哪个作家能与屈原、李白等相提并论。再者,传统的中国文学一直推崇用文言文写就的诗歌、散文,用白话文写就的小说被看作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4]。后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能阅读文言作品在当时仍被看作是有身份、有知识的象征。再看赞助者维。林纾的前两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呼吁天录》由朋友资助出版。在这两部译作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商务印书馆便成了其主要赞助者。据统计,商务印书馆先后共出版了100多部“林译小说”。如何让作品最大程度受欢迎,赢得最广泛的读者群,进而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必然是其考虑的重中之重,也是对译者林纾的要求。
三、适应与选择下的“杂合”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但是,基于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维度,他的“适应性选择”也是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笔者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为切入点,就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的十部“林译小说”*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的十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吟边燕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拊掌录》《块肉余生述》《不如归》《离恨天》和《现身说法》。其中,《不如归》和《现身说法》是根据英文本转译的。与其原文进行比对阅读后发现,林纾的翻译并非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过度归化或任意重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半农先生的评论:“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转引自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46.)而是表现在语言、文化、诗学各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的 “杂合”。下文将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描述和分析林纾是如何、缘何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而采取“杂合”策略来呈现译作的。
(一)语言维的“杂合”及原因
林纾采用文言文翻译,大多数措词符合文言词法,多用四字格、叠词等;句子的组织也符合文言文法,如宾语前置、定语后置,这让译文带上了明显的归化特征。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林纾译文中所采用的“古文”与其著作中的“古文”还是有所区别的:译文中会出现一些十分奇怪的音译词,别扭的搭配和拗口的长句,正如钱钟书所评,“意想不到的是,译文中包含了很大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答’,却像通外文而不通中文的人的硬译。”[5]例如,林纾对称谓进行音译,对大多数人名、地名及物质名词或音译,或音译加注:几乎将原文中所有的“Mr.”“Miss.”“Mrs.”“Master”“Esquire”分别译为“密斯忒”、“密斯”、“马司忒”和“爱斯瓜尔”,在《黑奴吁天录》中,把人名“Eliza”译为“意里赛”,在《迦茵小传》中把“Samuel Rock”译为“三母尔洛克”,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把地名“Sheffield”译为“歇非儿”,在《块肉余生述》中把“Blunderstone”译为“白伦得司东村”,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没有将物质名词“pork”译为“猪肉”而是“斯汪”,并用括号加以注释“撒克逊语名猪者”;另外,对于一些货币单位如“franc”“pence”“shilling”等都进行了音译,而没有换算成当时汉语所对应的货币单位。再看句法层面。根据连淑能的观点,汉语句子的最佳度为7至12字[6]。林纾译文中大多数句子都能控制在此范围之内,但也不乏一些欧化的句子。如“来文杰私念格雷芙虽老,而言语锐厉,能爬搔人痛痒处。吾若决然许以爱玛者,彼亦仅能笑而不答,心自狂喜耳。天下穷人恒不择,难人多自炫,哀哉吾老友也!此事果成者,彼晚年当得噉饭之地。吾今但祝亨利勿胶己见,则事或可成;若龈龈讲节概者,则大事去矣。”[7]此句中,划线部分长达113字,动词“私念”后跟上了极长的宾语。显然,这样的句子不合文言句法,明显受了原文表达的影响。以上各种处理,让“林译小说”在语言层面呈现出“杂合”的特征。
不难理解,林纾在语言维的转换上采用“杂合”策略,是其能动地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中社会维、译者维、诗学维、读者维和赞助者维基础上做出适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为了让其心目中的读者士大夫阶层接受并阅读外国小说,进而达到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林纾采用该阶层极为推崇的文言文进行归化翻译;另一方面,上文所提及的各种异化处理,显然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为,而这又能帮助其赞助者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获得作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双丰收”。
(二)文化维的“杂合”及原因
阅读外国小说,带给当时读者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文化方面。怎样既能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外国小说,又能帮助他们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进而化解民族危机,这是林纾处理文化内容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杂合”策略无疑是最佳选择。现以“林译小说”及其原作中最突出的三个文化内容“宗教”“伦理”和“政治”的处理为例展开描述与分析。
宗教内容的处理请看下例:
"Pass on, whosoever thou art," was the answer given by the deep hoarse voice from within the hut, "and disturb not the servant of God and St. Dunstanin his evening devotions."
"Worthy father," answered the knight ,"here is a poor wanderer bewildered in these woods, who gives thee the opportunity of exercising thy clarity and hospitality."
"Good brother," replied the inhabitant of the hermitage, "it has pleased our Lady and St. Dunstanto destine me for the object of those virtues, instead of the exercise thereof. I have no provisions here which even a dog despises my couch; pass therefore on thy way, and God speed thee."[8]
久之,始有应门者曰:“孤客远行,吾为天主之小奴,方在晚祷,幸勿见呶。”此英雄曰:“道人听我,我为迷道之人,无地假宿,幸道人见容。”庐中人曰:“以理而言,当纳汝,惟屋中百无所有,刍豆皆空。天主佑君,君行可矣。”[9]
本例中,林纾省略了一些基督教内容,并对一些基督教内容进行了改写:没有翻译“St. Dunstan”和“Good brother”,将基督教中的“Worthy father”译作中国文化中的“道人”;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如将“the servant of God”译作“天主之小奴”,将“God speed thee”译作“天主佑君,君行可矣”。
再看伦理内容。为了增强译作的可接受性,林纾将一些西方观念进行改造和调试,使之符合中国伦理。如《现身说法》中的“居丧一年”被改为“居丧三年”,《块肉余生述》中描写女子贤淑的四个形容词“good”“beautiful”“earnest” 和“disinterested”在林纾笔下变成了“德言容工(四德)”。有时林纾又对一些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进行了保留。譬如,《迦茵小传》中为了更好的表现出女主人公迦茵的自我牺牲精神,唤起国人为国献身的移情意识,林纾保留了迦茵未婚先孕的内容。可见,在读者维和社会维的适应上,林纾选择了后者。
林纾在政治内容的翻译上也采取了“杂合”策略。如:
"He is, to some faded courts held in Doctor's Commons——a lazy old nook near St. Paul Churchyard——what solicitors are to the courts of law and equality."[10]
“此浪迹之律师,无定踪也。此等人专在圣保罗礼拜堂隅陬之间,为会审员,若律师则为人辩护于公堂,此浪迹之律师则但陪庙鞫耳。”[11]
该例中,林纾采用了异化手段保留了西方司法体制中的一些表达,如“律师”“会审员” ,但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又将“courts of law and equality”做了归化处理,将其译作“公堂”,同时兼顾了译者维和读者维。
(三)交际维的“杂合”及原因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有其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正如Vermeer所认为的那样,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语篇”[12]译者在交际维上所做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目的维和读者维的结果。上文已提到,林纾始终将“开民智”作为其翻译事业的旨归。为此,在交际维的转换上,林纾大多保留了原作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倒叙方式、章节安排和大篇幅的描写性内容。这对习惯了章回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新颖与震撼的。章回体写就的传统小说发源于“话本”,通常划分为不同的 “回”,每个“回”之下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按时间先后讲述,有整齐对仗的标题;每个故事均通过第三者视角以“话说”“且说”“再说”等开头,以“请听下回分解”结束;不重描写,一笔带过。为了适度缓解冲击,保证译作的接受性和读者群的广泛性,林纾按中国诗学传统适时进行了一些改造。如在《块肉余生述》中,林纾将原文中的 “Whether I shall turn out to be the hero of my own life……”译作“大卫考伯菲曰:余在此一部书中,是否为主人翁者……”。“大卫考伯菲曰”的添加顺应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如,狄更斯用了大量文字对Doctor Strong 进行了描写,林纾却用“衣履不甚休整,见余似无神采”一笔带过。遇到倒叙内容,林纾在保留的同时辅以解释。如《撒克逊英雄劫后略》的第二十一章属倒叙部分,林纾在该章开头用“吾书叙洛克司列部署迄矣,今且回叙被劫之众”进行了过渡、解释。这些异化与归化并存的处理手法让译作带上了鲜明的“杂合”特征。由于林纾的译介和坚持, “林译小说”成了中国新小说的模仿对象,开启了中国新小说的先河,其本人被称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可见,林纾在交际维上所做的适应与选择是多么恰当与成功。
四、结束语
林纾的小说翻译并非一味地归化,而是归化与异化并举,并行不悖;林纾在其小说翻译中采用的是“杂合”策略,这种“杂合”是表现在语言、文化、诗学各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的 “杂合”;是其多维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社会维、译者维、诗学维、读者维、赞助者维和目的维的基础上,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翻译适应选择论从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的方法。这样,像“林译小说”等作品,不仅可以享有感性的赞誉,而且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解释,翻译批评也会因而变得更加多元和宽容。此外,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林译小说”的“杂合”现象,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如何把握“杂合”的适度性,如何正确把握“翻译生态环境”,我们都可以从林纾的小说翻译中得到启发。
[1] 朱纯生.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 [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44.
[2] 王秀梅. 翻译杂合性与汉语的演化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4):124.
[3] 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33.
[4]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司,1996: 125.
[5] 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312.
[6] 连淑能.英汉与对比 [M].厦门:厦门人民出版社,1993:64.
[7] 哈葛德.迦茵小传[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0.
[8] SCOTT W. Ivanhoe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 2006: 143.
[9] 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M]. 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0-81.
[10] DICKEMS C. David Copperfield[Z].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 280.
[11] 狄更斯.块肉余生述[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4.
[12] NORD C.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 2006: 12.
[13] 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2):54.
[14]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陶震华]
AProbeIntothe"Hybridity"intheApproachofTranslationasAdaptationandSelection——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Strategy
ZH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China)
By bringing in the notion "hybridity" to re-examine Lin Shu's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he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his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Lin Shu takes "hybridity" a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ch is reflected on the level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poetics. It is his adaptation/selection focu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society,himself as a translator,poetics,readers,sponsors as well as his purposes of the then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translated novels by Lin Shu; the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hybridity
2014-04-15
张 锦(1980-),女,甘肃白银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H315.9;I046
:A
:1008-6021(2014)04-0067-05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