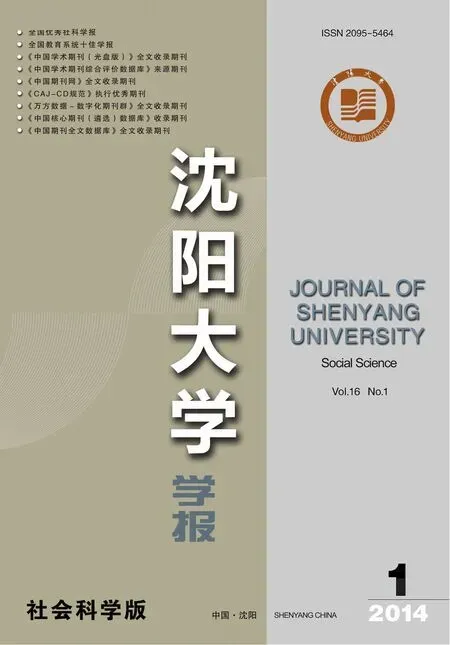论孟子德性思想之情理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 敏,杨文宇(陕西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陕西西安 710021)
论孟子德性思想之情理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 敏,杨文宇
(陕西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陕西西安 710021)
从“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耻感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性格方面的体现,乐观精神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三个方面,论述了孟子伦理的基本内容。认为孟子伦理不仅在理论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风格和发展方向,而且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德性思想;情理精神;中国文化
西方道德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把道德与知识当作纯粹理性的认识逻辑,德性的形成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到了近代唯理论的先驱笛卡儿,更是“强调演绎推论,理性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康德道德哲学虽然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与中国道德哲学中的情理相比,德性还是倾向于理性。被西方公认的理性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里,伦理精神是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中辩证发展的,其理性主义特征不言而喻。即使是西方后来的非理性主义者,也是在理性研究受到制约的情况下,转向对神秘的非理性境界的探寻。如“近代的耶可比和谢林,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们和海德格尔,其实都是把传统的理性运用到极致的理性主义者。”[2]这与中国道德哲学中蕴含的情理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从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正是孟子真正系统地把“情”提升为“道德情感”,第一次在形上的层面发现了道德之情、伦理之情,开创了以情理精神为核心的德性论之先河,不仅在理论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风格和发展方向,而且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耻感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性格方面的体现;而乐观精神则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
一、面 子
“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世俗生活中的表现,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社会赋予一个人在某一特定共体或伦理实体的人格,它既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资源能力,更代表着一种社会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世俗性表现。”[3]301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面子’的观念。”[4]319林语堂先生则将“面子、命运、恩典”认作统治中国的三女神。其中,面子居其首位。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讲,“面子”极其重要,它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也表现出了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面子”?樊浩教授认为:“‘面子’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在‘礼’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实体中安‘伦’尽‘份’所获得的社会性人格及其成就。而一旦失去与他的伦理份位相对应的地位和成就,便会感到‘耻’。”[3]304可以说,“面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它依赖于人们彼此之间的心意感通和情感回报。如果一个人在对方需要之时给予相应的关怀、帮助,就是给“面子”。对方给自己“面子”,自己一定要“领情”。当下次遇到类似的境域时,自己要“知恩图报”,给对方以“面子”,还以人情。而不给“面子”则意味着不尊重人格价值。“面子”与“脸”是相互牵连的,它们是人们获取声誉以及稳固或提升地位的标准。“面子”在中国代表一种声誉,是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是对个人;伦理身份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人的价值与尊严。而“脸”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会履行应尽的义务。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它代表社会对于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则个人便很难继续在社群中正常运作。‘脸’不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约制力量。”[5]可见,“脸”是涉及个人道德品格的概念,是个人对自己是否遵照合宜的行为规范的判断,它是决定“面子”多寡的条件之一,一旦失去了“脸”,“面子”便很难维持。不顾自己的“面子”是无耻,不顾他人的“面子”是无礼。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可以不要“面子”,但绝不能“不要脸”,因为“不要脸”意味着道德人格的破坏。对于“面子”来说,适度的名声、声誉的宣扬,可以树立个体至大至刚的形象,不但自尊自爱,而更重要的是促使自身以道义标准来对待他人。
也正因为如此,通情达理、合情合理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品格。在儒家那里,通情、合情也就是有情的本质与核心是恻隐之情,即在人与人之间以情感为互动的媒介。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道德情境下,能理解、体谅他人的感受,喜其所喜、恶其所恶、哀其所哀。正因为人能够通情、有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才能得到贯彻。孔子通过爱亲、爱人之仁方面为培养通情、有情之人奠定了基础,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之深化。他认为,同情他人的不幸遭遇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非人也,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讲,情比理更为重要,如果不合情就很难达到合理。
二、耻 感
耻感是道德主体的意识和行为与伦理普遍性产生距离,或违反伦理普遍性的规定和要求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能力,其“哲学根源和本质力量是人对自己的普遍本质即伦理性实体的认同和皈依。”[3]302在孔子那里,耻感既是德性的起点、动力,也是德性的最高体现。孟子则把这种情感能力即羞恶之心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之一,强调“耻”对于德性人格的根本性意义。“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之所以耻感成为人的本性之一,就在于人有主观自觉的能力,人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自觉意识认识到作为特殊性的“我”与伦理普遍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距。而人的本质存在应当是作为伦理实体性的存在。当人没有达到这种本质性存在时,就是人自身与伦理实体、伦理普遍性的差别、距离,当人意识到这种差别和距离始就会产生耻感。“耻之于大人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人不可以无耻矣,无耻之耻,无耻矣。”(同上)后来的荀子把孟子的“羞恶之心”深化为“荣辱之辩”;法家的管子则更是把“耻”提高到了“国之四维”之一的高度,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的防线。若守不住这个防线,国家的命运便万劫不复。
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差别和距离的话就是没有“面子”和“脸”。当一个人“面子”受损时,便会产生一种羞耻感。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西方那样通过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法理来调节,而是通过彼此之间的心意感通和情感回报来维持。“面子”体现的是正面的情感回报,而耻感则是人在交往中,由于不顾情面或知恩不报得不到他人认同而产生的一种愧疚、不安的情感。耻感具有很强的自律特征,它“完全与行为的他律无关,是一个人因有理想的境界,或有一理想之自我认同”,当“不能达到此一理想或不能满足自我的认同时,就会产生耻感。”[4]342可以说,耻感是维持情感回报、实现人伦和谐、人性提升的重要机制,也是一个人自觉修身、挺立德行人格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人的心理,“知恩图报”是一种重要的品德,当一个人“忘恩负义”时,便是无耻,这是对一个人彻底的伦理否定与道德唾弃。耻感激励人“知恩图报”,以此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回报”,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互动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畅通无阻,从而实现人伦和谐。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情、理、法当中,始终把情放在第一位,“情在理先,法在理后”。情成为协调人伦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首要机制。当情讲不通时,才诉诸于理,若理亦不可行,最后才用之于法。在中国人看来,“对簿公堂”是无奈的选择,是“不顾情面”、“撕破了脸面”。一个有耻感意识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合理的道德规范之中,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体向善的重要激励力量。由于中国人心中沉淀着深厚的耻感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都会涌现出众多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人士。
三、乐观精神
情理精神除了体现为面子与耻感外,还培育了一种特有的乐观精神,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一方面表现为刚健进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
“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八年》)是儒家一贯的刚健进取精神。《易经》中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乐道”精神、孟子的“浩然之气”都是进取精神的具体表现。孔子追求的“乐”是一种在道德逆境中亦能“求道”、“行道”、“持道”的仁者之乐,而孟子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乐除了内涵仁者之乐,还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孟子与孔子具有不同气度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给人们的感觉是老成持重、温良恭俭、心平气和;孟子给人们的感觉是生机勃勃、刚健果敢、心直口快。若说孔子有圣哲风范,孟子就具有英雄气概。”[6]正因为孟子的这种刚健果敢和英雄气概,所以他的乐观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世的自信。孟子处于先秦的战乱时期,当时各国崇尚武力、处处充满杀机,然而孟子一改怀“道”之人的忧思,确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与信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而中国人即便是“知命”,但仍奋力拼搏。正如梁漱溟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乐观精神时所言:“知命而仍旧奋发,其奋发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失败,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之谓,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又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7]同时儒家的乐观精神又倡导人在日常生活中“知足常乐”,使人始终保持一种中庸平和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养性情之正。这种“知足常乐”的精神一方面肯定人的私欲的正当满足,另一方面告诫人不应当囿于私欲。正因为中国人的“知足常乐”,不为私欲所纠缠,因此不仅能在社会中形成其乐融融的景象,而且也能与自然融洽和谐。
乐观精神除了以上两种表现外,还包含了四种境界,亦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自然境界中,人只知道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需求,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境界虽处于最低阶段,但却是个体的必然需求。功利境界中,人逐渐摆脱动物本能的驱使有了自我意识,不再满足最低的生存欲望,而是进而要求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以使自身能够优越于他人。道德境界,是先秦儒家在“此世间”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其本质是人的道德价值得到实现和认可后而体验到的生命的安适和满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就是这种的道德境界的体现。天地境界是儒家乐观精神所体现出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中,个体完全摆脱了自我任意性的束缚、道德他律的强制,完全进入到道德的自律状态,即进入到一种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之中。“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当个体把自己融入到宇宙的大生命中时,就能体会到“赞天地之化育”的“生生”之意,达到“与天地参”,从而进入自由之境。此时,物我一体、天人合一,道德上的“应然而然”成为了生命活动“自然而然”,亦即道德规律成为了自然规律。
总之,比起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情理精神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情因按照理所规定的秩序发挥自身的伦理统一力而具有道德属性,成为德行的内在动力;理虽然给予情以运作和扩充的秩序,但是必须建立在情的基础上,德性才能找到最终的根基。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认同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那么,他就会自觉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因情而有义,在这里非理性的情感却导出了理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理”精神的奥妙所在。情是理的根本,只有建立在情之基础上的理,才是通情达理,才能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然而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如果将人情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当作实现一己私欲的工具或手段时,人情互动就会发生异化,成为束缚人、制约人的异己力量。人情在法治领域的泛滥,必然产生诸多弊端。较为严重的就是违背,甚至践踏社会的伦理、正义,使各项法律规范充满弹性,降低了其公正性与严明性;在政治领域,正是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使得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成为可能,败坏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1]王英.黑格尔对抽象的普遍的辩证法批判:以《精神现象学为例》[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7.
[2]邓晓芒.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J].现代哲学,2011(3):48.
[3]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01.
[4]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8:319.
[5]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
[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104 105.
[7]梁漱溟.东西方文化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4.
【责任编辑 田懋秀】
Impact of Sense and Reason Spirit in Mencius Virtue Thought on Chinese Culture
Wen Min,Yang Wenyu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21,China)
The basic content of Mencius’ethics is discussed:the“face”“shame”and“optimism”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emotive reason spirit reflected respectively in Chinese social life,Chinese people’s characters and Chinese spiritual life.It can be said that emotive reason is the key to Chinese culture.Mencius’s ethic not only determined in theory the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al life of Chinese people.
Mencius;virtue thought;spirit of sense and reason;Chinese culture
B 222.5
A
2095-5464(2014)01-0136-04
2013 03 11
文 敏(1980),女,陕西泾阳人,陕西科技大学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