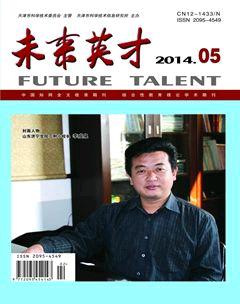哲学意识下儿童的诗性智慧浅议
马季梅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关注人的转向的研究,一些十分重要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都十分重视从“诗化”、“诗性”的角度入手,思考语言的本体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从儿童的立场出发,如何将“诗性”与“童性”有机融合,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诗性智慧。
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不妨这样理解儿童的诗性智慧:它是儿童最初的智慧形态——一种强烈的感觉和广阔的想象力,是儿童的个体生命与外界相遇时,通过自己已有的经验和创造生成能力,逐渐形成对自我、对人生、对世界带有审美能力的体悟。
之所以如此重视诗性智慧,是因为在理性的统治下,儿童最大的失落就在于失去了生命原初具有的诗性智慧,割断了感性和理性的天然统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儿童诗性智慧的研究恰恰能够找回儿童失落的东西,不断生成和涵养儿童的生命智慧。
新生代小语名师周益民老师就很擅长从诗意语文的角度,点亮儿童心灵的诗情,唤醒儿童内心深处与童话世界共同的梦幻家园。下面就以他执教的《逆风的蝶》为例——
……
师:大家已经读出了自己的体会。同学们,文字中是有温度、有声音、有丰富的感受的,再静静地看一看,是否会有新的感受?(生默读,体会)
生:我似乎听到了蝴蝶喘气的声音,他飞得好艰难啊!
生:我似乎感觉到了蝴蝶被风吹裂的伤口,多疼啊!
生:我觉得蝴蝶此刻一定非常寒冷。
师:你们用心感受,便走近了蝴蝶。看着他艰难的飞行,想着他忍受着剧通,真让人心疼。带着这样的感受朗读这几句话。(学生朗读)
师:狂风蹂躏着他,撕打着他,吞噬着他,看着风中艰难飞行的蝴蝶,同学们,让我们来劝劝他吧。
生:蝴蝶啊蝴蝶,你歇一歇吧,多累呀!
生:蝴蝶啊蝴蝶,风太大了,你明天再去吧!
生:我说蝴蝶,你今天就别去了,否则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呢!
师:蝴蝶是怎么想的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吧。(出示)
“那儿有一棵蔷薇,我们去年相约,今天是我和她相会的日子。”
“我可不能等,真的不能等,我不能让她失望。”
“今年她只为我开放;如果我今天不能和她见面,她就会凋谢。”
“在别人看来,她也许是一朵普普通通的花,但对我来说,她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该呆在帽子里,让您带着我走。我要自己飞到她的身边。即使这大风阻挡我飞到她那儿,我的灵魂也会飞去见她。”
(学生各自轻声读,随后老师和个别学生对读,再和全体学生对读)
师:啊,蝴蝶,是谁给了你力量,让你如此地坚强?
生齐:“那儿有一棵蔷薇,我们去年相约,今天是我和她相会的日子。”
师:我们到那边的亭子里歇一会儿,等风停了再赶路。
生齐:“我可不能等,真的不能等,我不能让她失望。”
师:为什么,这约会那么重要吗?
生齐:“今年她只为我开放;如果我今天不能和她见面,她就会凋谢。”
师:那是怎样高贵的一朵花啊!
生齐:“在别人看来,她也许是一朵普普通通的花,但对我来说,她是独一无二的。”
师:来吧,来吧,快来避避风,刚才多危险啊!
生齐:“我不该呆在帽子里,让您带着我走。我要自己飞到她的身边。即使这大风阻挡我飞到她那儿,我的灵魂也会飞去见她。”
神奇的文字魅力冲破了人与自然生理性的界限,儿童打破了思维的束缚,把阅读的自身演变成了逆风飞翔的蝴蝶,从身临其境地仿佛看到挣扎的蝴蝶——“我似乎感觉到了蝴蝶被风吹裂的伤口,多疼啊!”到口不能不言,情不自禁地“飞”到蝴蝶身畔劝慰蝴蝶:“我说蝴蝶,你今天就别去了,否则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呢!”后来,在老师一步步走向泛灵性殿堂的引领下,儿童达到忘我的境界,他们不再是自己,俨然变成了一只只逆风飞行的蝶,一只只意志坚定、向着友谊、美好、梦想展翅的蝶:“我不该呆在帽子里,让您带着我走。我要自己飞到她的身边。即使这大风阻挡我飞到她那儿,我的灵魂也会飞去见她。”
如果让成人来进行阅读,未必能够有这么真实的联想产生。究其原因,儿童的泛灵现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赋予万事万物以生命,他们天赋的诗性智慧帮助儿童对诗歌的阅读鲜活起来。由此可见,泛灵心理会让儿童在审美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儿童更深入地进入到文本所描绘的虚拟世界,并以文之乐为己乐,文之悲为己悲,一花一草皆有生命,一文一字皆入吾心。
懂得了儿童智慧的泛灵性,笔者又思考: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试验儿童的泛灵性?儿童能够把世间万物赋予生命,逆向思维,也一定能够把自己放入具体场景中,幻化为世间的万物。为了求证,老师先给孩子们读一首儿歌:
ɡuò shān chē
过 山 车
shànɡ tiān le , rù dì le ,
上 天 了 , 入 地 了 ,
ténɡ yún le , jià wù le 。
腾 云 了, 驾 雾 了 。
ɡuò shān chē, xià shān le ,
过 山 车 , 下 山 了 ,
wǒ biàn chénɡ ,liú xīnɡ le。
我 变 成, 流 星 了。
抓住“我变成,流星了”一句,启发孩子们发散思维:(什么时候),我(变成什么)。
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孩子们的思维如泉涌,激起朵朵灵性的浪花,让所有的成人自叹不如——
吃蛋糕的时候,我变成了小花猫;
我妈妈想打电话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手机;
荡秋千的时候,我变成了快乐的小鸟;
滑下来的时候,我变成了旋风;
上学的时候,我变成了小学的太阳花;
看《天空之城》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飞行石,飞起来了;
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变成了爱心;
挨骂的时候,我变成了小可怜虫;
玩儿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小皮球,蹦来蹦去;
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小聋子;
速滑的时候,我变成了兰博基尼;
睡觉的时候,我变成了毛毛虫;
……
难怪诸多大师都感慨: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儿童在遭遇语言文字时所表现的泛灵性,不仅仅表现在他与描绘对象之间的同一,而更表现在他对艺术形式的生命感受和美的表达。很多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如歌德、贝多芬都是具有泛灵倾向的,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保护儿童的泛灵性,具有泛灵性的儿童才能真正展现诗性智慧,并在诗性智慧的引领下创作出色的作品。
(二)儿童诗性智慧的幻想性
我国著名民间故事家刘守民指出:“儿童欣赏故事的快感来自故事的深层结构同儿童心理结构的自然契合,使儿童从故事中发现了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儿童对幻想性故事的偏好,在于故事与儿童的精神智慧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儿童喜爱欣赏一个故事,决不是为了深入体会主题意义、社会价值、人生哲理等文本的深层内涵,而是故事中奇妙的童话幻境、无所不能的天使仙人,惊险奇特的人生经历等这些无拘无束的想象牢牢吸引了儿童,他们契合了儿童好奇思爱幻想的天性,顺应了儿童与生俱来的诗性智慧。
以皮亚杰的认识发展理论来看,3~6岁的学前儿童处于儿童智慧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前运算阶段(2~7岁)。这一阶段是感知运动阶段到智力性概念阶段的过渡,是自我中心表征活动阶段。幼儿在这一阶段思维较前阶段有了质的飞跃,过去他们常常束缚于眼前的实际具体之物,现在能够用象征来代表他环境里的物体、地点和人物。想象也在这一阶段发生并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是儿童想象力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的思想可以超越此时此地而自由飞翔。
如果教师能够在儿童幻想性飞速发展的时间段,有效进行智慧启迪、诗意创生,帮助儿童发展思维,那么对于儿童的一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园中有一枝烂漫的花束——“读写绘”实验,它一针见血地穿过了无数迷人眼的“乱花”,直指儿童语言、思维、想象等发展的核心——诗性智慧。
新教育实验开展的“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阅读的最初一级就是“读写绘”。在基本的教学策略中有这么两条:儿童将老师讲的故事复述给父母听,然后完成写绘作业,将故事进行创造性地续编并以“绘画+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幼儿园及一年级的孩子,可由父母将孩子讲述的故事内容帮助写在孩子的绘画作品上。
笔者执教一年级时,借鉴了“读写绘”的做法,将之融入课堂,的确收到了一箭三雕、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
有一个绘本故事叫《我妈妈》,读给孩子们听时,孩子们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有趣的故事和丰富的想象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心灵。我又让孩子们想想自己的爸爸,鼓励他们创作一本有关爸爸的绘本。孩子们出色地完成了创作,有一个孩子图文兼美,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其水平不亚于专业的绘本大师,令人惊叹。
如图:
画本上,为了表现爸爸爱“我”,把自己画在爸爸的掌心;表现爸爸很累,休息的时候呼呼大睡,就在床上画了一只酣睡的猪;生气时候的爸爸直接变成了一只大老虎;而游戏时的父女又成了一对蚂蚁;呵护自己的爸爸是一把巨大的伞,大伞下的小伞甜甜地喊着:“爸爸!”
可见,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让他们进入到广阔的幻想空间。想象,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与天赋。及时把握儿童想象的契机,因势利导,提升儿童的思维品质,语言智慧的深度就能够呈现儿童灵思的深度。儿童的创作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游戏,而变成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连同自己的灵魂一同带出的;是一种儿童心灵与文字、绘画的审美对答。坚持这样的习得,必定可以将儿童的生命推上高高的诗性智慧之巅!
(三)儿童诗性智慧的体验性
儿童智慧的体验性是一把帮助他们打开诗意大门的钥匙。
伏尔泰是将儿童体验上升到生命本体论的第一人,他认为,体验即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以思悟之。只有通过体验,儿童才能真切而内在地将自己置身于语言文字的环境,并与作者、文字的生命融为一体。体验打开了旁人与儿童、儿童与世界的障碍。体验关乎儿童的生活方式,即儿童人生诗意化的问题。儿童的生命体验和诗意表达不能借助逻辑思维,而只能借助由儿童的个体生命进入到诗歌生命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一起。
庄子曾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其实是将儿童审美对象的感受和经验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耳目感官的初级体验;二是心意情感的中级体验;三是直觉精神人格的气的高级体验。
试以儿童解读苏教版四年级上册《江雪》,来对儿童诗性智慧的体验这一动态过程进行分析:
师:孩子们,你从什么地方读到当时雪下得很大呢?
生:从“鸟飞绝”和“人踪灭”。正是因为雪很大,所以看不见鸟和人。
生:还可以从“寒江雪”看出来。我想江面上可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所以非常寒冷。
师:老师有个问题不明白——雪这么大,天气如此寒冷,老渔翁为什么要出来钓鱼?
生:渔翁很坚强,很乐观。
生:渔翁很孤独。我从“孤舟”和“独钓”体会到的。
生:渔翁很寂寞,很无聊。我也是从“孤舟”和“独钓”想到的。
[分析:儿童这一层的体验正是耳目感官的初级体验。从“鸟飞绝”、“人踪灭”看出雪很大,画面上没有人。从寒冷联想到老渔翁非常坚强和乐观。应该说,此时的儿童还是一个置身物外的旁观者形象,所以诗歌的画面到达了儿童的脑海,然而,诗歌深处以诗人整个生命为背景的诗意并没有占据儿童的心灵。]
师相机出示补充资料一:
唐朝中期朝政腐败黑暗,柳宗元积极参与了“永贞革新”运动,可是革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他被贬至人烟稀少的永州。此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亲戚、朋友也不在他的身边,唯一的老母亲随他来到永州半年后去世了,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怕被牵连,周围的人都不敢和他接触。
师:读了这段话,你想想老渔翁为什么冒着风雪出来钓鱼呢?
生:他当时很孤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生:他当时孤独无助,内心是痛苦的。
[分析:以柳宗元所处的境况作补充资料,帮助儿童深入体验诗歌,儿童处在心意情感的中级体验,以自己的生活情感经历影射柳宗元被贬谪、妻离子散时孤苦伶仃的心理,从刚才只能眼中看到雪,到现在体验到诗人的心灵深处那份抑郁愁闷。对于诗歌的审美体验提升了一个层次,儿童自身的诗性智慧也得到了彰显。]
师相机出示补充资料二:
柳宗元被贬后,他的政敌仍不肯放过他,四次派人对他的住所放火,还不停地诬蔑攻击他。因为生活的困苦,柳完元还生了好几场大病,差点死去。但是柳宗元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屈不挠地与政敌进行着斗争,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诗篇。
师:随着对柳宗元了解的深入,你把自己放置在他的冰天雪地体验一下,想想柳宗元乘一叶扁舟,他钓的仅仅是鱼吗?他还想钓什么呢?
生:柳宗元钓的是一种心境,不被世俗叼扰的清静世界。
生:我觉得柳宗元在钓一种解脱,他经受了那么多磨难,在这纯洁无瑕的白雪里,没有那么多肮脏和丑陋,他可以干干净净地活着。
生:我觉得柳宗元在钓一个明君。朝廷不相信他,皇帝不肯重用他,他空有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所以他一定在钓一个明君,能够识人才、明是非,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来。
生:我觉得他在钓一个春天,一个自己能够洗清冤屈的春天,一个天下百姓幸福快乐的春天!
[分析:儿童的审美体验,作为儿童对世界的审美把握,直接呈现出儿童生命的深度。儿童从一片沉寂的画面中,渐渐体悟到渔翁精神世界之光在扩展,传达出诗人在世俗里坚定求索的执著。可以说初步达到了直觉精神人格的气的高级体验!还可以再深一层去细细体味,从生命、宇宙的高度出发,教师可继续带领儿童行走于体验的长廊,蓦然警醒:渔翁身居千山万径之中,泛舟江湖之上,俯仰宇宙而心宇澄静。这样的体验才是儿童生命里的沉醉迸发。只有体验才能照亮生命存在,唤醒沉睡的自我意识,达到精神内海的感悟。]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诗性引领下阅读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与工匠式地完成一件作品是截然不同的。诗性阅读下的文本相遇过程是无预设的,通过儿童不断的领悟和体验,在不断变化中生成了最后的习得。可以说,这样的文本解读是儿童在某个时空以自己的生命与文本相遇而成的结果。这样的解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有生命力的。反之,如果儿童阅读时仅仅模仿声、形,机械式地重复他人,那么这样的解读是肤浅的、缺乏生命力的。蕴涵诗性智慧的文本解读有了永恒性和超越性,人们可以通过对它的欣赏而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与创造。
当然,虽然很多语言大师说儿童是天才的艺术家,并且试图从儿童的语言中寻找创作的灵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儿童的艺术已经相当完美了,因为儿童的诗性智慧处在一种朴素的状态,儿童所具有的诗性智慧仍为初始,对于儿童教育来说,首先要保护儿童本能的诗性智慧之种子,另一方面不断发展、丰富、提升他们的诗性智慧,使他们在不失去自己天性的语言感悟的完整性的同时,体悟生命、感受意义,引导他们完善自己的童性,丰富自我的想象,提升自己的思维,不断走向诗性的王国,用诗性智慧创造出更多、更美好的语言、艺术世界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