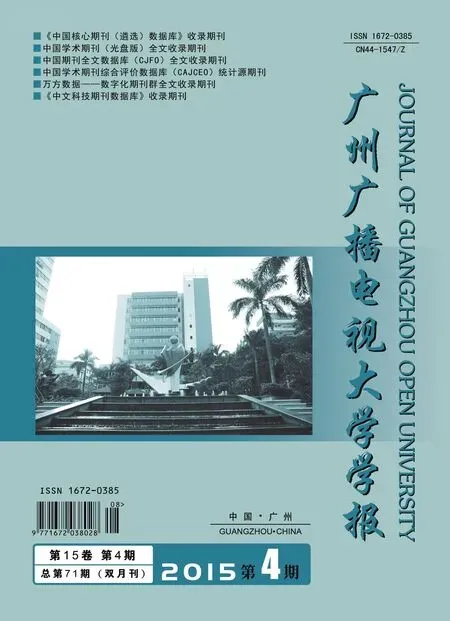南朝时期“言与志反”现象研究——以谢朓诗为例
摘 要:“言与志反”现象存在于中国古代某些诗人的诗作中,尤其在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以贬抑的态度评价 “虚述人外,言与志反”这类诗歌的矛盾特点。笔者欲从剖析总结这类诗歌的特点出发,选取谢朓为研究对象,结合谢朓“言与志反”诗歌创作的范式、成因、实质三个方面,探讨和研究这类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收稿日期:2015-06-06
作者简介:许瑜娜,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体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曾经批评这样的文章风气:“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幾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 [1]为什么刘勰对当时的文章风气有这样的评价?其主要是为了强调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的观点,更遑论因“采滥忽真”而作出“言与志反”的作品。本文拟从谢朓的诗体范式入手,探索刘勰的评定出处。
一、“言与志反诗”的文体特征
“言与志反”一词出自《文心雕龙•情采篇》,根据文中作者的阐述,“言与志反”指热衷高官厚禄,却反而空虚地歌唱田野的隐居生活,一心牵挂世俗的政务,却又空说尘外的逸趣。
“言与志反”的现象古已有之,翻阅《遂初赋》、《秋兴赋》、《思归引》等汉晋时代的作品,已是颇有“虚述人外”的意味。 [2]
到了南朝时期,这类作品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南朝之前的文人们空唱归隐之歌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高蹈出世的姿态,那么到了南朝,随着时间的累积,玄学的发展,道家学派的重新抬头,社会政治的愈加黑暗,以及贵族文人没落的家世背景,这时候的文人唱这首隐逸之歌,更添有在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两者间的痛苦撕扯,在建功立业和飘然远去的矛盾中难以抉择,然而,这种犹豫和徘徊,是以道家的出世希求来掩饰文人们对高官厚禄的渴望。
从诗文中不经意表现出“言与志反”意味的文人不在少数,除却汉代刘歆、晋代潘岳、石崇等南朝前的人物外,在刘宋时期的谢灵运,其玄言诗化的山水诗,也是这种范式的代表,只是到了谢灵运手里,这种范式又有所改变,谢灵运本身功名之心就很强烈,以“宜参权要”自许,对自己的才能有绝对的自信,所以才会因得不到重用而“常怀愤恨”。 [3]
尤其在谢朓这里,结合他的作品看其人生经历,他清新自然的诗风似一条叮咚作响的小溪,流入读者躁动的心田,使人获得一份安宁,思绪得到沉淀。无怪乎梁武帝萧衍有“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①的高评。只是看谢朓的生平,为官做宰是他内心的渴望,毕生的追求,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时可谓意气风发,是“竟陵八友”之一;在荆州萧子隆府上时,以文才颇为子隆赏识,“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受,流连晤对,不舍日夕”。 [4]直至被王秀之进谗告密,仿佛晴空一霹雳,春天一下子进入秋天,诗人的心理发生急剧的变化,本来比较软弱的性格又遭遇背叛,忧谗畏讥成为他此后人生的一个基本状态。经历此次劫难,谢朓在诗歌中的隐逸意愿非但强烈而且不乏真诚。如果说先前某些诗篇表达隐逸只是顺应时代风尚,到了此时,他的思想已悄然变化,情绪激动时,便一直向往游弋于山水之中的隐逸生活,但是一旦回到现实,谢朓比任何人都知道他不愿隐逸,而且从不讳言这两者的矛盾,诗人的后半生就在这种撕扯中痛苦着。
谢朓和谢灵运两人在人生经历和结局上有某些惊人相似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性格。谢灵运因才高,地位也不低,故时常是一种睥睨的姿态。而谢朓本身性格就较为软弱,又因为门单且家世没落,已没有谢灵运式的自信,再加上宫廷政变频繁,血腥残酷,所以谢朓面对政治时有忧惧也有焦虑。
正是源于这种心灵上的痛苦与焦灼,谢朓试图在诗歌中寄意隐逸以寻求解脱,但在现实政治中谢朓又没可能真正做到,于是他的诗中出现“言与志反”的现象就尤为频繁。而后来的诗人一旦在仕途中失意,就难免偶有如此种风格特点的作品的创作与流传,只是没有谢朓这样的数量以及旨意的集中罢了。
评论家诸如刘勰、钟嵘,或者是后来的何焯、方东树 ②对于谢朓这种“虚述人外,言与志反”是颇含贬抑的。而从谢朓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选择上来看,与其说其中带有贬抑之韵味,笔者却宁肯说如刘勰一类的读者其实是谢朓的知音。因为这类诗恰恰表现了谢朓厌弃官场却又对爵禄难以忘怀的矛盾心理。这类诗是他自永明时期之后心境的真实写照,是他难以超脱的写照,评论者对其带有贬抑,又或许可以理解为其对谢朓的境界期望高于谢朓所能达到的境界。
二、谢朓“言与志反”的诗体范式
以曹融南先生的《谢宣城集校注》为底本,观看现存的谢朓诗文,其在诗歌中强烈表达归隐夙愿的,主要集中在从萧子隆府中遭谗被召还的永明十一年至离开宣城的齐明帝建武四年这三年里。
谢朓钟情于山水,对山水诗派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他的一类“虚述人外,言与志反”的作品,常常表现为于描山画水的末尾处表达归隐的愿望。
钟嵘在《诗品•齐吏部谢朓》中是这样评述谢朓的:“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世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 [5]其中“末篇多踬”后人多予以申辩,论证谢朓诗文并不“多踬”,而于钟嵘本意,也不是含贬。如果从“言与志反”这个方面来说,评其“末篇多踬”也因其篇篇隐逸之旨。
魏晋南北朝时代,玄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6]在这整个时代里,玄学达到了鼎盛,玄谈占据了士大夫朝里朝外的大部分生活。士大夫的玄学思想受到儒、道、佛三家的强势影响。很明显的是,士大夫在玄谈中所涉及的归隐念想,所企慕的仙风道骨,来自于道家。在这个以谈玄说道为风尚的时代里,谢朓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但谢朓的隐逸愿望与这个时代的文人又分明不同。
谢朓诗中的隐逸是波动的,以时间为节点的话,分别有得遇于萧子隆时期、萧鸾称帝时期、外放宣城时期。谢朓常以恢复先祖气象为己任,也即“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的夙愿。无论在竟陵王子良西邸,还是荆州萧子隆府上时,都得遇于主上,颇有少年意气风发之势,此时诗中的归隐意向纯粹是时代风气对诗人的同化,并不见得真有归隐的心思,只是感染了时代风气而已。作《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7]时是遭王秀之背后进谗而被召还。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王秀之是随王萧子隆府上的一名长史,因嫉妒谢朓得到随王的顾遇,故向齐武帝进谗,企图离间萧子隆和谢朓的关系,结果就是谢朓被召还京。如“鹰隼”般随时准备陷害他的小人,政治环境又似“严霜”般令人不自禁打冷颤。“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传达出谢朓的忧惧惶恐,也算是开启了以后进退难保的状态。“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这一句满满的高蹈姿态,此时的王秀之还在西府任上,作这首《赠西府同僚》中的同僚自然也包括王秀之,推想而知,此时的谢朓,既有遭人陷害的苦闷感,但同时因自己已远离是非之地心情暂时放松了。在回京的路上,沿途的景色皆入诗人的眼更入诗人的心,此时从诗中似乎不能明显感受到诗人“言与志反”的趋向,须知,诗人虽坦言“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但何尝不是满满的不甘与愤恨,寥廓虽能高翔,但翔于何方?何方真是寥廓?何方能任诗人高翔?一切都是未知数,“寥廓已高翔”也表明了谢朓在随王府上的一切经营与努力也随他的“高翔”消散成云烟,他的“平生仰令图”又得推倒重来,在另一处不知前路如何的未来细密绸缪。
到了明帝萧鸾自辅政到称帝这前后五、六年中,齐宗室一直处于腥风血雨中,明帝性格孤鸷好猜疑,且手段残暴,在他称帝前后曾三次诛杀诸王,《南史》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四的《齐武帝诸子传•临贺王子岳传》中有记载“每一行事,明帝辄先烧香,呜咽涕泣,众以此辄识其夜当杀戮也。” [8]而谢朓可以说是亲历其中的,本来政变杀戮于政治家来说是何等平常之事,奈何对于诗人谢朓而言,性格不单敏感且软弱,经历了这几年的世事,谢朓已经从软弱忧惧的性格发展到全身远祸、处处保全的状态了。而偏偏在明帝称帝之后,谢朓的岳父王敬则起兵谋反,起兵前曾密告其欲起事,其时正当“主猜政乱,危亡虑及,举手扦于地,人思自兔” [9]的时局,故谢朓为求自保,向明帝告发自己的岳父,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于后来的部分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谓其卖翁求官。从《始出尚书省诗》中可窥见谢朓此时的心境。
惟昔逢休明,十载朝云陛。 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
宸景厌昭临,昏风沦继体。 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
防口犹宽政,餐荼更如荠。 英衮畅人谋,文明固天启。
青精翼紫轪,黄旗映朱邸。 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
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 趋事辞宫阙,载笔陪旌棨。
邑里向疏芜,寒流自清泚。 衰柳尚沉沉,凝露方泥泥。
零落悲友朋,欢娱向兄弟。 既秉丹石心,宁流素丝涕。
因此得萧散,垂竿深涧底。
看此诗可观诗人内心已是千疮百孔,所以目之所及皆是惨败衰颓的乱象。虽能“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可人与人之间要“防口犹宽政,餐荼更如荠”,这种见喜不喜、忧惧惶恐、全身远祸的情绪在《直中书省》中也有直接表露。
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弘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
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
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
册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两诗的结尾“因此得萧散,垂竿深涧底”;“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直接清晰地表达自己追求赏山泉、垂钓竿的隐逸生活。这个时期的谢朓,由于看见过多的血腥,他心目中的隐逸已经不是年少时的单纯追随时代潮流,而渐渐生发出一种真情与实意了。可是,齐明帝萧鸾对他的“顾遇”、光复谢氏荣耀、不甘埋没自己才能的这些信念使得他始终没法挣脱仕途,去寻求心心念念的山水之乐。
待到外放宣城时期,固然有“皇恩竟已矣”(《游敬亭山》)类似的牢骚之语,但此时远离权斗中心,劳累惶恐的心灵能得到一丝的放松,谢朓好似终于找到一条平衡之路了。试撷取谢朓在宣城时较负盛名的一首《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来加以分析: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是他厌弃官场又无法彻底抛下功名利禄的一条折衷之道,也是对他来说一条平衡出世与入世的最好选择,虽然“嚣尘”不一定就能够“隔”,诗人也未必全能“赏心于此遇”。
对于谢朓来说,他在诗中表达的“言与志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有变换发展的,由单纯的附会时代潮流,到对悠游山林的真心向往,又到认识自己终不能归隐山林这个现实,以及试图寻求仕途与归隐两者平衡的理想。但归根结底其变化始终摆脱不了“言与志反”的范式。
三、“言与志反诗”范式的成因与实质
谢朓的隐逸倾向向来被视为一种言不由衷的虚假表现。实实在在来说,之于谢朓曾经辉煌而今没落的家世以及他的个人才能,窃以为,如若不是时代与外在环境的险恶,谢朓断断不会有隐逸的想法,假使有,也不会造成“篇篇一旨”的诗体范式。这才会有钟嵘在《诗品》中作下的“末篇多踬”的评论。常常见到有文章评论谢朓诗中的道家思想,简略来说,道家是含有提倡不作为、少作为、断绝贪欲的成分的(参考道家各类经书,从头至尾,粗浅谈来,以上旨意大致不错)。道家的信念恰恰是奉劝人们少欲,因为它认为欲是一切痛苦、灾难的来源。
而于谢朓来说,他虽然也说道家语,但观其一生的行迹,他思想深处是不信道的。相反,其绝对是出世入仕的忠实拥趸者。这从他面对人生两次大转折时所做出的选择中可以看出。其一,向萧鸾告发岳父王敬则谋反,审时度势之后,谢朓发现,摆在他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与岳父一起谋反,但风险系数极高,不符合他的性格。另一条是告发岳父,这样的结果是会遭人诟骂,骂其贪生怕死、贪恋权位,以岳父的尸骨作为自己上位的垫脚石。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残酷的,而结果,谢朓自然选择了风险系数较低的第二条路。其二,是致他被捕下狱被杀的另一次抉择。明帝崩,东昏侯继位,始安王萧遥光欲夺帝位,谢朓因感遇于明帝,故固辞,始安王等便反诬其谋逆,谢朓终因卷入齐王室夺权漩涡中而殒命。
从以上两种选择来看,谢朓于仕途中,是能极敏感地察觉到其中的凶险的,他也在尽力地规避危险。
于此,我们便可以说,谢朓在他的众多诗篇中或明或暗地透露隐逸思想,是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中受群体意识影响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这种隐逸倾向只是他较为软弱的性格在面对残酷现实的一个倾泻口,在人生理想受挫时逃避的一种较为贵族式的舒心选择。其真实度虽然随他的人生经历而有所提高,但本质上“言与志反”是一贯如终的。还是陈祚明评谢朓评得深刻到位,其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中评道:“诗所以述情也,然每观作者之辞,必与衷情乖反,若追原素志,则本怀轩冕,谅重匪轻,怅望君恩,嗟柏朝恋。然造语之体不可直陈。……不得以热中触望,取消来兹。……然发情止义,仅在篇末。按之胸怀,不无殊尚。读诗者考其行事,诚为较然,则志仍可见也。” [10]
谢朓“言与志反”的诗体范式可说是由其历史环境、个人遭遇和性格共同铸就的。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11]是恩格斯在评论斐迪南•拉萨尔的剧本《金济根》时给悲剧下的一个定义。其可以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合理要求、理想等未能实现。对于谢朓来说,他的人生悲剧也暗合在这个定义之下,他有“平生仰令图”的志向,又少有才学,对自己光复谢氏荣耀寄托希冀,奈何南朝政治动乱,如谢氏一般的大家族皆已没落,故经常在实现理想与不如归隐的臆想中挣扎徘徊,这种情绪也便在诗中有所表露,探索谢朓诗歌“言与志反”的现象,从谢朓的身世出发,不对他的人生选择做出苛求,对我们全面了解谢朓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谢朓作为南朝不可多得的文学俊才,其诗体风格研究应不仅仅局限于永明体、山水诗体,观其所处时代,“言与志反”是其特征之一,故以刘勰所评为切入点,当可以略窥南朝文人
(下转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