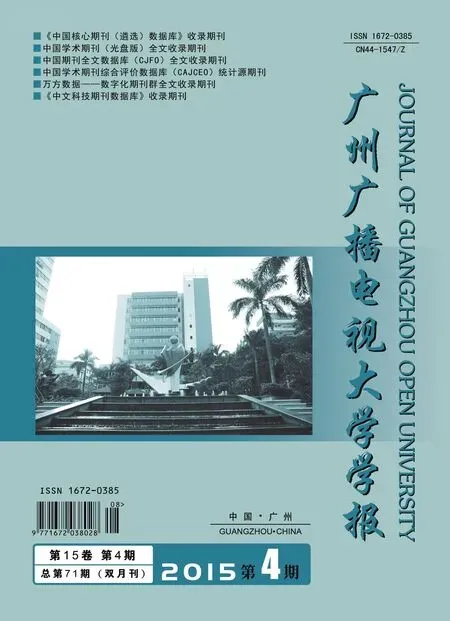“肆意笔落,无所羞畏”——李清照诗词创作观再解读
摘 要:李清照一向被归为正宗的婉约派,但也有不少学者如繆钺、龙榆生则认为李清照的词作蕴有潇洒的气度,并非婉约可以全然概括,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李清照的诗作不仅没有流于俗套,并且十分善于采用诗歌创作的技巧来作词。从李清照唯一的词学文论——《词论》切入,通过考察李清照的具体创作和传统诗教观念,可以进一步呈现出李清照诗词创作观念的丰富内涵。
收稿日期:2015-06-05
作者简介:张亮,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作家作品流派分析。
李清照一向被归为正宗的婉约派,是极具“当行本色”的“婉约词宗”, [1]但也有不少学者如繆钺、龙榆生则认为李词蕴有潇洒的气度,并非婉约可以概括。宋代著名学者王灼曾说,“(李清照)自少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 [2]的确如此,李清照的诗作也不落俗套,屹然为一大宗。然而,沈增植、缪钺、龙榆生等学者立足李清照的创作和创作观,认为李清照并不是完全的婉约派词人,或者说她不仅有婉约的一面。今人顾易生、彭玉平等学者则从其《词论》出发,坚持李清照词风受到传统诗风影响的观点,指出李清照并不赞同“词为艳科”的论调,所以用“婉约”来全然概括李清照的创作似乎有待商榷。那么,李清照究竟算得上“完全”的婉约派吗?她的诗词创作观蕴藏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呢?
一、李清照诗词风格的异趣之处
李清照的词作主要以三种题材为主:情思、事理和物景。其间“情思”又以伤春悲秋、离愁别绪为主,例如“春又去。忍把归期负。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以及“草绿阶前,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事理”类以物是人非、心事难寄为主,例如“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 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物景类以难禁风雨、红绿易败为主,例如“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显而易见,李清照的词作内容上多为自然风光和孤独哀愁。在艺术风格层面上,李清照的词风确实“忽悲忽喜,乍近乍远,所为妙耳”,诚如缪钺先生在《论词》中概括的“本色”词风那样,一是其文小,李清照所选意象都是轻灵细巧者,如“窗纱”“帘幕”“夹衫”“残云”等。二是其质轻,李清照晚年的词作尤其善于用轻灵宛转的手法来表达忱挚的情感,例如她流落临安后某年元宵节所作的《永遇乐》,只是轻描淡写昔日的繁华和如今的凄凉,最后一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3]更是轻之又轻,但是传达出来的情感却是重之又重。三是其径狭,说理叙事不宜入词,而最适宜的是表达幽怨的情思,四是其境隐,词境讲求隐约凄迷,李清照的词作在这两点上亦称冠绝,她的词不仅真实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伤时念旧的情感,而且在意境的经营上也往往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
相对而言,李清照诗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但在总体风格上趋于一致。在内容方面,她的诗作少见儿女情长和闲愁思绪,往往多是对当时政事和国家危亡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最具代表性的她的《上枢密韩肖胄诗》以及在这两首诗前作的序,序云:“易安父祖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 [4]自述家世和生活困境之后却突然调转笔锋,“神明未衰落,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 [5]这种心忧时局的诗作在两首失题诗和《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中亦有表露。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枢密韩肖胄诗》这首诗当中,我们可以窥见李清照对待诗歌的态度。第一,诗序的末尾有言:“以寄区区之意,以待采诗者云。” [6]众所周知,“采诗”出自《礼记•王制》,古代有专门机构采诗,为统治阶级观风俗、知得失的一项政治措施,并逐渐成为正统诗歌的一大要义。由此观之,李清照的诗歌创作意识中仍然遵循着 “诗合为事而作”以及“美风化,文章典正”的“大传统”。第二,李清照在诗中讽刺了宋高宗俨乎其然,不愿意“迎回”徽钦二帝的做法,所谓“三年复六月,天子视朝久。 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宋高宗对金人的仇恨,对于堂堂一位“中兴之主”来说确实可悲。其实,在别的诗作中,李清照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7]“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 [8]宋人庄绰在他的《鸡肋编》中对这两句诗也有记载,“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 [9]五胡乱华之时,晋怀帝、晋愍帝被掳而晋元帝则南渡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李清照借此来讽刺两宋之交的政治时局,又以光复神州的忠臣王导、刘琨等人来讥讽当时苟且偏安的失节之臣。
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李清照批评南宋君臣,忠愤不已而又不曾直陈其恶,取而代之的是委婉讽刺,这里面当然要考虑到有避讳的原因存在。俞正燮这样评价李清照的诗歌,所谓“忠愤激发,意非语明,所非刺者众”, [10]其实体现的正是李清照对传统诗歌“讽一劝百”之道的遵循。从艺术风格上来看,李清照的诗风与婉约派的词风相去甚远,表现为刚健高昂的品格,例如与《武陵春》写作时间和地点均相近的《题八咏楼》,这首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极大地抒发了李清照心忧国事,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哀叹宋室之不振,其中“江山留与后人愁”一句,堪称千古绝唱。将《武陵春》和《题八咏楼》对照后发现,同李清照在同一个地点、时间,同样是写“愁”,其词其诗却很不相同:《武陵春》哀婉凄美,所谓“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而她的诗却愁肠中充满豪气和壮阔,一句“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还是相当符合“典赡”之说的。总之,正如宋人朱彧所发现的李词与诗的“霄壤之殊”那样:“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 [11]只要继续稍加考察,很容易发觉“诸如此类,虽未得其皮毛,也略见一斑了。”
二、《词论》中的“文雅”观
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不仅成为宋代的重要词论,而且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若从李清照唯一的词学文论——《词论》切入,通过考察李清照的诗词观,应该能够进一步透视李清照诗词创作的复杂内涵。
叶嘉莹先生认为,词本是文人飨宴之余写来的“歌辞之词”,内容皆关乎“风月”,风格偏于妩媚,这正是自打晚唐以来形成的词作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苏轼却将“言志载道”传统注入词中,对花间词派影响下婉丽的正统词风进行强有力的反拨,也正源于此而招来批评之声。 [12]李清照正是批评者之一,她在《词论》中标举的旗帜除了“文雅”、“典重”、“铺叙”、“故实”等填词要求,还力主“富贵态”和“妍丽”,说明李清照创作的“一只脚”还是固执地踩在“婉约”词风这一路的,这是需要把握的一点。无怪乎吴组缃会认为“李清照在词作上是走传统的婉约之路:即把词限制在抒写离情别绪及个人幽怨与哀愁方面,不认为爱国爱民的大题目可以入词。” [13]
在《词论》中,有关词的艺术特质和表现手法方面,李清照的最重要的一个口号便是“文雅”,强调情调的纯正和语言的纯净,认为词应该具有高雅平和的审美范式。在这一方面,李氏二主和冯延巳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而处于“文雅”对立面的则是那些“词语尘下”的柳永等人。李清照将词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认为西蜀花间词于“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之际,沉溺花间樽前是“斯文道熄”的表现,完全不符合治世之音的标准,而李氏君臣以“亡国之音哀以思”,符合“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社会教化标准,两相对照之下,前者自然不及后者承载有厚重的历史感,其实这里李清照还借此否定了柳永等人不加提炼就以俗语入词,并且浸淫艳情的鄙俗格调。
李清照认为,“文雅”是对词内质的要求,词风要庄重典雅,不能轻浮,而实现这一要求则需“铺叙”、“故实”这些外在的写作手法来达成,这样词的整篇就是一个完整的境界。所谓“铺叙”,即铺陈叙述之意,李清照批评了小晏“苦无铺叙”,肯定了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因为慢词这种适合铺叙的体裁为宋词开脱了新的领域。在张端义的《贵耳集》中,作者就指出李清照的代表作《声声慢》这首词连用十四个叠字,即是用了“《文选》诸赋格”。 [14]李清照还批评了秦观“专主情而少故实”,“故实”一般说来就是指用典用事,按照李清照的说法,秦观的不足正是由于“少故实”而“乏富贵态”,其实秦观作词并不全然不懂“故实”,只是未达到李清照的“高标准”罢了,而且李清照批评的着落点最后还是落在了“乏富贵态”上,可见她的指摘并非全无道理可言。
事实上,“文雅”等要求并非词这种体裁的特点,反而是诗歌中常见的要求,即诗歌要有典正风华的功能。此外,李清照在《词论》中肯定了诸多词人的成就之后,她认为这些词人由于不同程度地忽视“文雅”“铺叙”“故实”“典正”等特质,故而他们词作的艺术水准是大打折扣的,但我们要清楚一点,那就是这不代表李清照漠视词的传统,正如顾易生先生所说,“铺叙”“故实”的前提是词要先具备“情致”的特点和“妍丽丰逸”的特色,“并非她专以铺叙、典重、故实、华尚为贵。” [15]
三、李清照的诗教观
在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中,中正平和是文学的最高审美标准。李清照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观融入了她的词作中,所以说她的词并不缺少沉稳蕴藉,相反地,其词婉丽中见健拔,柔厚有余,雍容不迫,这一点其实已被不少学者发现,例如,缪钺先生认为,易安体的首要特点不在其他,而是“神骏”。 [16]至于易安体之“神骏”,它出自沈增植的《茵阁琐谈》:
易安跌宕昭彰,气韵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太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
“神骏”之说是指其用笔和气象两个方面,笔力矫健劲拔,气象潇洒空灵,不落软弱之流。
《渔家傲》在李清照的集子中是非常独特的一首,恰能印证“神骏”之说。原诗为: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词无论是意境、意象还是用典,全不似“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的词之特性,相反地,意境开阔,意象宏大,丰容宛转,且大鹏之“典”也不似婉约词所能包容,加之主题是表达个人高远之志,与《漱玉词》中的闺阁情怀、伤春惜秋相去甚远。因而梁启超也认为这首词“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 [17]顾易生先生分析这首词时说,“‘学诗’之句渊源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清照是以杜甫作诗态度去作词的。她的词……兼有清新俊逸之致。颂扬高风亮节而关心民生疾苦,远非婉约词风所能范围。” [18]叶嘉莹先生在《漱玉词欣赏》中认为,历来人们推崇《声声慢》作为易安词代表的做法颇有问题,倒是这一首《渔家傲》健举而自然,更能体现李清照词作深处的特质和其创作水准。 [19]换言之,易安词虽为女性化的词,但是“芳馨俊逸”而没有脂粉气,反而多了豪举飘洒的气度,所以《历朝名媛诗词》评价《声声慢》是“玩其笔本自矫拔,词家甚少,庶几苏、辛之亚。”此外,李清照的《如梦令》也可谓是矫拔潇洒的代表作。谈到这股矫健洒脱的风格,龙榆生先生对此有一番比较贴切的见解,“易安性格则风流跌宕,环境则前期极唱随之乐,后期多流离之痛,咸足以酿成其词格,入于凄壮感怆一途。又其论《淮海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乃亦主气象。由此推之《漱玉词》之全部风格,实兼有婉约、豪放二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沈氏所谓‘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其言不我欺。” [20]
李清照不仅将儒家诗教观融入了她的具体创作中,而且还体现在她的词学批评——《词论》中。张惠民先生认为,《词论》诗学观的本质论就是以儒家诗教观为基础,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是李清照论词的内涵之一。 [21]这便也进一步证明了李清照算不上完全的婉约派词人。原因如下:李清照对最符合“本色”的花间词派提出了批评,谓其为“郑卫之声”和“流靡之变”,任其发展的结果只能是“斯文道熄”。“郑卫之声”出自《吕氏春秋•季夏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由于儒家认为其音淫靡,不如宫廷里的雅乐高雅,所以把它贬斥为淫声,提高到“乱国、衰德”的政治高度。“斯文”则出自《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用来代指礼乐教化、典章制度。由此可见,李清照的《词论》带有浓厚的儒家诗学观念色彩,她秉持正统儒家“捍圣卫道”的诗教观念,纠偏香艳淫靡的词风,其目的在于着力革除掉晚唐词风中的不健康因子。
综上所述,关于李清照算不上“完全”的婉约派的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说服性的。从李清照的具体创作来看,她的词虽多为闺阁情怀和儿女情思,总体风格偏于婉丽,但却没有一味地“软”下去,反而推崇典雅、庄重的词风,时常流露出潇洒之气,树立了雅词的标准,这主要得益于她在词的内质和形式方面对传统诗歌有所借鉴,呼吁人们用典故、铺叙等手法来祛除晚唐以来词风中的香艳萎靡之气,反而使得词作合于“文雅”的标准,在有限的篇幅里得以填充更丰富的内涵,而且还没有背离“典正”的教化功能。至于她的诗歌创作,更是严格遵循了传统诗歌“讽一劝百”之道,对此不再赘述。王灼对李清照诗词创作的丰富内涵概括得最为准确:“肆意笔落”就是不婉,“无所羞畏”就是不约,与李清照诗词观念相适应的风格便不可能单单是香软、纤弱,这既是传统诗教观念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清照本人创作个性的独特体现。前者的驱动辅之以后者的飞扬造就了李清照特有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理论和示范意义,而且还反映了她的文学通变观,毕竟李清照指明了词这种体裁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引领了一种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