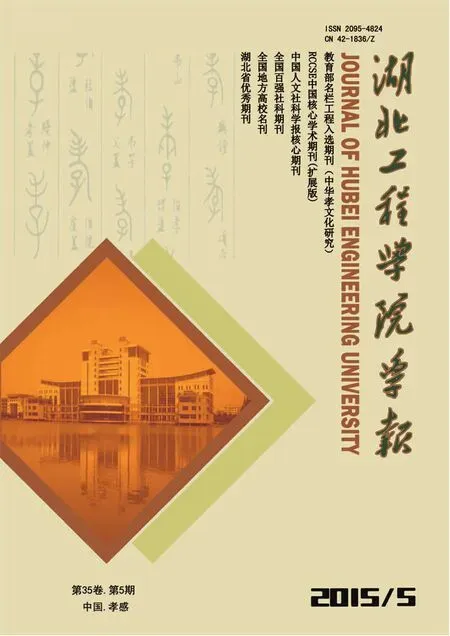乾卦中的哲学观念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李 娟
(1.黄冈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乾卦中的哲学观念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李 娟1,2
(1.黄冈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因其所包含的“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而成为“儒家的玄思”所从出之点。尽管其经文和传文本身都不是讲美学或者艺术的,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乾卦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深远影响。它的一些基本命题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六位时成”、“知几其神”等成为中国美学、艺术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依据。
乾卦;阴; 阳;中;和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风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本文所用《周易》之《经》、《传》均采用《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周易正义》,兼参考黄寿祺与张善文的译注本。除特殊情况外,凡引用《经》、《传》原文只以篇名标出(如《系辞上》等),不一一注释版本及页码。具体版本信息为: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这是《易经》乾卦的全文,就卦、爻辞本身来说,很难让人理解,但经过《易传》各篇,特别是《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的解释后,其哲学意涵就非常突出了,以致于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的玄思”从此中来。[1]5-7建立于哲学观念之上的中国美学的一些核心理论由此生发出来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对于乾的字义,《说文·乙部》这样解释:“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段玉裁注:“此乾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之后,乃用为卦名,而孔子释之曰:‘健也。’健之义生于上出。上出为乾,下注则为湿,故乾与湿相对。”[2]按照《说文》及段注,乾的本义是万物萌出,但有了文字以后,一直是作为卦名而存在的。作为一个卦名,乾卦(同卦相叠,上乾下乾)位列《易经》六十四卦之首,与坤卦一起,在整个六十四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系辞上传》云:“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下传》亦云“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也就是说,在六十四卦当中,乾坤两卦就像一对门户一样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关于这个门户,《系辞上传》进一步解释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就是这一阖一辟产生了六十四卦。乾纯阳,所以称阳物,坤纯阴,所以叫阴物。就是因为乾坤的存在,所以才有“万物资始”、“万物资生”,这就是阴阳合德。乾坤两卦之所以这么重要,牟宗三先生解释说,这两卦包含着中国哲学中两个最具根本性的原则,即“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而乾健所代表的原则就是“创生原则”,即创造性原则。坤所代表的原则就是“终成原则”,即保聚原则。[1]12
单就乾卦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乾卦的卦辞为:“乾,元、亨、利、贞。”对于这四个字的解释,颇多异议,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四德”说:“《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3]1所谓元,就是开始;亨,就是亨通;利则是和谐有利;而贞就是正,它们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如果将这个过程比拟为四季的话,乾卦就包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意。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乾卦本身就是一个纲领性原则,它可以容纳坤卦所代表的原则,因为“元、亨、利、贞”整个过程就包含了“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元、亨”所标示的是创生原则,“利、贞”所标示的是终成原则)。[1]12这样一来,乾卦就在整个六十四卦中更具根本性的地位。
乾卦的这种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居于第一卦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哲学观念对中国人的审美、艺术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崇阳贵阴”的审美品位
在乾卦所蕴含的哲学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阐述六十四卦卦序排列原理和各卦的属性意义的《说卦传》开篇即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下传》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这就是说,阴爻、阳爻组成各卦,而爻仿效万物变动的情状,同时爻又有上下的等次,从而才能组成物象,推而广之,整个宇宙也都能用阴阳来表达。但是对于乾卦来说,其依乾而成象,六爻皆阳,内外皆乾,似乎没有阴、柔的存在。实际上则不然,因为乾卦不是一个由六爻组成的简单的死的卦画,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萦绕其间的是氤氲的元气,是一种“气积”,正是这虚灵摩荡的气,使乾卦各爻之间不断变动、转化,因而使得乾卦非常强调生生、动变、刚健的生命精神,当然,这种刚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乾卦内部“创生”、“终成”的协调发展,也就是《系辞上传》所说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下传》的:“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以及“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卦这种强调事物内部阴、阳具有各自的特征,互相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观念直接促成了中国美学将美区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当然,阳刚之美不仅仅是刚健遒劲,而且是刚中蕴柔;阴柔之美则不但柔婉妩媚,而且柔中带刚。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这两种美的特征与关系的分析非常精辟:“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出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4]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段文字,姚鼐在此只是陈述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在文章中的表现形态,并未做出理论的界定。但毕竟他看到了两种美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特性,也即他所说的二者可以“偏胜”,但不可“偏废”。不仅作文要如此,填词也应该做到“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书法讲究“兼备阴阳二气”;绘画则坚持 “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的审美理想,如此等等,其实都可以溯源于乾卦的哲学观念。
尽管乾卦内部也是阴、阳之气推动着不断变化,但是乾卦的卦象毕竟是纯阳之象,所以《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系辞上传》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系辞下传》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显然,在承认阴阳对立统一的条件下,更强调阳刚所居的支配地位,这也就是《系辞下传》所言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乾坤位矣”。乾卦中这种崇阳贵刚的倾向,对生生不息的动健精神及创造品格的推崇,使得中国美学在肯定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不可偏废”的同时,更倾向于追求阳刚之美,其中汉魏风骨、盛唐气象最具代表性。不仅如此,乾卦强调生生、刚健不息的精神,从整体上塑造着中国的艺术,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艺术表现着宇宙的创化。”[5]366中国艺术特别醉心于这种创化、生生不息的动健精神。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首标“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雄”,至大至刚之谓,如何能显示诗歌之雄?那就是要“反虚入浑,积健为雄”,与宇宙的无限生命力融为一体。不仅诗文中推崇生命力和气势,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也对“无机无气”,了无生机的作品嗤之以鼻,而对生气灌注、气势磅礴的艺术推崇备至。这种礼赞生命力的审美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到乾卦中来。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5]365
二、“六位时成”与推崇“意境”的审美追求
乾卦六爻成一卦,在六爻的变动中,时间的观念得以显现。所以《彖》说:“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每一卦就是一个时,一时之中又有变动,故有初、二、三、四、五、上六个爻位,因此,各个爻位只是一时之中的一个点而已,所以王弼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6]从《乾》卦的爻辞也可以看到,六爻“历经‘潜’、‘在田’、‘在渊’、‘在天’、‘亢’等不同的阶段,而有‘勿用’、‘利见大人’、‘有悔’等种种不同的表现,说明的道理……只能是‘时’,就是不能违时,只能依时而行。……可以说,《乾》卦六爻,虽然没有一个‘时’字,但没有哪一爻不是在说‘时’。‘时’是《乾》卦的核心精神”[7]。
对于《乾》卦中的这种“六位时成”的时间观念,宗白华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解释,他说:“说出时间对空间的密切联系和创作性关系的,莫过于《易经》,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是世界创造性的动力,‘大明始终’是说它刚健不息地在时间里终而复始地创造着,放射着光芒。‘六位时成’是说在时间的创造历程中立脚的所在形成了‘位’,显现了空间,它也就是一阴一阳的道路上的‘阴’,它就是‘坤’、‘地’。空间的‘位’是在‘时’中形成的。卦里的六爻表示着六个活动的阶段,每一活动的立脚地、站点,就是它的‘位’。这‘位’(六位)是随着‘时’的创进而形成,而变化,不是死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就是说时间骑在这六爻所代表的六段活动历程上统治着世界,这六段活动历程千变万化像六条飞龙。六位就是六虚(《易》云:‘周流六虚’),虚空容受着运动。”[5]476-477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解释,乾卦的时间观念是表现在“位”(空间)之中,这个“位”也是不断“变”化的,“时”与“位”(空间)不相分离:空间的“位”是“时”短暂的停留处,但它本身也是在“时”中生成变化的,随着“时”的变化而变化。 方东美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最早是用宇宙来指代时间、空间。他说:“上下四方的三度空间叫做‘宇’,往古今来的一系列变化叫做‘宙’,宇和宙一起讲,就表示时空系统的原始统会,就是代表一个整合的系统,只在后来分而论之的时候才称空间和时间。”[8]在《乾》卦这种时空合一体的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念不是外在于人,而是与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白华先生说:“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西南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9]
《乾》卦“时空合一体”的宇宙观渗透于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方方面面。中国古典艺术中,无论是诗歌、书法还是绘画、园林,都以是否有意境作为评品的标准,而意境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就是情与景、诗与画的交融,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时间与空间的交汇,要在空间里引进时间的感觉,在流动的时间里展现空间的画面。以绘画为例,中国画家不以临摹与再现外部世界为己任,而是要用笔墨表达自己的心绪与意境,也就是倪云林所说的“仆之所谓画者,逸笔草草,不求形式,聊以自娱耳”(《答张藻仲书》)。在创作技法上,中国画也不同于西方的焦点透视法,而是以“三远”之法来达成节奏化、流动性的意境。宋代的郭熙曾在其《林泉高致》中提出“三远”的创作技法,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10]这种创作技法正是“时空合一体”的宇宙观在画家身上的体现。“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不同于将视线集中于一个焦点的透视画法,这是一种流动的散点透视。由高至深,由深到近,再向平远横去,这是一个节奏化的行动。所以宗白华先生对“三远法”给予高度评价:“‘三远法’所构的空间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着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由‘似离而合’的方法视空间如一有机统一的生命境界。由动的节奏引起我们跃入空间感觉。”[5]432-434中国的园林同样也强调要在空间中引入时间感,所以中国的园林建筑通过各种手法(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来创造、扩大空间,其目的就在于使观赏者能够在静止的空间中获得时间的流动性。
当然,中国的诗歌、建筑等其他的艺术门类也是以“时空合一体”为特点,以追求意境为旨归,其根源正在于乾卦哲学所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这种“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绘画境界的特点, 也是中国古代《易经》里宇宙观的特点, 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形成了艺术思想和表现的基础, 尽管艺术家不一定明确地意识到它”。[5]474
三、“知几其神乎”与重“势”的美学传统
《文言传》在解释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时说:“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意思是说,知道进取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的人,可以跟他探讨事物发展的征兆。为何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九三卦居于下卦之极,有“知几”进取、审慎“无咎”之象。这里蕴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即“几”的观念。所谓“几”,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采取最开始最具体最动态的观点看事件”。[1]8这种强调“几”,强调“见几而作的观念”在《乾卦》及《周易》,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系辞上传》中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正义》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是:“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这说明圣人用《易》之精深。《系辞下传》又一次论到“几”:“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也,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里就对“几”进行了定义:“几”是“动之微”、“吉之先见者”,《周易正义》解释说,“几”是“已动之微”,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因为如果事件已经显露出来了,就不能称作“几”,反之,如果没有发动之前,“寂然顿无”,也不能称之为“几”。也就是说,“几”是事物变动的微小征兆,也就是将动未动之时的苗头或萌芽,这种苗头或萌芽虽然“微”而似无,却能够预示事物发展变化方向的吉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解释,任何一件事情在宇宙间、人世间的发生,只要一开始发动,将来的所有结果就统统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开始一发动就是“几”。[1]9周敦颐在《通书·圣第四》中阐释“几”时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又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11]要成为“圣人”,“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件。周氏有关“几”的解说可以说是把握了“几”这一观念的精义,所谓有无之间,就是说它一方面还没有彰显出来,但另一方它却又已经发动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先生说“几”的观念属于中国“气化”哲学[1]10,是有其道理的。
这种重“几”的哲学观念进入美学领域后,使得审美欣赏与艺术创作非常强调“势”,强调“最具包孕性的时刻”。中国书法中一直有重“势”的传统,书势、体势、字势、笔势,等等。所谓“势”,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张力形式,书法在形式上努力造成一种冲突、不平衡感,“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是也。晋人卫恒的《四体书势》谈到篆书的时候,引用了东汉蔡邕的《篆势》,蔡邕认为,篆书应能达到“扬波振撇,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12]14的效果;《四体书势》中还收录有崔瑗的《草势》一文,在谈到草书如何表现那种瞬间的力感时,崔瑗说:“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12]16草书就是要将像兔子突然被惊吓,正准备逃跑但还没有逃跑的瞬间那样的妙处表现出来,这种将动未动的瞬间,是最有张力的空间,也具有最大的“势”,其实也就是一种虽然还没有彰显出来,但已经发动了的“几”。画论家也推崇画作中的“几”,比如唐代张彦远就将绘画的功能提升至“穷神变、测幽微”[13]的高度,这其实就是说观画能够把握“几”;宋代的黄庭坚则将具有“几”的态势的作品视为有“韵”的作品,有韵才能不俗,他在论李公麟(伯时)画骑射时说:“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题摹燕郭尚父图》)也就是说,画作要达到韵的效果,就必须在描画射箭之时,要把握“最具包孕性的时刻”,引而不发,令人想像。
在审美欣赏领域,同样需要审美者能“研几”、“知几”。“几”又可以称为“机”,与“天机”之“机”相同,都是指宇宙大化中潜藏着的那种神变幽微生命奥秘的机缘显现,因为其幽深,又与“玄”、“妙”的意思相同。[14[15]所悟的是什么呢?是审美对象中的造化之玄机以及深层的审美意蕴。中国美学中这种追求感性的、直接的触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审美方式,不能说与乾卦“知几其神乎”的哲学观念无关。
四、 “刚健中正”、“保合太和”与尚“中和”的美学旨趣
“中”与“和”的观念也是乾卦哲学中特别重要的观念。《文言》中有这么几处论及到“中”:“龙德而正中者也”,“刚健中正,纯粹精也”。“龙德而正中者”,是《文言传》在解释九二爻辞时讲的,九二居内卦之中位,也就是《周易正义》所说的“九二居中不偏”,所以说“正中也”;对于“刚健中正”,《周易正义》解释说:“谓纯阳刚健,其性刚强,其行劲健:中谓二与五也,正谓五与二也。”正因为九二和九五都居正位,所以称为“中”,而九三和九四就非如此,故而《文言传》说“九三重刚而不中”,“九四重刚而不中”。高亨先生在解释“中正”时说:“中则必正,正则必中,中正二名实为一义。《易传》又认为人有正中之道德,而能实践之,则能胜利,故得中为吉利之象。”[16]41《系辞下传》中说《易》的卦爻辞时,也提到了“中”:“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对于这个“中”,《周易正义》解释说:“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就是说卦爻辞的语言曲折切中事理。这也就是高亨所解释的:“中谓合于事实,如射之中的也。或曰:‘中,正也’。”[16]581根据这一说法,“中”就是不偏不倚地合于正确之点。这种“尚中”的思想,在后世儒家那里得到极大发挥,如《论语·尧曰》里“允执其中”之“中”等,如果引申开来,其实质就是对正确事物或者事物中确正之点的坚决追寻、把握与运用。
再说“和”,乾卦的《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即大的、极致的和谐。关于“太和”,高亨解释说:“太和,非谓四时皆春,乃谓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气皆极调谐。不越自然规律,无酷热,无严寒,无烈风,无淫雨、无久旱,无早霜,总之,无特殊之自然灾害。天能保合太和之景象,乃能普利万物,乃天之正道。”[16]54按高亨的解释,这种“太和”,是宇宙间最大的和谐。而要达到这种和谐,一方面要求万事万物在运动中联结、交流、渗透、转化,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另一方面则是事物在转化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总之,宇宙间的这种大和谐,正是由于这些各持自身性命之正的不同事物在其不断的相参相化的运动中构成的。
由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需要,“中”与“和”渐趋合流,成就了中国哲学、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和”。这一概念在发展中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和”成了“中和”的主导方面,它使中和成为一种普遍的和谐观,使中和强调着、肯定这统一体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对立联结、转化生成的运动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结构,或者说这个统一体的整体和谐状态;而“中”则是中和的内在精神,它促使中和具有不偏不倚的特性,它要求动态和谐过程必以“中”为基准来进行,而整体的静态和谐关系结构也必以“中”为内在根据而构成。朱良志先生如是评论“中和”:“儒家中和思想以中为基础,以和为大用,强调过犹不及,中度合节。这正是为了化解冲突,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儒家并非都将此奠定在强制性的道德约束之上,而是致力于认得内在情感的和谐,由此实现中节合度。”[17]正因为“中和”具有这一体两面的特征,使得后世儒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就特别强调其中的道德因素,当这种道德因素渗透到文学艺术中时,就要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否则过了头,就有悖于“中和”的审美理想。即使有些艺术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中和”,但其深层次的因素还是“中和”这一审美理想在起作用,叶朗先生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对于‘中和’这一审美形态,应更多地从其深层背景上去理解何谓‘中和’,而不应该仅仅从表层前景的形式特征上去肤浅地理解。应该说,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乾健刚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气概,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还有崇义不崇力的怀柔和平政策,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怨诗、讽刺诗、兴寄诗、反战诗传统的精神支柱。虽然它们的面貌不那么温柔敦厚,但这正是‘中和’的宇宙、社会和心理秩序被破坏以后,由挠、荡、激、梗、炙、击而后所发的不平之鸣,其深层背景仍是要‘致中和’,‘致平’。”[18]
总之,尽管乾卦的经文和传文都不是讲美学或者艺术的,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乾卦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一些基本命题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六位时成”、“知几其神”等成为中国美学、艺术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依据。
[1]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100.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10-512.
[5]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6] 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604.
[7] 廖名春.《周易·乾》卦新释[J].社会学科学战线,2008(3).
[8]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2.
[9]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31.
[10]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97.
[11] 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3.
[12]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
[14] 李天道.论中国文艺美学之“几”范畴与“知几”说[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00.
[1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
[16]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17]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0.
[18]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85-86.
(责任编辑:李天喜)
The Influence of Qian Hexagram on Chinese Aesthetics
Li Juan
(1.SchoolofFineArts,HuanggangNormalUniversity,Huanggang,Hubei438000,China; 2.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HubeiWuhan, 430072,China)
The Qian hexagram is ranked the first in Zhouy’ s sixty-four hexagrams since it contains the principles of “creativity” and “completion” which have become the source of “Confucian speculative thought”. Although the scripture and the text themselves do not touch upon aesthetics or 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can be seen on the Chinese classic aesthetics and art in the philosophy idea from Qian hexagram. Some of its basic propositions such as “the successive movement of the inactive and active operations constitutes what is called the course of things”, “the six lines in the hexagram are accomplished in its season”, “those who knows the springs of things possess spirit-like wisdom” have become the most fundamentally philosophical basis which can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esthetics and art and the western aesthetics.
Qian hexagram; Yin; Yang, Mean; Harmony
2015-08-02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2013017);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
李 娟(1983- ),女,湖北应城人,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B221
A
2095-4824(2015)05-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