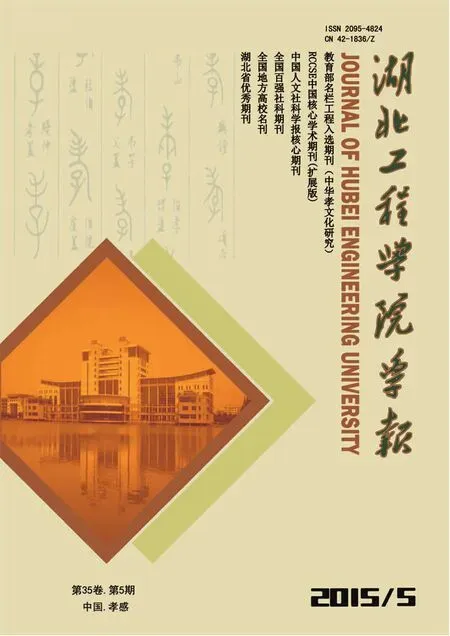从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到成就焦虑和学业竞争
——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的原因分析
邓银城, 左建桥
(湖北工程学院 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湖北 孝感 432000)
从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到成就焦虑和学业竞争
——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的原因分析
邓银城, 左建桥
(湖北工程学院 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湖北 孝感 432000)
古代中国是一个盛行等级制度、等级意识浓厚的国家,但古代中国在等级森严的同时,又为社会底层成员提供了通过学业成就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所以,许多社会底层成员都有通过学业成就来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生追求。在现代中国,人们的这种人生追求已演变成“平凡恐惧症”和“成就焦虑症”等不良心态。为了取得优异的学业成就从而跻身社会上层,学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学业竞争,因而给广大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课业负担。
等级制度;等级意识;成就焦虑;学业竞争
一、中国的等级制度与中国人的等级意识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之后,就出现了原始的社会等级。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巫”和“部众”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巫是自然神权的代表。“由于巫以神的名义行事,巫的身份在自然神权时代是神圣的,地位也是崇高的,他们往往是氏族部落的决策者、管理者、领导者。”[1]巫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从事的是各种取悦神的巫术活动,由从事体力劳动的部众来供养他们。由于等级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2]
我国是世界上等级制度十分盛行的国家之一,有学者认为:“等级制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堪称是其中的‘典范’。”[3]从古代中国的女娲造人神话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造人神话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平等意识。东汉学者应劭在其所著的《风俗通》中写道:“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根据女娲造人的神话,人天生就存在富贵和贫贱之分,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但普罗米修斯造出来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富贵和贫贱的等级之分。
在进入存在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文明时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等级已经开始制度化;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服饰装束、建筑陈设、交通形式、婚姻关系、丧葬规格、法律地位、家族形态、礼仪规则等方面都体现了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孔子、孟子等人提出过许多有关等级制度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论述。孔子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因为他是孔门弟子中最聪明的学生,也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学生。但颜回死后,其父请求孔子为颜回置椁时,孔子没有答应,他认为颜回的社会身份还没达到用椁安葬的等级,不能因为师生之情破坏了社会等级制度。孟子讲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要建立的礼治社会就是一种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安守本分、和谐相处的等级制社会。
在中国古代长达几千年的等级社会中所产生的等级意识十分强烈。所谓等级意识,是人们将社会中的阶层、群体、职业、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并对不同的等级采取不同的态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心态。虽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但在几千年的等级社会中形成的等级意识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与此同时,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依然还存在着许多社会等级。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可能只有中国的大学存在着“副部级高校”、“正厅级高校”和“副厅级高校”之分。学术领域本来是远离等级、远离世俗的“象牙塔”,但在当代中国,学术刊物、学术组织、学术奖励、学术研究项目都有不同的等级。公司、学校、机关、厂矿、社团等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都分成不同的等级;社会成员同样也存在着等级制和身份制。这种等级制现象必然会强化中国人的等级意识。
二、跻身社会上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人生追求
在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生活、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处于社会上层等级的人,可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生活在下层的社会成员,终生劳苦,饥寒交迫。而且,上层社会成员可以享有下层社会成员所没有的许多社会权利。在中国古代就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古代罗马,奴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做人的权利;在古代印度,外来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本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茶人,达罗毗茶人成了最低的社会种姓首陀罗,没有接受教育和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在《摩奴法典 》制订之后,首陀罗已经被置于非人的被奴役地位,他们在种姓等级制度的束缚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中国古代虽然存在着等级制度,但与建立在典型的奴隶制度上的古代罗马和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古代印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中国古代不存在古代罗马那样的奴隶制,更没有出现过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社会下层成员与社会上层成员一样,同样有着受教育的权利。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过“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也说孔子对学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在中国古代,虽然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接受的教育在等次上存在一定的区别,但社会下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还是能够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 “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从孔子时代一直到科举制度问世之际,社会下层成员可以通过教育来加入“士”的行列。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士、农、工、商”等几个大的等级,而“士”一直被视为社会的上层等级。科举取士制度问世之后,求学、读书、通过科举考试,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下层成员跻身社会上层的重要途径。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学子,无论其何种出身,无论其财产多少,只要他能通过各种层级的科举考试,他就能成为社会上层成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传”,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社会等级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流动。由于古代中国的下层成员可以通过教育途径来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标,因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底层中的年长一代从小就教育年轻一代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人上人”就是社会等级中处于上层等级的人。一个社会底层成员的后代,在其成长过程中,其父母和师长总在不断地告诫他,只要胸怀大志,奋发图强,寒窗苦读,将来一定能金榜题名,成为“人上人”,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中国古代文人也编出了许多寒门学子在求学过程中历经磨难,但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金榜题名乃至考中状元的人生目标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底层成员为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而寒窗苦读。
星移斗转,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迈入了21世纪,但这种成为“人上人”的人生追求依然还存在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头脑中。在中国任何一所小学,如果询问一些小学生“将来的理想是干什么”,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回答的是经理、官员、文体明星等社会上层职业;但在西方一些国家,学生的回答可能是五花八门,如烹调师、水管工等等。有人对中日两国儿童的理想作过比较研究,日本小学生中男生有26.7%的人想当“体育选手”,女生中有32.6%的人想作“蛋糕店店员”,而且据日本生活调查公司的多年调查,这两种职业一直在日本小学男生和女生的理想中排第一位;但中国少年儿童的偶像中除了雷锋之外全部是文体明星。[4]这种当选手而不是做冠军、当店员而不是做经理的理想在中国人看来真是“没出息”,因为当代中国人普遍都有一种“平凡恐惧症”,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平凡就是平庸,平凡的人生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人生的代名词。
三、为追求社会成就成为上等人而产生的焦虑
在古代社会,多数国家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等级是取决于社会门第、血缘关系、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但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一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有志向和才华的青年能通过自己优异的学业成就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废除了世袭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会成员的个人素养、能力和成就等后致因素成为影响社会成员等级变化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就,是成为社会上层成员的重要条件。一个人的社会成就也是其成为上层人的重要标志。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社会下层成员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传统,在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都怀着中国人特有的“状元情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了,但通过教育成就来选拔人才的制度依然存在,社会下层成员通过教育成就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比过去变得更宽了。
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底层成员中,胸怀大志,寒窗苦读,实现金榜题名的人生理想的人,一般是来自有一定家产,在解决家人温饱问题之后还能提供子弟读书费用的家庭,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底层成员都有这种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更多的社会底层成员的生活目标是实现家庭的温饱,争取做到衣食无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极“左”时代,在现代中国出现了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因为家庭成分而沦为政治“贱民”,完全失去了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家庭成分和出身不再成为束缚社会成员流动的政治因素。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已经步入了小康社会,十三亿中国人中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生存需要解决之后,发展需要和成就需要就成了优势需要,所以,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社会精英,还是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乃至整个草根阶层,都有很强的成就需要。上层等级的社会成员希望通过自己或子女的社会成就守住家族的上层社会地位,而社会底层成员则希望通过自己奋斗所取得的成就进入上层社会,或者努力创造条件来帮助和激励自己的后代通过努力奋斗来改变家族的命运,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
当代中国的社会层级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处于社会上层的成员只能是少数人,但希望跻身社会上层却是广大社会成员的人生追求。一个人要成为上等人,必须要取得十分突出的社会成就。在科举时代,这种社会成就主要是科举考试的成绩,但是在今天,这种社会成就的外延扩展了,它不仅包括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各种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的考试成绩,还包括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卓越表现,歌坛新秀、体育明星、经商能手、写作高手等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成就来成为一个“人上人”。但是,在改变命运的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在音乐、体育、经济、文学等领域中取得卓越成就,脱颖而出,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绝非易事。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农家子弟考取了大学,基本上实现了跳出“农门”跳入“龙门”成为“人上人”的愿望,完成了由社会底层跻身社会上层的社会阶层流动。但是在今天,一个农民工的后代考上一般大学之后,毕业以后的工资可能不如做农民工的父亲,还会成为蜗居在都市中的“蚁族”,这是因为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太多了。一个出身农家的学生,只有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85高校,将来才能跻身社会上层;而考进二本或三本高校,能成为“人上人”的概率则很小,而进入高职高专后成为“人上人”的希望更加渺茫。
处在金字塔尖上的社会上层的人太少,处于金字塔中部和底层的人太多,而且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怀有登上金字塔尖的人生梦想,然而登上金字塔尖,成为“人上人”,需要以各种优异的社会成就作为登塔的条件;但无论哪一种优异成就的取得,都需要一定的天赋、特定的机遇、良好的环境和个人的勤奋努力。在通向成功的大道上,天赋、机遇、环境、努力等影响成功的各种因素都具备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在实现谋求社会成就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或者感到力不从心,或者觉得时运不济,出现了一种紧张、烦躁不安的焦虑情绪。所以,在当代中国,有许多人在染上“平凡恐惧症”的同时,又出现了“成就焦虑症”。
四、学业成就与学业竞争和课业负担
社会成就是社会成员能够成为“人上人”的先决条件,在社会成员所取得的各种社会成就中,学业成就是一种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学业成就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成就,同时又是取得其他社会成就的重要前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道出了学业成就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意义。“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造就人生”体现了学业成就在今天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父母都十分重视子女的学业,因为子女的学业成就是决定其未来社会等级的重要因素。在中小学阶段,一个学生如果没有好的学业成就,就不可能进入名牌大学,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文凭,就不可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属于上层社会的职业,而职业又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基础。有个课题组作过专门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5.28% 的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有48.7% 的家长甚至经常向孩子灌输‘只有好好读书,才是唯一出路’这类观点。对于未来前途的选择,有67.29% 的学生和85.39% 的家长不假思索地希望高中毕业能够进入学术性的综合类大学,而不是技术类的高职学校。”[5]从这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有着“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传统的中国,孩子的学业承载着多少家庭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然而,社会上层成员只占人口中很小的比例,但是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怀有跻身社会上层成为“人上人”的梦想,而学业成就又是社会底层成员流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途径,所以,社会阶层流动的竞争直接演变成孩子学业的竞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自然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共识。当代中国的父母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十分积极,不惜一切代价。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教师和家长只好给孩子加班加点,用时间和汗水来提高孩子的分数,最终给广大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课业负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我国各级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同时还颁布了很多制度,但成效甚微。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学生课业压力问题是行政力量难以治愈的,它最多只能给基础教育的这块肿瘤‘消肿’,却难以将之彻底除掉,斩掉课业负担病根的任务只有求诸于教育系统改革的整体推进才有可能。”[6]其实,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等级意识如此强烈的国家里,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成为上等人的追求,而学业成就又是成为上等人的重要条件,这就必然会导致激烈的学业竞争,激烈的学业竞争又必然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基本相似,所以,只有加班加点地学习,用时间加汗水来提高学业成绩。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上,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这将为改变目前等级化的社会现状、改变人们的等级意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将会越来越小;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平等价值观将会深入人心,人们的等级意识将会日趋淡化,那种为跻身社会上层而产生的成就焦虑也会逐步减轻,学生的学业竞争也会日趋缓和,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种社会难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1] 杨剑利. 中国古代的“巫”与“巫”的分化[J].学术月刊,2010(5):129-13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3] 张友国,董天美.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445-448.
[4] 蒋丰.中日两国儿童的理想比较[J].教师博览,2012(7):23.
[5]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课题组.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的综合分析与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6(1B):47-52.
[6] 龙宝新.论学生课业压力的形成与释放机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5):15-21.
(责任编辑:张晓军)
2015-07-03
邓银城(1953- ),男,湖北黄梅人,湖北工程学院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教授。
左建桥(1969- ),男,湖北广水人,湖北工程学院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G4
A
2095-4824(2015)05-00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