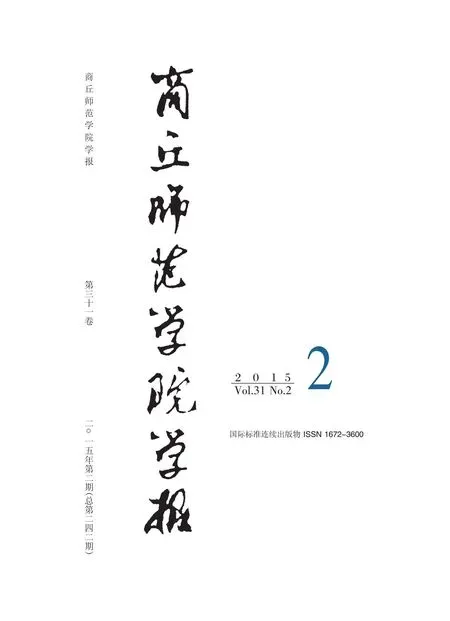六朝道教中的“清”思想
张 晓 立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六朝道教中的“清”思想
张 晓 立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清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获得不断的扩充,由简单的对天、水等物质的形容词,发展成为具有哲学宗教内涵的重要概念。六朝作为中国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征是这个时期大量道经被造作;道教吸收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引进儒、佛两家思想,充实自身理论。而道教对自身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则反映在新出道经中。“清”的概念不断在新出道经中出现,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观念,成为六朝士族道教标榜自身宗教特质、区别汉代以来的民间道教的重要特征。“清”的观念还直接影响到以后道教教义和道教宗教实践,在教义中主要的体现就是戒律,而在宗教实践上就是道教徒在斋醮与修炼的实践过程中追求“清”的价值取向。
清;道教;六朝;魏晋玄学;戒律
六朝时期是中国道教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的道经被造作出来,充实了道教的思考内容,提高了道教的理论高度。在这一时期丰富的道经中,屡屡能看到“清”字的出现。“清”字的反复出现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它反映了六朝时代的精神气质,反映了玄学思想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推动和容纳,反映出“士族道教”[1]34区别于汉代民间道教的根本特点。
一、“清”的观念来源
在《六朝贵族制度研究》中,川胜义雄引用他人的见解说:“上田早苗氏曾经提出,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之间,再没有比‘清’更频繁使用的词了。”确实如上田早苗所言,从汉至魏晋南北朝,“清”这个词出现在政治、哲学、宗教、社会阶层等个方面,是一个流行词。那么,“清”这个词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流行,它的流行能够反映出六朝道教什么样的精神风貌与宗教特质,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清,从字面上来看,是指水的水质很好,洁净透明。清字与浊字对立。在先秦典籍中,“清”主要是用来形容水或者天。清这个词比较早的使用,见于《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郑玄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清即是天之德。而在《老子》第15章有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老子》第39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按照当时哲学家的观点,清是天与水的共同特征。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与水都是带有着宇宙本原特质的概念。
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与道合一,《老子》第8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水就成为最接近于道的一种物质。人们要取法天与水,就要学习天与水的精神——清。所以《太平经》云:
故清者著天,浊者著地,中和著人。天地各长于一,故天长于高而清明,地长于下而重浊,中和长养万物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故古者上皇之时,人皆学清静,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学真道,乃后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天地之性,清者治浊,浊者不得治清。精光为万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当用清明。
人学清净之后,才能够得天心地意。《老子》第45章也说到:“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成为人沟通天地的方法。而“清”则成为形容一个人的高尚品格的词。《庄子》也说到:“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楚辞·渔父》中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清与浊相对,与精、净相联系。从此以后,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清”成为一个重要的元素。
在随后的历史中,清的概念扩大,与廉的观念连接在一起,进一步与政治思想发生关联。《史记·乐书》曰:“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由于汉初崇尚黄老,黄老思想中的清净无为成为当时治国的主流政治思想,由此“清”字开始与政治有了关系。据《汉书·循吏传》载:“汉兴之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净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清”有了治国之策为简易的内涵。
由于汉代施行察举制的取士制度,道德成为取士的标准,清廉的道德属性得到了推崇,“清节”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美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总结的几种汉代人所重视的美德高行中就有:“第八清节。一介不取,推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洁。”但是,汉代的道德成为取士的标准,为了获得取士资格,便有很多人冒充道德高尚,做出一些可笑而矫情的事来。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举到的廉范、范冉的例子。这个时候,“清”的道德属性已经逐渐变质,下及六朝,则更为扭曲和异化。
到了东汉后期,“清”完全与政治发生关系,主要表现在于太学生参与政治进行清议和清流这一政治势力的出现。清流的出现是与外戚宦官集团的浊流相对立的。之所以用清字,大概是强调这一党是由士大夫组成的,且具有高尚品德,与庸俗且品德低下的外戚与宦官势力相对。在随后的历史中,清流势力成为三国争霸过程中的主要家族势力,进而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世族的前身。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强调:“在共通的儒家国家理念,在打倒浊流政府这一共通的目标之下,清流士大夫与豪绅结集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军团领导者——豪侠通过与曹操的结合,以排除其他武力集团作为目标也走到了一起。”[2]101“产生魏晋贵族的母胎即是汉末清流势力。”[2]15
二、六朝思想中的“清”
(一)六朝士人“清”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
最能体现六朝士人“清”气质的材料,应该算是《世说新语》中的第一则故事:“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而 《晋书·殷浩等传论》有云:“有清徽雅量,众议攸归。” 《南史·衡阳元王道度传》亦载:“吴郡张融,清抗绝俗,虽王公贵人,视之傲如也。”而以品鉴人物为目的的《人物志》卷上则有:“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气而不清则越”,“声清色怿,仪正容直”,“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的说法。可以看出,六朝时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志便是“清”。甚至刘劭还专门以清为特质,在划分人才的不同类别时,将之作为单独的类别,如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而他将清节家放在十二人流的第一位,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在这一时期,“清”成为了品评人物的标准。而同样,“清”也成了政治上选拔官吏的标准。《世说新语·赏誉》曰:“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注引《山公启事》:“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莫能移。’”在当时,作为一个选拔人才的吏部官员的首要素质是能否辨别被选拔人的清浊。可以看到,六朝时代似乎和汉代一样,考核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官,不是强调这个人的能力,而是强调这个人的道德品质。而道德品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但是,这种“清”似乎已经成为士族垄断官位的一种借口和手段。中村圭尔认为,“清浊是表示由清议所维持的秩序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份的一个词,认为此二者相当于士人和一般庶民”[3]167。而且他还强调:“谈到这一点,使人不免想起当时官人屡屡散赐俸禄的故事。这一行为一再被人们当作‘清’的价值观的表现乃至作为意识形态问题提出讨论。……就上述问题而言,散赐俸禄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他们的本分,是否由于他们本身对俸禄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呢?”[3]163六朝士人通过散赐俸禄来突出自己“清”的品格,进而保证自己获得官位,以维持士族的统治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清”的价值取向成为士族的精神护符,是他们获得官位和其他优厚权利、区别于一般庶民阶级的特质。
(二)“清”与六朝玄学思想
“清”这种气质和价值趣向,不仅仅是巩固士族政治势力,区分士族与寒族的标尺。它肯定也与士族所持的内在精神有一定的关联。这样的关联应当体现在与当时主流哲学思想的交融上。魏晋时期的士人崇尚三玄,融合庄子的无、佛教的空,形成了自己时代独特的一套宇宙论,其主要哲学思想是贵无论。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注》)作为本体的无,是魏晋玄学家们考虑的重点。而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无”这一形而上的本体反映出的气质就是“清”。六朝时期的士人们厌倦日常生活中的俗事,将贵无论中的“无”作为最高的本体,他们强调要远离琐碎和庸俗的日常生活,将真与俗区别开,去追求虚静的生活。这种虚静的生活态度和品格,就是清。
王弼在《老子注》中解释“天无以清将恐裂”说道:“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则清不失,用清则恐裂也。故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无用其功,恐丧其本也。”这条解释可以很好地体现清与魏晋玄学思想中本体论的关系。一在老子思想中是指道,王弼认为清是道的一种特质,但如果只是纯粹去追求清的特质而忽视道,就会丧失道的本体性作用。所以,如果想真正地达到清的境界,就必须要守一,即守护住自己对道的本体论认识。过分和片面地追求清,就可能会丧失清的真正含义,从而落到表面。所以,追求清的气质,就必须追求清的本体性来源,否则将丧失其真正的本质。
王弼的这种解释,还是从他的贵无论思想而来的。他非常重视道的本体性,强调不能为清的价值取向而去否定道的本体性,否则就是虚伪之清。只有依靠无用或者无为,才能够维持好道的最高本体性,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达到清的价值追求。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王弼对清的定位及其诠释,应该是有其现实考量的。发展到了六朝,前文中探讨的汉代士人的清的气质的异化和扭曲更甚,很多士人崇尚空谈玄理而不追求事功,表面上追求清虚无为,生活中却奢侈享乐。清的精神气质在此时受到的扭曲和异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士族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清”是六朝名士所追求的人格魅力,也是六朝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它涉及六朝的个人道德、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三、六朝道教中的“清”
(一)道教神格中的“清”
在《抱朴子》中,“清”字常与“太”字连用,以太清指代天。前文也强调,清字最早使用是用来表示水或者天洁净无瑕的状态。以太清指天,早已有之。《鹖冠子·度万》曰:“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南宋陆佃解曰:“太清,天也。”《楚辞》曰:“譬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东汉王逸注曰:“上凌太清,游天庭也。”《庄子·天运》曰:“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唐代成玄英疏曰:“太清,天道也。”《淮南子·精神训》曰:“抱其太清之本而无所容与,而物无能营。”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中有以太清指天的传统。那么,在道教中,“清”也往往是天的代指。根据黄海德的研究,三清名称的最早出现,应该是东晋末年的《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他还认为,道教信徒长期将三清仙境视作“常乐净土”或“常乐境界”。《云笈七籖》引《妙林经》说:“若有修善,当得往生三清妙土。” “三清仙境”遂成为早期道教修行者修道往生的最高信仰境界。道教三清信仰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对三清仙境的信仰。三清信仰的第二个阶段才是对“三宝神君”的信仰[4]。葛洪在《抱朴子》中,也将天用太清来指代,应该与其道教信仰相符合。《云笈七籖》卷3曰:“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亦名三天,其三天者,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是也……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
以今所见,“三清”作为神格的名称最早始见于南朝梁时陶弘景所撰的《真灵位业图》。该书排列神仙序位,分为七个层次,每一层设一个中位。第一中位,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第二中位,上清高圣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为万道之主)。第三中位,太极金阀帝君,姓李(壬辰下教太平主)。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为太清道主,下临万民)。其中较为明显地提出了上清、太清的名称,但“三清”之名位次序尚未确定,并且第三位为“金阀帝君”,太上老君却居于第四中位。以后“三清”神名逐渐流变发展,至唐代才成为定说。《道藏·太平部·三洞珠囊》卷7引《老君圣迹》云:“此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位,在三十五天之上也。此即上清境,太上大道君(灵宝天尊)位,在三十四天之上也。太清境太极目,即太上老君位,在三十三之上也。”于是“三清”遂成为道教的最高神。道教中用三清来指代最高的三位神仙,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在以前的典籍中,用清字还形容天,而天是道教信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神灵都居住在天上,而神灵是具有等级的,所以不同的天还有不同的层次,因此用来指代天的清,进一步成为指代神灵的词汇。二是清还与道教信仰中的道有一定的关联,毕竟在《老子》中已强调:“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8章)。老子用水来比喻道,似乎水的清特质也应该是道的特质的体现。于是,“清”便成为了道教神格思想中的重要内涵,成为道教最高本体和最高神的代称。南宋金允中在探讨与总结以上三清、三宝、三洞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三尊之号在经中只称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其别号则曰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以三境之名而称之则曰玉清、上清、太清;以三洞之书而名之则曰洞真、洞玄、洞神” 。三清与三尊、三洞构成了道教信仰与经典划分体系。
(二)清规戒律中的“清”
既然道教中信仰的主题与“清”字有关,那么道教戒律中肯定也强调“清”。最早,道教是没有正式戒律的。道教戒律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信仰中的斋戒。斋戒是指人在祭祀之前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斋是取“齐”的意义),不与妻妾同房,减少娱乐活动(戒是戒除欲望),表示诚心致敬,称为“斋戒”。《论语·乡党》谓:“斋必变食,居必迁坐。”其实斋戒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自己肉体和精神上保持清净,以能够接近神。朱越利认为,“原始道教已有戒律。初期有些戒律和斋合在一起。所谓节食斋、心斋,要求祭祀必恭敬清洁,要求去欲除秽,实际上就包含着戒”[5]261。所以,清便是道教戒律中的重要要求。“清”在道教戒律中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身体活动,饮食活动上的清;另外一个是指心神上的清静。
目前,学者一般以“道德尊经想尔戒”为道教最早的正式戒律。其戒文源出于《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分上中下三品,共九条。上品戒文是:“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中品戒文是:“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下品戒文是:“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在这部最早的道教戒律中,就有行清静一条。而清静这一条也是《道德经》中的重要概念,体现出了老子的哲学诉求。
在《老君说百八十戒》中,关于清的戒律就更多了,但大都是关于身体活动上的清洁。如说:
第二戒者,不得淫他妇女。第十戒者,不得食大蒜及五辛。第二十四戒者,不得饮酒食肉。第一百十六戒者,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之水。第一百十七戒者,不得与寡妇亲。第一百四十二戒者,当念清俭法,慕清贤鹿食牛饮。第一百七十二戒者,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戒者,见杀不食。第一百七十四戒者,见膻不食。
而再往后发展,道教戒律不断充实,但是这些保持自身清净的戒律,却一直保持并且更加严密。
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中,批评李家道“未纯为清省”。言曰:
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市买所具,务于丰泰。精鲜之物不得不买,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复未纯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绝之列。
由此可知,在葛洪看来,“清省”是道教饮食戒律的重要部分,即使李家道已经不像其他诸妖道那样血食祭祀,但是李家道福食过于丰富浪费,还是违背了道教清省的戒律。葛洪站在自身士族道教的立场上来批判李家道的未为清省,一方面是为了维持道教戒律中福食清省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其葛氏道的“道流”的正统性与奉戒的严肃性。由此可见,六朝士族道教对民间俗道的排斥和打压,“清省”之清也正体现了六朝士族道教的精神特质。
道教戒律中一直强调要保持心神上的清静,只有依靠保持心神清静,才能够真正地达到戒定慧,从而获得真正的开悟,进而性命双修,实现真正的解脱和超越。清静的戒律要求便往往与道教的某些修炼理念联系到了一起。
(三)清静的修炼理念
道教修炼方法的根本学理就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用张广保在《唐宋内丹道教》中所说的“人体小宇宙理论”。“而中医、内丹术的人体小宇宙理论认为,从宇宙观方面看,人体是整体宇宙的缩影,包藏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在渺小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之间,存在着息息相通的全息关系。道家、道教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演绎成两种层次的思想:其一,在各种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互相的全息映现;其二,作为宇宙构成部分的各种具体物质形式与宇宙的终极实体即道体是全息的。”[6]3-4那么,作为天的特质——清,就成为道教修炼过程中模拟天道运行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六朝道教灵宝派、上清派都否定民间道教的斋醮仪式和传统道教中的一些房中术的内容,其理由就是这些斋醮仪式和房中术是浊的方式和方法,与道教的“清”的主题不符。而最能反映道教强调清静修炼方法的,则是《太上老君说清静经》。
《清静经》仅401字,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是道教修炼术的重要资料之一。它首先阐释无形、无情、无名的大道具有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功能;而道有清、浊、动、静,“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因此,“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接着说明,人神要常清静,必须遣欲澄心,去掉一切贪求、妄想与烦恼,实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的常寂真静境界。“三者既悟,唯见于空”的说法应当是来源于佛教思想。最后指出,“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清静经》是教人遣欲入静的修炼要领,是道门日常讽诵修持的重要功课之一。虽然现代很多学者认为,《清静经》应该出于初唐时期,理由为其内容有重玄学的思想在内,且有佛教思想的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清静经》上接六朝贵清思想,是六朝道教“清”观念的集中体现,它的思想根源是老庄道家“虚静”思想,同时还容纳了玄学的哲学创造及其佛教空论。它的出现,是六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互相影响的结果。
四、结语
“清”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中传统的文化气质,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士人心态等。清的观念的不断丰富影响了六朝以后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也成为道教教义中区别于佛教的重要特色。道教把“清”作为自己的宗教特色,以区别于民间宗教和外来宗教,使得自己在宗教地位和宗教理论方面有所依仗,从而不断地将其他思想融汇入道教。清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道教神学、戒律、宗教实践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在研究道教的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道教中,清的精神内核与道教教义的神圣观念、救赎观念的联系,也是今后道教神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1]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通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2][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日]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黄海德.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演变[J].世界宗教研究,2004(2).
[5]朱越利,陈敏.道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6]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高建立】
The Thought of Qing of Tao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ZHANG Xiaol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Qi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Its connotation gets enlarg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changing from the simple adjective modifying heaven and water into an important concept with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n connotation.The six dynasties, 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aoism, saw the creation of many Taoist scriptures; Taoism enriches its own theory by absorbing Taoist philosophy and taking in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refining and summary of its own theory is reflected in the new Taoist scriptures. The concept of Qing repeating in the new Taoist scriptures becomes a characteristic of scholars Tao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The concept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reeds and practice of Taoism. It refers the discipline in creed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Qing in Taoists' rites and practice.
Qing; Taoism; the Six Dynasties; Dark learning in Wei Dynasty and Jin Dynasty; discipline
2014-09-12
张晓立(1987-),男,安徽蒙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道家道教哲学和六朝道教文献研究。
B95
A
1672-3600(2015)02-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