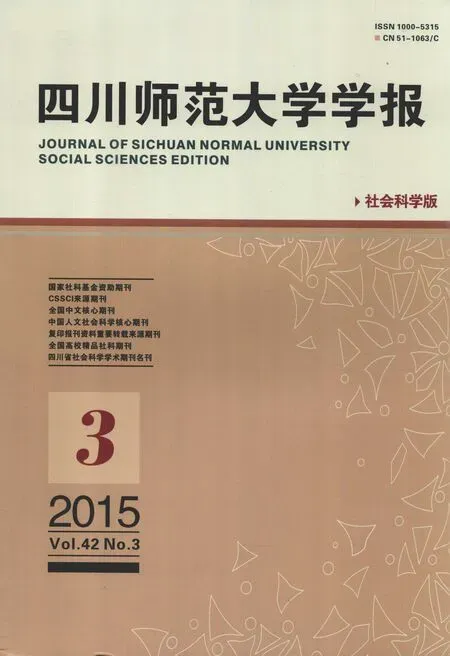清末编修民律之争议
冉 琰 杰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州510275)
清末编修民律之争议
冉 琰 杰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州510275)
宣统二年底,大清民律草案脱稿,但未能核定颁布。不久,清王朝覆灭,清末民律编纂成果付诸东流。然而,这样的结局,不仅是时势使然。通过考察民律编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对民律的关注和讨论,民律脱稿后朝中的人事变化,民律核议时有关亲权条文的争议,以及报刊舆论的反响,可以呈现修律过程的复杂性,民律的结局是朝中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不宜简单地以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局限来评判。
清末修律;大清民律草案;刑民之分;礼法之争;报刊舆论
学术界对清末民律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1-4]。有学者从相关奏折档案中梳理了一条脉络,注意到民律编修工作正式启动的契机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礼部与大理院的修律权之争,研究遵循的是“近代化”范式,旨在吸取法典编纂的经验教训,指出修律者是“政府代言人”,民律与民众的生活习惯有差距[5],但却未能重视清末修律过程中“刑”“民”概念的分野、“民”的概念及内涵的变化以及民律草案脱稿后朝野人士对它的态度和围绕其中亲属编亲权问题引发的争议。虽然也有研究提到,新刑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给民律的编修造成了影响,使民律草案“在编纂时注意了对中国固有传统的继承”,法律编修馆也派人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但研究仍然没有留意礼法之争的延续性,忽略该争议对民律草案稿本修订的影响[4]。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回到清末修律与政局人事变动的历史脉络,考察民法草案编修核议的情事语境和史实细节。
一 “刑”“民”之分及编修民法的讨论
《大清律例》不存在区分“刑事”、“民事”的语言,但是清人有“词讼”(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与“案件”、“细故”与“重情”(谋反、叛逆、盗贼、人命、贪赃坏法等)的概念,不过这些词汇的内涵也不固定,或有混称[6]41-43。 “刑事”、“民事”,这是晚清修律时受欧洲大陆法系影响才出现的新概念。修律伊始,废除《大清律例》中的凌迟等酷刑和审案中的刑讯[7-8],成为朝廷臣工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情境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五,曾任刑部御史的刘彭年奏呈看法,不同意将刑讯完全禁止,指出应视民事、刑事案件的性质而酌情使用刑讯,称:
东西各国裁判所,原系民事、刑事分设,民事即户婚、田产、钱债等是也,刑事即人命贼盗斗殴等是也。中国民事、刑事不分,至有钱债细故、田产分争亦复妄加刑吓。问刑之法似应酌核情节,以示区别。所有户婚、田产、钱债等事,立时不准刑讯,无待游移。至于人命、贼盗以及情节较重之案,似未便遽免刑讯,相应请旨饬下修律大臣体察时势,再加详慎。并饬于刑事诉讼法告成后,即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克期纂订,以为完备法律,则治外法权可以收回。[9]
修律大臣伍廷芳上奏覆议刘折,引用各国法律和香港实例批驳刘“酌核情节,以示区别”的问刑建议;至于纂订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以完备法律的意见,伍廷芳表示:“洵属有条不紊,臣等俟刑律告竣后,即行分别编辑,陆续奏闻。”[9]
此为民律编修被正式提上修律议程的第一次契机。刘彭年把户婚、田产、钱债等案视为民事案,把人命、贼盗、斗殴等情节较重之案视为刑事案,这样的分法并非一家之言,朝中大臣多有相同看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二,伍廷芳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进呈御览,在该法第一章总则第一节“刑事民事之别”中,把“凡叛逆、谋杀、故杀、伪造货币印信、强劫,并他项应遵刑律裁判之案”定为“刑事案件”,“凡因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等事涉讼”定为“民事案件”;他在奏折中还指出:“中国旧制,刑部专理刑名,户部专理钱债田产,微有分析刑事民事之意。若外省州县,俱系以一身兼行政司法之权,官制攸关,未能骤改。然民事刑事,性质各异,虽同一法庭,而办法要宜有区别。”[10]41-44
伍廷芳以日本为鉴,认为先变通裁判诉讼法,是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可化解因华洋争讼而酿成的外交问题,藉此收回治外法权,所以他在刑法、民法尚未修成之前,先行编纂出刑事民事诉讼法。他这样的工作安排,得到了修律大臣沈家本及修订法律馆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的理解[11]。
但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先行编撰引来了很多批评,不得不暂缓施行。在众多批评意见中,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在上奏中指出:
民事诉讼法,当以民法为依据,今既未修订民法,则民事诉讼法将何所适从,未免先后倒置。至民法为刑措之原,小民争端多起于轻微细故,于此而得其平,则争端可息,不致酿为刑事。现今各国皆注重民法,谓民法之范围愈大,则刑法之范围愈小,良有以也。[12]833-836
可见,张仁黼也是把民事案件看成小民因细故引发的争端,刑事案则是由细故引发的大案。
有研究者指出,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法部与大理院的权限之争中,张仁黼和沈家本就已积怨,同年五月张的奏折又挑起了修订法律权的争夺,因为张仁黼意在请朝廷“钦派部院大臣会订”法律,削弱修订法律大臣的修律专权[13]。法部尚书戴鸿慈提出不同意见,而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又复议戴折。戴鸿慈主张特设立法机关(即修订法律馆),以资修订法律,将来法院编制法、民法,修而未备的商法,待改正的刑法、民刑诉讼法等一切法律,都应由修订法律馆编纂提议改正;王大臣可为总裁,各部院堂官、督抚、将军请旨特派会订、参订法律大臣,法部开单请派编纂协纂之人[12]839-842。 奕劻既不同意一切法律都统归修订法律馆编纂,也不赞成派王大臣为总裁,主张将来刑法、民法、商法诸法典由修订法律馆草拟,其余各项单行法由各该管衙门草拟,最后都统归宪政编查馆覆定[12]849-851。奕劻的意见得旨依议。这些奏折体现了修订法律权的争夺和讨论,固然需要注意,但有关修律步骤的看法,促进了民法编修的议程,也值得重视。
在上述争论期间,朝廷新设的民政部也看准时机议论修律,并奏请派修律大臣厘订民律,会同该部奏准颁行。民政部奏称:
臣部所系为民,查欧美日本皆以此为内务行政之枢纽,惟是规模初具,绵蕞方新,凡所设施,略无成轨,自非立法周详,相为表里,将欲变通,尽利其道无由。查东西各国法律,有公私法之分,公法者定国家与人民之关系,即刑法之类是也,私法者定人民与人民之关系,即民法之类是也,二者相因不可偏废,而刑法所以纠匪僻于已然之后,民法所以防争伪于未然之先,治忽所关,尤为切要。各国民法编制各殊,而要旨宏纲大略相似,举其荦荦大者,如物权法定财产之主权,债权法坚交际之信义,亲族法明伦类之关系,相续法杜继承之纷争,靡不缕晰条分,著为定律。……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李悝六篇不载户律,汉兴增庙户为三,北齐析户婚为二,命曰婚户,隋唐复更定次第,改为户婚。国家损益明制,户律分列七目共八十二条,较为完密,第散见杂出于刑律之中,以视各国列为法典之一者,尤有轻重之殊。……职守窃以为推行民政,澈究本原,尤必速定民律,而后良法美意乃得以挈领提纲,不至无所措手。[14]
其意见得到朝廷采纳,开启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清末民政部由巡警部改名而来,下设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九,思想较为开明的肃亲王善耆被任命为民政部尚书[15]。善耆奏请朝廷编修民律,是以该部职权所系、民政所需为立论点,绕开了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常见的论调,所逞述的观点颇有新意,如“民”为“内务行政之枢纽”,法律有公法私法之大别,“私法者定人民与人民之关系,即民法之类是也”。善耆还注意到各国民法的体例内容,民法不是小民闹细故那么简单,物权法、债权法、亲族法、继承法都在民法中有定律,这些律条涉及财产之主权、人们交际之信义、家庭伦理、继承等方面。奏折中使用“民律”一词,与同时期的“刑律”相对应。“厘订民律”得旨依议,此后“民律”成了官方钦定的对民法典之称谓。不过,“民法”一词仍然被朝野使用。
二 礼部、学部预闻民律草案
在民律编修之际,礼与法的调和问题就受到了朝廷臣工的关注。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辽沈道监察御史史履晋以“维礼教而正人心”为由,奏请礼学馆与法律馆共同商订法律。八月,会议政务处上奏覆议该折,各部尚书与军机大臣的总体意见是:
近日修律大臣多采外国法律,于中国礼教诚不免有相妨之处。除学部曾经条奏奉旨,饬修订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再行详慎斟酌修改删并外,京外各衙门亦多有指摘。查方今教育之责注重学部,应请敕下学部择其有关礼教伦纪之条,随时咨会法部暨修律大臣虚衷商榷,务期宜于今而仍不戾于古,庶几责任不纷,而可以收补偏救弊之益,较为简要易行。[16][17]
该折谕旨依议。自此,学部便能名正言顺对修律工作指手画脚,当然也预示着此后学部可与法律馆共同商订民律草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以军机大臣身份管理学部[18]。张之洞是朝中礼教派的代表,他以维持礼教为由,上奏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颇得京外各大臣响应。所谓“学部曾经条奏奉旨”,应指张之洞批评新刑律的奏折和谕旨[19]。
宣统二年(1910),资政院核议新刑律草案时,议员们围绕有关伦常诸条(如子孙违反教令和无夫奸)进行了激烈的礼、法之争[20]。在此背景下,民律编修中礼与法的调和问题,又引来朝中大臣奏议。先是,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奏请宪政编查馆、礼学馆、法律馆共同核议新编的法律。十二月,礼部大臣覆议支持甘大璋,认为:“民律则日用民生在在与礼教相为表里,臣馆若不预闻,非特法律馆所编民律,恐有与礼教出入之处,即臣馆所编民礼,亦恐与民律有违异之端,将来实行之时,必多窒碍。”礼学馆建议由本馆与法律馆会同集议民律,再咨商宪政编查馆覆核,最后交由礼学馆与法律馆共同奏呈颁行;其集议章程如下:一、两馆馆员应互相联络,一、法律馆编出草案底稿,应一律分送礼学馆,一、两馆书籍案卷,准彼此检查,一、民律议定之后,由礼部礼学馆、法部法律馆会同具奏;这些建议,得旨依议[21-22]。十二月二十七日,任职于宪政编查馆,且为法律馆第二科总纂的汪荣宝得知礼部奏议,又听说宪政编查馆拟于明年召守旧派劳乃宣参与核议民律,他“不禁为法典前途惧”[23]760。
礼部覆议甘大璋折时,恰逢民律草案脱稿。草案共有五编,其中总则、债权、物权编由法律馆顾问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起草,亲属编由章宗元和朱献文起草,继承编起草人是高种和陈箓。章宗元留学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习商科;朱献文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法科。高种是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学士;陈箓是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学士。此时的法律馆中,随着旧馆员知识转型和留学归来之新馆员的调进,新式法学人才成了法律馆主干力量[13]。
翌年正月,《大公报》听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与礼部尚书荣庆核定:“嗣后除有应行会核之件,当知照礼学馆随时协商外,并于每月举行会议三次,研究一切问题,以资联络,此举准由二月起当即实行。”[24]二月,礼学馆开始核议民律。
报界舆论对礼学馆核议民律之举颇有批评意见。《北京日报》刊文称:
法律馆修订民法、商法草案,本定于去年十二月进呈。因礼部上一折言民法与礼教攸关,必须会同本部逐条商榷方可,并要将来须会同共奏云云。礼部此折上后即奉旨依议,法律馆因此遂将民法、商法已定之草案暂行搁起,未能进呈。盖法律馆皆新学之士,礼部多旧学之士,此中甚难融洽,会同商订一事,不知如何结果。[25]
这段评论被《申报》引用,并以《礼部人员亦有商订民法之学识乎》为题,讽刺礼部“旧学”之士参与商订民法之不妥[26]。《北京日报》还探得,礼学馆认为民律草案内容“丧失亲权太甚”,俟会同法律馆商订时“将力争之”[27]。《大公报》也得知礼学馆正签出民律草案中违背礼教之处分别驳议,但未悉沈家本意见如何[28]。
三 民律脱稿后修律大臣的更换及舆论反响
刚刚脱稿的民律草案正被礼部礼学馆牵制,似难奏呈,报界舆论又对民律的前途十分关注,法律馆承受着朝野内外的压力。恰在此时,法部尚书廷用宾因患重病,请辞开缺,传闻沈家本有补升法部尚书之消息[29]。不久,廷尚书逝世,朝廷命绍昌为法部新尚书。沈家本非但没有升职,反于宣统三年(1911)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开去修订法律大臣及资政院副总裁之差,回法部本任(左侍郎)供职。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充任修订法律大臣,学部右侍郎李家驹充任资政院副总裁[30]。法律馆的汪荣宝对此非常吃惊,并在日记中记述为“殊出意外”[23]816。
沈家本被开缺,报界纷纷猜测原因。《大公报》说到:“沈子敦侍郎修订法律大臣一差,日前奉谕开去。兹闻其原因,系为政府以该侍郎所订法律多与礼教不合,屡被言官指摘,且在资政院毫无建白,监国深滋不悦,故有同日开去法律大臣及资政院副总裁之旨。”[31]若依该报之言,那么沈家本被开缺一事,暗示着宣统朝新当权者(“监国”指摄政王载沣)的政治风向,即不过度羡慕西方宪政,敦崇礼教,支持守旧派。《大公报》又报,沈家本得旨谢恩,感到轻松愉快,曾语人云:“予今开去此两项兼差,外间多有为予惋惜者,殊不知修订法律与充资政院副总裁,此两差最难理处,稍有不慎,非受责于政府,必受谤于舆论,无论如何,恒处于丛怨地位。今一律释此重负,何快如之。”[32]沈看透时局,深知修订法律大臣与资政院副总裁是腹背受怨的差事,既要应对朝廷,又要承受外界舆论的批评,行事如履薄冰,故得旨开缺而感欣悦。
其实,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请旨开缺后,沈家本已感孤掌难鸣,萌发退意。光绪三十三年(1907),各省督抚奏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时,沈家本的修律工作遭到许多批评。同年,大理院正卿张仁黼上奏影射沈家本大权独揽,沈家本顺水推舟请旨开去修订法律大臣差;但宪政编查馆覆议张折时,肯定了修订法律大臣和修订法律馆是必要的差职和机构,谕旨采纳宪政编查馆建议,不久又任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由此可见,沈家本当修律大臣的几年中,并非一帆风顺[33]。
《时报》认为沈家本开缺一事不简单,沈开缺资政院副总裁,同时溥伦开缺资政院正总裁,继任的资政院正总裁世续是奕劻保举,副总裁李家驹乃那桐保举[34],这些都是军机重臣奕劻和那桐上奏促成的。《时报》评论道:溥伦对议员“感情既深”,有恩威并济、涵盖众流之度;沈家本“威望似不如伦,然沈固法律专家也,于旧律既经验数十年,于新律亦研究数载,其智识实远出于诸老朽之上”;那桐是“著名守旧之辈也,当在军机时,碌碌无所短长,曾未闻有所建白,久已不协于众望,即转而掌内务府事”;庆亲王奕劻和那桐,既握军机中之大权,又握外务部之大权,“去岁,因弹劾军机处案,屡为议员所迫也,固已恶之深而恨之极矣。然语有之,蛇无头而不行。庆、那以为议员之所为,皆由伦贝子酿成之,于是以恶议员恨议员者,转而迁怒于伦贝子,此则庆、那之处心积虑也”[35]。
似乎刘若曾充任修订法律大臣,也是由那桐所保,而且就在沈家本开缺上谕发出的第二天,曾为学部右参议、现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刘廷琛便奏参沈家本,请饬礼学馆和法律馆以大清律例为本,删订各新律以维礼教。《时报》隐晦地说:“枢臣因沈家本修订法律专主从新,故保刘若曾代之,复嗾令刘廷琛奏请申明新律宗旨,饬礼学律学两馆依据旧律参订各新律,以维名教。”[36]《申报》有《时评》称:“沈家本既开去资政院副总裁差,又开去修订法律差,而仅饬回法部侍本任,动辄得咎,可怜。刘若曾既肯为枢臣傀儡,又能傀儡刘廷琛,故得一修订法律差,心劳日拙,可怜。”[37]这些议论隐射了修律背后的人事纷争。
刘若曾是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八旗学堂副总办、湖南辰州府知府[38]第六卷,720-721;第七卷,137。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任太常寺卿,同年九月改为大理院少卿[39]第二册,1339;第四册,3090-3091。 从刘若曾履历可知,他对修史、科考、学务有经验,但法律方面的工作较沈家本资历浅。宣统元年(1911)七月,《申报》报道了刘若曾的近况,称他是“礼教家之专门”,以孝行闻名,最得张之洞器重,被赞为“才堪大用”,将升授礼部侍郎[40]。虽然他没有真的进入礼部,但从其仕途经历、品行、传闻情况来看,他于宣统三年(1911)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说明朝廷对待新律编纂的倾向性态度变化,即更加偏重维持礼教。
四 民律宗旨和亲权条文的争议
民律草案上呈御览的进度,既因礼学馆的核议工作而受到牵制,又因沈家本的开缺而受到打击,而且其编修宗旨和一些具体内容还遭到朝中礼教派的批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首先上奏称:
窃维政治与时变通,纲常万古不易,故因世局推移而修改法律,可也,因修改法律而毁灭纲常,则大不可。盖政治坏,祸在亡国,有神州陆沉之惧,纲常坏,祸在亡天下,有人道灭决之忧……今年为议民律之期,臣见该馆传抄稿本,其亲属法中有云,子成年、能自立者则亲权丧失,父母或滥用亲权,及管理失当危及子之财产,审判厅得宣告其亲权之丧失。又有云定婚须经父母之允许,但男逾三十,女愈二十五岁者,不在此限。各等语,皆显违父子之名分,溃男女之大防……该法律大臣受恩深重,曾习诗书,亦何至畔道离经若此?臣反复推求其故,则仍以所持宗旨不同也。外国风教攸殊,法律宗旨亦异,欧美宗耶教,故重平等,我国宗孔孟,故重纲常。法律馆专意模仿外人,置本国风俗于不问,既取平等,自不复顾纲常,毫厘千里之差,其源实由此。[41]
刘廷琛上奏一事被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舆论哗然。《申报》载文批驳道:“刘廷琛云礼教尽灭,新律可行,不灭则万难施行。尤如断凫续鹤,指鹿为马之瞀语……至谓忠义之衰,由于孝悌不明之故,而牵引三纲以武断其词,尤属不通之论……往者礼教与法律视同一物者,因学者无法律之智识,而依托礼教以规律本族之故,乃遂误认为一种之成文法尔。不知礼教云者,属于国民之秉彝,固为吾数千年来立国之一要素,而特不能与一国之法典相混。”[42]《申报》还刊登文章,以“隔墙似有吠花声”①为副题,暗喻刘言似犬吠,“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奏参沈家本一事,闻者莫不大哗”,“无礼教则天下亡”,此论“奇哉”!可惜“上监国为之动容,诸老为之起敬,而新律一线之生机,又归消灭矣”[43]。这篇评论旋即被《盛京时报》转载[44]。
《时报》也刊文发表意见,称:“新旧党竞争之烧点,无过父子夫妇伦理之问题,记者对于此项新律,原不敢绝对之赞成。诚以民间习惯既久,而骤然易之以新法,则社会之心理必将为之杌隉不安,无宁受之以渐,使潜移于不觉之为愈也。然此不过就事实上言之耳。其于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之大义,固未尝有丝毫之损害也”;刘廷琛“其手挥目送之巧,意固别有所在。殆欲举宪政之全局而推翻之,非徒争新旧刑律之优绌而已”[45]。
刘的奏折被军机处抄发法部和礼部。礼部堂官对其中内容极力赞成;法律馆认为该折所言殊与新律大有牵掣,表态将尽快会同礼部妥议办法[46]。不久,法律馆开会讨论刘折,《时报》详为报道,感叹新律“前途颠倒”。会中,担任法典起草员的诸日本法学家,如冈田朝太郎、严谷孙藏等,皆力持文明诸国法律通例,认为:“凡法律之定,自有法系,断无合篇采用新法系,而中间忽间杂旧法系中语之理,法律礼教,各有范围,不能牵混”;但礼部尚书陈宝琛、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皆著名维持礼教之人”,极力支持刘廷琛折;最后,法律馆妥协,“议订调停之法”,将男至30岁、女至25岁、结婚不必得父母承诺一条酌情删减,至于父母丧失亲权条则作出限定:“所谓亲权者,不外数种,一管理财产权,一惩戒权,一监督权,一教育权,中间惟财产管理权,关系自由能力者大,而在亲权中不过一小小部分,特提出另订外,其余各种亲权,均不在丧失之列。”[47]
结婚须得父母同意,但男满30岁、女满25岁之后不受此限制,这是1898年《日本民法》中的内容。梅谦次郎曾解释该条立法原由:“子之配偶者,与父母生姻族关系,又况乎其夫妇间所生之子,复为父母之实孙,是更安可置父母之意于度外耶?时无论古今,国无论东西,结婚均须得父母之同意,盖以此耳。惟此种之同意,果为永久且绝对之条件与否,则各国法例不一。”“本条之条件,为法律上之条件。自德义上言之,则子无论若干岁,均须求父母之同意,此固当然之事也。”[48]56-57法律馆民律起草者似乎照搬了该条。而《大清律例》则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或父母已故,由余亲主婚[49]551。换言之,不管男女年龄多大,只要家中尊长健在,那么婚事就要由尊长做主。这有维护父母、祖父母亲权之意,若男女超过一定的年龄,婚姻可自主,便意味着尊长亲权将部分丧失。
礼学馆对亲权问题不让步,不能接受父母亲权有任何丧失,法律馆中留学生群体则相持力辩。据《申报》载文称:
礼学馆对于民法草案,自奉谕旨以来,只会议一次。会议之时该馆某提调谓中国政体向重立纲,外国政体向重平等,父为子纲,亲权断不可抛弃,如亲权可抛弃,将来乱臣贼子弥满天下矣。此说颇为一般旧学究赞成,而章宗元等十数人则竭力反对。谓中国政体向重立纲,因便于专制故也,今既改为立宪政体,即应变为个人平等自治独立主义,以矫其依赖性,使人人均有独立营生之能力。若亲权终世不停止,父母终世有教育子女之义务,而无享子女奉养之权利。且子女犯法可问及父母,因其父母有管理之责也。果如此,则父母终身有管理保养子女之义务,子女终身有依赖安全之权利,为人父母者,不亦苦哉!况所谓抛弃者,不过俟子女成年时,或嗣有自治能力时,始抛弃其管理权,非谓从子女出生后即抛弃其权也。……新旧聚讼不决,两派争持甚力,因此未能解决。[50]
亲权问题之争,反映两种修律的理念,即基于纲常的家族主义与基于自由的平等主义,而且也象征着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大家长制、子从父纲的礼教观开始受到欧美个人主义思想的挑战。不过,从北洋政府时期《法律草案汇编》所收录的《大清民律草案》内容来看,清末法学馆在修改民律草案时,还是向礼学馆妥协了。比如亲属编第三章婚姻第一节成婚之要件第二十二条有言:“结婚须由父母允许。”无男逾30、女愈25岁者不在此限的字样。又如亲属编第四章亲子第一节亲权中有关父母亲权丧失的规定,只限于母亲再嫁后不得行使亲权,女儿出嫁后,父母不得行使亲权;子成年后,父母依然享有亲权,财产归父或母管理,关于财产上之法律行为,由行亲权之父或母为之代表[51]。
法律馆之所以妥协,与当家法律大臣的个人意志有关。刘若曾担任修订法律大臣后,修律态度和办事方针都以维持礼教为宗旨,甚至有另起炉灶之意。《大公报》探知,刘若曾“决定将尚未入奏的法律草案,亲加详阅,大为修改,总期符合礼教,便利通行”[52]。《北京日报》载文说:“修订法律大臣既经易人,办事方针亦略有改变,闻沈大臣手中所业经订成各草案,现在刘大臣均拟另行纂辑云。”[53]《大公报》亦报道:“刘仲鲁少卿对于修正法律一事,抱定维持礼教宗旨。”[54]至于民律,刘若曾很不满意其中的亲属编和继承编,有意今后奏呈民律时,将两篇除开,暂时不奏。法律馆的汪荣宝在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一日日记中写到:“到修订法律馆,子健告予亲属及承继法中,问题甚多,仲鲁畏首畏尾,意主迁就,现拟将此两编提开,暂不具奏,委诸将来编纂云。甚矣!编订法典之难也。”[23]893九月,修订法律大臣果然抛开亲属、继承编,只将民律草案的总则、债权、物权编上呈御览,奏折称:“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取诸现行法制,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敝……亲属、继承二编,关涉礼教,钦遵叠次谕旨,会商礼学馆后再行奏进。”[12]911-913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局骤变,民律草案不了了之。北洋政府修订之清末民律,虽未颁行,但民间诉讼仍以清末民律草案为法理依据之一②。
编修新律是清末新政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是近代中国政制转型的重大举措,但民律的编纂议程和进度却相对滞后,民律草案脱稿后还陷入礼、法之争,并且未能核定颁布。正因为有这样的结果,导致学术界对民律的研究,多致力于寻找它的局限性,并把它放入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给予定位和价值评判。前述通过对民律编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对民律的关注和讨论、民律脱稿后朝中的人事变化、民律核议时有关亲权条文的争议以及报刊舆论的反响等方面的考察,一定程度呈现了清末民律编修核议过程的复杂性。可以说,民律编修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是因为清末修律参照了同时期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的各种法典,修订法律大臣和各部臣工开始区分“民事”、“刑事”为不同的概念,编纂单独的民法典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也是朝中各方分争修律权使然,大理院、法部、宪政编查馆、民政部、礼部、学部都把参与核议民律纳入自身的职事范围,推动了民律编纂核议工作的进程,而修成的大清民律草案则是朝中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因此,恐怕不能简单以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局限来评判清末民律草案的编修核议过程,而应回到清末修律与政局人事变动的历史脉络,考察民法草案编修核议的情事语境和史实细节,从而更深入、更细致、更客观地揭示民律草案编修核议进程的复杂性。
注释:
①清中期诗人李勉有诗云:“谁家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
②张生教授在《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一书中认为,民律草案未经清廷正式审议,在清末民初都没有正式公布施行,裁判官的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与草案“存在较大距离”,“当时大多数法律界人士对该草案知之甚少”。此观点并不准确。因为虽然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有令对清末民律草案不予援用,但是草案亲属编的离婚条文却在民间婚姻诉讼的案例中被律师援引,而北洋政府大理院也承认该条文内容有效。比如:1913年,北京附近大兴县的于某与妻张氏诉讼离婚,于某不满京师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上告大理院,诉状陈述离婚的理由,全部引自清末民律草案离婚条文;大理院接受了诉状,依据原诉讼记录,又通过审讯,了解事实后,逐一驳回了每条离婚理由,认定离婚事由与法定离婚条件不符。此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六册《大理院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458页。
[1]杨志昂.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
[2]张生.大清民律草案摭遗[J].法学研究,2004,(3).
[3]孟祥沛.《大清民律草案》法源辨析[J].清史研究,2010,(4).
[4]王彬.清末民律修订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李欣荣.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J].学术研究,2009,(5).
[8]李欣荣.清末死刑方式的转变与争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9]修律大臣外务部右侍郎伍、刑部左侍郎沈奏复御史刘彭年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J].东方杂志,1905,2(8).
[10]伍廷芳,等.大清新编法典[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7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11]伍侍郎编纂裁判法之用意[N].申报,1906-03-29(3).
[1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G].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4]民政部奏请厘订民律折[J].东方杂志,1907,4(7).
[15]上谕[N].申报,1907-06-19(2).
[16]掌辽沈道监察御史史履晋奏礼学馆宜专派大臣管理与法律馆汇同商订折[J].政治官报,1908,(234).
[17]会议政务处奏议覆御史史履晋奏礼学馆宜专派大臣管理与法律馆汇同商订折[J].政治官报,1908,(300).
[18]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J].历史研究,2000,(3).
[19]李欣荣.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J].学术研究,2010,(9).
[20]李欣荣.清末关于“无夫奸”的思想论争[J].中华文史论丛,2011,(103).
[21]礼部奏遵拟礼学馆与法律馆会同集议章程折[N].北京日报,1911-02-14(3).
[22]礼学馆将参预民律[N].申报,1911-02-19(1:4).
[23]汪荣宝.汪荣宝日记[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21-62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24]法律礼学两馆之联络[N].大公报,1911-02-16(2:1).
[25]新律延搁之原因[N].北京日报,1911-02-26(2).
[26]礼部人员亦有商订民法之学识乎[N].申报,1911-03-06(1:4).
[27]反对民法因恐丧失亲权[N].北京日报,1911-02-28(2).
[28]大清民法尚须详拟[N].大公报,1911-03-08(2:1).
[29]沈侍郎将升法部之预闻[N].大公报,1911-01-17(2:1).
[30]上谕[N].申报,1911-03-23(1:3).
[31]沈侍郎开去兼差之原因[N].大公报,1911-03-26(5).
[32]沈侍郎撤差后之愉快[N].大公报,1911-03-30(2:1).
[33]史洪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的政治困境[J].史学月刊,2013,(1).
[34]专电[N].时报,1911-03-23(2).
[35]论资政院更调正副总裁事[N].时报,1911-03-24(1).
[36]专电[N].时报,1911-03-24(2).
[37]时评[N].申报,1911-03-25(1:6).
[38]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9]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0]京师近事[N].申报,1909-09-11(1:5).
[41]刘廷琛反对新刑律奏折[N].时报,1911-04-05,06(4).
[42]辩刘廷琛反对新刑律[N].申报,1911-03-29(1:3).
[43]刘廷琛参沈家本之原奏[N].申报,1911-04-02(1:5).
[44]刘廷琛参沈家本之原奏[N].盛京时报,1911-04-12(2).
[45]刘监督参劾新刑律疏书后[N].时报,1911-04-07(1).
[46]法律馆与刘廷琛[N].大公报,1911-03-28(5).
[47]新刑律之前途颠倒[N].时报,1911-04-08(2).
[48]梅谦次郎.日本民法要义(亲族编)[M].陈与燊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49]大清律例[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0]礼学馆亲权之争议[N].申报,1911-04-22(1:4).
[51]大清民律草案[G]//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一).北京:京城印书局,1926.
[52]刘大臣调阅未奏法律草案[N].大公报,1911-03-29(2:1).
[53]法律草案另纂之风闻[N].北京日报,1911-04-06(2).
[54]刘大臣修正法律之方针[N].大公报,1911-04-21(2:1).
The Dispute of Drawing up the Civil La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AN Yan-jie
(History Depart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The Civi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completed in the end of 1910,but it had not issued.Soon the Qing Dynasty collapsed,which means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Civil Law became in vain. However,That is the unchangeable the trend of times.By study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the attention from all parties of the royal court and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Civil Law,personnel changes after the complete of the Civil Law,and different opinions of the parental right in the Draft of Civil Law,and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newspapers and press were all proves to show the complexity of amending the law.The Civil Law was a compromise of various views of the court so that it’s improper to evaluate the Civil Law with the simple conclusion as being whether traditional or modern,progressive or limited.
amending the civil la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raft of Civi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riminal and civil;the dispute of feudal ethics and law;the public opinion in newspaper
DF092.49
A
1000-5315(2015)03-0149-08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4-06-29
冉琰杰(1985—),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从虐童事例切入